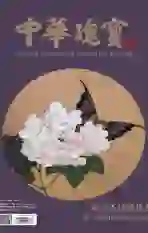花,一种诗化的中国文化表达
2019-09-10周武忠
中国是世界上花卉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度之一,很早就开始种植培育花卉,是花卉栽培的发源地。通过采花、种花、用花、与花朝夕相处,人们逐渐掌握了丰富的养花、用花知识,把对花的思想感情与岁时地域的习俗、习惯、心理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以花为中心的文化。这种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生活内容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体系,可以称为中国花文化。中国花文化体现了国人与植物积极互动、和谐共生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药之食之 信仰寄情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与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把对植物的利用和欣赏打上各自的文化烙印,就形成了具有不同国家和民族特色的花文化。
狭义花卉是指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如君子兰、水仙、菊花、鸡冠花、仙人掌等。广义花卉的范畴则要大得多,除了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以外,还包括草本或木本的地被植物、花灌木、开花乔木以及盆景等。另外,南方地区的高大乔木和灌木移至北方寒冷地区,也可做成温室观赏盆栽,如白玉兰、印度橡皮树、棕榈植物等,这些花木也属于广义花卉的范畴。花文化中的“花”,通常指的是广义的花卉,可泛指所有对人类有用的植物。
中国花文化按照载体的存在性质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类。在物质文化方面,早在远古时期,神农氏就遍尝百草百花,测试它们的药用功能和效果。此后,人们将各种不同的花草分类定性,针对不同的病症入药,同时作为各个季节的食材,花草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药物和食物来源。后世出现的菊花糕、桂花鲜栗羹、木香花粥、梅粥,以及用栀子花、芙蓉花、玉簪花、金雀花、紫藤花等四季鲜花做菜的方式更是数不胜数。
在精神文化方面,花卉花木很早就成为人们信仰象征和情感寄托的对象。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录了夜郎国的故事:“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这个故事说明古代西南地区将竹视为有神性的图腾物加以崇拜。《后汉书》还描述了西南地区的竹子较其他地区更为粗壮的特征,“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彝族等,把竹子视为他们祖先的象征,竹文化对他们而言有着特殊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
除去祖先崇拜以外,后世更多的是将花卉花木作为欣赏与审美的对象,对各类具有独特品性的植物寄寓深厚的思想感情。
清代戏剧家孔尚任创作的戏剧《桃花扇》就以扇子上所画的桃花作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用扇面上的桃花诗与桃花画来象征女主人公李香君的美丽容颜和不屈个性。在剧中,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落第未归,留在南京,阉党余孽阮大铖托杨龙友资助侯方域,让他得以遇见江淮名妓李香君。相处之际,侯方域为李香君的美貌和才情所打动,赠她一柄洁白的宫扇作为定情信物,并即兴在上面题诗一首:“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他将普通女子比作辛夷花,而将李香君比作桃李花,通过花卉来赞美李香君的美丽。后来侯方域被诬告暗通叛军而出逃扬州,李香君被阮大铖逼嫁他人,她以死相抗,以头撞桌,当场血溅诗扇。杨龙友后在扇面上就着血痕画成了桃花图,于是诗画相配的扇面桃花就成了全剧中李香君人格的代表。作家孔尚任也借剧中的花卉来抒发心系国家兴亡的情感,表达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
入诗入画 雅俗共赏
对花卉花木的利用和观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各阶层人们的集体习俗与审美习惯。
政府有时会将某种花卉定为官方正式场合使用的花卉。如清末清廷曾将牡丹定为国花;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在1929年宣告将梅花作为国花。这些都可以视为官方对花卉的认可实例。古代宫廷中也常因帝王喜好而種植或使用特定花卉。如清代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中种植的敖汉莲,为康熙帝从内蒙古敖汉旗引种而来。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此花道:“莲以夏开,惟避暑山庄之莲至秋乃开,较长城以内迟一月有余。然花虽晚开,亦复晚谢,至九月初旬,翠盖红衣,宛然尚在。苑中每与菊花同瓶对插,屡见于圣制诗中。”这表明了宫廷中赏花观花、以花入诗入画的传统。
古代民间(包括官方以外的文人、民众等各界人士)也有对花卉花木把玩、食用、使用或欣赏的习俗和传统。民众喜欢在不同的时节用花卉进行装饰装点,食花用花,借助花卉花木来表达岁时的美好愿望和集体的情感等,这是中国花文化中的俗文化,多与岁令风俗相关。文人雅士则经常举行与花卉花木有关的雅趣活动,比如文人独处或雅集时,围绕花卉展开吟诗作对、写字作画、填词谱曲等活动和艺术创作,这是中国花文化中的雅文化。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诗人热爱自然,与菊花为伍的精彩写照。后人画作中描绘陶渊明时,经常把他画成将采好的菊花放在筐中、戴在头上的隐逸高人的形象。宋代诗人林和靖隐居在杭州的孤山,他并未娶妻生子,而是种梅花养仙鹤,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对于梅花的欣赏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共识,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闲情高致也在文人中传为佳话。
以花比德 焕发新生
中国花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花文化相比,具有典型的“以花比德”“托花言志”和将花“意象化”“形而上化”的审美倾向与传统心理。
花卉花木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审美情趣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如果说对于植物的种植、食用、药用等各种实际价值的使用是中国花文化物质文化中独特的魅力所在,中国花文化的审美传统更是中国花文化精神文化中的瑰宝。花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建构的有机力量。中国人对重要的花卉花木常以“花中四君子”“岁寒三友”等称呼,表达与花为友、以花比德、对花移情的审美传统。传统文化中的“物我合一”“天人相生”的人生境界和哲学理想也离不开对花卉花木的情感转移。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既表达了对竹子清雅高节的推崇,更体现了人与自然相生相合、物我和谐的生活起居方式。
当代中国人仍然承袭了长期以来的花文化传统,在饮食文化、起居文化、艺术审美与民俗节令中都离不开各类花卉花木。与古代不同的是,今天对花卉花木的审美更多地转化成了实际的生产力,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自2013年以来,中国花卉协会启动了国家重点花文化基地的申报工作,迄今全国共有20个国家重点花文化基地获得认定,北京植物园、上海梦花源、江苏南京梅花山、浙江杭州花圃等一批花卉主题景区成为全民体验中国灿烂花文化的“国字号”基地,也是现代人休闲旅游、修养身心、拥抱大自然、感受中国悠久的花文化传统的绝佳去处。
周武忠,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花卉协会花文化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