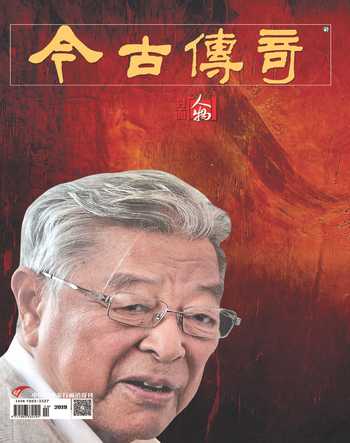文强人生百年亦是亦非
2019-09-10游慧冰罗军生刘延民何蜀著
游慧冰 罗军生 刘延民 何蜀著
文强一生历尽劫波,自谓“千死一生”。他在国共两党都担任过高级职务,最后沦为战犯。他认罪却拒绝悔过:“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直到晚年才思想彻底转变。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开篇 历尽劫波,“千死一生”
他的父辈曾追随孙中山;他本人是文天祥的23世孙,还是毛泽东的表弟,曾追随朱德转战川蜀;他当过林彪的班长,两人打了一架;他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加入国民党,却又在国民党掌权前夕退出国民党;他在共产党内出生入死,却不得同志的信任,最后含冤脱离共产党;他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却不肯响应周恩来的“归队”召唤;他重返国民党,进入军统,又离开军统;他作为战犯被关26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却因祸得福躲过了“文革”劫难……
他就是文强。他说:“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他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出生于满清末年,离开人间时已经进入21世纪。
文强一生坎坷曲折,刀光剑影,历尽劫波,自谓“千死一生”。他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半,自称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
他的前半生走过了政治上的两极:
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重大军事实践,还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等职务。
脱离党组织后又加入了国民党和“军统”,历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军统局本部三处处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和代参谋长。
他的后半生,先是作为国民党高级战犯在山东益都和济南白滩头、北京的功德林监狱、秦城劳改农场、秦城监狱关押,接受改造长达26年之久。他自知问题严重,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
1975年3月19日被特赦后,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在填写今后志愿的表格中写道:“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作出了一定贡献。
1978年中秋节,文强寄给台湾友人一首诗,以表达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殷切之情:“谁道蓬莱岛有畛,海天原是一家亲。乡心萦绕关山梦,故国常怀草木春。隔海鹏程明月共,满江渔火友情真。中山陵祭鲜花灿,茗奠先贤少故人。”
晚年的文强生活幸福安康,思想彻底转变,发自内心歌颂祖国的光荣伟大,歌颂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歌颂爱国主义的黄埔军校精神,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
文强是中国当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创建苏区、敌后抗日、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
文强的人生际遇,已远超传奇二字。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成为林彪的班长,两人打过一架
1907年9月19日,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的一个书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文强自小称呼他为“毛大哥”。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少年文强正是受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靠着变卖母亲缝在他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和毛泽覃等人乘船抵达广州。8月,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学,还当了他们的班长。有一次,因林彪枪支走火,他还跟林彪打过一架。
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与此同时,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他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毅然选择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成为一名宣传员。9月,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春,杨森接受朱德的建议,以黄埔军校为蓝本,办起了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文强被任命为该校学生大队大队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第20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
在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奉命离开武汉,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20军(军长为贺龙)第3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3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起义失败后,文强随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后,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当时他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的革命信念还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寻找党组织。
1928年2月,文强辗转四川万县、重庆、成都等地,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正当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他在成都公园里偶然碰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
廖宗泽帮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合旅第2团(团长是邝继勋,中共党员)开展兵运工作,文强任该团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职。
一年半后,文强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1929年底,文强被四川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在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下被打散,无奈之下,文强在陕西境内的一支土匪队伍里混了一段时间,后经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
1930年10月,文强回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被省委留下,先后担任过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3个月后,四川省委进行改组,文强被派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周恩来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文强没有答应
1931年6月,文强遭遇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审查一番后,文强被认定“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罗世文,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随后,文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决定到上海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不久,经友人介绍,文强参加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文强执掌该社后,该社的通讯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他的化名“文浮生”也是声名鹊起,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舰来长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议,反而派人携带厚礼慰问献媚,这种无耻行径有损国格和省格,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何键看后大发雷霆,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文强到案法办。
在这生死关头,文强再一次遇到了廖宗泽。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把文强带上了歧途。
此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来到杭州。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1936年秋,文强在父亲的老友、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经研究,参谋本部虽将文强的分析备案,但并未真正重视。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后,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性。
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文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收集国民党军驻上海各个司令部的战况。这期间,他遇到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在江浙一带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文强把其中的一部分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任政训处处长。后来,文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被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破坏殆尽。文强受命潜赴上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强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的策反和对日情报收集工作。在上海,文强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策反高级军官,但成效不大。日伪情报机关知悉文强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后,对他进行了大肆的追捕。戴笠考虑文强的危险处境,乃电令他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强取道香港,历尽艰险辗转回到重庆。他还没有安顿下来,1942年2月,又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唯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
恰在此时,戴笠来电调文强为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还没动身前去重庆赴任,戴笠又一纸电令改派文强为设在河南的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并立即履职视事。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2000多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这一行动不仅有效地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训练班无一人伤亡。于是,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陕、晋、察、冀、豫、鲁6省和平、津2市的军统工作。在任职北方区区长期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由于功绩卓著,文强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为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戴笠交给文强的主要任务是“防苏反苏反共,为打内战出力,对付北朝鲜、外蒙古亲苏的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在东北期间,文强认识了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杜聿明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经常往上打小报告,很喜欢与其共事。可是,这个好印象却害了文强,后来,他被杜聿明拉进了淮海战役。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夏,文强在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的帮助下,成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正式脱离了军统。文强后来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军令难违,文强还是卷入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命运真会捉弄人,试想如果当时文强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和程潜一样是起义将领了。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解放军7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7个人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7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7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1950年春,文强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监狱。他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觉得有生之年也难以走出这高墙大狱,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但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也许是文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戰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特赦之日,文强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几天后,他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在功德林监狱最初的几年中,文强除了不写悔过书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还是很好的。这种表现是全面的,包括劳动学习、遵守监规(值得一提的是,功德林监狱的监规就是由文强拟订的)等各方面。由于表现好,文强先后当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
1959年10月1日,功德林监狱的战犯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想想自己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中所看到的天翻地覆的新面貌,不禁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长诗《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参观述怀十韵》,其中“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等句,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文强被特赦后,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强,选组长也要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连续当了15年小组长。
1983年,文强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文强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
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愧疚。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際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又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台湾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照片中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军长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军长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赶紧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国的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国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直到90岁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文强大事年表
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
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6年1月:同时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3月,退出国民党。
1926年9月:随朱德转战四川,在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
1927年3月:回到武汉,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28年春:第二次入川,在成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他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
1929年夏: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
1931年秋: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被地下党救出,被省委主要领导误解,加入国民党。
1940年秋: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4年11月:晋升为国民党中将。
1948年8月:脱离军统控制。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敌指挥所副总参谋长。
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被安排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1975年3月:获得特赦,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1年10月22日:以94岁高龄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