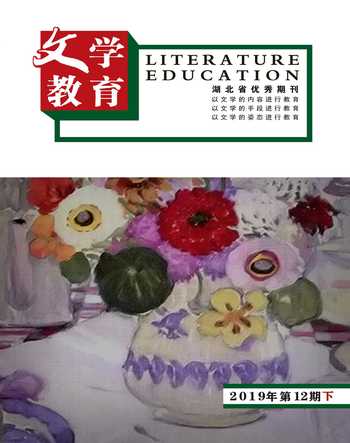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与中国
2019-09-10龙丹
内容摘要:本文以美国现代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和《群芳庭》以及论文集《论男女》为研究对象,聚集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题,即女性如何平衡女性自由与家庭义务这一论题,探索赛珍珠的自由女性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文化对其女性思想的影响。三部作品就书写对象而言形成自我与他者的对位,在文类上形成虚实对照,共同展现了赛珍珠与中国妇女的对话、协商、认同的动态过程。她吸收中国文化的精髓,形成了有别于其她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自由女性主义思想,并以此反观中国妇女,将理想的女性形象投射到作品中的中国妇女身上。本文借拉康的镜像认同理论阐释赛珍珠在跨文化书写中体现的自我他者化的认同模式。
关键词:《大地》 《论男女》 《群芳庭》 自由女性主义思想 中国妇女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就主体的形成指出,自我不能单独确立,而是在对象化的他人关系中认同自己。跨文化语境中的他者之镜如何作用于自我?雅各·拉康的镜子理论提供了理论的启发。他提出婴儿在镜子阶段形成自我,“也就是说主体在认定一个影像之后自身所起的变化”,婴儿兴奋地“将镜中的影像归属于己”[1](90)。镜中的影像(image)让婴儿误认为这是“理想的我”(the ideal I),而实际上是他的影像和他人的表情、行为形成的非我的投射,是对他者的想象性认同。主体通过镜像认同建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而这一过程伴随对外在对象的内化吸收。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精通汉语,浸淫在中国儒家文化中成长,与中国伙伴一同玩耍、成长,由中国阿妈照顾起居,她称中国与美国都是自己的祖国,她的自我认同中有抹不去的他者痕迹。本文选取赛珍珠的三部作品——小说《大地》和《群芳亭》以及论文集《论男女》为研究对象,聚焦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题,即女性自由与家庭义务的关系,分析其女性思想嬗变的三个阶段以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大地》
《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是让赛珍珠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地》是一首描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史诗,书写了农民王龙发家致富的故事,而改变他命运的正是他那沉默、丑陋、勤奋的妻子阿兰。
阿兰勤劳、勇敢、坚韧。从踏入王家门槛开始就承担起所有家务,她独自一人准备了她和王龙的婚宴,让丈夫感到自豪。婚后她勤劳的双手把王家的两间破房子变成了温暖的家:“一天又一天,她不停地做这做那,直到把三间屋子都搞得干干净净,差不多有了生气。”[2](23)她把自我欲望压抑到最小:“她生儿育女,完成了家庭向她提出的所有要求,但从来不提自己的要求;她少言寡语,恪守生活给她规定的伦理道德。”[3](38) 阿兰并没有因为她在丈夫面前奴隶般的地位和踐行无我教而让西方读者鄙夷,相反,她对家庭的无私贡献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亲睐,因为作者赋予她崇高的品德。彼得·康认为阿兰是整篇小说的道德中心,她是王家的灵魂。奥斯卡·卡吉尔(Oscar Cargill)强调阿兰就是“大地中的大地。她最终击败了她的敌人,尽管她的丑相是深入骨髓的”[4](149)。
阿兰这一形象反映了赛珍珠对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的认同,表达了作者在这一时期的女性主张,认为女性身份认同的要素是家庭。在中国生活的四十余年里,赛珍珠认识了不同阶级、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中国妇女,这些妇女的美德和智慧助她形成了上述女性价值观。
赛珍珠的中国小伙伴就像一面镜子,让年幼的她形成了关于自我的初印象——她是白皮肤的中国人。赛兆祥夫妇曾收留过一个中国孤儿彩云做养女,赛珍珠出生时,这个中国姐姐已经结婚,她婚后共生育了六个女儿,她们与赛珍珠成为亲密的伙伴,赛珍珠称自己在学会英语前先学会汉语。她与她的中国小伙伴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零食,一起玩游戏。
婚后赛珍珠随丈夫罗辛·布克(Lossing Buck)走访安徽宿县偏僻的农村以调查中国农村经济情况,也给她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妇女生活的机会:“那些年我走遍了穷乡僻壤……我走进白人不曾到过的家庭,访问千百年来一直住在偏远城镇的名门望族。坐在女人堆里,从她们的聊天中熟悉她们的生活。”[5](9)
《大地》创作于中国,当时赛珍珠与第一任丈夫布克的婚姻并不令人满意,布克与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一样沉迷工作,对妻子冷淡,而布克夫妇唯一的孩子患有先天性智障。这两个因素让赛珍珠无法与她的中国姐妹一样投身于家庭,于是她开始写作,在虚构的世界里将自我投射在阿兰这一他者身上,抒发了一个女性对家庭的热爱,赞美女性奉献家庭的牺牲精神。
二.《论男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自由-女性主义思想萌芽,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的性别角色,努力从精神和身体上解放妇女,思考女性如何处理自我与家庭的关系。赛珍珠对二战前夕美国的性别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发表了论文集《论男女》,提出妇女要在家庭以外的世界实现自我。
在《论男女》中,赛珍珠提出“火药型”妇女(gunpowder women)的概念,她们往往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智力非凡,对家庭主妇的生活不满[6](77-78)。家务不能耗尽“火药型”妇女的能量,她们常常感觉空虚,显得焦躁不安。“火药型”妇女面临三重困境:第一、女性被戴上天使的光环,被迫赋闲在家,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第二、女性的自我无法在家务中得到满足;第三、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接受了现代教育,却被要求回到传统的性别规范之中,二者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裂缝。为了突破这一困境,赛珍珠提议女性打破“天使”的传统,走出家庭,在工作中实现女性自我。
《论男女》定义了一个不甘囿于家庭,需要在广阔的社会领域与男性并肩作战的美国女性自我。《论男女》中关于女性自我与家庭的论断比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中相似的观点早22年出现,后者被认为是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宣言,是美国自由-女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作。1963年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时,赛珍珠曾应邀为其写封面上的介绍。
《论男女》创作于赛珍珠返美之后,此时她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被视为现代新女性的典范,她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女性可以创造与男性同等、甚至更大的成就。号召女性走出家庭这一主张明显背离了赛珍珠在创作初期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与中国的认同困境不无关系。
《大地》的出版乃至获奖引起了民国知识分子对赛珍珠的不满,他们质疑她对中国传统的理解。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具有代表性:“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伯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7](496)。鲁迅对赛珍珠的否定打破了她对他者的认同之境,究其本质,她不过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而已,何以能够代表中国人说话?赛珍珠离开中国时虽然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就,但与中国传统的认同破裂。她在书写《论男女》时大胆地否定《大地》中的女性主张,号召美国妇女在社会上实现自我。
三.《群芳亭》
赛珍珠1946年发表小说《群芳亭》,再次探讨女性与家庭的关系。《群芳亭》是对《大地》和《论男女》的重写。作者在《大地》中歌颂无私奉献家庭的中国农妇阿兰,在《论男女》中却鼓励美国主妇们离家出走。这种小说与非小说、他者与自我的差异在第三部作品《群芳亭》中得到调和。吴太太兼具阿兰的传统美德和“火药型”妇女的自由主义诉求,是作者从自由主义的女性关怀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美德,也是从家庭伦理出发重新理解女性自由的意义。从1931年到1946年,从小说到非小说,《群芳亭》代表了赛珍珠思考女性与家庭这一问题的顶峰,小说塑造了兼顾女性自我与家庭的理想女性,她将这一理想自我投射在他者身上,实现了他者自我化的认同,这是赛珍珠女性思想的第三次嬗变,也是她与中国文化传统再次协商的结果。
吴太太具备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她美丽、聪慧、勤劳,二十多年来把吴家上下打点得井井有条,吴家四世同堂、六十口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吴太太的前半生与阿兰一样,忠实地践行着“无我教”,埋没女性自我的灵魂追求。
但是吴太太“贤妻良母”的角色之外始终存在一个未得到满足的女性自我,这个自我在儒教性别规范的约束下沉睡了24年,终于在她40岁生日这天苏醒,她决心摘掉“天使”的光环,后半生将为自己而活。她宣布结束与丈夫的肉体关系,从他的卧室搬出来,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一个自由-女性主义者的独立宣言,通过获得一个独立的女性空间来解放女性身体,救赎女性灵魂。吴太太把身体从对丈夫的义务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追求灵魂的救赎。身体不再是取悦丈夫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是自己灵魂的居所。她在兰园不仅翻阅公公留下的古典书籍,而且向安德鲁神父学习各种人文知识,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等,感觉自己因多年压抑而日益枯竭的内心又充實起来。
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不同,赛珍珠强调女性在追求自我的同时不能放弃对家庭的义务,尤其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这种思想透露出她对中国家庭伦理的理解。在赛珍珠看来,家庭并不一定是束缚女性的地方,它反而可能是女性权力和智慧的源泉,是值得女性好好经营的地方。赛珍珠接受的儒家教育无疑为这一思想埋下了种子,在她童年时期,母亲一边教她阅读美国的教科书,一边请孔先生陪赛珍珠学习儒家经典,每天朗读两个小时,期间她学会了孝顺、礼仪、因果等儒家哲学[8](52-53)。
与儒家知识分子的交往对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好友林语堂。林语堂书写了《吾国吾民》并于1935年由赛珍珠推荐的庄台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赛珍珠为该书作序,称“《吾国吾民》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9]。赛珍珠返美后,林语堂也移居纽约,两家有亲密的交往。林语堂对中国女性的解读,与赛珍珠有几分相似:第一、林语堂认为中国家庭赋予了女性权力,“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脑”,“她们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作为掌握权力的最优越的武器”[9](143);第二、林语堂认为理性女性必然是伟大的母亲:“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训之诲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诱导之以达成人”[9](149)。
女性如何在自我实现与家庭义务之间做抉择这一主题贯穿《大地》、《论男女》和《群芳亭》,这三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15年,共同呈现了赛珍珠女性主义思想的三重变奏,即女性献身家庭、出走家庭和回归家庭的变化轨迹。赛珍珠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与中国有莫大的关系,她在中国生活的四十余年结交了形态万千的中国妇女,她们用鲜活的生命体验向她讲述了女性无私地贡献家庭的美德,在她的女性主义思想中留下印迹。
参考文献
[1]雅各·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2]《大地》三部曲,王逢振、马传禧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3]王逢振:“关于赛珍珠和她的《大地》三部曲”(分序),赛珍珠著,王逢振、马传禧译,《大地》三部曲。
[4]Oscar Cargill. Intellectual America: Ideas on the March. New York: Macmillan, 1941.
[5]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尚营林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6]Pearl S. Buck. Of Men and Women,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1.
[7]鲁迅:《鲁迅全集》(第1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赛珍珠:《群芳亭》,刘海平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9]林语堂,《吾国吾民》,郝志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大学校级项目“主体与镜像的辩证关系”sisu201606
(作者介绍:龙丹,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