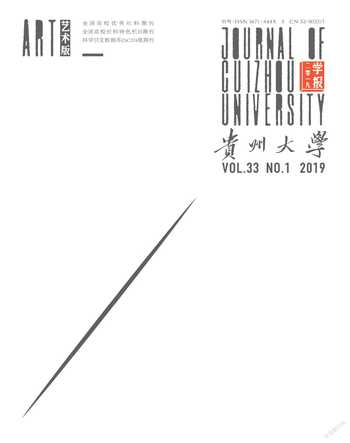“危机”亦或“转机”:杜威的“经验”观念对当前艺术史研究困境的启示
2019-09-10李晓燕
李晓燕
摘 要:面对当前艺术史研究标准与边界的危机,我们不妨从杜威的理论资源中探寻解决之道。杜威的哲学为学界清理危机提供了理论镜鉴,同时他以传播学的理论视域,通过将艺术在本质上理解为人类审美经验的共享,将艺术定义为:“艺术家以唤起受众的审美经验为目的,将日常生活的经验通过媒介转化为艺术作品并传播给受众的一种活动”,为当前艺术史学界化解危机提供了一种启示。
关键词:经验;杜威;艺术本质;艺术定义; 艺术史;传播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1-0060-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1.011
进入20世纪,随着艺术史学体系的完善,艺术史学界开始专注于学科方法论的探索,却很少意识到传统艺术史学体系记录的是特定社会与文化背景下艺术的历时性增长,拓展学科方法可以丰富观照艺术现象的维度,却不能改变各类新兴艺术实践超越原有理论框架的现实。20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类艺术实践严重挑战着学界对艺术的理解,诸如大地艺术、偶发艺术是否属于真正的艺术,能否纳入到艺术史研究领域当中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困扰艺术史论界的难题,学者们意识到当前艺术史研究已陷入到某种危机当中。①更为严重的是,在21世纪中国开创致力于打通各门类艺术的艺术学学科后,作为二级学科支柱的艺术史学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视觉艺术的范畴,远滞后于整个艺术学科的发展。可见,艺术史学界只有认真分析当前研究的困境,找出并清理造成困境的障碍,才能更好地化解“危机”,变“危机”为“转机”。
一、现状与危机:当前艺术史研究之困
回溯艺术史的研究历程,自从1747年法国艺术理论家夏尔·巴托提出“美的艺术”后,学界就以“美”的名义将艺术划分为两种类型:高雅艺术、通俗艺术。从此被称为“美的艺术”的高雅艺术成为艺术史学研究的对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其间不乏像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发出善意的提醒:“应该扩大艺术的概念的外延:‘艺术不应只包括世界上那些无用的、美丽的和富有诗意的东西,还应将实用性的工具在内的所有人造物包括进来。’”[1]但工艺美术、装饰艺术等实用性较强的艺术依然难以进入艺术史视野,就遑论电影、电视、录像等非文本性的视觉文化作品,以及以数字、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艺术了。如果说艺术史产生之初,理论家严格“美丑”分野是囿于彼时艺术门类稀少所致的视野局限的话,那么艺术发展到当前这样一个各艺术形态渐次涌现的背景下,其关注对象还停留在“高雅艺术”,不对实用艺术、新兴艺术实践等丰富的艺术形态做出积极回应,而深陷于观念与物质、虚拟与真实、技术与艺术之辩,逃避甚至拒绝对其做出文化阐释的话,无疑会加速艺术史学游离于当代学术主流之外的速度。而从现实层面看,当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呈现出两方面特征:第一,当前艺术史没有摆脱传统艺术史观的影响,研究对象聚焦于高雅的“视觉艺术”。从哈佛大学教授奥列格·格拉博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芝加哥艺术史教授詹尔斯·埃尔金斯的《没有理论的艺术史》中所引证的材料看,基本集中于毕加索、罗丹等人的绘画以及雕塑等视觉艺术门类,并未涉及听觉艺术(如音乐)和视听综合艺术(如电影)。第二,欧洲中心意识依然是艺术史家划定范围的隐性维度。这一如近代被贡布里希誉为“艺术史之父”的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对欧洲之外艺术的看法,当前学界对欧洲之外艺术的偏见桎梏了艺术史的叙事范围。
美的分类标准和研究范围的局限已成为当前艺术史研究之困,而究其原因是由于不同艺术观所带来的困局。从现象层面看,艺术史研究呈现的高雅与通俗、先锋与传统、文化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反映的是艺术史家对艺术边界的态度;而从逻辑层面看,艺术史家对艺术本质和定义的理解是决定其态度的深层动因。关于艺术本质,两千多年来可谓众说纷纭。主流的观点有:形成于古希腊的“模仿说”;兴起于近代的 “表现说”“直觉说”等。这些本质观几乎涵盖了从柏拉图、列夫·托尔斯泰并延续到20世纪克罗齐等经典的思考,也成为理论家进行艺术定义的逻輯基础。于是“艺术是模仿”“艺术即表现”“艺术即直觉”等定义成为引领各自时代的成果。无可否认,每个定义都是在对前人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有时代进步性,当约翰·凯奇(John Cage)的《4’33”》(1952年)、约瑟夫·库索斯(Joseph Kosuth)的《一把和三把椅子》(1965年)等作品面世时,艺术史论家们突然意识到似乎过去所有定义都无法涵盖这些先锋性的艺术实践。艺术陷入实践远超理论的困惑当中,期间分析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尝试从艺术的定义上探寻问题的根源。他认为给艺术下定义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韦兹运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进行论证,他认为不同名称所指称的事物只可能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关联,因而事物不存在共有本质。“艺术的本质问题类似于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我们即使观察了艺术也找不到共同的属性,艺术有的只是相似性。相似性并不能帮助我们描述、解释或理解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事物”。[2]韦兹以“相似性”关联取代“共同”特征进而消解艺术的本质进而否定艺术的定义。而分析美学家肯尼克(Williom E.Kennick)则将艺术“不可定义”论变为现实,进一步“开放”了艺术边界。至此,从表面看分析美学以开放的边界为将新兴艺术实践、各种艺术形态纳入艺术史领域提供了理论预设,但其取消艺术概念、反本质主义的做法实则取消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界、最终不仅没有解决当前艺术史研究困境,反而以“开放”的名义将艺术史专业推向被取消的边缘,使艺术史研究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当中。诚如罗蒂所述:“每当分析学派无路可走时,杜威就等在路的尽头。”[3]当前艺术史学界要想解决危机还要从杜威的理论资源中寻求启示。
二、中心论的误区:杜威对当前艺术史危机的诊断
首先要澄清学界对杜威学术身份认识的误区。一直以来,杜威都是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者的身份被纳入到学术视野中的,而他作为艺术史论家、传播学者的身份却很少为人关注。“我的目的并非对艺术史进行经济学的阐释”,[4]11艺术是“仅有的、完全而无障碍地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4]121艺术理论家和传播学家的身份使得杜威看待艺术问题时往往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作为一位被罗蒂视为与海德格尔齐名的现代著名哲学家,杜威认为凡是正统哲学都会创造出两个世界:一个是希望民众信仰的、超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经过形而上的翻译会变成人类最高的世界,并成为另一个为民众所生活平常现象世界中个体行动的指南。因此正统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证明一个绝对的、超自然的本体可以带给民众这个本体的性质来换取哲学的尊严。但杜威认为几千年的事实证明,正统哲学并没有引导人们找到那个独立于人和世界之外的超现实的实在。对于如此“自负的”正统哲学,自然会招致许多哲学家的否认和反对,但杜威指出,这些哲学家的否认最多只能指向这样的层面:“向来的否认大都是存疑的(agnostic)和怀疑的(skeptic)……只肯说,那绝对的,最后的本体是不可知的。”[5]15怀疑论者以本体的不可知论来取代对哲学中本质问题的反思,进而回避对哲学正当研究范围的思考。无疑分析美学家属于此列,而要化解当前艺术史研究的危机最重要的是要从哲学上找对根源。杜威认为哲学的本质不可消解,它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本依据,是决定世界万事万物独立存在的基础。以不可知论为借口进而回避对事物本质的思考,是基于个体对所处客观世界认识不深入所导致的知行分离的表现。艺术定义和本质本就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那种“艺术不可定义”或者定义影响新艺术形态产生的说法,只能说明现有的艺术的定义并未跟上时代艺术的发展,理论家没有在艺术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重新定义的生长点。
杜威认为,艺术本质问题并非构成定义的障碍,相反它是进行定义的理论基础。对于艺术本质这个学术谜题,杜威并没有通过批判历史上的各种“本质论”做回应。他采取了一条与传统相反的思路,尝试通过探求哲学根源寻找解决办法。在他看来,肇始于古希腊的摹仿论之所以风靡西方几千年,根源就在于18世纪前期,西方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客体中心论:即认为主体必须围绕客体活动,反映到艺术方面,理论家们需要解释的是艺术主体如何契合对象的问题而并不需要考虑对象如何适应主体。摹仿论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尊重,因此,温克尔曼在艺术史中对完美体现摹仿论的古希腊艺术会做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评价;进入18世纪中后期,当康德完成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轉向后,主体开始成为学术界关心的重点,艺术的表现说、直觉说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杜威对康德引起的哲学转向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主体中心论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康德的“它(指心灵)是用一套本身完善的力量去进行认知的,而且它也只是作用于一种本身同样完善的事先存在的外在材料上的。”[6]223对自我心灵的过分强调会使人的理智脱离作为其生存环境的自然和社会,片面地强调客体世界也会导致主体和世界的分离,无疑近代以来的各种艺术本质观属于前者,摹仿论属于后者。对于绝对的主、客体中心的追求致使从古至今的各种艺术本质论无论是以何种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都难以弥合艺术主体、客体间的裂痕,进而使得理论家们对艺术本质的认识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这种认识导致的结果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几千年来所尊崇的那些本质论究竟是否如实反映了艺术的共同属性,就依照传统思维仅将“美”的艺术纳入到艺术研究的范围之中。一旦遇到新兴艺术实践打破或超越了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就变得无所适从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造成当前艺术史研究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从至今统治西方哲学界几千年的主、客体中心论。杜威的哲学为当前艺术史论界探寻危机根源提供了启示。
三、经验的艺术观:杜威对艺术本质和定义的界定
杜威认为无论主客体中心论以何种面貌呈现在艺术当中,最终都难以避免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正如地球或太阳并不是一个普遍而必然的参考系的绝对中心一样,自我或世界……都不是这个中心。在交互作用着的许多部分之间有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每当努力向着某一个特殊的方向改变着这些交互作用着的各个部分时,就会有一个中心浮现出来”。[6]224他认为哲学真正的中心或出发点在于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克罗齐“从经验及实用上来说,杜威都未能克服心灵与自然这个二元论”[7]9的误读,正好相反,杜威利用“经验”这把钥匙打通了个人和客观世界的藩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全新的艺术观。
对于杜威所说的“经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它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英国经验学派提出的人与客观世界分离的经验。杜威认为经验与自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经验与人类社会生活也不可分割,它是个人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二,杜威的“经验”既包括经验的主体也包括经验的对象,它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其三,经验也包含过程,它是一种贯通人与世界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可以消解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其四,经验是动态的,它始终处于主体与世界互动作用的动态平衡当中;其五,经验有完整和不完整的区别,日常生活的经验通常是不完整的、琐碎的。而对于备受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和斯蒂芬·佩伯(Stephen Pepper)推崇的“本世纪用英语(或是所有语种)写成的最有价值的”[8]可以跻身世界伟大美学著作的《艺术即经验》中所提到的“一个经验”,则是完整的“经验”。它具备满足主体寻求圆满的完善属性。
但“艺术”还不能等同于“一个经验”,杜威所提出的“艺术即经验”命题杜威在同名专著《艺术即经验》中提出此命题。主要指的是审美经验。他关注的重点是“艺术”与“审美经验”的关系。“艺术作品与机器不同,不仅是想象的结果,而且在想象性的而非物质存在的领域起着作用。它所做的是集中与扩大一种直接的经验。换句话说,所形成的审美经验的质料直接地表现那想象性地唤起的意义;它不是像材料在一种机器中被引入到一种新关系之中,仅仅提供手段,通过它,对象存在之上与之外的意图可以得到处理。想象性地被召唤、集合与综合的意义体现在此时此地与自我相互作用的物质存在之中。因此,艺术作品在那经验到它的人那里是对一个同样通过想象而进行的召唤与组织动作的表现的挑战,而不只是对外在活动过程的刺激而产生它的手段。”[4]317杜威认为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它起作用的方式和所提供的个性化经验。它通过想象的方式作用于“经验到它的人”,为艺术欣赏者提供一种集中、扩大的经验。如果艺术家创作审美对象的经验是饱满的,那么他会将自身丰富的经验传递给欣赏者,并想象性地唤起和加强接受者的经验,使欣赏者也接受到丰富、饱满的审美经验。艺术在逻辑上表现为审美经验在艺术家、作品、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艺术家将日常生活中碎片化、零散的经验提取出来,通过合适的媒介加工为具有累积性、完整性,并充满意味的“一个经验”,再通过想象等方式使“一个经验”完善为一个“审美经验”,提供给艺术接受者。另一方面,接受者也不会被动地接受“刺激”,他们会根据艺术作品所唤起的想象进一步丰富“审美经验”, 并积极地反馈给艺术家。杜威认为艺术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艺术家与接受者之间审美经验的共享。以审美经验的共享作为艺术的本质,杜威不仅打破了横亘于艺术家、作品、接受者之间的界限,“作为经验的艺术”也成功克服了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这种本质观有可能弥补历史上出现的种种艺术本质观的不足,在有效清除分析美学家反本质主义的危害的同时为更全面地进行艺术定义提供了现实可能。
在定义方法的选取上,杜威意识到,艺术作为艺术家与接受者之间审美经验共享的实质决定了很难用“属加种差”的方法进行定义,因为这种传统的艺术定义方法首先要求找出与被定义项“艺术”临近的属概念,将其归属到某一个类当中,而艺术在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人类审美经验的交流活动,内部同时包含人和活动这两个属性差异悬殊的范畴,属性不同的范畴是很难归于某一类别的,定义者会因属概念产生的不确定性难以找到与被定义项所反映对象的属性相似的种类,无法有效将种差与属概念有机结合进而影响对艺术的定义。“艺术表示一个做或造的过程。对于美的艺术和对于技术的艺术,都是如此。”[4]54杜威不止一次地强调艺术的活动性,用发生定义的方法往往更能有效地描述艺术发生的整个过程。杜威是以一种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的活动来定位艺术的。他认为将传播的三大核心要素:传播者、传播对象、受众运用到艺术定义当中的话同样成立,作为芝加哥传播学派开创者的身份使得杜威能够转换思维,跳出传统艺术定义的窠臼,尝试以传播学的理论视域为艺术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定义方式。“艺术……通过找到与所有表现的东西构成最完全融合的、严格的性质上的媒介,以一种强调的与完善的方式表示了一种成为许多其他经验的特征的联合”,[4]301“一般所说的一门艺术的力量在于选取自然的、生糙的材料,通过选择与组织而改变它,使之成为强化而集中的建构一个经验的媒介。”[4]278杜威运用传播学的媒介思维对经验加以重构,将艺术理解为:艺术家以唤起受众的审美经验为目的,将日常生活的经验通过媒介转化为艺术作品并传播给受众的一种活动。
四、新的起点:当前艺术史研究的转机
杜威通过探寻艺术本质及重构定义的做法为艺术史论界解决当前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杜威并不认同传统意义上将“美”作为划定艺术史研究对象标准的做法。他认为那些世所公认的经典艺术品在产生之初也并非全部以“美”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他列举被公众誉为“伟大艺术品”的帕台农神庙为例加以说明,神庙的创造者在建造之初首要考虑的并不是美的问题,他们只想将有共同宗教信仰的雅典公民的日常经验以一种城市纪念物的形态表现出来,对雅典公民而言,神庙只是更好地唤起了他们对日常生活及宗教的经验;对于创造者而言,当时雅典公民对他们这种整一、完善经验的认可远比后世学者将神庙表现出的审美经验进行抽象化,并赋予美的名号要重要得多。只不过后来随着经济、政治、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博物馆、画廊的兴起,有一部分君主、贵族、资产阶级新贵、军事掠夺者、以及收藏家为了显示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崇高地位,有意地称这些艺术品为“美的艺术”,从而为历代艺术史的叙事提供了与日常生活经验错位与分裂的力量,使艺术史退变为“美的艺术”的历史,远离民众的世俗生活。致使“那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具有活力的艺术(the arts)对于他(指美的艺术的倡导者)来说,不是艺术:例如,电影、爵士樂、连环漫画。”“室内用具、帐篷与屋子里的陈设、地上的垫子与毛毯、锅碗坛罐……将它们放在博物馆的尊贵的位置。”[4]6-7杜威认为只要认真考察艺术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艺术在发端之初是以满足普通民众审美趣味为旨归的,作为戏剧艺术之源的舞蹈和哑剧就是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结果。那些艺术史中的经典的艺术品也很少仅考虑审美而不顾及实用标准。“美”或“高雅”只不过是强权意识主导下,怀有人为文化偏见的精英阶层强加于艺术之上的权力话语,而并非展现艺术史真实图景的客观标准。以“美”作为标准本就是一种基于错误逻辑之上的荒谬思辨。一旦接受实证检验,便会陷入自相抵牾的哲学陷阱当中。通俗、实用的艺术不应被排除出艺术史研究的范围,因此,要解决当前艺术史研究之困不妨以杜威艺术观中的经验作为重新考量艺术史研究标准的核心范畴。即:不纠结于高雅与通俗、审美与实用、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之辩,以作品是否源于日常生活经验、并能够很好地转化并传播审美经验作为进入艺术史研究范围的参照系。这样就可以为艺术史回应大众、民间、实用、新媒体、数字艺术以及各类新型艺术形态、实践找到充分的理论预设。
对于以“视觉艺术”取代所有门类艺术的问题,杜威的经验观念同样会提供启示。艺术作为共享性审美经验的实质决定了进入艺术史研究对象范围的艺术形态、门类并非由艺术家决定,当然喜好视觉艺术的某些特权阶层也不应成为决策者,艺术史论界应该考虑的是整个艺术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的审美感受。“由于听觉与有机体的身体各部分都有联系,因此声音比其他感官都更能产生反响和共鸣”,“音乐的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要更为广泛”,“由于这种情感效果的直接性,音乐……被归为最高的艺术”。[4]217杜威认为听觉艺术同样重要,其感染力甚至远超越视觉艺术,各门类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力量,艺术研究不分高下,更不应厚此薄彼。在《艺术即经验》“各门艺术的不同实质”一章中,杜威全面梳理了各门类艺术,特别是对文学、音乐做了大篇幅的介绍。杜威对电影、电视等当时新兴的视听艺术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如果艺术史论研究能以是否唤起艺术接受者的审美经验为标准,将艺术史研究的范围扩展为各门类艺术组成的集合体,艺术史研究中的视觉艺术倾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样对于当前艺术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杜威的观点同样会提供启示:审美经验作为文明生活的记录和赞颂,它推动着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在逻辑关系上,共享性的人类审美经验是促进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带有地域性文化偏见的西方学界并不可以依靠其所掌握的话语权评定艺术的优劣。所以杜威欣赏欧洲古典艺术,但同时认为非洲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也可以引发人们更为完满的经验,“20世纪早期的作品的特征以埃及人、拜占庭人、波斯人、中国人、日本人和黑人的艺术影响为其标志。”[4]385杜威预言未来将会迎来一个亚洲和非洲艺术的世纪。
当然杜威的经验艺术观也有很多不足。例如,我们很难从其著作中找到有关艺术定义的逻辑严谨、语序严密的语句的表述。这一方面可能源于他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并未将给艺术下精准定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杜威也意识到精确的语言往往会封闭艺术概念的外延,从而阻碍新艺术形态的产生。但我们还是能从杜威的《经验与自然》《艺术即经验》当中凝练出艺术这个带有集合性质范畴所具有的实在意义,更重要的是杜威经验和艺术观念中的某些真知灼见确实可以为当前艺术史论界克服危机提供有益的启示,学术界如果能够重新认真挖掘杜威的理论资源,不仅有助于走出当前艺术史研究的危机迎来新的转机,而且还有可能为描绘艺术发展的全新图景提供新的起点。
参考文献:
[1] George Kubler, The Shape of Time: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Thing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1.
[2] Morris Weitz ,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15, No. 1 (Sep, 1956).
[3]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viii.
[4]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 杜威.哲学的改造[M]胡适,唐擘黄,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5.
[6]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
[7] Corce,Dewey’s Aesthetics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 [美] 托马斯·亚历山大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
[8] Monroe Beardsley, 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Macmilian,1996: 332.
(责任编辑:杨 飞 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