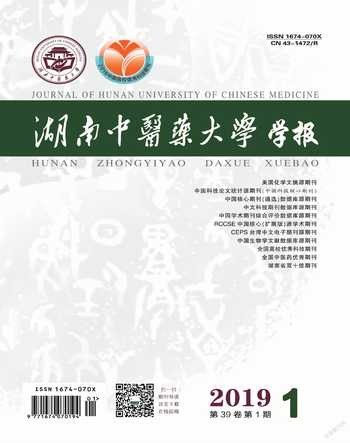生态翻译观视域下李照国译《黄帝内经》的 适应性选择分析及启示
2019-09-10张丹肖平
张丹 肖平

〔摘要〕 着眼于《黄帝内经》的价值及英译历程的简要梳理,介绍较为成功的威斯译本、吴氏父子译本和李照国译本,从中总结中医文献翻译的共识性原则,即阐释医理和传递民族特色。同时,在生态翻译观的视域下阐述了翻译生态环境和翻译中的适应性选择。深度结合李本翻译实例,详细分析了采用直译、音译、转换译法和加注译法,分别体现其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选择。从而得出李本成功的经验:译法的选择应该结合对译入语市场需求的准确判断,以及读者群体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对中医术语、中医思维可接受程度的合理前瞻。这在新时代下,关于中医翻译如何继承中医文化精髓,如何体现译者对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信,如何服务文化强国战略等,都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黄帝内经;生态翻译观;适应性选择;传递民族特色
〔中图分类号〕R2-0;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doi:10.3969/j.issn.1674-070X.2019.01.031
Analysis of Adaptive Selection in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Translated by
Li Zhaoguo from Eco-translatology and Its Enlightenment
ZHANG Dan, XIAO Ping*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value of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and its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thesis makes a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 by Ilza Veith, Wu Liansheng and Wu Qi, and Li Zhaoguo, and draws the comm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at is to illustrate the Chinese medicine and to delivery of national features i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the thesis gives a brief demonstration of ecology in transl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 and then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daptive selections embodied by literal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noting in Li Zhaoguo's translation version. The above analys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in light of the accurate judgment of need of target language market, and of the reasonable foresight of foreign reader's interest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heir acceptance to Chinese medicine terms and thinking patterns. This thesis is supposed to give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keeping its essence and showing the full culture ascription and confidence of nowadays translators.
〔Keywords〕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Eco-translatology; adaptive selection; delivery of national features
《黃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不仅是中医第一部理论经典,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成就,更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石。《内经》,明确体现中医理论体系与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引入了大量的唯物主义哲学元素,如“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中医特有的整体观念和恒动观念,符合现代唯物主义普遍联系和永恒变化的基本观点[1]。
《内经》不仅对中国传统医学有着非凡的意义,同时也是世界的瑰宝。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内经》的翻译,便于各国学者在医学、生命科学的角度之外,拓展哲学、伦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科学等多维角度来研究它,挖掘更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1 《内经》的英译历程及翻译原则的基本共识 近百年间,《内经》,尤其是《素问》部分,英语译本多达13种,目前广为流传,在海外接受程度最高,且国内外研究集中的有以下3种。
首先,在海外第一部《内经》翻译是由美国医学史博士伊尔扎·威斯(Ilza Veith)于1949年出版的“The Yellow Empire’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此译本仅翻译了《素问》的1至34章,重点介绍了针刺疗法,但遗憾的是将《内经》译为“内科医学”,与原著的偏差比较明显。
旅美华人吴连胜和吴奇父子于1997年出版了“Yellow Empire’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是上世纪末《内经》翻译的成功之作。吴氏父子有着多年的从医经验,但并无语言学习经历,由此该译本翻译原则重在阐释医理,力求保证译本的严谨性和规定性,翻译策略上多倚重意译、加注和解释,极少用直译、音译。客观而言,吴氏父子对当时中国传统医学在海外已经启蒙的现状,以及译入语读者群体对中医传统文化的热情略微低估;并且,与古代汉语高度凝练和中医术语多义性等语言特征相比,吴氏父子译本不可避免地损失了一些民族性特征。
李照国具有语言学和医学双重知识背景,系统分析当下英语国家对中医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并基于其对中医传统文化的自信,以及西方读者对中医理论和中医文化的兴趣值和理解能力,出版了《素问》和《灵枢》的完整译本——“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李本翻译策略多用直译、音译,并针对中医术语的负载词和多义现象,少量使用意译和添加注释的方式,最大程度保留了中医文化和哲学理念。李本是21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译本,目前已在国内外享有高度认同,收录入《大中华文库》。
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外翻译家知识背景不同,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同,然而,都能就《内经》及中医文献翻译的原则达成基本共识:既要阐释医理,同时要传递中医的民族特色[2]。
2 生态翻译观
生态学是指研究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近年来,随着人们保护生存环境意识的提高,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纷纷问世,生态翻译学就是将翻译与生态学结合研究的一门交叉性学科。
2.1 生态翻译观的发展
著名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于1988年最早提出译本的传播过程中体现着某种的生态学特征,但直到2003年,米歇尔·克罗尼恩(Michael Cronin)将视角扩大到不同语言之间“翻译的生态”的关注,正式提出了“翻译生态学”这一术语。但西方学者并未系统地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翻译活动,也未构建翻译实践的理论框架。国内学者张明权、季羡林、崔启亮等人都曾借用“翻译生态”术语来研究翻译问题。2004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 《翻译适应性选择》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许建中的2009年《翻译生态学》和胡教授2013年《生态翻译学:构建与诠释》两本著作,不仅为生态翻译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同时将其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应用于翻译实践和翻译评价的研究中。
此外,生态翻译学研究者于2010年发起成立了“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刘崇杰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生态翻译学正在国际、国内的翻译研究中焕发着新的生机和魅力。国内大量研究集中于将生态翻译与诗歌翻译、散文翻译、电影字幕翻译等结合,产生了大量成果。
2.2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
胡庚申教授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适应性选择为核心理论,是一项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做出符合生态理性的综观和描述。”[3]
2.2.1 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场,或者一个网络系统,是在一项翻译活动中不同分工的人群组合,包括原文作者、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译文编审及编辑,甚至包括赞助商、出版商、版权所有人、译评人、营销商等。由此可见,译文是否能够达成理想的传播效果,必然依赖于翻译流程中所有人的协作,生态场中的和谐共处。
2.2.2 适应性选择 就翻译理论本体而言,不仅需要包括生态环境中从事翻译活动的相关人员,更应该涵盖翻译实践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译文读者情况的分析与判断。这也就是需要正确回答适应性选择中,要适应谁,以及怎样适应的问题。
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即适应选择之过程,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通过多维度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的生态理性和自然规律从而得出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作品。”[4]适应性选择是生态翻译观理论系统的核心,并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各种翻译原则和策略熟练掌握运用,更要对时代的要求,目标读者群体的要求、兴趣、可接受程度等具有合理的评估,并依据这些因素来指导翻译实践,在翻译策略上做到最为恰当的适应性选择[5]。
3 李照国译《内经》的适应性分析
3.1 音译法体现适应性选择
吴氏父子的《内经》译本是上个世纪的代表之作,而李照国翻译为本世纪较为权威的译本,分别为二十世纪前后中医典籍翻译的集大成者。两种译本的对比中,最为直观的差异体现在中医核心术语翻译策略的适应性选择问题。
李本更多采用音译法,而吴氏父子译本中多采用解释、注释的策略。相较于吴本,李本呈现出几个突出优势:首先,音译法不用过多解释说明,也不偏向英语分析、解构的思维方式,反而更有利于保留中医术语的多义性,突出体现中医语言的模糊性和神秘感,例如“精神”、“五行”、“脏腑”,采用音譯为Jingshen、 the Wuxing \ the Zangfu-Organs[6],更明确提示整体名词概念,也更有利于体现中医的整体观念。其次,吴本对术语译文更普遍采用小写,而李本翻译中术语普遍大写,看似是简单的处理,然而提示作用显著,有效避免理解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忽略或混淆[7];此外,采用音译法,回译性方面无疑得到极大的提升,更便于译入语读者领悟中医术语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在保留中医语言特色方面,也更具优势。具体见表1。
3.2 直译法体现适应性选择
从句法结构角度分析,李本翻译中也采用直译法居多,直接采用和原文一致的平行、并列结构,保证每个小句的主干部分信息统一,而从属部分信息用来体现不同的病症或表征,对译文读者而言,不仅降低了理解难度、突出了信息重点,同时保留了语言结构的工整划一,以及由此产生的韵律美,很好地兼顾了阐释医理和传递中医民族特色的功能。例如李本翻译《素问·疟论》中“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一句,就采用“Malaria in autumn is marked by……; malaria in winter is marked by……, malaria in spring is marked by……; and malaria in summer is marked by……”[8]同时,此例中的“多汗”,并未对应为英语的多汗症“hyperhidrosis”,而是采用“profuse sweating”,最大程度地做到了文化保真。此外,《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一句,出现了4次“犹”,用明喻的方式解释说明针刺疗法的不同手法及效果,阐述“善用针者”的技法高超。李照国翻译为“Those who are good at acupuncture treat disease just as simple as pulling a sting, removing a stain, untying a knot or clearing away silt in a river.”[9]其中“as simple as”保留了原文中的修辞,同时采用4处现在分词形式列为并列结构,也体现了直译法的应用。不仅激发译入语读者了解和学习中医的兴趣,而且很好地体现了翻译中的适应性选择。
选择音译法和直译法,不仅是基于李照国的医学和语言学知识背景,更是源于译者对译入语读者群体和读者市场的客观现状判断准确:近百年来,中医文献翻译不断实践,译本在海外流行,已经培养了一批对中医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群体,对中医术语、中医理论体系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接受能力。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倾向于采用直译和音译,才能保证既不会造成理解障碍或文化隔阂,还有利于激发译入语读者了解和学习中医的兴趣,阐释医理的同时传递民族特色,成功实现了翻译中的适应性选择。
3.3 转换译法体现适应性选择
首先,医界和译者都认为《黄帝内经》不仅包括内科学的医理、诊疗等理论总结,同样也体现中国古代的解剖学知识,涵盖古代外科诊疗方法。李照国对《黄帝内经》的标题译法为“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直接取消了“内”的局限,打破了之前多种译本中均采用的“Internal Medicine”的传统翻译,破除了译入语读者原有将《内经》定位为内科医学著作的误解。这是李本中灵活转换译法的最直观体现,也是最为重大的实事求是实践之一。
中医与西医,虽然从哲学基础和诊疗理论上存在极大差异,但两者对生理结构、生理现象,以及病症、病征的认识和表述,基本能达成共识、保持一致。在这个前提下,采用转换译法,迁就英语表达方式,就可有效降低译文读者的理解难度,从而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程度。例如在《素问·脉要精微论第十七》中“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与。得守着生,失守者死”一句,着重论述“藏”的功能与对生命的意义。李本译为“Failure of the Canglin (granary) to store up is due to failure of the Menhu (anus) to restain. Incontinence of urine is due to failure of the bladder to store (urine). Normal functions [of the viscera] ensure living, while dysfunctions [of the viscera] cause death.”[8]将“水泉”转换为尿液“urine”;“水泉不止”译为尿失禁“incontinence of urine”;“膀胱不藏”译为不能储存尿液“failure of the bladder to store (urine)”;此外,将“得守”和“失守”分别译为“normal functions of the viscera”和“dysfunctions of the viscera”。
3.4 加注译法体现适应性选择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都显现“意合”的鲜明特征,既不注重形式衔接,结构松散,独立、平行小句较为多见;相比之下,英语往往呈現“形合”特征,强调使用大量显性形式衔接成分,使句式呈现结构整合、逻辑严密的特征。英语和汉语在语言结构紧密程度上的显著差异,必然要求译者在翻译策略上做出选择。
李本翻译除了译出汉语原文中的主干信息之外,也采用了加注译法:一方面,在译入语中添加必要的衔接成分,不仅加强了译文的衔接紧密程度,使译文更符合英语高度整合的形合特征;另一方面,使用“[……]”将加注部分显性标记提示译文读者,这些衔接性的信息在汉语原文中其实不存在,而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有选择性的添加。例如在《灵枢·百病始生第六十六》中:“夫百病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一句,李本翻译中就多次使用加注译法:“The occurrence of all disease is caused exclusively by [attack of pathogenic] wind, rain, cold and heat, coolness and dampness [as well as emotional changes such as] excessive rejoicing and anger damage the Zang-organs. [Pathogenic] wind and rain damage the upper [part of body]. [Pathogenic] coolness and dampness damage the lower [part of body].”[9]
采用加注译法来体现适应选择性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当前产出了可接受程度更高的译文;更加在于建立起这样的长效机制,可以直观地引导译文读者去体验和思考汉语与英语不同的形式结构特征,在慢慢的调整、适应、接受的过程中,培养了更优质的译文读者群体。这为后继的翻译者创造了良好的译文讀者基础,以后再翻译中医文献时,需要添加注释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就更有利于在中医翻译中达成传递民族特色的功能。
4 李照国译《内经》对当下中医翻译的启示
李本《内经》翻译基本达成了中医文献翻译原则的基本共识,既兼顾了阐释医理的语用功能,也很好地承担了传递民族特色的文化功能。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了译者对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信,完全符合新时代下,文化强国、文化兴国的战略。另一方面,李本翻译体现了其对译入语市场和读者群体的准确判断,不仅结合海外市场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需求,对中医药文化兴趣的深度分析;同时,结合译文读者对中医术语、中医思维接受程度的合理性前瞻,甚至于已经深入到为后继翻译者培养优质的海外读者的阶段。
李照国对上述现状的合理判断和前瞻性视角,以及对译文读者的培养与塑造,不仅是李本翻译中适应性选择成功的经验,更是对“翻译到底要适应谁,以及怎样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来达成适应”等根本问题的最佳回答。在新时代下,这些理据和经验都对当代译者,尤其是致力于中医药文献翻译和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的人员,关于中医翻译如何继承中医文化精髓,如何体现译者对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信,如何服务文化强国战略等问题,都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邱海荣,姚 欣.“译者为中心”翻译观在《黄帝内经》英语中的体现[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7,23(3):415-417,420.
[2] 李照国.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的概念、原则与方法[J].中国翻译,2008,29(4):63-70.
[3]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构建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6.
[4] 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25(3):40.
[5] 胡庚申.翻译适应性选择[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0.
[6] 吴连胜,吴 奇.《黄帝内经》英汉对照[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7] 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8] 李照国.黄帝内经·素问[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9] 李照国.黄帝内经·灵枢[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