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头运
2019-09-10汪菊珍
汪菊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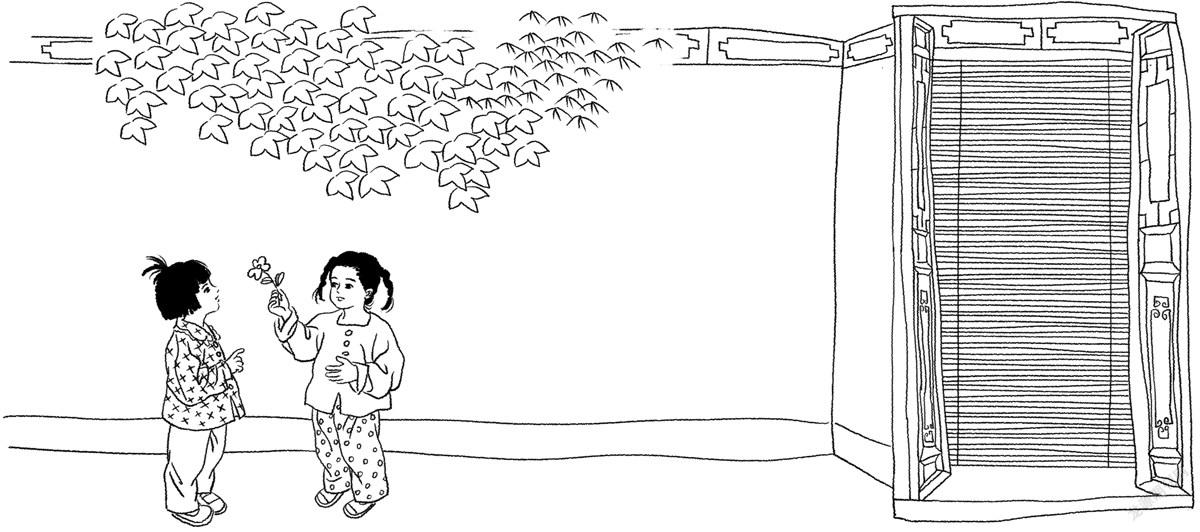
阿红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动不动就往她家跑。
二房厅最后一进,镇志记载,它叫德逸馆,我们却称它后堂前。也有一道仪门,照例也只剩下一个光溜溜的石头门槛。不同的是,这个仪门两旁的墙壁完整,只是都成了黑色。墙壁下依次放着各家的粪缸,缸沿儿都光溜溜的——男人大解,会从自己家门后拿根扁担,搁在缸沿儿,完后再藏到门背后。
这个院子比前院浅,铺设的石板也小。晴天搭有各家的三脚棚,晒衣服、被头。下雨时满院积水,雨过,石板马上干了,只留下石板缝里的几棵青草,在阳光下闪着雨珠。这进院子也是五间楼房,格局与前面一进相似。只是,它没有穿堂,除了西边第二间关着,其余都住了人家。
院子的西北角有门,通向大街。我开始跟了爷爷,经过这里去街上,看到成群结队的孩子玩在一起,好不羡慕。后来我独自上街,就停下来看他们。再后来,可能是阿红招呼了我,我才逐渐和他们玩到了一起。由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阿红家是我每天必到之地。
刚开始玩的是廊柱。这里的檐廊更宽,足有两米。廊柱也更大,下端垫有椭圆形的石墩。我好不容易爬上石墩,想往上攀,但是,才抱住廊柱,手就被廊柱开裂处的倒刺戳伤了。看着虎口上的一根褐色木刺,我差点儿哭了。赶快跑回家,让爷爷给我挑出刺,搽上鳖蛋油,才罢。
看阿红他们玩一字跌,我也想学。檐廊下的地面,铺的是洋红和蓝灰的花崗石,非常光滑。尤其是那间空房的廊下,简直照得出人影。阿红见我玩这个,马上阻止,还告诉了我道理。原来,这一字跌必须刚会走路时学,不然,脚骨会伤。我没有听她的,继续玩着。她就吓我,要把这事告诉我爷爷,我才不再坚持。
登堂入室到阿红家,是读小学后的事情。我和阿红都很高,是后排的同桌。早上我起得迟,吃完爷爷烧的水泡饭,一路跑着,才能不迟到,所以各自上学。中午放学回家,我家里的饭菜老早等着了。我吃完中饭,就说读书去了,其实是去阿红家,等她一起上学。她父母忙,下面有两个弟弟,家务几乎由她包了。
我看着她洗好碗,淘好晚上的米(早点儿淘米,能出更多的饭),有时还跟着她去埠头洗衣服——她去的埠头总是石棉厂门口的那个,我常担心被母亲看到。有时,还要等一只母鸡,它在鸡舍里面蹲着,让我着急。直到阿红捡了蛋,喂了鸡娘,才一起上学。为此,阿红总是不无羡慕地对我说:“你家里有爷爷外婆真好。”
我却一直羡慕她家的楼房。阿红家住了后堂前居中的一间,特别宽阔,还有两道雕花大门。第一道,用的花格子木门,第二道也是大门,只是没有雕花。因此,她家虽然只有一间楼房,但是光楼下就有宽敞的三间——前堂、后灶,居中的一间,她家放了花秆、稻草、农具等杂物。
阿红母亲沉默寡言,终日坐在石棉车上,也不见她对阿红姐弟吩咐过什么,阿红和弟弟总是踩着钟点忙乎。阿红父亲原先是生产队会计,后来进了社办厂。他除了上班,还到自留地劳动。他还早早给土灶安了风箱,后来又在灶头桌旁打了一眼水井。看了他们的风箱,我才几次要求父母,也给烧饭的爷爷装一个。
看人家饭碗头,是要被大人责备的。别的人家开饭,我肯定识相地回家。独有阿红家,我不见外。也是,阿红家堂前宽敞,一张小桌吃饭,只占据了一角,我坐在另外一边,也和他们隔得远远的。当然,结果我还是会经常扫视他们桌上的饭菜。
她家喜欢香胡笋,时常有这么一碗。咸菜汤是在饭镬里蒸的,菜切得很细,汤很清白。她家的带鱼很肥,比我家的太公辫子大多了。阿红母亲烧带鱼很特别,咸菜放得不多,酱油却放得不少。吃的时候,她竖起筷子,把一块带鱼戳得细细碎碎的。有一片金黄的鱼皮粘连了雪白的鱼肉,我看得垂涎欲滴。
初高中路远,更要约了阿红一起同行。这条路快走十五分钟,我和阿红比赛,总是她快。后来还互相学走路姿势,八字脚,也是那时学她的结果。下雨路滑,我还摔过几跤,阿红却从不这样没出息。——当时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这其实是阿红做惯了家务,手脚利落的缘故。
我有时晚上也去阿红家,主要听故事。故事以鬼怪为主,我听得怕了,就有阿红或者讲故事的人——时常是阿杜的大弟,送我回家。隔壁的连婆也经常在场,她会讲二房厅的旧事。她说:“这前后几进大宅,都是明朝的严嵩送给谢阁老的,后来这里出过很多大官。”一次,她指着阿红家的后面说:“这后墙上还有两个字,谁也解释不出来呢。”
高中毕业,我马上代课,阿红务农纺石棉,不久做了生产队会计。想不到的是,我考上大学第三年,她就通知我喝喜酒了。我吓了一大跳,结婚?和谁?回家才知道,新郎是六坊宅的儿子,住水龙间旁边。他是退伍军人,能说会道,知道阿红和我要好,对我非常客气。
阿红出嫁那天,我第一次上了她家楼上。楼梯宽阔结实,也有楼梯门。楼上分为前后两间,前半间朝南搭了一张大床,靠窗口朝东,是阿红的单人床。后半间也宽敞,住着阿红的两个弟弟。我想起了连婆当年说过的两个字,探头朝外张望,果然看到雕刻在方砖上“在相”两个字。我自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但看得出,这两字的字迹古朴苍劲,真不是凡家手笔。
关于阿红家,还有一个趣事。我小时没有读过幼儿园,却上过托儿所,由我爷爷接送,姐姐送中饭。姐姐半路偷吃了我的饭,害得我肚子饿,偷人家碗里的糊头吃。一个叫聋娘的——当时的保育员——看到我总是用手指刮她自己的脸,还冲我伸舌头。我知道她这是在羞我,但是,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有一天,我忽然想,这个让我背了一辈子罪名的托儿所,到底是二房厅的哪间?——二房厅虽然是深宅大院,但是,我闭着眼睛也数得出那几户人家。问过姐姐几次,她只记得送饭、偷饭,甚至记得偷饭吃的地方,是一条四下无人的小弄堂,却忘记了送饭的地点。
直到前年,我才问了比我大八岁的哥哥。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托儿所是我小时每天去的阿红家。听闻此言,我吃了一惊,问了哥哥几遍,口吃的哥哥,却每次回答得干脆。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小时大人常说的脚头运,可能是真的呀!——人在不知不觉间,会往自己熟悉的地方走去。
[责任编辑 王彦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