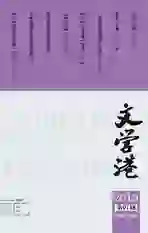为林逋卸妆
2019-08-26柯平
柯平
结庐的真相(下)
在巨浪二型导弹射程已达一万两千公里的当下,谈论诗经时代的冷兵器显然是个滑稽的话题,但彼此精神上的血缘关系依然丝丝缕缕,若断若存,不可能完全割断。比如躺在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的《豳风图》,这幅传为出自北宋马和之手的巨作,全卷由七首相关作品组成,雄浑沉厚,元气淋漓,不类凡工。开首《七月》展示“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后周人小康生活的温馨画面,末尾《狼跋》则宣告一个曾经辉煌的时代的结束。而在其中的第二幅《鸱鸮》和第三幅《东山》里,可以找到某种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一座形状盘屈的土山,一棵高大苍夷的亭亭如盖的古树,一条树下不远处闪着亮光奔腾而过的大溪,以及一队正从树下出发奉命前去东征的士兵,更重要的还有树顶原该有的鹊巢以及藏在里面的佛罗髻发。尽管走在队伍前面的周公“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哀吟千古之下尚令闻者心伤,但值得关注的显然还是士兵们手中武器的样式,将画面放大后,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它的形状:即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缚有一布结模样的玩意,大约也即后世枪矛棍棒之类的祖宗了。与其说是临阵对敌所用的搏命之具,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便携式的宗教秘密武器——作为对其时禁祀的古木鹊巢这一宗族图腾力所能及的模仿。由此联想起战争的‘战字为什么左边是个占卜的占,现存最早的古书《说文》想必很乐意告诉你:“战,鬬也。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鬥(古文斗)之形。”《广韵》补充说“凡从斗者,今与门户字同”,大意就是古代只要有战事发生,双方交手的地方必为关门,关为水关,门为堰门,俗以水门为斗门,其义出此。《尚书无逸》又透露战斗的内容为“厥口诅祝”,后有疏云“诅祝谓吿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吿神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就是通过以向本族的神祖祷告的方式,祈望能無情地加祸于对方,从而取得战争胜利。事实上周家两位祖宗文王武王都是这方面的高手,“祈于六末(太末)山川,攻于商神”(详《尚书》程寤篇),他们的死党宋家祖宗微子启自然也不甘落后,“宋王筑为巢,帝(立)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胃,从下血坠流地”(详《吕氏春秋》过理篇)。当然,喜欢《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读者不看这些玩意也没关系,只要看电视就行了,同样也能心领神会,因前者的升级版就是赵子龙顶端有红穗的龙胆亮银枪,而后者《红楼梦》廿五回赵姨娘请马道婆剪纸人对付凤姐宝玉的相关细节描写,即《战国策燕策》秦昭襄王抱怨“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的秘术在民间的出色运用,包括康熙原立太子胤礽的被废,亦与此有直接关系。考虑到这种精神战法实为西周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有号称三公之一的冢公专司其职,《周礼春官》所谓“诅祝,掌盟诅之祝号”是也。不仅历代流传有序,还能时常发扬光大,推陈出新,甚至到了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八四一年,船坚炮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明标志,而新任广东军务参赞杨芳的马桶还在从广州城头不停地倒下来——作为对付英法联军惟一有效的秘密武器,让四库版《武备志》里号称威力无穷的红衣大炮显得相当委曲,尽管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在胡闹。
在周公丧失家园后率带他的精神战士被迫东迁的两千年后,另一位有类似身世背景的人物也风尘仆仆行走在路上,不过方向正好与他相反,一个由西而东,一个由东而西,就是说在离开宁海西湖之上或土山树巢精神领地的八年后又回到了那里。包括手里拿的玩意,模样也有些相似,不过不是所谓兵器,而是更潇洒的钓竿,但如果你能听懂前者枪头布结与后者竿端纶丝之间的喁喁私语,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既非北语,也非南音,而是更亲切的浙东土话。
一幅作者不明、疑同样出自马和之手的画卷为我们描绘了此次搬迁途中的情景,老妻少子,瓶瓶罐罐,场面寒酸,人物毕肖,在没有手机自拍的年代里,也算是难得的现实场景的精彩重现了。此画原藏晚宋的梅花党魁刘后村处,并有题跋,此人在南宋的重要性,无论文学史和宗教史似乎都有些忽略他了,后世只给他挂了一个主战派的头衔,希望这个战不是前述战斗的战。生平留下《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重要部分残缺异常,希望也真是爱好文学的蠹虫们的功劳。即以此段题跋为例,周亮工《书影》赞为“常觉依稀隐显都在目中,反疑诸画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后一人而已。”可见他的厉害。但也许正因太聪明,对梅花怀有秘密情感,如首倡百咏,广征和诗,与林氏后人关系密切,又号称“若向鼻端参得透,孤山不必在杭州”,难免树大招风,至少本该是以林逋搬家为题材所创作的画卷,出现在他的文集里已是《跋杨通老移居图》了,甚至还有一番令人啼笑皆非的考证,原文如下:
“一帽而跣者,荷药瓢书卷先行。一髫而牧者,负布囊驱三羊(童)继之;一女(童)子蓬首挟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儿。一奴荷荐席筠蓝、帛槌之属又继之。处士带帽执卷骑驴,一奴负琴又继之。细君抱一儿骑牛,别一儿坐母前,持箠曳绳,殿其后。处士攒眉凝思,若觅句然。虽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极天下之酸寒滥缕,然犹蓄二琴,手不择卷。其迂阔野逸之态,每一展玩,使人意消。旧题云杨通老移居图,不知通老乃画师欤?或即卷中之人欤?本朝处士,魏野有亭榭,林逋无妻子;惟杨朴最贫而有累,恐是画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当访诸博识者。”(此据适园丛书刘后村题跋卷四)
看似严肃认真的考证,实际上只是一出闹剧,作者好像不知道杨朴先生是太宗时候人,于真宗还没来得及封禅的咸平六年(1003)就已死去,而善琴在北宋隐士中只有林逋是强项,其余不闻焉。加上处士头衔为国家封典,朝廷恩宠,不是你自己随便想称就能称的,而姓杨的终其一生未能有此幸运。因此所谓《杨通老移居图》,原题当为《林逋老移居图》,或讹或伪,如此而已。何况林为马和之精神偶像不是什么秘密,此人一生留下画作虽然不多,但大多与此有关,如《西郊寻梅图》、《高士观梅图》、《邀月赏梅图》、《和靖观梅图》、《雪屐观梅图》、《月下观梅图》等,其中又以《和靖觅句图》为最有名,同样为刘某囊中之物,且有《跋马和之觅句图》称“夜阑漏尽,冻鹤先睡,苍头奴屈两髋,煨残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缺唇瓦瓴贮梅花一枝,岂非极天下苦硬之人,然后能道天下秀杰之句耶?”与上跋中的“处士攒眉凝思,若觅句然”正好形成互证关系。刘殁后此图流出,落到一个叫王任的人手里,明州大儒舒阆风当年见到后亦有题云:“图上着帽隐几而坐,若有所思;案上置笔砚纸墨,案前有古罍插梅花,此和靖也。背后一童子坐,举足加火炉上。后有一鹤就地欲眠,引颈反顾,与周道士本同格。”(《阆风集》题王任所藏林逋索句图)相比前者的吞吞吐吐,后者说得明明白白,但也不能完全怪这姓刘的,毕竟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政治立场允许有所不同。
重新回到湖区,却非原来故宅,而是像杂技演员一样居于树间危巢,可谓真正返回到上古时代,尽管从形式上看,多少显得有些怪异,让关心他崇仰他的那些朋友们放心不下,实际上如果真能安心住下来,生活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因树顶如冠,可以遮风避雨,树间有洞,干燥通气,冬暖夏凉。更何况还有高官粉丝的捐俸资助,内部设施想必也一定不会太差。他的《山阁偶书》“绕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轩。但将松籁延佳客,常带岚霏认远村。吴榜自能凌晚汰,湘累何苦届芳荪。余生多病期恬养,聊此栖迟一避喧。”应该正是此次搬家后的产物,跟那首更著名的《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写于同一时间,因所谓寿堂即山阁也。当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离经叛道的姿态显然带有某种行为艺术的特征,或称精神表演,但当时的人看法不是这样,普遍认为是行迹高逸的表现,与伯夷叔齐不食周栗、陶渊明拒用义熙年号、张志和垂钓不设饵、吾子衍楼居不置梯、张岱生前自为墓志铭、梅兰芳蓄须明志之类是同样的玩法。而相比之下,又以林的处世形象为更复杂,自然也更艰难,犹如冰与火置于同一器皿——在身体应诏出仕以后,精神方面却走得更远,前者因屈服而卑微,后者因决绝而高洁。此前八年地窟生活的修炼,显然已让他学会了灵肉分离的本领,进入到更高的境界。至于黄宗羲生前自营生圹,是否系对他自筑寿堂的模仿,因没有详细考证,不敢轻下结论,但寿堂非指坟墓是可以肯定的。按孙奕《示儿编》卷十一寿堂条云:“今士人尺牍中称人之母曰寿堂,盖不知忌讳。按陆士衡挽歌云:寿堂延魑魅。注曰:寿堂,祭祀处。言既死,于祭祀之处独相处。魑魅,楚辞曰:謇将澹兮寿堂。王逸曰:寿堂,供神之处。林逋自作寿堂诗曰: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踈。茂陵它日求遗藁,犹喜曾无封禅书(原注:《皇朝文鉴》),又指邱塜为寿堂也。究而言之,称人之母者,岂不背理伤义乎?毛诗自有寿母二字(原注:閟宫),何不称之?”他这段久积于心突如其来的牢骚有两个重点,一是寿堂非坟墓,为古人祭母之所的特称;二是其名不很妥当,当从毛诗称閟宫为是。考《诗鲁颂閟宫》:“閟官有侐,实实枚枚。”毛亨传:“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想起宋祁在《伤和靖先生君复二首》里说的“姬姜生不娶,封禅死无书”,又想起其时主封禅、禁祭母的闹剧,觉得他当时所做的一切真的很不容易。
筑于树间的新居,自然是对已被废除的鹊巢的补救,因此这处居所在以后年代里就被称作巢居阁。而树本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有多大规模,形状如何?以拥有七部宋元方志而名列全国第一的明州,于此却偏偏吝于一辞,不作交代。好在有清人袁枚的《随园纪游册》,其乾隆六十年四月初四条下记云:“茶后过黄泥岭、布阵岭,甚高。旋至阿育王寺。大门内正殿前有石台,台上有古松一株,围抱约五尺许,高不过八尺。老干下垂,破地而起,夭矫拳曲,着地如有根者七株,卧而复起者十三枝,覆阴约三亩,名曰放光松,以宋(南朝刘宋)时舍利飞来挂树故也,相传为晋人手植。”又当天晚上无法返回,就住在阿育王寺里,“御书楼下,古梅一枝,高出楼上。楼有四高山包住,对面二山,远山浮青,近山浓绿。”这部日记不见于今本《袁枚全集》,如果不是在美国的袁氏后人捐献,谁又能想到即使到清代中期,我们和靖先生的寄身之所,在他的家乡依然古貌犹存。而如果有人认为仅仅文字描写还不太过瘾,又有寺内高僧大觉禅师老友苏轼生平唯一留下的画卷《木石图》,可供观摩怀想。画面展示的正是此树的主体部分,枯木在右,状似鹿角;怪石在左,形如蜗牛。卷后首跋刘应时字良佐,四明人,最后装裱收藏者沐璘,即所谓云南沐府宁王。尤其上面米芾的题诗“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剔幽发隐,欲言又止,颇耐人寻味。在去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这幅画拍出了四亿六千万的高价,如果知道它与林和靖的身世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想必价格应该更高。
现在大约可以安心坐下来好好学习他的大作了,这首被认为一生写得最好、或流传最广的诗,因历代皇帝自身政治功利的需要,因此拥有无数不同的版本包括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标题,复杂得就如那团神秘的佛罗髻发,忽焉隐忽焉显,剪不断理还乱,但有关鹊巢的事既然已大致澄清,封禅的真相亦浮出水面,更重要的是对写作背景和作者的心路历程有了新的认识,一个曾经那么遥远如同传说中神仙般的人物,现在终于青鞋布袍向我们逐渐走近,虽然尚不能达到像你家孩子的班主任张老师、或小区门口超市王经理那样音容笑貌,宛然在目的程度,至少身上涂抹的重重油彩已被洗去不少,脸部五官的轮廓也能基本辨清。既然如此,哪怕前人在这首诗上做的手脚再多,抄写时用的也非墨汁而是蒙汗药,要真正弄懂想必也已经不难。
“湖上(外)青山对(守)结庐”,首句传世诸本大致无异,只是文义有些欠通,如果青山是湖中土山,结庐就在山上,又怎么个对法?孙奕《示儿编》引吕祖谦《皇朝文鉴》“湖上”作“湖外”,《尧山堂外纪》亦作“湖外”,诗题为《书寿堂壁》。这就对了,因前面已多次强调,此诗是迁家之年即筑新居时所作,而新居即为寿堂,亦所谓巢居。他因真宗封禅离开故居的时间为大中祥符四年(1011),在它山梅梁下的洞穴深居八年,天禧三年(1019)应征出洞,在王随资助下筑新居于湖西活着的那棵梅树下,实际上是像前辈鹊巢和尚或延寿禅师那样居于树巢之中,其《山阁偶书》所谓“绕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轩”,一个穿字,一个危字,早已泄露个中机密,因此,几乎不用怎么动脑筋,就知道“对”字必为“守”字之讹或伪,而原文当为“湖外青山守髻庐”也。至于湖,自然是宁海西湖,梅圣俞看到的周边环境是“高峰瀑泉,望之可爱,即之愈清,挹之甘洁”,而杭州西湖不仅古代,就是现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雄壮景观。
“坟(坆,梅)前修竹亦萧疏”,此句北宋或南宋初版本都作“亭前”而非“坟前”,如曾巩《隆平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等,而亭即寿堂,实班固所记鲒琦亭,至和靖复出,重加修缮而已。《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条下记云:“鄞有镇亭有(名)鲒埼,亭东南有天门水入海。”颜师古注:“鲒音结”,说明鲒不过与结一样,亦为髻之变书而已。但让人颇觉意外甚至不无恐怖的是,这个亭前的‘亭字或许同样也靠不住,如果有一天他自刻此詩的石碑能有幸被挖出来,相信原文一定是个“坆”字,而非今传本所谓“坟”和“亭”。按《字汇》所释:“坆,古梅字。”《说文》梅、坆通用,可见自古已然。往好里说,这是汉字丰富的典范,或古人为我们精心准备的又一道文化大餐;往坏里说,不过造假集团设下的另一陷阱和圈套,以便在“坟”字上做的手脚为后人识破时,还可将责任推到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身上。因利用字形相像从而达到歪曲文义的目的,正是某些不怀好意的古人所惯用的作案手段。比较一下,亭是休憩之处,坟是死人葬所,坆(梅)是精神依托,一字之别,篡改者的用心不难分辨。
“茂陵他日求遗稿(草)”,《苏轼全集》《隆平集》“稿”都作“草”,虽然现在小朋友写作文要打草稿,但在林和靖时代,两者的关系就像灵隐寺的蜡烛和阿育王寺的放光松,或钱塘的瀵水和雪窦的清泉,形象迥然有别,含义也完全不同,而且还是宗教意义上的专用字汇(宋以前今天用的‘草作‘艹),指的就是落水梅梁身上特有的灵异景观,“有草一丛生于上,四时常青,耆老传以为龙物,亦圣物镇堰者耶?”(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而《乾道四明图经》亦称“山有不死之草,赤茎绿叶,人死三日,以草覆之即活”,尽管语涉夸张,但晋初陆云说秦始皇在鄮县逗留三十多天,他要苦苦寻找的不死之药,除了它还能是别的什么?至于黄宗羲非要称作青灵子,而且‘灵改成‘棂还不够,必须写作‘櫺才过瘾,那是他古文水平比较高的缘故。即使后世艹、草混用,为维护这种仙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特意造出一个“騲”字来专用,《正字通》说“騲,本作草”,《玉篇》则坦称是“牝畜之通称”。这样,哪怕“畜”不是“蓄”之讹,更不是“祭”之伪,所祭之神的性别总算是弄清楚了。当然你要称她天姥、嫫母、天母、海神、余杭阿姥,妈祖、天妃甚至女娲都没问题,但生前的常用名只能是太姒,考之正史,即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著名军事家兼胎教艺术发明者,古今贤母典范,只是容貌方面让人不敢恭维,或者说长得有点另类,至少头部比较光滑,走路时身体也不稳,略向右倾,对此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犹喜曾(初)无封禅书”,欧阳修《归田录》、《苏轼全集》“曾”作“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作“独喜初无封禅书”,“独”为“犹”或属字讹,“初”为“曾”可没这么简单了。号称一生隐逸高蹈,死前以诗明志的人,怎么也该说“犹喜终无封禅书”或“犹喜从无封禅书”才对,却很奇怪地只称初无,看上去也不像是谦虚的缘故,那就多少有点不妙了。这个破绽大约进入南宋以后已被人发现,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林诗定本易“初”为“曾”,俨然是“犹喜曾无封禅书”了。曾无是曾经没有的意思,虽然跟初无相去无几,不过外延毕竟要大一些,同时也因语义较前者含糊,更有利于后世乾嘉大儒们的发挥。而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恶毒的诗题如《临终作一绝》之类,整体效果就出来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无论初无还是曾无,最有效的时间坐标就是此诗的写作日期天禧三年,此前为无,此后为有,区分起来相当简单。至于那些掌握话语权躲在幕后的家伙为什么要如此折腾,往好里说是历史教科书上需要有这样一位道德楷模,毕竟那时距严子陵时代已有千年,张志和的形象又太过严峻飘忽以致知名度有限,必须有效地培养出一位新的接班人来,因此只好恭喜他获大奖了。往坏里说是历史连续剧的编创者们已为他设计好新的档案和身份证,就等着他在宁海西湖之上、梅山巢阁之中修成正果后,换套行头再上台了。怎么说呢,如同宁波的“宁”字可以有十三种写法,梁山伯的庙可以是内蒙古的文化遗产,雪窦的千丈岩可以在镇江的江心,西湖更是神通广大,截止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全国居然已有三十六个。而由古代史官导演的历史剧同样如此,集数太多而剧情单调,舞台太大而演员太少,因而不仅是他,很多名人事实上都被迫扮演着多种角色,这一点相信只要是涉古稍深,或多或少应该都有体会。为了保护自己已经少到可怜的一点理想主义色彩,还是让我倾向于相信是前者吧。
最后理应有个小小的总结,或者说归纳,先把整理后最接近原文的诗抄下来:“湖外青山守髻庐,梅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初无封禅书。”到底想说什么呢?前人提供的现成答案是:“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谪守黄冈谢表云:‘宣室鬼神之问,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惟期死后。此一联每为人所称道,然皆直用贾谊、相如之事耳。林和靖诗:‘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虽说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严有翼《艺苑雌黄》)“和靖高士,自知封禅之非。若相如,以赀为郎,病免,家贫无以为业,观其题桥之语,可知为心慕荣利不甘寂寞者”(叶炜《煮药漫抄》)。但其中重点不是赞同封禅的司马长卿,而是抗拒封禅的王元之即太宗朝名相王禹偁,晚年因此流放黄州而卒,临终前仍然宣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宋书本传》)!说实话,王的文学水平在彼时不过二流,而“其诗时人贵重,甚于宝玉”的林,居然甘居其下,有《读王黄州诗集》云“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想必是被后面这段话搔到痒处,以其时出仕为世人误解,精神方面需要有支柱的缘故。因此,具體到诗本身,译成白话后大约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在湖西青山守望先祖祭台
肉体渐渐融入梅竹了
后世来此寻访遗迹的人啊
你一定要相信,他是干净的
一定要相信,哪怕后来
身体为世俗所污,他的心
依然是干净的,要相信
一定要相信啊,他是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