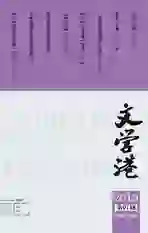失重的山村
2019-08-26刘从进
刘从进
一、有望转世做人的狗
半山腰上一条旧了的小路哆嗦着拐了个弯,伸到尽头是一片绿沉沉的树和几垛白楞楞的墙,那是田弯村。
村庄半月形地打开,很宁静,宁静得有些奇怪,时间好像老得走不动了。那些停在草叶上的蝴蝶,你伸手去抓,它也不跑;甚至在飞舞的过程中都能随手抓到。是村子里没有了人,它们放松了警惕?远远的一个老农孤零零地戳在地上,像一棵落完了叶子的老树。
这里原有二十多户人家,到早几年的七八户、三五户,去年只剩下一户,一对快八十岁的老夫妻带着一只黄狗住着。
老夫妻虽然老了,依然种一些地,番薯、毛豆、白菜、玉米、油菜……常常是老头漫不经心地在地里劳作,狗跟着他,田間地头转,嗅嗅这土,闻闻那草,突然箭一般嗖嗖地跑出去一程,又在某一处趴到地上用前脚抱着一块石头歪着头看着闻着,有时还会汪汪叫几声。老头大多不理,偶尔侧目。黄狗在中午或傍晚的时候跟着老头回家,有时半途自己走了,过一会儿又跑回老头的身边摇着尾巴,呜呜地叫两声。老头就明白该吃饭了,放下农具跟它回家。
那天我不经意间转到他们的屋前。一排低矮的老房,围出一个院子,打扫得很干净。阳光下,老头和老太蹲在院子门口,一左一右团住趴在地上的黄狗,翻着狗毛。老太对着黄狗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黄狗则“呜呜……汪汪……”地哀叫。
他们在做什么呢?我轻轻地走近。老太说狗身上长了一种虫子,她说的是方言,说了好几遍我都没记住,大意是“山虱”之类的意思。她把狗头上的毛翻开来让我看,一种黑色细小的干粉粒状的东西,很深地粘在狗毛和狗皮之间。老头说,这东西是从山上来的,现在村子不住人,山林旺了,各种不干净的东西又多起来了。它钻到狗的身上吸血,严重时会把狗弄死。
怎么发现的呢?老太说,狗无端地叫,好几天不吃东西,翻开它的毛看了一下,满是“山虱”。也许以前的山村里时常有这种事发生,他们有经验了。
老太用手颤颤抖抖地捏住“山虱”顺着毛根小心翼翼抽丝剥茧般地把它捋出来。因为揪着毛,狗痛得呜呼呜呼地叫。老太就训它:“叫叫叫,这点痛都不能忍一下,痛死了一样……”老太每挖出来几粒,老头就拿一个瓶子往鲜红的伤口处倒一点液体,那是敌敌畏,消毒用的。老头的手或许提着瓶子久了,控制不好,一倒下去就多了一些,被老太一顿臭骂。狗随即很配合,“汪”地大叫一声,接着又是“汪汪”两声长叫。这更激起老太的愤慨。老头子闷声不响,任骂,但再倒出来的量明显少了。老太骂完老头又来骂狗:“就像痛死了一样——”这时狗就节制一些,先是低低长长地呜一声,再汪汪地小叫两声。很明显,狗是知道老太在给它治病的。
老太不时蹲下去抱住狗,在它身上拨拉来拨拉去,非常仔细地查看。狗的头上背上太多这种黑色的粉粒了。两个老人认真地伺弄着,要何时才能弄干净啊。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我没有再看下去,转身走了。
一个夜晚,我心有所念,又来到这个山村。深秋的夜,在一片模糊中山路有点晃,这是少数没有通水泥路的村庄之一。山弯里黑色在积聚,夜有些厚,有薄如蝉衣的风声,还有一些树叶和流水发出的幽光。来到村口,突然一团深井似的黑挡住了我,让我不自觉地停下来。我站在黑暗的边缘惊惧良久,这就是白天来过的村子吗?
摸摸索索前行,忽然前方闪着一束微微发亮的红光,从红到蓝,从蓝转红,里面闪着一个带血的“0”字,像夜的血管。我不寒而栗,全身紧绷,慢慢镇静下来后,突然意识到那是电表。对,电表!这里还有电表在走动!
我小心地移动着自己,拐过一个弯,隔着竹林,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在说,原来已经来到了老夫妻的矮屋前。屋里的灯亮着,从门缝里和房顶上漏出来。山村就这一处光源,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根救命稻草,一阵微风就会把它吹灭。狐疑间,屋里又飘出了声音。女的,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老头说话,更像是对着屋里的客人说,听那语气是在诉说往事或数落某人。山村有多少秘密要诉说啊,我急切地走到院子外边,又不敢太靠近,怕不小心弄出响动来会很尴尬。这时门口的狗汪汪汪地叫起来,我吓一跳,忘了还有狗在,立马倚墙不动。老太婆不说了,等了好一会还是没说,我失望地走了。走出去一段路,又传来了说话声,还是老太婆的声音。
我悄悄地潜回去,狗又叫了。我正懊恼,突然门开了,泄出一片幽亮的光,老太婆来到门口查看。狗随即大叫起来,但它只是叫,并没有追,大约它的伤没有好。我赶紧把自己藏好。老太婆不明就里,大声训斥道:“眠下去困!叫什么叫,这么夜了,路上又没有人。”然后又说:“喏,给你点吃的,吃了安稳睏觉。”没有门的阻隔,她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可以清晰地听出声音被掉了牙的嘴巴压出来的形状。狗却不理老太婆,只顾自己叫,朝着我站的方向叫得更猛了。老太碎碎念地骂着狗,狗却不理,依然执着地叫,她有些无奈。此时,老头出来,对着狗说了声,不要叫了。狗就不叫。老头子刚回到屋里,狗又叫了。老太婆又在絮絮叨叨地说狗:“黑死夜,平白无顾地叫什么叫……”又给它喂了一点吃的,转身关门回屋了。我深深地同情并敬畏起这狗来,虽遭主人的误解,依然忠于职守。
半年后黄狗明显老了,身子驼了,背上一搭一搭地掉了毛,露出红褐色的皮,骨头戳出来,像一棵棵枯树枝,见到人也不叫。我有些不解,老头说,它快要死了,“山虱”吃得它走不动了。说起来脸无表情,似乎随时在等它倒下。老狗蹒跚的步履和凄凉的晚景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旋——某一天,它倒在路边死了就像一片树叶落了地。
又过了一阵,我再来。村里没有人也没有狗,我很奇怪,来到村后的山坡上,看到他们都在!老头拿着铁锹锄头在默默地挖坑。老太趴在地上,捋着黄狗的毛,把毛一簇簇捋直,然后哆哆嗦嗦地给它穿上衣服,再戴上帽子,原来黄狗已经死了。我问怎么死的,老头说躺在门口无声无息,叫它不动,喂它不吃,一看已经死了。我转而小心翼翼地问老太,这穿上衣服是什么意思啊?老太空洞的眼窝里流出了两碗水——给它穿上人的衣服,让它转世好去做人啊!
那晚,矮屋里漏出来的灯光,照着坐在门口的两个身影,没有了狗叫声。山村的夜无所不包,一张一合地波动在梦的边缘。我黑黑地站了一会,又黑黑地走出村庄。在山村孤寂的时光里,人狗一家,演绎着白天黑夜的全部生活。如今狗走了,这样的日子也就残缺不全了。
二、老村归燕
善岙杨新村迁到山下,造得很好,成了新农村样板。老村却越发老了,好在那条通往老村的路还在。
四月春深,我在善岙杨老村。“杨宗家庙”门口放着一排大石头,边上有树,是以前村民休闲聚会之所,如今石缝里长满了野草。阳光下,老屋的门框发热,道地舒展,门口的旧杂物弥漫着陈香。
村庄深处,是成片的老屋和倒房,乱石堆荒凉,野草疯长,与孤零零的残墙争高。越往后走越荒芜,一垛长长的老墙被爬山虎密密麻麻地攀附着,看不见一丝墙体的缝隙。墙角处有鸡飞狗走,不见人。
绕到西边一处老旧的小四合院,弄堂边竖着三四个手拉车的架子,尸骨一般,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小心地穿过弄堂,是一处幽深的小院,木结构老屋,板壁上是褪了漆的深红色,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院子里堆着废弃的杂物,野草伏在瓦缸边。房门关着,没有人。中间那个门口放着一把躺椅,上方挂着两件衣服,应该还有人住着。过去一摸,躺椅很干净,随身躺下来,阳光落在身上,一只白蝴蝶在台阶的边沿飞舞。
一会儿,飞来一只燕子,钻入檐下,这才发现檐下有个燕窠。随即又飞来一只燕,停在旁边的挂衣绳上。初没当回事,真想睡一会了。可是,燕子反反复复地进出引起了我的注意。
原来,两只燕子,趁天气好正在努力筑窝。它们双进双出,身姿轻盈,剪刀翅一张一合,掠过前面的屋脊到外面的田野上啄泥去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燕子总是出双入对的。
燕子是候鸟,“燕来不过三月三,燕走不过九月九。”今天是农历三月十八,春天燕归来原是儿时经验中的常事。燕子吃害虫,通人性,人们视燕归来为好事,谁家檐下的燕子多,说明谁家是好人;哪家人不好,譬如有戳燕窝等事发生,燕子明年就不去他家了,那家就很没面子。
后来农药用多了,环境不好了,水稻种得也少了,燕子慢慢少了。再后来,农村里新造的房子跟城市里的楼房一样,全封闭,没有廊更没有檐,燕子无处筑窝,没法住,不来了。我在想,燕子不能住的房子应该是不对的,我们或许出错了,不该把房子造成那个样子,房子还是应该有廊有檐有院子的。
早些年,一些荒凉的山村,又有燕子來了,山村里还有田地,还有老屋和老人。老屋有檐,老人是种过田的,这些燕子都认得,它仿佛在哪里睡了一觉又回来了。
我躺在古老幽深的小院子里,暂别人世,晒着阳光看燕子筑窝。不知过了多久,弄堂口走来一个老头,全身黑衣,手里拿着三段朽木,弯着腰,慢慢慢慢地移动着。他应该是小院的主人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怕猛一声喊会吓着他,想等他看见我再说,他毕竟无法想象一个外人无端地坐在他的院子里。可是他一直往里走,竟没有发现躺在旁边一二米远的我。他把两根木头放到瓦缸的沿上,嘴里说了一句什么,听不清。这朽木应该是从别的倒屋里捡来的,也肯定是没有用的,他可能只是习惯性地拿一些东西回家,农民每去田垟,不空手而归是一个习惯。放完后,他继续往里走,在一间更阴暗的小屋前,打开了门,向里面看了一眼,把剩下的一根乌朽木放了进去,又说了两三句话,再看一眼,然后慢慢关了门,折回来。老头在此独住应有很长时间了,他的话既是说给自己听,也是说给那些旧物件听的,对着有感情的旧物说说话,或许是他孤老的岁月里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这时我已经站起来了,向他笑,他也向我笑。我说你一个人住这里啊?他大概耳背听不清,只是笑,我也笑,他还是笑。他也对我说话,罗罗罗罗的听不清。我们说着话,相互听不懂,但一直裂着嘴。你一句我一句说了好一会,我勉强听懂了他两句话——“嬉一会”“哪里的客?”最后,我指着燕窝说,有燕子来!这一次,他听懂了,嘿嘿笑着。
我到燕窝下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梁上钉了两枚长钉,中间缠绕了一些塑料布,燕窝就筑在上面,这是为燕子的到来做准备的。再一看,这个燕窝的里面那根梁上还有一个燕窝,小一点,或许是去年的吧,下面也有钉,也缠着布。房梁有二米多高,他要叠两条凳子,再爬上去,才够得着,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他一定费了很多心力。残存的岁月里,还这么细心地准备着为燕子筑窝的事,可见美好的旧事在老人的心中是很难忘怀的。也好,燕子能陪伴他一个长夏。可是冬天,燕子走了,老人还是得跟他的一屋旧物相伴,对着它们说话。
三、岗后村老伯
山岗向后甩了一下尾巴,把一个村子藏在后面,叫岗后村。一排古樟一个庙很庄严地蹲在村口。
村中间一座老屋,上面写着“提高警惕”,下半句没有了,边上一颗五角星,星边画着一道道光芒。屋前竖一块牌,写着“岗后村”。这显然是建国初期的大队公屋,已经破了顶,墙面被粉刷过,前面浇了水泥地。即便清冷,但一眼便可知这里是村子的中心。地上、路边瑟瑟的野草枯死着,乱石白刃刃地横着,让寒冬里的村庄充满了萧瑟的凉意。
老屋那垛尚完好的老墙前坐着一个老伯,穿着睡衣晒太阳。我从他身边走过,他没有反应,老僧入定一般。我回头,喊了他一声“老伯”。他缓缓抬起头,盯着我看,问,找哪家亲戚啊?我说不找亲戚,村里阳光好,来走走。
一聊,他说自己中风了,腿脚不便。说着他慢慢地起身示范给我看,鸡啄米似的一点点两腿分开,膝盖弯着,脚掌摸摸索索地探身前行,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在空中乱抓,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样子。他说拐杖是孙女买的。我一看,是一个很简陋的拐杖,着地的一头已经开裂了。
虽说中风,但说话正常,手能动,就是脚不方便,在中风者中应该算轻的。问几岁了,说65,一会又说,错了,是85岁,中风了,记性不好。
就一个人生活吗?老太婆还在吗?
她呀,苦命,早走了,比我少五岁,七八年前走了。小时候家里苦,给人当童养媳,后来解放了,上头让解除婚姻,回来嫁给了我。一生很苦,我们一共生养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三个儿子啊,大儿子和小儿子都丧命了,命苦。
大儿子做木匠,给人造房子时,跟人家选的日子冲,无缘无故从楼上掉出来,掉在一个沙堆上,送到医院就断气了。刚娶了媳妇,生了一个女儿,才两岁,嫁人走了。
他很努力地转了一下头,指着边上两间老房,说这原是大队公屋,中间两间就是大儿子买的,现在人走屋倒,只留下给狗拉屎了。
小儿子嘛,那年家里造房,我说不让他回来了,可他姐妹非要他回来,结果开着大货车,在一个拐弯处翻了,压死了。
他一边说一边眼里就含了泪,但好像掉不下来,用手不停地擦。
只有二儿子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外地的女人(一般在当地找不到老婆的人才会找外地女人当老婆,这些女人有一个现象就是即便十年二十年后,孩子好几个了,什么时候说走就走了,村里很多外地女人,已经跑了不少),结婚后跑了,也留下一个女儿,现在宁波。后来又找了一个外地女人,也不结婚,却生了一个女儿十三岁了。
他还不停地跟我说,他的儿子也就是唯一的二儿子明天就要回来了,来给他做几天饭。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拭着泪,老泪已混浊,里面不包含许多悲伤了,悲伤早已成了往事,风干了。
又说起女儿。
大女儿,嫁在本镇的桃下村,丈夫是个赌鬼,赌得倾家荡产,可是我这个女儿是个厉害角色,她狠心治服了赌鬼丈夫。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打,棍棒砍刀一齐上,打得他哭爹喊娘,再也不赌了。现在家境挺好的。(说到这里他笑了)
二女儿,嫁了一个手艺人,本来不错,生了一儿一女,本以为不再生养,自己去结扎了,可是没多久丈夫却生病死了。后来有一个男的说可以接受她,不要孩子,就这样结婚了。结婚后,男的却与别的女人来往,生了儿子,丢在家门口。我女儿又只好把他带起来,现在都长大了。
小女儿嘛,当时老太婆就说不要了,扔了算了,一个小贱女。我想不能啊,自己买了剪刀、酒精、药棉、尿布等,自己把她接生了,洗下来了。她嫁在长街,三年不会生育,丈夫见她不生养,就在外多年不回,无奈只好去法院单方离婚。二十年前重嫁,从人家那里花一百元钱买了一个女儿,后来自己却又生了一个,还怀着一个,多了还要打胎。(他又嘿嘿笑了)
他说,三个女儿都有本事的,日子都过得不错。儿孙辈加一起有二三十个了,但在村里在他身边的一个也没有。大的要赚钱,小的要读书,每个人都很忙。很多孙辈都赚钱了,这让他很欣慰。听得出他把能赚钱了当作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
现在他一个八十五岁的中风老人独自生活在村里。他说衣服女儿隔一星期来洗一次,菜也隔一段时间送来一次。
我说你一个人穿衣吃饭上床上厕所都能行吗?
他再次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努力地加大两脚分开的弧度,然后一只手向前一只手向后,向我示意,从灶头到桌子到水龙头这么这么弄。他指了一下对面路边的小屋,那就是他的家。一扇门就对着路开着,门里就是灶间。
为了安慰他,我说你看上去气色很好,要是不中风一定还能干活的。他说自己年轻时很健,什么活都干,谁叫都干,都给人家白干的。
我静静地呆着,冬天的午后,阳光好,在山村,墙角落,一朵朵跳脱,特别爱戴似的围着老人团团转。我说日头好啊。他说,日头好,放在口袋里带点回去。我说好。
我站起来,要走了。他又说,你是看哪家亲戚的啊?或许他只是问习惯了,或許年末了,他一直在等待回家看他的儿孙们,一边坐着晒太阳一边努力地看着村口,也不知道他的视力还好不。
拐过墙角,一股寒气逼来。村庄看上去像一个陈年的筛子四处漏风,扫过一处处的悲凉。
第二天中午,我再来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晒太阳的老伯,只有那把竹椅子空着,我有些失落。这时他主动招呼我了,一看,原来他坐在屋里吃午饭呢。
我进到他屋内一看,桌上两口碗,一个空酒瓶。说医生说,他这个病要每餐喝点红酒。他说,喝着喝着就喝出念头来了。这个酒要100元一箱,一箱才6瓶,很贵的。再一看碗里面,一口碗里盛着硬硬的饭粒,像个开裂的冷馒头,另一口碗里是猪肉炒栗,说是外孙女造房子,请客人吃剩下的,送过来。我一看干巴巴的不剩一点汤了,带着血色的红,一定是炖过很多餐了。他一边用筷子戳着硬饭粒,一边说,刚才炖猪肉时炖太久了,把那个大碗也炖裂了。一碗冷饭一碗冷肉,没有蔬菜没有汤,他不停地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饭,说不想吃,吃不下了,像个赌气不吃饭的小孩子,只不停地找我说话。我再一看,桌子下面有一箩青菜,放久了干了。怎么不放一碗菜汤啊?他说,要洗要炒啊。单把一棵菜拿到水槽里洗干净就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放一个菜汤成了一个工作量很大的工程。
为了不打扰他吃饭,我走了出来,坐在他昨天晒太阳的竹椅子上。一会儿,他吃好了,往外走时,又是抖抖索索,十分艰难,走几步就要歇一会,不然脚抖起来就有冲倒在地上的危险,就三四米的路,走了有十多分钟,犹如长征一样艰难。他好不容易走到墙角的水槽里洗碗,洗好已经快下午两点了。对一个老人来说,一天三餐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还有上厕所、晚上脱衣上床、早晨穿衣起床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他已坦然接受这样的老年生活,痛苦已从他面容上消失殆尽。
四、胜利村的长生者
胜利村像一个摔成数瓣的瓜躺在一座矮山边,过年了仍然蔫蔫的没有一丝儿生气,不多的房子横七竖八就像一片荒草丛长出的乱石堆。
村子的中间,是几间矮屋,坐着一个老人。一个老婆子坐在裸露着黄砖的小屋后门那块洗衣服用的水泥石板上,背靠着墙,面对着空洞的小路,一动不动,像一尊佛。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我小心地走到她的身边,发现她眼睛微闭着,悲苦的脸沟沟壑壑硬如岩石,就这么坐在阳光的阴影处,任风吹着她的丝丝白发。她个子蛮高,脸狭长,年轻时应该长得不赖。
我试着跟她说话,她睁开眼睛慢慢说起了往事,就像跟自己无关似的,这让我想起了祥林嫂。
胜利村原是从郑畔村分出来的,那时几个村一起在这里围出一片塘叫胜利塘。因村庄离这里有点远,生产生活不方便,于是一部分人搬迁到这里来居住,以塘地为生。也算迁徙吧,当时海边的村庄这种情况不少。
老妇人说自己来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现在八十多了,是这个村庄里年龄最大的人。问她八十多多少。她想了一下也没想起来,说自己老糊涂了,记不得了。她说这话时没有一点的矫揉造作和难为情,仿佛年龄对她来说就像一块用久了的抹布丢了就丢了,根本没什么可惜,更不会去找回它。按她的说法,胜利村起码有五十多年历史了,然而事实应该没有这么长,应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三四十年的历史吧。看来她真的是糊涂了。
她说,那时筑塘苦,冬天的时候要用铁锹敲破白勒勒的厚冰,站在水塘里劳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家里孩子多,妇人总是背上背一个,怀里吊一个,照样整天干活。老头子大她八岁,六十四岁时因胃癌死了,在的话应该有九十多了。他们一共有三个儿子,现在每个儿子有两间屋,就在后面,她指给我看。而她自己则住在一个破旧的裸露着砖块的房子里,她特别强调房子是自己造的。一個儿子去年在村口新修的公路边被别人撞死了,她流了很多泪,现在眼泪也没有了。本来三个儿子每人每年给她三百元钱的零用,共九百元。现在一个死了,不负担了,只两个,六百元。自己去年又摔了一跤,医了不少钱,现在走路也走不了,只能扶着墙在房前屋后转转,大部分时间就这么坐着。耳朵还灵,眼睛不太看得清了。现在自己不会做饭不会洗衣,吃的是儿子给她做,衣服也是儿子给她洗。媳妇在的时候,桌罩都不许她打开看一下。
自从村庄迁到这里以后,她只回过几里外的老家两次。此外就没有离开过村子,在这个巴掌大的新村生活了一辈子。问她想不想再回老家去看看,她说走不了了。
她停了一下,好像打了个盹,然后缓缓地说:“死了好啊,活着遭嫌弃的。”话说得很轻柔很抒情,像是在安慰我似的,没有半点对人世的怀恋之情。本来那些苦都在我的接受范围,就这句话,仿佛从遥远的天国飘来,袅袅地钻进了我的身体里。我蓦然感到白日茫茫,天地荒荒,人世是那么的苍凉,活着是那么的飘零。
她是一个老人,她老了,身体骨头都老成最硬的,再也老不下去了。时间再也不会给她带来什么,也无法在她身上搜刮到什么。她的生活里已经废除了时间,白天与黑夜都回到了一种原始混沌的状态。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快乐也没有了烦恼,进入了不生也不死的另一种涅槃境界,她成了村庄里最初的长生者。她的生活是苦的,又或者无所苦。她,是一个活着的文物。她的存在的真实性和坚实感远远大于这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村庄。假若某日一阵飓风吹来,村庄或许一下子被吹得无影无踪,而她不会被吹走,村庄只是她的外壳和无用的衣裳,她的灵依附在大地上。
这时,她的孙子从屋里出来,骑着电瓶车经过她的面前。她问:到哪里去?孙子说:“大域。”她说:“奶奶可以坐你后面出去吗?”孙子没理她,拐了一个弯,突突突地远去了。大域就是山弯那边离胜利村最近的一个村,大概有两公里路。那个村子很大,人都集中在养老中心,每天有很多人坐在一起聊天晒太阳。她或者只是想到人多的地方去看看,但显然不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愿望罢了,她怎么还坐得了电瓶车呢。我想,她可能每遇到一个人都会这么说,对方也明白她只是说着罢了,所以都不理她。
就在她的小屋边有一间简易的移动房。横过一垛矮墙,越过一片草丛,看到房前坐着另一个老者,相距大约就在六七米,却好像各自坐在两个星球上遥遥相望,无法说上一句话,更无法坐在一起。她说他82岁了,是村里除了她之外最老的人。我看着这个铁皮围成的绿色的移动房,忽然生出许多感慨来。这种移动房近年才有,主要用于在深山或海边等没有人家的偏远地方施工的工人临时住的。结构非常简单,面积很小,除了一张床几乎放不下别的东西。一间临时的移动房,安在一个历史很浅的村庄里,一切都显得那样地飘荡和不安,让我突然多了一份客居尘世的不实感。
或许是老人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又或许儿子们新建的楼房怕被老人弄脏了,所以想出了这个方法。我走过去一看,他一直勾着头,对我的到来无动于衷。直到我走到他跟前,大声地跟他说,他才轻轻地回了一句:做什么?他边上一条小凳子上放着一口碗,碗里是红枣和桂圆一起煮的茶水,也不知是谁放着的。他的手里拿着一颗红枣,两只手在慢慢地剥着红枣的皮,十分十分地缓慢,不仔细,你都看不清他的手是在动的。他的脑子似乎不好使了,不管问什么,只回答三个字:做什么?生存的本质就是以某种方式把一生的时间打发掉或者把时间的虚空填满,而他的方式就是——慢慢慢慢地剥着红枣皮。
他的边上有一个石头结的狗窝,一条拴着的狗趴在洞口,汪汪地叫着。这只狗或许是他的儿子们养着照看他的。
我想,村庄里的她和他是山村里老年时光的写照,也包括我。人生所有故事的结尾都是——他死了。一个哲学家说,离开人世的时候要送出祝福,不要留恋。我想他们是既不会留恋也不会祝福的了。
苏格拉底警告说,村庄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神管的事,不要研究村庄,那是亵渎神灵的,然而,似乎有神灵在指引着我走向山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村庄是一个“自然位置”,现代人很难找到这个“自然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