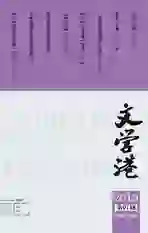紫云英顺着风
2019-08-26干亚群
干亚群
五荒六月,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总之,过了三月,镇上的姑娘不再出嫁。
偏偏,紫云英接引了春風,把乡村染成紫色,风一吹,涌出好看的波浪,像镇上姑娘们曼妙的身姿,忽闪在田间地头。
紫云英的花一边开一边落,层层叠叠,一个月过去了,它还是如此,仿佛有人在它耳边说情话,哄得它发疯似的想把自己的名字种满大地。只有傍晚的时候,它才似乎发一阵愣。那时哼了一天嘤嘤嗡嗡的蜜蜂,准备回家了。
紫云英,或卧在山脚下,或横亘在村庄外,旁边有时站着几棵树,有时穿过一条小溪。我忍不住采集了一捧,带到寝室,找了一只盐水瓶插起来。结果,晚上飞出来几只蜜蜂,在窗帘上一阵啪嗒啪嗒,似乎对我的行为甚是气恼。
原来紫云英的花蕊藏得很深,蜜蜂采蜜时差不多把自己埋了进去,即使我粗暴的动作,也没能惊醒它们。它们太专注了,对采蜜以外的事几乎无动于衷了。
有人说,花蕊是花的生殖器官,蜜蜂采蜜,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完成了性爱。
我已记不起这是谁说的,但它让我想起解剖课。
教我们的老师刚从学校里出来,帅气,年轻,温厚恭良,看见学生习惯性地侧过身,再轻轻叫出你的名字。每次上课,他腋下夹着解剖挂图,一手捧教案,在铃声结尾的时候,慢斯条理推开教室的门。他上课时很少看教案,所有的讲解都在挂图前面完成,既讲解剖结构,又强调生理功能。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教鞭从一张图滑到另一张图,卵巢、子宫、输卵管……而年轻的我们掩饰不住脸上的羞涩、尴尬、窘迫,似乎挂图上的组织器官是自己的。
或许老师看到底下的目光有点低小散,不够聚焦,他停下教鞭,在挂图下面站着,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子宫,两只手臂作为输卵管,手指握成伞状,说是当卵巢排卵时,这顶伞就会把卵泡吸收进来,送到输卵管,在子宫里等待精子的相遇。底下的我们鸦雀无声,也不知道大家都明白了没有,只晓得每次考试总有人在这方面被扣分。我也答错,把输卵管的几个峡部弄错了。
老师似乎很难过,认为这样的错误是低级错误,于是,再次把自己扮成挂图,替答错题的学生重新讲解一次。
我还犯过更低级的错误。有次,老师正讲解子宫的解剖结构,我冷不丁地问老师前列腺在哪里。之前,我不晓得自己走神了,还是午后的困倦让我大脑一时糊涂,总之,我像是很意外地扮演了一个勤问的好学生。教室本来还有些小窸 窣,似乎有人在偷吃零食,但突然一片死寂,然后一阵哄堂大笑,笑声简直是一浪打向一浪,吸引底楼的老师们不住把脖子朝上仰。老师在讲台上默默收起自己的真身挂图,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把教案翻过去,脸上似乎微微红了一下。我非常不解地问同桌,我问错了?同桌笑得像一颗暴晒过的白蒲枣,说,女的哪有前列腺?我起初还有那么一会儿空白,但立刻被尴尬、难堪覆盖,脸一烧,忙把头埋进肘弯里。
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学习生殖解剖图时非常吃力,那么多的解剖名与组织原理,仿佛彼此能打架,背着背着,概念就混淆了。
所以,我看到蜜蜂时不得不惊叹,它居然辨别出雄花与雌花来。
我在门诊碰到过一位病人,她结婚三年一直没有怀上,她婆婆三天两头冷嘲热讽,过后又鸡飞狗跳似的去弄偏方,逼着她喝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每次她喝下,总要反胃一星期。她原来白白胖胖的,在娘家时是一个很开朗的人,现在整个人黄皮寡瘦,沉默寡言,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才二十五岁的人看上去跟三十五六似的。这次她突然停经四十多天,全家人都很兴奋,尤其是她婆婆,一张苦瓜脸变成了一朵南瓜花脸,对她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整天围着她转,还不停地问她喜欢吃酸的,还是甜的。她知道她婆婆的用意,吃酸的是生女儿,吃甜的是生儿子,可她都不喜欢吃。
本来,我跟她是医生与病人关系,她最多给我讲停经几天的事,可她说着说着,怎么也控制不了,把她在家的事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我也不忍心截住她的话,虽然那些事并不是我所需要的病史。那天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人和婆婆,一前一后地陪着她。到了产科门诊前,她婆婆说产科是暗房,她念佛的,就在外面等。她男人也没进来,门诊室里不准他抽烟。
我让她去做早孕试验,她似乎很犹豫,问我能不能给她搭个脉。我说,我虽然知道滑脉的意思,但没有专门学过。她接过化验单,有那么一会儿她的神情很木然,甚至是茫然,似乎前面有不确定的事情正等着她,而她已经猜中了一半。
这时,她男人与婆婆在外面探头,问,医生,她有没有生(怀孕)?娘俩异口同声,只不过一个像男的,另一个像不男不女的。
她婆婆虽然仅露了大半个脸,但感觉她的表情很硬,包括看人的目光里似乎隔着一层生姜,嘴唇往上牵,鼻翼旁似乎挂着冷冷的心思。所以,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完全是女声,似乎她的声音一半被她的心思笼罩了。
我说,先去做个化验。
一刻钟后,她拿着化验单回来了,上面写着阴性。我说,没有怀孕。她突然失声哭了起来。我想安慰她,可张开嘴发觉自己并没有把话准备好,只得抽了几张餐巾纸给她。她男人走了进来,似乎明白了情况,用极不耐烦的声音说,哭有什么用,回家去。他用一双关节粗大的手去拉她。不知是她抽泣引起的颤动,还是她弱弱的反抗,她的肩膀往左右甩了几下。她男人猛地去拽她的手,一用劲,她半个身子离开了凳子。
阿来,回家去,下午还要去田里,雄花不摘掉,影响年成。怪侬眼睛长在头角,雄花雌花都勿晓得,介木。
这是她婆婆在外面指桑骂槐。这时不女的声音占了大部分。
我说,不能生育,不能全怪女方,双方都要去检查一下。她男人似乎很愕然的样子,盯着我,说,生小孩的事当然是女人的事。我说,小孩是女人生的,但如果没有精子跟卵子相遇,女人是没办法的。说完,我自己都觉得意外,像是在重复解剖老师的话。
她男人差不多是剜了我一眼,我也回了他一眼,还好,没翻白眼。
紫云英热闹田野的时候,农民一次次翻晒谷种。谷种是上一年备好的,饱满、金黄,阳光一照,晒谷场上弥漫着分泌的气息,吸引蝴蝶前来翩跹。农民又似乎怕谷种喝醉了阳光不肯用功,于是把它们堆在阴凉的地方,说是醒几天。
蜜蜂仍一次次保持着整齐的节奏,吟唱,然后一头扎向紫云英的花蕊,那里分泌的不仅仅是花蜜,还有花香。
紫云英的花香,并不浓烈,甚至有点拙,是慢慢渗进来的。就像村里的姑娘,心里明明藏着大海,却始终不敢说那片辽阔。我在窗前看到过一位梳着长辫子的姑娘,曾一次次徘徊在小学后面的小路上,旁边是紫绸缎被似的紫云英。黄昏时,一个英俊的后生去那里散步,有时腋窝下夹一支笛子,对着日落下的紫云英吹一曲。笛声悠扬,悦耳,滑音、颤音一个个飞扬起来,仿佛把人带入了落满细节的故事里。他是小学里的一位音乐老师,因家在另一个镇上,所以长年住校。可她看到他的影子,便假装路过,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走的方向有时朝东,有时往西,我也不清楚她到底住哪个村。当那位男老师有一天牵着女朋友的手去散步时,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位姑娘。而《小芳》正风靡大江南北,镇上的理发店、音像店全播放着这首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紫云英的气息里带着甜味,我觉得镇上的每个角落里都飘荡着它们的花香,甚至还溅到了在天空中奔跑的蟲儿,它们飞雾样的形状,似乎尝试着盲目的低飞。
春风也推动蜜蜂,从这片赶到另一片,仿佛接续一个漫长的乡村故事。
我常常发呆,回过神来,发现暮色已四合,开灯,拉窗帘,取一本书,开始夜读。
有时,书读得很专注,有时浮皮潦草,一页页翻过去,不晓得自己读了些什么,于是把书扔一边,开始写日记。提起笔,写的还是自己的心情,翻开前几天的日记,仍是对自己每天重复的日子感到苦闷。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伤感、孤独、低落,仿佛是成群的飞蛾朝我扑来,而我无力挣扎。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把桌上那瓶干枯的紫云英扔到了垃圾桶里,此刻对它相视,犹如失意人与离恨人相逢。只是,它缘于离开土壤,而我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土质。
每年,计生办都会制作一批奖品,或脸盆,或杯子,上面烫着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计生办在年终表彰时会留一个名额给卫生院,童医生是不二人选。计生办的张阿姨可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平时她大多把病人送到我这儿,便从奖品那里取了一份。我自然推脱,而且是真诚的推脱,但张阿姨丢下就走。白色的搪瓷似乎故意让上面的字烧红起来,一同烧红的还有我的脸。
我始终没勇气把这样的杯子拿到办公室喝。
就像有些病人没有勇气推开我的诊室。
目睹一些姑娘家凄惶无奈地在门诊室外面来来去去,神情苦涩,面容忧戚,间或还有羞涩、不安,甚至惶恐,一见有熟人朝自己走来,惊慌失措,磕磕绊绊编织出一个谎言。她们有的非磨蹭到下班的时候,才犹犹豫豫迈进来,目光像一头惊恐的小鹿。
在我按下负压吸引器械开关的时候,所有对胚胎的赞美,顷刻间被小半瓶粉红色泡沫所嘲笑。每次手术后我都要检查瓶里的容物,以防残留。碎片样的内膜与碎肉样的胚胎组织,像一只被挤坏的蕃茄,鲜红已经无法完整。
如同病症,我看到蕃茄,总有一种异物感,然后是一阵阵反胃。
我实习时,我的邻居,也是我小学时很要好的同学,她躲躲闪闪地找到了我。那时她怀孕已五个多月,每天用半尺宽的布条紧紧绑住自己的腹部,而且躲着家人的眼睛。后来实在没办法再继续这种方式,胎儿已经会踢会蹬了。她男朋友骗过她的父亲,以愿意上门做倒插为条件,把她从家里带了出来。那天我在门诊室,看着她涨红的脸和往外鼓的腹部,我已明白了个大概。她在我面前也顾不得羞怯,只求我帮她这个忙。我二话不说,帮她联系好引产床位,等她住进院后我才离开。
出来时,发现外面漫天大雪,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寝室走。这时迎风飘来《一剪梅》,瞬间我突然想流泪。我替同学觉得不值得,我忙前忙后的时候,他始终笑嘻嘻地看着我,也不晓得他这样的表情是出自什么内容,仿佛他卸下了一副担子。
隔了两年,她又来找我。这次更让我对他俩的关系产生质疑。她在里面忍受手术带来的疼痛,而他却跑到医院对面的游戏机房打游戏,直到我去叫他,他还全神贯注地盯着游戏画面,根本一点都不在乎我同学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同学自那次手术后差不多停经了半年,我让她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担心她因此而影响生育。后来,她告诉我月经恢复了,我这才放下心来。他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我同学依然痴情一片,看他的眼神像看男神一样,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新娘,而他像完成某桩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一样,草草敬酒,言辞之中听不到任何喜悦,包括看我的眼神,一点都没有难为情的意思,仿佛他们的往事在婚礼开始时已烟消云散。
别的同学也找过我,有的甚至是同学的同学。在她们眼里,或许我的医技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能替她们保守秘密,如同大地保守紫云英也有雄花的秘密。
我替同学开手术单子时写的是云英,或者阿英、阿云。这当然全都是假名。在一个远在百里之外的小镇,我也不担心她们会碰上熟人,但我也不希望她们的名字躺在手术单子上。
紫云英被村人称作披欢。我第一次听到时心里就冒出来这两个字。我知道这样的叫法跟写法是不对等的,如同有些字写进了词典,但它似乎没有使用的机会,偶尔地出场,还得有偶尔的人会记得住它。有些叫法,虽然始终挤不进书里,却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瓷实般地踩着每一天。没有人跟我解释紫云英为何叫成披欢,有可能是批幻,或是皮还,可我就是喜欢写成披欢,披着欢快的外衣,迎接三月、四月,还有五月,像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当谷种在浸泡中慢慢发芽的时候,牛被农民牵出了牛栏,在鞭子的抽打下,犁铧插进了地里,褐色的泥块顷刻间覆盖了紫云英。
那些紫色的小花,将在无光的世界里慢慢沤烂自己,然后引领着大地的孕育。
风掌握生长秘密
村庄的迹象在风中。春风浩荡,把一件件农具荡下墙,它们被人赶进了庄稼地里。锋利的犁铧插进大地,褪色的泥块一床床翻身,散发出浓郁的气息,吸引翅膀与羽翼不停地颤抖。锃亮的锄头咬住了杂草,它们匍匐于泥土,把自己交了出去,荒芜的概念慢慢得到清理。一把化肥,小把种子,从风里挤身而去,卧在了刚翻好的泥上,像完成庄严的孕育仪式。
人们在地上卑躬屈膝,极力讨好种子,还悄悄念叨,念出一片红晕,叨出一些往事,迎着春风披挂上阵。风把那些话那些事吹进地下,在湿润的泥里反复酝酿。种子坚硬的外壳,被一点一点顶出缝隙,再慢慢长出一片芽。油菜开花,桃花含苞,风在它们中间捻出一个个动作,引来蜜蜂义无反顾地吮吸。风笑了,扇出一朵朵鲜花来,香甜的气息沉醉着村庄里的男男女女,好像有一个个民间故事在村庄上空铺开辽阔的情节。
风在村里飘一阵,歇一脚,在张三门口听听,也到王五窗前停停,红尘滚滚的细节被风截在了村庄深处。那里狗追着鸡跑,鸡跳着上树,唯独猫躲在灶膛里打盹,它对白天的欢娱打不起精神。
一把柴火,惊吓到了猫。猫呜呜啊啊地逃出了灶间,蜷缩在柴堆里惊魂未定,风把它的毛吹成一团球。猫叫着叫着,把春天叫来了。每晚在春风沉醉的时候快刀斩乱麻似的忙碌,且一直忙到天亮才一身疲倦地回来,后面吊着一根尾巴,像是给风做个样子。
炊烟,袅袅起身,顺带着锅碗瓢盆的声音,站到了屋脊,风忙不迭地在半路接住,青烟负责捎带消息,余下的把生活分量埋进地里,继续人间烟火,夯实日子的底部。如果冰灶冷窠,风也跟着呜呜,一副枯瘦的骨架,怎么也撑不起生活的外衣。
生活的起承转合,付诸给了风,有时是冷风,有时是暖风。风碰见一个老人的离世,他的故事,他的经历,还有他的秘密,风送给他烟消云散。风也遇见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把婴儿的啼哭传给村庄,在每一扇木门前结一个风铃。风由东南西北坐了一圈,婴儿长了一大茬。风不停转换位置,婴儿变成小孩,在村庄里跑的面积越来越大。每个孩子都是见风大。老人坐在屋檐下总结村里孩子长大的原因,她们的话里漏着风,充满了岁月的骨感。
谁也不知道医院里扬起的那阵风,是从哪里启程的,一路上又挟来了多少孕育的秘密。虫欢虫爱的声音被风推起一丈高,呢喃喘息的声息在风里打转。村庄像一只丰满的口袋,装了许多隐密的事,可风却恣意地跑进跑出,逢人便呼呼,似乎它最忙碌。
也是,风最懂大地的心思。小草睁开惺忪的眼眸,风快活地忙着暖床。还有地里的作物,眼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风把僵硬的泥块刮松了。夏天,风摇晃着抽穗的水稻,留下一路的哗啦啦,像是合不拢嘴,但又管不住嘴。秋天,风的事情多了起来,树要换衣,山要染色,果子要熟,风像中年人,不停地吹,各个角落要吹一遍,似乎收集一切欢娱的信息。撞上风的更年期是冬天,情绪阴晴不定,时而冷若冰霜,时而又喋喋不休,在大地上絮絮叨叨,只是大地沉默不语。
自然,没有风不知道的事,也没有风不知道生长的规律。
有人用大棚骗了种子,种子心急慌忙地抽芽,长叶,开花。蜜蜂在白色的塑料布下撞一下,磕一下,夜深了它们中有的还在找路。风在棚外徘徊,一次次离去又一次次回去,却始终无法把消息带给棚里的种子。
有人把鸡鸭圈在一间屋子里,每天用别样的饲料喂养它们,一排排密集的大支光灯照着,它们光吃不睡,吃了蹲,蹲了吃,身上的肉肉越来越多。它们亢奋的叫声被风带到了村外,可没有人管。
因此,神明替代了风。一个掌管心思,一个掌管事物。看得见的风在村庄里飘荡,看不见的神明坐在位置上,有的被称为寺庙,有的被叫成神龛,有的甚至绘成图像贴在墙上,或灶前。恭奉迎请者是她们,跪拜祈祷者也是她们,在香烟缭绕中合掌恭敬,俯身说出一个个秘密,许下一个个愿,用响亮的磕头以恳求神明在天保佑。似乎只有神明,才能守口如瓶。
我有时搞不清神、仙与佛的区别,也弄不清楚这些神仙与佛的人称代词,不知道用“她”,还是“他”,至于“它”,肯定不行。比如观音是男的,但法相是女的,乡村称观世音菩萨,也称观音大士,没有性别色彩。在乡村人的心里观音大慈大悲,也救苦救难,用千种化身普渡着众生。笃信者有之,临时抱佛脚有之。
我认识一个老的接生婆,她是跟她母亲学的接生技术,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仅有的一点助产知识无非拼接了她母亲的经验和她自己的接生经历。她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殖解剖结构都不太清楚,却接了很多小生命。她随身携带一个小产包,里面的器械极其简单,似乎提醒着村里人生孩子很简单。固然有简单的分娩,孩子顺顺利利娩出,母亲也没什么大碍,她这一趟很轻松。别人给的报酬也是五花八门,条件好的,给她两块钱,外送些鸡蛋,或糖果,条件差的,可能也就一包枣子或几只鸡蛋,她也不计较。
也遇上过难产,胎儿久久无法娩出,产妇的身体越来越弱,家人焦急万分,她的内心更是充满不安。她把自己的恐惧与焦虑归结于不够虔诚,于是,她供了一尊瓷观音,每次接生前她会沐手洗脸梳头,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在观音像前点燃三支清香,然后在蒲团上默默地跪上片刻。袅袅青烟拂过瓷观音后,再拂过她的头,似乎隔着青烟,观音与她的距离越来越近。她有时接一次产,膝盖上要淤积很大一块乌青,就像胎儿身上的胎记。
我到镇上时她已不再接生了,主要是不允许她再接生了。她看上去慈眉善目,手软软的,声音也是柔柔的,看你的目光含着慈祥,像个观音。只是,她有个很大的遗憾,她本想跟同齡的老太一起去寺庙念佛拜佛,可那些老太不愿意接纳她,嫌她原来是个接生婆,双手沾满了血污,包括原来曾请求她去家里接过生的老太太,她们都嫌弃她暗房里待得太长,身上有秽气。她郁闷难当,但又很无奈,索性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念佛,坐在观音像的下面默默念诵,仿佛她还要去接生。
观音是村里最具人缘的菩萨,不仅仅住家里,也住在庙里,既被人求平安,也被人求子。尤其是婚后一直没有孕育的,隔三差五把送子观音面前的香炉旺起来。只是,这个香烧得有点偷偷摸摸,没有人愿意被人看到自己在求子。但人只要进了庙里,还没开口许愿,人的心思其实全泄漏了。
她们怀揣着希望与煎熬从一家医院奔赴另一家医院,在医生的问讯里重复着自己的隐情,而医生对既往病史的追溯像锋利的刀子切开她们内心的伤痛。她们的矜持与羞怯在诊断面前荡然无存。她们一次次揭开自己的私密,接受各个医生的检查,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无人知晓她们躺在手术床上时心里在念想什么,她们的目光里留存着什么,只看到她们卑微的笑容里堆满忽闪的渴望,怀上成了她们生活里的关键词。
尽管医生的字像天书,估计任何人都看不出病历上的诊断是什么,但不孕不育仍像利剑一般刺向她们的神经,以至于过度敏感,听到有人说不下蛋的母鸡诸如此类的话也会让她们掩面哭泣。她们小心谨慎,她们惶恐不安,在村庄里尽量让自己变得无声无息。即使一趟一趟跑医院也是避开耳目,似乎不能生育是她们的原罪。只是,忏悔的心声在她们心底成了一个结。
其实,她们有的并非不孕,而是不育,停经四十多天开始见红,甚至更早的,想尽一切方法保胎,差不多医巫兼用,中西结合,哪怕不可信的偏方也宁肯信其有,不愿错过孕育的可能,但所有的努力仍没能留住孕育的希望,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性流产,其痛苦带有某种羞辱,也蒙着自卑。有的不是原发性不孕不育,因过多地流产导致子宫内膜越来越薄,孕育的土壤遭到严重破坏,就像一枚青果子,还顶着花蒂,就被风吹离了枝头。
是的,风曾经住在村外不肯进来,村庄成了一只干瘪的布袋,盛不住年轻人的激情,也装不下中年人的心事,她们心有戚戚却躲闪着旁人的目光,用一个底气不足的理由把自己劝进医院。她们惊恐不安,为一桩意外的孕育。
当我按下电动按钮,一场风就刮错了地方,它急吼吼地顺着引流管探入宫腔,热流贴着管子从我手心里一截一截地跑出去,下面有一只瓶子静静站在那里,热乎乎的液体被吸到瓶子,慢慢变成红色,像一只被榨汁的番茄。错误的风数次误入,引起数次的创伤,精美的种子从孕育的一开始就遭遇了搁浅。
风一次次地刮,从天上刮到地上,刮起一阵阵的尘埃,空中的云层越来越薄,地上的种子把大地刮薄,种子的消息被带到了空中,如同在一次美丽谎言的笼罩下,生长的秘密瞬间暴露无遗。
同样一阵风,我手中的风,却稀薄了孕育的希望。我懵懂过,以为自己在帮助她们过滤冲动的杂质,那些毛茸茸的心思从此不再幽微。所以,她们痛苦地呻吟,我变得很麻木。我偶尔劝慰,也只是浮皮潦草。
有一天,我在车站偶遇她,她正拎着大包小包的药,看见我笑了笑,笑得很苦涩,一边还拼命想把药往包里塞。我咧了咧嘴,不知道有没有把笑表达出来。我心里正在措词时,她急匆匆地离开,走得像是被心事散漫了一身。我想起前几天她来看病,停经35天,以为自己怀上了,但一查仍没有。她不会掩藏失落,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发了阵呆,整个人的表情书写着失魂落魄四个字。我曾经开过一个方子,可我根本没有把握,后来我劝她去大的医院看看。
那张方子被我揉成团。结果风把它衔到了花坛里,一株娇艳的大丽花照着它。许多天过去了,大丽花慢慢枯萎,一瓣瓣花凋零下来,落到处方上,上面的字迹已风化。风收罗了一切。
风中呼啸的娘
像是跟天气打了一个招呼,小雪这天下起了雪。下着下着,雪花变成了雪粒,然后刮起了大风。纸屑、尘埃,还有棉球、纱布在医院里磕頭碰脑,数只麻雀在楼梯的转角处惊慌不已,蹦跳成一团乱线。
没有病人。坏天气把病人都留在了家里。医院里住满了风声,和冷不丁传来的哗啦、啪啦。
医生们有的往肚子里塞热水袋,有的搁在电热板上烘手,连闲聊的兴致都被冻僵了。
这种天气,最适合坐被窝,脚下躺两只灌了热水的盐水瓶,怀里再抱一只,把台灯的脖子拧到最低,翻翻书,旁边放一袋话梅。
可轮到我值班。
我翻看了下产包,还有二只。我在犹豫间下了一个赌注,今天不会有人来做产。因为,今天下雪了,今天刮大风了。
整个上午,我冰冷冷地坐在诊室里,搓手、跺脚带来的热量都贴不到肉里。索性,我练钢笔字。写了一张,手指头差不多变成鸡爪。我对着手心哈气。窗外花坛里的一棵桂花树被吹得披头散发,像是一位疯狂的女人热爱着她的生活。
这时,一个老年人结结巴巴地闯了进来。他戴顶雷锋帽,一只帽檐翘着,一蓬蓬的白气从嘴里吐出来。他说,他老婆生了,能不能去他家看看。我几乎愣住了。他老婆?他看上去是做爷爷的年龄,至少60多岁,头发半白,脸上的皱纹像机耕路,只有满口的牙齿倒还显示他的硬朗。
我说,你老婆在这里建过卡吗?我一边去拿挂在墙上的产检卡。镇上所有的孕妇名字在这里能找到。
他有些尴尬地说,没有建过卡。他勾下了头。外面正好有一阵风急吼吼地跑过去。咣当。风不知把什么东西撞倒了。
我不由得鼓鼓囊囊地站起来,看着他说,你们没有红卡吧?什么时候生的?
他说,是早上8点多的,现在胞(胎盘)还没下来。没有红卡。他老婆脑子有病。他说得有些磕磕绊绊,似乎靠回忆才能回答我。
没有红卡?脑子有病?疑问像两阵寒风龇牙咧嘴地钻进了脖颈。
我一看手表,已经10点半了。胎盘在子宫里已两个多小时了。我顾不得收拾桌上的字帖,到产房拿了接生器械和手套。我向他问来住址和姓名后奔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正捧着茶杯看财务报表,表上的一个个数字似乎正揪着他的眉毛,一副愁容惨淡的样子。院长听后,让我赶紧去,他会打电话给镇计生办。
临出门时我又拿了支催产素针,怕胎盘滞留时间长后影响宫缩。
到了外面才知风真是疯了,劈头盖脸,根本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的,似乎被人推搡着,拽拉着,裤脚管里好像有人塞进来一支支冰棍。我眼睛躲在风帽里仍不太容易睁开,也不敢多朝前看,时间稍稍一长,感觉眼珠子不太会动了。其实,风把我的思维也冰镇住了。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甚至对产妇的估计也麻木了。
他家在医院后面的莫家岙,路倒不远,只是风实在太大了,大得实在不像样子,简直能把人鼓起来,还刺骨的冷。一路上只有我跟他俩人,像是风中的逗号。
他在前面走,缩着身子,头不时朝左朝右偏,时不时用手去摁头上的帽子,爷爷的形象活灵活现。我跟在他后面,在风中的呼啸声里一次次侧过身去,如同半身不遂。
我们像两片叶子一样踉踉跄跄地终于被推进了一幢小屋。
屋檐下站着三个人,都是老人,像是闲聊,也像是什么没说,在等人的样子。他们背后是黑乎乎的屋子,门槛上缩着一只猫,背弓得老高,眼神懒洋洋的,似乎风在理它的毛,它正惬意地享受。
我用发硬的手指揉了揉眼睛,问他产妇在哪里。一边抬脚迈进了门槛。站着的三位老人神情黯然,又默不作声,但目光很散乱,一个朝外看,一个往地上瞅,另一个对着屋顶,各顾各的。
他说,我领你去。说完,他一脚跨出了屋檐。我愕然。拢共也就二间平屋,产妇不住里面,难不成借宿在别人家里?这时候的疑问终究有点白乎雪糟,我人已经到他们家了,我来的目的是看产妇产后的情况。但愿不要有什么意外。因心里转到“意外”两个字,我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
他把我领到的居然是后面的一间茅屋。一扇柴门跟他的年纪还要大,上面豁着,下面漏着,中间还透着。我脑子一时空白,手里的产包差点磕到了柴门上。他麻利地推开,朝里面努了一下嘴,说,她在那里。我感觉自己的手脚一阵阵发麻,身子怎么也走不过去。
产妇躺在一条破棉絮上,盖的也是一床旧被,上面的污渍像是积攒了多年,几乎可抠出块来。她的下面塞了一层稻草,稻草下面就是泥地,她连张床都没有,四周冷风嗖来嗖去。我只看到产妇在旧被外露出半个头,头发干枯,但没有一根白头发。我抖着牙说,她怎么睡这里呀!太冷了。
他仍用“她脑子有病”来回答我。
在她的左手边躺着一个婴儿,被裹在破襁褓里,小脸上沾满了血渍,还有白色的胎脂。婴儿时不时哭几声,呼啸的北风把哭声挤得粉碎。
我觉得“罪过”两个字在心里跳来跳去,难过的情绪快速地啄着我,啄得我心底一片兵慌马乱。
我掀开被子,她几乎光裸着身子,下面拖着一根脐带。我探出身子,问她有没有不舒服的。她浑浑沌沌地看着我,一脸的干瘪。他拢着手,说,她脑子有病,听不懂的。不快的情绪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我。我吸下好几口冷气。
我用手按压她的腹部,子宫还没完全收缩,所幸出血不多。我让他拿条毛巾来,盖在她肚子上。我拆开产包,拿了一张垫纸铺上,又戴上手套,一只手拉脐带,一只手轻轻揉她的子宫。她一动不动。慢慢地,子宫开始变硬,脐带也一点点被我拉长。三分钟后胎盘娩了出来。
我检查了一下她的会阴,没有破裂的地方,出血量也不多,但我决定还是给她打针催产素。针头扎进她屁股时,她的手突然来抓针管。我下意识地用手去阻止,却一把捉住了铁链。她被铁链锁着。我再次抖着牙说,干吗锁着她?
他说,不锁,她要乱跑的。我没再问下去,只是觉得浑身发冷。
我半跪在稻草上,确定针管的位置后替她拉紧被子,慢慢把注射液推进她体内。
我拔出针头后,棉球在她屁股上摁了一会儿,透过被窝的缝隙看看没出血点了,便收起针管。她的手再一次伸过来,手指骨一节节往外突出,像一只笊篱。
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在柴门外探头探脑,头发乱蓬蓬的,跟鸡窝似的,身上穿了件不合身的旧军大衣。男孩突然叫了声娘。产妇的脸侧了过去,吃吃地笑了起来。男孩也笑了,鼻子下拖着亮晶晶的鼻涕。婴儿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在一间四处透风的茅屋里一声接着一声。
我感到一阵酸涩,但又不知所措。
我从柴门出来后,屋檐下多了一个女的,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李阿姨。李阿姨一见男的,就大声斥责起来,介呒数倒账,老婆有病还要去睡她,现在连孩子都生了下来,你有能力去养啊?男的神情很尴尬,嘴上却“嘿嘿”着,也不回话。
另外三个老人你一句我一句,半是数落半是同情,同情产妇,也同情他,说他不容易,老婆经常要犯病,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力,儿子又有些半痴呆。如果不是因为穷,也不会讨个脑子有病的女人。李阿姨白了他们一眼,还说呢,知道自己老婆脑子有病,还生什么小孩啊。有一个老人接上来说,家里香火也是要紧的。李阿姨气乎乎地说,生个呆儿子反而讨债,再说介老的年纪了还不懂避孕啊。
男的仍“嘿嘿”着,似乎说的都是别人的事。
李阿姨问我,产妇怎么样啊?真是作孽。我说,现在看看还好。只是那茅屋实在太冷了,最好住到平屋里来。
李阿姨的气又来了,夹枪带棒地说,介呒有良心,把老婆锁在茅房里,还要去睡她。
风继续呼啸着,我隐隐听到有人在叫娘。转过头去,男孩正趴在柴门上。
我想起一件事来,问他谁接的生,孩子的脐带怎么处理的。
他说,是他接的,用家里的剪刀剪的。
我差点惊出汗来,破伤风这个病名蓦地跳出脑海。我说我赶紧处理一下。
他似乎有些不太情愿,靠着水缸边不动,还是在李阿姨的指责下把婴儿抱了过来。我解开襁褓,婴儿居然赤裸着,是个男婴。男婴的皮肤已冻得发紫,蜷曲的小腿不停地颤抖,肚子上拖着一截脐带。我用血管钳夹住,剪去多余的脐带,碘酒棉球涂了几遍,上面盖上消毒纱布。
我回去时让他一起到医院,像产妇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用些抗生素。起初他不肯,推三却四的,后来旁人都劝,医生说要配一定要配的。他这才勉勉强强地跟了出来。
回去的路上风弱了些,可我一路抖着,刚才的情景像蒙太奇一样在大脑皮质层切换着。我想借深呼吸来平息情绪,结果打起了嗝。我掐合谷,按内关,仍无济于事。到了医院胃跟着痛起来。
我开处方时问产妇的姓名,他似乎愣了一下,过后好像用力忖了忖,说是阿梅。我说姓呢?他又接不上。我有些厌恶地看着他,老婆姓什么都不知道的啊。他的嘴唇咧了咧,终于咧出一个李字来。
我在处方上写了李梅花。我也不晓得自己怎么会写这个名字,或许产妇有属于她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在队里的户口名册里有,她的父母肯定知道。現在,她的男人差点叫不出她的名字,而她却为他生了一个婴儿,还被他锁在茅草屋里,只有北风在她的周围唱着破歌。
我在门诊室里麻木地喝了几杯热水,嗝倒不打了,可身子仍抖着,心里空荡荡的难过。
第二天,有人在镇上的老街那里发现一个男婴,把他抱到镇政府的民政办。曾有人跑到镇政府想领养,也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最后放弃了。男婴被送到了县里的福利院,镇政府民政办看着刚出生的婴儿,担心路上有什么意外,让医院派个医生护送。我便随车同行。路上是我抱的婴儿,他哭一声,嘴里呷几声,呷几声,哭一会儿。我泡了半瓶奶粉后,他才安静下来。
几天后,那位产妇死了。
娘,这个词让我难过了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