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传山河
2019-08-26海坤李庚
海坤 李庚
1954年的第一次江南写生正是李可染深入探寻现实生活实践的开始,他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师造化,到大自然中进行中国画改革的探索。虽然以写生的方式改革中国画并不是李可染的首创,但是此时的李可染确实将改革中国画的命运与自己相连,这是50年代一位中国画家面对厄运时的自觉意识,源自内心最深处的艺术良知与责任担当。然而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拥有改革的勇气与能力,因为中国画的改革不仅仅要面向生活,还要拥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和对西方绘画的理解掌握。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
李可染曾说:“用传统的水墨画表现方法作真实景物的描写,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所以我们的目的与要求也比较简单,这就是: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
“在太湖,在西湖,在苏州,在富春江……处处可以看到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游人,使我们认识到解放了的人民对祖国的美丽河山是如何的热爱,同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这样如画的环境里,真是很大的幸福,因之更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勇气。在太湖,在西湖,在苏州,在富春江……处处可以看到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游人,使我们认识到解放了的人民对祖国的美丽河山是如何的热爱,同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这样如画的环境里,真是很大的幸福,因之更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勇气。”
在20世纪中国画坛呈现出一派创新气象。当然,也有人微词,有人批评“是受了传统的毒”,有人讽刺说“这哪里是中国画”,但李可染不以为然。出发江南前,李可染还曾专门请邓散木篆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是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有人说李可染是一位胆小谨慎的人,但是他在艺术创作中却有巨大的能量与勇气。他把“胆”字放在前面,为自己改革中国画的江南写生之旅壮行,为中国画命运置之死地而后生勇于寻求突破。当然只有胆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魂”,这个“魂”字不仅仅是画家将时代精神与自我情景相融合的灵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灵魂,是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精髓所在。所以,李可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家家都在画屏中》、《雨亦奇》等美术史上令人称颂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6年李可染再度提出出去写生,美院助教黄润华当他的助手。出发前,李可染约法三章:一,不能到地方就打电话说李可染来写生了;二,必须能吃苦;三,回学校要出成绩。显然,李可染是带着问题去写生的。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他们反复寻景写生8个月,路程数万里。经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麓山、韶山,转赴三峡、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凌云山、嘉陵江、岷江,过栈道险阻,越宝成铁路,辛劳的程度难以想象。年近五旬的李可染,患有失眠症和高血压,迈开两条腿穿梭于祖国山河。炎炎烈日下,一个画夹、一书包笔墨纸砚、一个小马扎、一个水壶、一盒午饭,外加遮阳伞和雨衣,背负十余斤重的必需品行进往返于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大自然中。为了集中精力作画,减少交友应酬,宁住车站附近小旅店也不住招待所,即使通铺、加铺也不在意。在四川,为了省钱,有时用人家摆完龙门阵后的桌子拼搭成床;有时在骡马店里打地铺;有时找个澡堂子,等营业结束了简单靠一靠。实在没有住处时,才打电话给当地美协请求帮助。为了保证作画时间,经常提前吃早餐,带干粮上路,晚上简单充饥。
如此衣食住行,客观上实在是相当劳累疲乏的。他们在重庆枇杷山上画山城和嘉陵江时,从早晨上山,一直画到落日几尽,李可染筋疲力尽,连收拾画具的力气也没有了,在黄润华的帮助搀扶下到山坡上歇息后方才下得山来。一路作画,一路艰难。到南京时,李可染的裤子膝盖都破了,鞋底磨了一个大洞,用一块瓦楞纸垫上,像叫花子一样。向姐姐借钱才回到北京。
李可染想要“为祖国河山立传”。这一趟作画近200幅,画了一批好东西。从山水入手,山水点缀人物、花草。山水解决好了,其他都迎刃而解。1956年李可染营造的意境不再是属于传统绘画营造的文人意境,而是主体精神外延空间的不断放大,主观而超越的同时,又是现实的,可以带领欣赏者身临其境——把观众拽到画里面,实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李可染本着“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理想再次出走,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突围。首次写生的作品中尚能看到水彩画的痕迹和西方风景画的影响,而第二次坚持不懈地行走在祖国山川之中,自然与人文互相关照互相生成,水彩画的色彩关系与西方风景画的透视关系逐渐合并包容,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对景写生。单论构图方法,1956年所作的《江城暮色》,仅在画面的最上部留出了不能再少的一缕白色,而这一点仅有的地方也并非空白,而是由淡墨描绘的江水、天空、帆船组成。画面饱满的构图和黑与白的强烈对比,使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力。
访问东德
1957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委派,李可染与关良应邀赴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历时四个月。乘火车途径西伯利亚、莫斯科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十多天后才到达东柏林。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东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在克林莫克教授家里为他们两人召开欢迎会,展示其部分作品,邀请了许多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参观,并建议其将带来的作品在柏林藝术科学院开个展览会。在柏林、德累斯顿、魏玛等地旅居、逗留期间,李可染水墨写生《东德金秋连作》约20幅,德国还专门为他精印大帧单幅山水写生作品七卷。柏林艺术科学院全体院士通过决议,为两位中国画家举办联展,还特别将展出日程安插在就近的日期内,使得展览两个月之后就得以开幕。此次展览反响强烈,名驰欧洲,观众参观异常踊跃,并热切地要求购买他们的展品。随后,两位画家应邀在法国举办展览,法国一家报纸整版刊载展览的作品,这在法国是少有的。

李可染《井冈山主峰图》。

淘尽红心为人民一九六七年摘录麦贤得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中语,可染。钤印:李(朱文)可染(白文)。
在欧洲展览期间,东德的对外友协安排他们到各个地区去参观访问。他们沿易北河流经的土地行进,田园式的宁静气氛、令人陶醉的清新空气、具有独特风韵的德意志农村田野、古朴庄穆的建筑物如“司维令博物馆”和“司脱尔特大教堂”等都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他们参观了德国东南部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又多次驱车直往西柏林的几个艺术博物馆,观摩伦勃朗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李可染参观大型博物馆,遍访西方大师油画原作,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令他激动不已。这种相当具有新鲜感与冲击力的参观访问,也许一下子勾连起近三十年前其在西湖国立艺专学习时的经验与记忆。李可染晚年回忆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学习情形时说及,绘画方面因为教授大都为法国留学生,并有法籍教授克罗多做研究生导师,故教学上主张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青年学子自然受此影响,但他们又心怀艺术反映社会和斗争的职志,因此也学习其他风格的绘画:“一是文艺复兴,米盖朗琪罗、达·芬奇、波蒂彻利,取他们的创作严肃认真、富表现力;波蒂彻利色彩单纯、线条明晰,近中国画。其外,是米勒,米勒反映农民生活,描写一些劳动人民形象,醇厚善良,虽然带有宗教性的人道主义色彩,但他那一幅倚锄男子却表现出农民被压迫、艰辛劳累的情景,很使人感动。还有多米埃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伦勃朗表现力强,用笔豪放。”在有机会见到这些青年时代业已心仪的大师的作品时,李可染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的写生一下子进入了最佳状态。经验与记忆一旦被激发,主体对于异国文化、异域风情、异国大师作品的高度敏感迅速转化为自己笔下“对景创作”的动力与结果。观念与技法的“中西融合”,开创了绘画写生创作的新路,李可染是在“以中化西”,坚持传统民族文化的主脉,咀嚼消化外来文化并化其为营养而吸收,这一理论坚持,尤其是艺术实践,在5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

李可染《万山红遍》,1964年作,款识: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写毛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可染。
1954年与1956年两次国内写生,李可染完成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过渡,已经能够相对自由地面对眼前景物,即他已然把握了传统山水画向现代转型的整体结构系统,熟练驾驭贴近现实兼具艺术表现力的笔墨语言。而德国写生,对于其整个山水艺术体系的转型来讲,既是契机,又是表征。
异国景物面前,李可染变得更加主动,娴熟地运用中国毛笔、水墨表达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情感,景、情、韵、色和谐自如,艺术才思挥洒淋漓,营构了令人惊奇、憧憬而诗化的欧洲世界。如此“对景创作”式实践,也让他的写生艺术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高峰,同时无意间以实践成果回答并解决了长期以来业界喋喋不休的“中西之争”,用他本人晚年时期的话说:“中华传统文化是血缘,外来文化是营养,营养是需要的,但不能代替血缘。”
万山红遍
吴冠中说:“李可染是把传统山水画的画室搬到大自然里去的第一人。”从50年代里几次写生实践来看,由理论主张到实地创作,李可染都是成功的。他的写生,是艺术家直接面对生活、吸取创作源泉、积累绘画经验、丰富生活感受的重要环节。反复强调追求时代意境的创造与意匠手法的探索,大大提升了山水画的表现力。尤其是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光,成为创造情景交融的独到而凸显的元素。换言之,意境可以自由召唤之、随意调动之,因意境的需要,光源活跃在不同方位,可以“白催朽骨”、可以“追光蹑影”、可以“流光徘徊”、也可以“黑入太阴”……开始阶段的对景写生,“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发展到对景创作时,已经能够明显看出李可染以饱满而强烈的主观情感渗透自然山水的努力,自然山水往往烙上主体的意绪情感,“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对景写生和对景创作都不是李可染最终最高的追求,“写生只是创作的基础和桥梁,是创作的过渡和准备”,“写生,是半成品,还有待反复加工和提高”。1960年,李可染提出“采一炼十”的主张,山水画创作进入驰骋想象、抒发性灵的自由新阶段,又可谓“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了。
真正的艺术创造必须兼有采矿工人和冶炼家双重的艰辛和勤奋。写生只是在采矿,作品的终极完成,还需要创作,就是冶炼矿石。虽然采矿已是无比艰辛的劳动,但在创新创造上,也还只是“一”;更要付出十倍、百倍的时间与精力去苦心冶炼,才能有十倍乃至更多倍的收获,是所谓“十”。李可染经过多次长、短途写生实践——采集矿石,辅之以十年师从齐、黄而得其笔墨堂奥,深悟无“炼”则不得。其实,“炼”从写生时就寓含其中,“采”中有“炼”,“炼”的是眼力;“采”之后,“炼”亦不止,千百攀登,“煉”的是手力;千锤百“炼”,循环往复,“炼”的是心力……“炼”,始终是个未完成式,这是一个没有停止、无尽追求的过程,也是艺术家整个思想、情感、精神与人格整体性与有形无形山水对话、拥抱和超越的过程。李可染60年代中前期的山水画作品,百炼成钢,收放自如,意境清新,丰富感人,完成了质的飞跃。
1962年,李可染完成了《鲁迅故乡绍兴城》、《黄海烟霞》、《万山夕照》、《春雨江南》、《陡壑夕阳》、《楼台烟雨图》、《雁岩一景》、《漓江》、《万山红遍(一)》、《犟牛图》、《五牛图》、《赏荷图》、《钟馗送妹图》等作品。
1964年,李可染完成了《清漓天下景》、《清凉世界》、《归牧图(一)》、《万山红遍(二)》、丈二巨幅《漓江》、《巫山云图》、《山下水田》等传世作品。

長征,设色纸本 1978年作,题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敬写毛主席诗意,可染于北京。
60年代初,毛泽东诗词逐渐成为中国画坛极为重要的创作主题,各家各派纷纷投入创作,以展现其诗词中的山水意境。其时,结束多年写生、重新回归画室创作的李可染,也自然而然地开始涉足这一题材,“采一炼十”,《万山红遍》可谓这其中的巅峰之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是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长沙》中的名句,描述了深秋时分,湘江之滨的岳麓山漫山古树皆红的壮丽奇景。自50年代开始,尽管中国画坛掀起了描绘毛泽东词意的热潮,但极少有画家敢于尝试“万山红遍”这一题材。一方面,“万山”之意境颇为辽阔深远,极大地考验着画家的空间驾驭能力,若非胸有千山万壑,则根本无法表现“万山”;另一方面,“红遍”给中国传统山水画出了个大难题:历来山水多以水墨描绘,仅作为点缀的红色在使用上可谓慎之又慎,更莫提“红遍”了。这两大创作难点,令当时的画家普遍将其视为畏途,无从落笔。李可染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多次写生之旅,跨越中西,千山万水。
从1961年开始,获得特许一连三年都在中央高层领导专属的疗养胜地潜心创作,其待遇之优在当时全国的画家中可谓绝无仅有。描绘“红遍”,“红”自是必不可少。什么样的“红”?怎么“红”?朱砂应需而来,妙不可言。李可染素来挑剔纸、墨等作画材料,普通朱砂难入其法眼。
颇为凑巧的是,1961至1962年间,偶然得到故宫流出的半斤乾隆朱砂(乾隆朱砂是千挑万选始得的极品朱砂,本是乾隆皇帝自备以钤御用宝玺的,其珍稀程度不言自明)。用朱砂作画前人有之,但多用于画佛像、钟馗、花卉等,大面积用于山水画,自李可染创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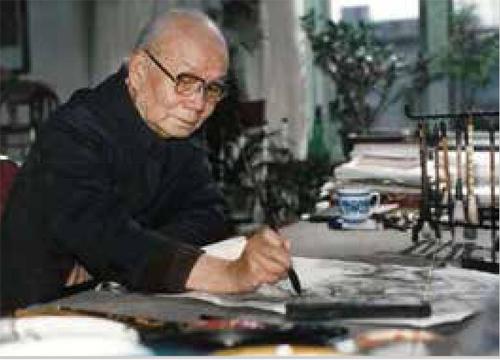
李可染认为“生活与艺术相比,生活是基础。”正如他的创作,源于生活的积淀,却高于生活的感观。
李可染首次尝试创作“万山红遍”题材是1962年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地,款识题于画的右上角,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二年秋可染作于从化翠溪宾舍”;第二幅创作于翌年,仍是在广东从化,款识题于画的右上角,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三年可染于从化”,此画1963年出版于第6期《美术》杂志,李可染把它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其他五幅皆在1964年创作于北京西山八大处疗养地。李可染先用半斤内库朱砂创作了四幅,其中两幅较小的,两幅大的。两幅小的分别为:一幅画右上角题“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可染写毛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八大处”。另一画左上角题:“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毛主席词意,一九六四年可染”,此画给了荣宝斋。而两张大尺幅的,一幅左上角题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写毛主席词意可染”,曾被出版。另一幅曾出版在香港《名家翰墨》第26期第47页,该画左上角题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写毛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可染”。同年,应荣宝斋之邀,为建国15周年国庆又画了一大幅给荣宝斋,此幅右上角题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建国十五周年大庆,可染写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此件现藏于北京荣宝斋。李可染先生画完这幅《万山红遍》后,从此再没画过《万山红遍》。
祖国的壮阔河山,在李可染的笔下被赋予了神圣而永恒的力量。《万山红遍》被视为“红色山水画”是不能回避的,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甚至极具代表性,也奠定了李可染在“红色山水画”群体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