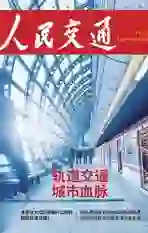我记忆中的交通工具的演变
2019-08-25刘海军
刘海军



通往村里的那条路,由土路变成柏油路,不知留下了多少人的足迹和车轮的辙印。
而我对车轮的认识,不是在路上,而是在树上。确切地说,是从老家村头那棵老柿树上悬挂着的牛车的铁轱辘开始的。
车,自古而今就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据说牛车是我国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发明的。最初,牛车的车轴、轮子甚至全身都是木头做的。荀子《劝学》一文中“木直中绳,鞣以为轮”的论述,就是对当时制作牛车车轮最好的描述。后来到了近代,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牛车的车轮由木制变成了铁铸,人称“铁脚车”。历史上的牛车,曾一度成为官员、贵族乃至皇帝的代步工具;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更是特别受到农民的青睐。
在我的记忆里,把牛车的铁轱辘悬挂于树上,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正像豫剧《朝阳沟》里所唱的那样:“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在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牛车因为轮子为铸铁制造的铁轱辘,自身笨重、行走速度慢、载重量小等原因,加上它的轮子没有弹性,与地面硬碰硬,常常轧出深深的车辙,破坏了路面,故而渐渐地被新中国成立后的马车所取代。马车与牛车相比,可先进多了。马车的车轮是橡胶做的且为可以充气的胶轮,车轴两端还安装了轴承,不仅拉的多,而且跑得快。这样,被淘汰的牛车的铁轱辘,就被生产队长废物利用,挂在了树上当钟敲,成为社员们每天出工或队里开会的号令。我就是伴随着车轮的“钟声”在农村长大的。
马车的问世,成为农村中当时最重要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年代,马车的驭手,俗称“赶大车”的,是农村中最吃香的一种职业。君不见,电影《青松岭》中伴随着画面的插曲中所唱的“长鞭一甩啪啪响,赶起了大车出了庄”,那种神气劲、那种自豪感,是何止用“吃香”二字能够表达的。如果用当代社会的情形来形容,你就是开个宝马轿车,也远远比不上当年的“赶大车”的马车驭手。那时,马车属于生产队的,平时用于搞运输,为生产队增加副业收入,遇到谁家有婚丧嫁娶的事儿,实行免费服务。所以,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宁可得罪队干部,不能得罪赶车的。得罪干部干重活,得罪赶车没车坐。”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20多年的那个时间段,在我生活的那个村庄里,有些劳动力多、挣工分多的家庭,陆续开始购买自行车了。不过,那时购买好一点的自行车如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天津产的“飞鸽”等名牌车,是凭票供应的,不易买到。而大多数家庭只能购买诸如安阳产的“飞鹰”、洛阳产的“东方”、五三一军工企业产的“剑鱼”之类的不要票的二流车。我家买的就是一辆“飞鹰”车,尽管不是名牌,但骑上它进城或走亲戚,也觉得蛮神气的。有了自行车,村里人结婚办喜事,也不坐马车了,借上几辆自行车,组成一个自行车队,就把新娘接回来了。自行车不仅是代步工具,而且也是载重工具。一辆自行车的后架上,载上—二百斤的东西没什么问题,即使载人也很方便。那时候,我们一家大小四口人出行,仅一辆自行车足矣:我是司机,一个孩子坐在车的前梁上,两只小手抓住车把,另一个小孩由我老婆抱着坐在后架上,只要不是连续上坡,一口气骑上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累。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自行车的普及,一些家庭为适应生產的发展,还买了“小拖”,就是洛阳产的那种“东方红”小四轮,平时用于跑运输挣钱,农忙季节还可收割、运粮运肥、耕地播种,可谓一机多用。新中国成立后辉煌了几十年的马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渐渐地悄然退出了交通运输的行列。
当历史进入新世纪之后,新兴的电动自行车和小轿车业已相继进入寻常百姓家里。如今,每每回村看到停放在路边的各种各样小轿车,就使我想起一件事来:1982年7月,我从总后基地某部调到老家的人武部工作后。有一天,我与政工科的韩科长乘坐部里的军用吉普下乡检查民兵工作,返回时,我顺便拐道回老家看看。那时候,别说是小轿车,就是这帆布篷的吉普车,县里也没有几辆。所以,车在我的家门前停下后,很多乡亲们围着车看。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吉普车的模样,有的还向司机问这问那的,似乎充满了神奇感。在我看来,也许从那时起,乡亲们就有了汽车梦。村干部告诉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村民们生活富裕了,全村现在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都实现了汽车梦。
是啊,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仅仅短短70年时间,农村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乡亲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征途中,实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梦!从车轮看变化,也仅为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