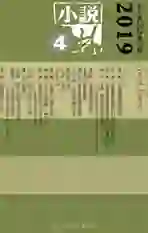扫瞄世界文学(三)
2019-08-13寇挥
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不会是什么可以与全人类双高峰《白鲸》和《悲惨世界》比肩的作品,他的思想意识尚未完全松解,古老庸俗的观念还限制着他,他挣脱不了,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的不够高大、不够崇高。布罗赫的《未知量》前不久有了中译本,是个不大的中篇小说,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来看一看。
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中文译本有一千二百多页,要读完它,得花费巨大的工夫,好在是上下两册,可以分开读。我记不清是用多长时间把它读完的。之前有一位酷爱哲学的朋友提醒说,这部作品要快读,读完之后,才能体会它的了不起。还说这部作品应该叫一个哲学家来翻译,精妙之处估计是在文字的哲理性上。可我读完之后,对这部世界巨著大失所望,为何把微小的、琐碎的事情用史诗那样的笔触来写呢?联想亚历山大·蒲伯的《劫发记》之滑稽模仿史诗,当然是可以这样写的,可我在穆齐尔的这部长河浩著里并没有读出戏仿与反讽的趣味。小事物里没有滑稽,无疑就分析不出好玩的意思来了。假如与俄国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奥勃洛摩夫》《当代英雄》中多余人众多形象挂靠起来,那么这个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也是一个与他的时代与帝国同样奄奄一息的没有希望的人,这样一个人物预示两个皇帝帝国的腐朽与没落,这样下结论的话,那么这部长篇就算没有白读。
短篇小说《古斯特尔少尉》,是一位叫施尼茨勒的作家写的,我最初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办的《外国文艺》上看到的。这篇小说中使用的意识流方法好像有别于其他作家的意识流小说,它用意识到的事物代替了主人公的行程。它基本是一篇行程小说,但行程却是逐渐呈现的事物与景象。帝国军人的荣誉遭受到了污辱,这位少尉要向面包师讨回荣誉,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折磨了他整整一夜,在次日早晨他得知面包师已经重病身亡之后,才如释重负。把这样一个短篇与穆齐尔的长篇巨著比较,似乎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这个皇帝统治下的帝国确实到了末日。一切都腐朽了,连军人的勇气都腐烂了。帝国军官既没有包容大度的胸怀,原谅他人的冒犯,更没有战斗的勇敢,只是在内心深处咀嚼着他受到的所谓的委屈,这样的人物已经是高度退化了的俄国多余人了。莱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实际应该叫做反英雄,尤索林与朋友决斗,一枪把对方打倒,他看着朋友的躯体滚下悬崖,不为所动——这样的多余人虽然血腥冷血,但还是有一种力量感,使读者心灵战栗。弗兰兹·约瑟夫一世的奥匈帝国的确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末日,作家们的感觉与眼光是多么灵敏与尖锐,他们在它还活跃的时候就准确地感知到了。无独有偶,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同样写出了这个帝国的腐朽,一个帝国行将就木之时,会散发出如此巨大浓重的气味吗?作家们是猫头鹰,是鸱鸮。一个出生于边远山区的卫队长的儿子,在战场上看到一个随从官员把望远镜递给皇帝,皇帝举起望远镜往远处看时,这位年轻的军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皇帝按倒的同时,一颗子弹射穿了年轻军人的肩胛,于是这位成了索尔弗里诺战地英雄的年轻人被皇帝册封为男爵。他的第二代、唯一的儿子成了地方长官,他变成了一幅画像。到第三代时,还是单传,地方长官把儿子卡尔·约瑟夫送上战场,献给了如今已经年老的皇帝。这个叫特罗塔的家族三代单传,断了根……就因为那样一个动作、一个行为,导致了这个家族的死灭。三代单传再也传不下去了,孙子在祖父的形象的压力下,甘愿为皇帝战死,中间一代没有从军,是个文官,他的父亲、也就是那个救了皇帝的战场英雄,坚决不让他的儿子从军,可是这个儿子在父亲的光环下,自豪、义无反顾、悲壮地把儿子送进了军队。皇帝需要这样的热血青年,他需要没有止境的血,鲜血。一个帝国腐朽时,就会需要更多的血。再多的血也不可能挽救它。这部小说使我感受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哀。这是一曲家族帝国的凄凉挽歌。
施尼茨勒的小说我最早买过他的《相思的苦酒》,薄薄的一本书,我没有读,一直在书架上放着,后来离开陕南时,也没有把它带走。后来买了他的《轮舞》,看了之后没有留下印象。他的大中篇《艾尔莎小姐》最早是在《国外文学》的杂志里看到的,艾尔莎小姐为了救她的父亲,把赤裸的躯体裹到大氅之下去见那个能够救她父亲的富商,从高高旋转的楼梯上下来,走到大厅时昏倒了,大氅滑落,艳惊四座——还算是一部有趣味的小说,情景设计得很美,也很野。
关于奥地利的文学,伯恩哈德是不应忽略的。他对他的祖国,对这个国家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他在他的遗嘱中毫不留情地拒绝奥地利出版他的所有的作品,他死后五十年不许出版。这个愤怒而有骨气的作家,生前靠一位老护士的资助完成了文学大业。这位大他几十岁的护士是给他看病的医生的遗孀,多亏这位对文学无私奉献的女性,托马斯·伯恩哈德完成了《英雄广场》《鲍里斯的节日》等不朽作品。这位作家对他受一位退休护士供养进行写作这样的现状羞恨难当,在《鲍里斯的节日》里,鲍里斯显然是作家自身处境的化身。
有人一定会认为我没有读过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或者是忘记了她。她的《死者的孩子们》是她小说的最高成就。其他如《钢琴教师》《情欲》《贪婪》等长篇小说,水平较低。她的一些戏剧,如《魂断阿尔卑斯山》《女魔王》《漫游者》《云团·家园》《死亡与少女Ⅰ-Ⅴ》,我十分赞赏。但我在这里确实不太喜欢谈论她,关键是没有心情。这也不知是为什么。这位女作家曾经赞扬过伯恩哈德,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她的才华明显在他之下。
全人类全世界的文学(我指的主要是小说)如此浩瀚,小说家更像是夜空的星辰,我花了数十年阅读他们的作品,现在要一下子回忆起来并加以评说,感到这样的工作缺乏创造性,没有激情,也就动力不足。问题是这项工作开始了就得进行下去,还得进行到底,工作虽然苦闷机械,做完了就会感到这是应该的。把经验告诉年轻人,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会获得回报的。哪怕是一个青年学子的一声“老师,你好”也能慰藉我的心。
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文学还是放到后面谈论吧,我就零散地谈一谈北欧和中欧那些小国的小说。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学史家,更不是文学评论家,仅仅是个小说家,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之外便是阅读。我对当代的作品没有多大兴趣,我是沿着文学史的脉络阅读的。我的阅读年龄与创作年龄同岁,我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八十篇中短篇小说,我把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翻译界翻译的世界文学作品做同步阅读。我读的是文学史中的杰作与经典,经典之外,我几乎不去问津。我有创作十一部长篇小说的经验,有创作八十篇中短篇小说的经验,有三十多年的小说阅读史,这样的经验与条件,我相信我对世界文学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
这一部分会轻松一些,我敲键盘的手指也就更自由一些。一说起捷克就必须说哈谢克,他的《好兵帅克》马原先生特别叫好,这样一部作品我几乎能够耳熟能详,但却没有读完,即使那萧乾译的删节本我也没有读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倒是看完了。也许我对它影响下的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看的次数过于多了,到我拿起这部小说读时,热情顿减。假如我是先看的《好兵帅克》,我的兴奋点就会一直持续到小说的结尾。它的前面有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还有果戈理的《死魂灵》,还有众多的流浪汉体小说,这一类型的小说家族实在是过于浩渺繁荣了,它的后面还有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缓刑》,还有索尔·贝娄的《奥吉·玛琪历险记》、约翰·巴思的《烟草经纪人》。在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书店,我常常看见哈谢克的短篇小说选,始终没有把它买下,今天想来是最大的遗憾。这部小说的人物帅克一人抵抗奥匈帝国,一个人戏弄哈布斯王朝,这样的以人物为亮点为关键的小说,无疑会写出无数笑话,是很热闹的小说。但这部小说没有写完,也就是说没有结尾,这种没有完整结构的小说,似乎是不需要情感结构,说白了,它其实是不可能有杰出的结构的。它玩的是人物,这个人物干的事可少可多、可长可短。像《堂吉诃德》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构,人物死了,似乎也就是最好的结局,也是没有办法的结尾了。《好兵帅克》假如能够写完的话,它的结局还不就是帅克死了,还能会有什么样非凡的结局呢?
捷克还有个剧作家哈维尔,民主革命后当了总统,他的剧本一直见不到,也就没有阅读的幸运。再就是移居法国的米兰·昆德拉,这是大家谈得最多的一个小说家。他也喜欢谈他阅读过的作家,比如他崇拜英国的斯泰恩的《项狄传》,曾一度成为我阅读方向的指南。我是1987年就盯上他的,那时韩少功与人合译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为了告别的聚会》《玩笑》《生活在别处》,我记得作家出版社一次引进了他四部小说,我邮购了他全部的作品。这位作家在中国内地算是红了,红了三十年了,还在红,还要继续红下去。针对这样一个當红作家,我2005年在哈罗德·品特以他的怪诞戏剧成为诺奖得主时,写过一篇文章,预言他不会获得这个奖。按照当时诺奖评委的观点与标准,昆德拉这样的作家确实是不够格的。比如他的成名作《玩笑》,把人类情感结构建立在一个可笑的玩笑上面,这样的小说能有多大分量呢?路德维希因为给他的女朋友写信时开了一个玩笑,被告发,结果被送进苦役营劳动改造。这个玩笑当然是一流的,是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他到劳改营后,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姑娘每天到公墓偷一束鲜花,然后把它送给这位苦役犯。她无法直接把鲜花送到他的手上,只好把它放到监狱的门口。这也是送给所有被监禁者的花。这位有精神病的姑娘是被她的党员干部身份的伯父强奸后患上精神病的。这是小说的前半部分,放到世界文学的一流行列中,顶呱呱的。问题是,这个苦役犯出狱后,去勾引把他送进苦役营的那位已经成了党员干部的同学的妻子,他成功了。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官员早就想甩掉他的妻子,一直没有机会,也找不到理由。路德维希给这位瞌睡得要命的官员头下垫个了枕头。瞌睡来了寻枕头,他的处心积虑的行动变成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低俗而下流,不具有文学的价值,更是与崇高伟大沾不上边。解析这部作品,可以看出昆德拉是个缺乏结构能力的作家,他找不到也创造不出人类情感的大结构,这样他的小说也就像他这部小说的名称一样,落到了一个玩笑的下场。假如把后一个玩笑整个儿删掉,这部小说的力量感会大幅度增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世上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可它宛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中的主角麦克白的台词一样,“它只是幻影而已”,没有实体。按照我的小说新理论“人类情感的新结构”标准,这部作品显然只是重复了一些人类情感的旧结构,除了其中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人物的压迫与残害有其杰出的意义外,它在主体性上存在致命的缺陷。社会政治对于人的压迫与残害,这样的有意义的作品,一个纪实性作家也能够完成,他只要如实把人物受压迫与残害的经历写出来,这就是一部纪实性杰作。像苏联时期的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还有中国的杨显惠对于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里右派们如草一样饿死的采访记录,这样的文献所具有的不朽价值不容抹杀。护士特蕾莎对于外科医生托马斯的爱情,她由边远小镇来到首都住在单身汉托马斯的家里,以及托马斯的情人女画家萨宾娜对于性的不倦追求——这些情感故事的背景是大专制帝国对于小国捷克的占领,知识分子纷纷流亡国外,托马斯因为一篇不同声音的小文章而被剥夺继续拿手术刀在医院工作的权利,他与特蕾莎到了边远的乡村种地度日。他们开卡车去参加一个乡村舞会,深夜回来的路上,车翻人亡。卡车被监视托马斯的新政权暗探做了手脚。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是巨大的,也许这就是它如此走红、如此有市场的原因。它的确安慰了我们不安的心灵。我对它不满意的是,托马斯与特蕾莎、还有萨宾娜这样的人物之间的情感结构没有突破人类已有的旧结构框架,在情感主体构架上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贡献。我这样批评这部小说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假如把特蕾莎、萨宾娜这样的女性人物去掉,把小说中的情爱情色元素剔除,只把外科医生托马斯这样一个人物留下,事情或者说事件还是原来的事件,他在苏联大军占领捷克之后,因为一篇异见文章而被情报机构盯上,失去了操手术刀的权力,被撵出了他工作的医院,只好到他以前给看过病的一个乡村大叔那儿种地谋生。即使到了这样的偏僻山区,情报部门的“沙威”也没有放过他,把他开的卡车的车闸做了手脚,以貌似偶尔车祸的方式把他除掉——这样一部小说同样具有巨大的震撼性,对社会专权的控诉同样强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添加特蕾莎与萨宾娜这样的女性人物呢?是为了调味吗?添加一些好看的颜色吗?昆德拉没有创造出情感的悲剧,只是创作了一部社会悲剧,情感人物成了可有可无的调料品。他也没有创造出情感的崇高形式与结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对珂赛特那样的伟大情感结构。
这位捷克裔的法国作家的其他作品还有很多,我就没有必要一一在这里分析了。还有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我侍候英国国王的日子》,我读了之后没有感觉,也就不胡说八道了。还有个叫塞弗尔特的诗人,1984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漓江出版社出过一本叫《紫罗兰》的诗集,我很早就读过,但是今天我几乎把他忘了。好了,捷克文学这一页就翻过去吧。
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是我惦记多年的伟大作品,它是文学中的诗歌,我没有能力像批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那样得心应手。波兰这个不幸多难的民族,长期遭受沙俄欺压,十九世纪的《先人祭》的创作背景与后来的昆德拉的作品的背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与昆德拉的小说相比,我更看重密茨凯维奇的鬼魂幻象的想象力。他无疑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中多方借鉴,把古典文学的经典元素注入到自己民族的幻想结构中,把一个民族的呻吟变成伟大的诗歌绝唱。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也是一个诗歌天才,他紧紧地咬住政治压迫不放,在他的作品中政治意识转化成了他的天才。一个作家如何把个人所受到的压迫残害转化为整个民族的心灵反抗的合唱,这与一个诗人的天赋关系重大。显克微支也是一个诺奖得主,有人把他的《灯塔看守人》喜爱得不得了,认为写出了什么爱国,可我并不看好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过于通俗化了,司各特与大仲马应该是他的导师。保加利亚有个叫帕·维任诺夫的作家,有一个叫《障碍》的中篇小说,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就阅读过,可它却一直没有从我的文学记忆里消失。一位中年音乐家从酒吧深夜回家,当他打开车门时,已经有一个年轻姑娘坐到里面了,她无家可归,在她的请求下,他只好把她带回了他的单身汉套房里。她似乎不是生存在现世的人,她的超然物外使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肉体的接触,他也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吸引住他的是姑娘的精神世界。姑娘说她常常在星空飞翔,她劝他与她一起飞翔。他与姑娘来到高楼的顶上,练习如何飞向星空。他试了几次,承认自己天生愚钝,无法找到遨游星空的感觉。中年音乐家因为公务外出,他把那姑娘留在他的家里,当他回家时,姑娘已经坠楼死亡。难以理解的是,那姑娘坠落的地点远远地离开了楼房,是在一片空地上。显然在星空与中年音乐家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有了这样的致命障碍,他也就不可能进入那姑娘的世界。假如剥开作家虚构加工的外壳,探寻原本的现实,可能会解析出这样的故事:一个中年人与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之间有了爱情,但是中年人没有勇气跟年轻姑娘迈向爱的星空,姑娘自杀了,留给中年作曲家的是无尽的痛悔。帕·维任诺夫把这样一个平常俗气的现实主义素材提升到了幻想文学的浪漫境界,把现实扩展到了梦幻里,冲出了地球,飞翔在星空……
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的《黑信封》,是一个恒久的黑色梦呓。主人公托莱亚的全称是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马内阿一会儿用多米尼克,一会儿用万恰,一会儿用阿纳托尔,一会儿用沃伊诺夫,频率用得最多的是托莱亚,五个名字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阅读者一不小心,就会当作好几个人,那样的话,一下子便乱了套,肯定就读成了一锅粥。这算是阅读障碍之一。阅读障碍最大的是小说里的隐喻和梦呓,迷乱的梦呓是黑色的,混沌的,足以使稍有不慎的读者触礁沉船。虚写与实写的手法并用。虚写的部分存在于实写部分人物的对话里,就是说有一些人物只活动在主要人物的话语中,对话存在,他们才有生存的环境和权利,对话消失,他们也就消失了,他们是一群漂浮在小说实写人物想象和对话世界里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次要的、无关紧要的人物,他们在小说里所起到的作用、所包含的内容甚至于重于实写人物,在他们身上所负载的象征、隐喻意义,几乎成了小说的核心。虚写人物有亚努利和他的夫人埃米利亚,有托莱亚的父亲老马尔恰,还有具有重要作用的摄影师塔维——他们都活在托莱亚的意识里,抑或梦幻,抑或想象,抑或与其他人物的谈话里。马尔恰家的毁灭,预示了一个邪恶时代的繁荣。老马尔恰的死亡是这个家族毁灭的关键,而导致老马尔恰死亡的罪魁祸首是始终没有出场的摄影师塔维。他是专制社会的特务机关“聋哑人协会”的骨干人物,托莱亚对他的寻找历尽千难万险,依然没有结果。这个摄影师塔维的名字也在不断变换,他好像与托莱亚的姐夫混合到了一起。托莱亚终于侦察到了他曾经居住的楼房,他去了近千次,那里一直没有人出现,最后出现的是个他把她叫作韦内罗的女人。这位女人与一条狗居住在这套房子里。这里对于狗的描述充满了暗喻。马内阿虽然没有明写,但我感到那狗可能就是摄影师塔维的化身,他变成了狗但仍像人一样与韦内罗同居一室,韦内罗把它当男人一样对待,托莱亚离开房间,在黑暗的楼梯上,听到人与狗相拥的声息……
托莱亚幻觉中的那群鬼魂是小说前后贯穿的重要象征。鬼魂们总是出现在污水河边的山坡上,托莱亚来到它们中间,辨认不出自己的父亲老马尔恰。“他从打头的人手里接过火炬,谁也没有看见他,但他可以看见自己。他微笑着接过火把。他吹了口气,病人头发凌乱的脑袋瞬间消失了。多米尼克先生微笑着走向下一个—— 一个憔悴的红发农民。他也把那人的脸吹灭了。就这样,他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都扑灭:蜡烛和脸庞,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世界异化成专制下的鬼魂炼狱,托莱亚被“聋哑人协会”的特务发展的线人——房东太太告发,赤身裸体地被拘入精神病院,走向了马尔恰家族的最后灭亡。
这实在是一部向读者理解力极限进行挑战的小说,我认为我只读懂了它的百分之八十,不懂的百分之二十还有待进一步的阅读。
已经不存在的南斯拉夫有个叫安德里奇的,他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中对于酷刑——桩刑的描写,能够使阅读的心滴出血来。我相信这里的酷刑描述一定影响了莫言的《檀香刑》。我觉得他最值得研读的是大约有五万字篇幅的《万恶的庭院》。老苏丹去世,大儿子巴耶塞特和二儿子杰姆争夺继承权,杰姆战败后逃往罗得岛上的天主教约翰骑士团,被以接待苏丹的规格盛宴款待,实际上是被控制做了囚徒,失去了自由——这段历史是一个叫恰米尔的年轻学者讲述给狱中难友哈伊姆的,哈伊姆把他听来的故事讲述给了另外一个狱中难友年老的塔罗修士,同时讲述了年轻学者恰米尔因为喜好研究历史而被省长关进监狱的故事。恰米尔所讲述的兄弟争夺权位的历史与他自己所属时代的现实惊人相似:当朝苏丹有一个兄弟被宣布为白痴遭到终身监禁。恰米尔在监狱里被狱官打死。年老的塔罗修士把从哈伊姆处听来的上面的恰米尔讲述的故事和他本人的故事在他临终前讲述给了狱中的一个年轻的教士。他本人的故事是他自己如何进了这所监狱——万恶的庭院的。我觉得这种层层讲述的金字塔形结构是对小说手法的一大贡献。这种方法也未必就是安德里奇所首创独创,但我确实是从他的这部小说里看到这种手法的。这种层层转述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一致的。我们听一个人讲了一个事情,他讲的事情是他听来的,而讲给他的讲述者也是从另外一个讲述者那儿听来的……这样推演下去,将至无穷。在安德里奇这里,每一个转述者自己本身也有悲剧,他们都在万恶的庭院里,都有不幸的历史,每增加一个转述者就会增加这个转述者本人的故事,这个由尖顶往下建造的金字塔就会扩大一级,没完没了地扩大下去的话,这座金字塔将会变得无限大,这种膨胀本身就是对于万恶的庭院的罪恶的象征化处理,黑暗变得没有边际……
作者简介:寇挥,男,陕西淳化人。西安医学院驻校作家。长篇小说《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北京传说》分别获得首届柳青文学奖新人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马车》获陕西省首届年度文学奖。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出版有小说选《灵魂自述》(新势力丛书)。著有《日晷》《朝代》《虎日》《大记忆》《枯泉山地》《血墨》等長篇小说。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近百篇。中篇小说《长翅膀的无腿士兵》入选《1999年最佳中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黑夜孤魂》入选《21世纪小说选2002年短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