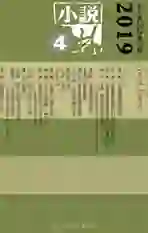苏童来了
2019-08-13陈鹏
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
——《圣经·诗篇·119-58》
A
2019年6月,天气暴热,昆明户外气温三十三度,所谓春城的名头就像个玩笑。我顶着滚滚热浪搬了家——从嘈杂的某小区向郊区撤退。虽出行不便,好歹有利于写作。是的,我是个作家,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得过一些小奖。一眨眼四十出头了,还没写出数十万言的巨著,但我坚信我能写出一部巨著。不信咱们走着瞧。五十之前我还这么浑浑噩噩干脆上吊算了。
我是整理旧报刊的时候发现它的:一只牛皮纸信封里塞了三封信,信纸泛黄,红色的“昆明市粮食局”抬头,纸张焦脆;还好,字迹娟秀工整,信尾落款是“郭婳婳”。记忆开始翻腾。我记得她,郭婳婳,当然记得。
我在乱糟糟的客厅里坐下来,抽出信,展开——
杜上君:
你好!
在文林街卡夫卡书吧一晤,分别已有月余,甚念!这样的文学活动,在昆明,不是太多,是太少了!真希望今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可我至今还不清楚,这次活动,是哪个部门、哪个杂志发起的?是某个大学的文学小组?还是你的朋友和熟人?虽然参与的人很少,大概不到二十人吧,可都是纯粹的文学爱好者,大家对文学的狂热全写在脸上。能参与这样的活动,我实在幸运,更幸运的是,能在现场遇见你。
我怎么进来的?哈哈,说了你可能不信,我就是路过卡夫卡书吧,看到你们举办活动,看到台上有人侃侃而谈,就溜进来了,有人告诉我活动内容,我既兴奋又紧张。我悄悄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听你们轮番上台朗读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原、余华和苏童的小说,听你们对这些作品展开激烈讨论;你争得面红耳赤,不时哈哈大笑,使劲儿喝酒。
从你们嘴里冒出来的文学名词我从没听说过,什么零度叙事,元叙事,反故事,叙事圈套,达达主义,自动写作……我惊讶极啦!我不是一个文学盲,从前还是读过一点勃朗特、司汤达、海明威、卡夫卡小说的(嗯,卡夫卡读不太懂)。中国作家,我读过苏童的,他写旧时代女性的小说挺好读也挺精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作家。至于马原,余华,还真没读过。
更让我吃惊的是,最后登场的你把大家吓着了。你说中国先锋小说基本是模仿的,因此,价值不大。你的话立刻遭到众人的攻击。可你说,马原的小说是博尔赫斯和海明威的混合体,余华小说有强烈的新小说气味;至于苏童,叙事是从塞林格那兒来的,故事则是张爱玲甚至张恨水的……你引起了公愤,一个明显喝多了的高个子家伙和你吵起来,其他人也嚷嚷着要把你轰下去。他们岂能容忍一个忽然冒出来的小子胆敢诋毁伟大的中国先锋派?不过,我能看出来,他们心里多多少少知道,先锋派们的来源和你说的大致相同;可是,他们强调了先锋写作的意义,说崭新的文学时代(80年代)呼唤着新的文学样式,俄国现实主义落后了,不能反映复杂的人性和多变的生活了,先锋派应运而生,他们带给中国文学的,绝非技巧那么简单。可你坚持说,如果技术和观念都不是国产的,它就很难长成参天大树……你们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高个子说,请你报上名来!你不慌不忙地说,鄙人姓杜,杜上,上下的上(我记得台下响起一阵哄笑),今年大二,也写小说——而且是先锋小说。你最后这句话忽然把大家镇住了,整个书吧出现短暂的沉默。一只啤酒瓶当啷摔在地上。你大步走下来,回到座位上。
你的座位,离我不到三米。你肯定没注意我。我默默坐在角落里,默默喝下一杯早就凉透了的黑咖啡。
后来我才从一个组织者那里,打听到你市内和省外的通信地址。我没料到,你是在武汉上大学呢,而且,是那么一所和文学压根扯不上关系的大学(体院,对吧?)!佩服啊!
我也不知道干吗要给你写这封信。我无法解释内心的冲动。我记得你们在活动结束时宣布,下月中旬,也就是8月15号,要举办一个苏童与昆明读者的见面会,希望大家多多宣传,都来参加。
我激动坏了——你们谈论的先锋作家,我唯一熟悉的就是苏童。著名的苏童就要来昆明啦!岂能错过?
而你,杜上君,恕我冒昧,我对你印象深刻。如果你收到此信(市内通常一天,顶多两天就能送到),能否请你大后天,也就是20日下午三点来我家小坐呢?地址是:昆都三合营瓦仓巷105号院,701室。我想沏一壶好茶,听你继续聊一聊先锋文学,好吗?
期待并感谢!
婳婳,1995年,7月17日
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前我心高气傲,对一批牛逼作家全不放在眼里,以为若干年后也能写出比他们还牛逼的小说。二十三年后我终于发现,写作太难了,干这行赌咒发誓一概没用。按我的昆明同行于坚的话说,你必须是天才,必须是才华出众的天才,还必须是勤奋的天才。好吧,具备以上条件还远远不够,你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好得不能再好的狗屎运。我,四十岁的杜上,能占几条?
总得试试。
我现在的职业是保险推销员。混到这把年纪也就勉强活着。不,我哪敢模仿伟大的卡夫卡?他白天卖保险晚上写小说,我奔波一天累个半死,最多周末动动笔。数十万言的扛鼎大作必须等我辞职才可动手。嗯,三年后吧,最多三年,我一定辞职。我说话算话。
其实90年代中后期,先锋派已经式微。苏童余华格非转向,马原,伟大的马原搁笔,洪峰销声匿迹。那时候“新写实”一夜爆红,他们那点鸡零狗碎比先锋派们差远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经常自我怀疑(虽然我还年轻):连马原都不写啦,杜上啊杜上,你还写个什么劲儿啊!
B
嗯,收到这封信应该是1995年7月18日下午。我激动得两手发抖——它显然来自一名文学女青年。16日当天的活动气氛热烈,我哪记得身后三米坐着何方圣神。是气质出众的美女?还是留短发、干净清纯的女大学生?在我想象中,她偏向前者:长头发,鹅蛋脸,文静内向,带着某种苏童小说人物的病态美。究竟什么力量让她提笔给一个陌生男孩写信?她哪来的勇气写信?她看上我了?以文学的名义看上我了?看上一个写小说的毛头大学生?我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浑浑噩噩熬过三十六小时,信上约定的20号终于来了,我骑上车,直奔三合营。1995年的昆明夏天哪有现在这么热,街边的法国梧桐绿得像火,金色老房子底层的小店铺、小酒吧塞满客人;鸽群疾飞,阳光撒在亮闪闪的柏油路面上,穿裙子的姑娘一个比一个优雅,微风中有各种香味:玫瑰花香,豆花米线的浓香,香粉和啤酒混淆的暗香,让人迷醉。
我没费多少气力就找到瓦仓巷105号院,绿漆的大铁门一推就开。我推车进去,迎面是宽敞的水泥院子,对面一幢灰色筒子楼,一把生铁焊接的楼梯由侧面向上,我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上七楼,沿长长的过道往里,701在最底端,门前阳台上种着茑萝,几朵三角梅迎风怒放,藤蔓几乎垂到六楼。门是普通红木门,剥落的漆皮像刀子划出来的。有人在屋内应声,快步走过来。门开了,一张与我想象吻合又似乎截然相反的脸出现在门后——瓜子脸,戴一副眼镜,脸上有不少雀斑;个头很高,很瘦,扎马尾辫,笑容极其苍白,给人莫名的焦虑感。
“杜上!快请进!”
C
杜上君:
你好!
你走了。你在我家里谈了两个小时的先锋文学。我不是得到了很多,而是失去了很多……天啊,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此时的感受。语言多么无能啊!
你走后,我收拾了茶杯,擦了桌子,打开门,望着门外的茑萝,望着蓝天。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向下眺望,似乎为了确定你有没有走远。我明明知道你早就走啦。你大概已经去往这个城市的尽头了,去往我无法想象的某条小巷,登上某幢相似的楼房……是的,我努力回忆你的样子。回忆自己哪句话说对了还是说错了。楼道空荡荡的。我回到屋里,找出苏童的小说,接连看了《井中男孩》《仪式的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而你,早就读过了。我真想知道,我读的,和你读到的,是一样的吗?是同一个苏童吗?我的目光从一行行文字上越过,说实话,我真不觉得我读到的比你告诉我的更多。或者,我对中国先锋派的理解,无法和你们这些小说家相提并论?
后来,光线渐渐暗下去。妈妈还没回来。他(你知道的)又走了,说有朋友请吃饭。家里就剩下我。我多么享受这一刻的孤独寂静啊,所以我没开灯,让昏暗淹没小小的房间。现在,此刻,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迫切地想捕捉你的气息……哦,请原谅。今天跟你聊了那么多,希望你明白,我不单单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女人,更是一个绝望的期待谁能拯救我的女人呀。是的,我是个女人。早就是个女人。你会厌弃我、恨我吗?可我多么希望再次见到你,再次聆听你滔滔不绝的讲述啊……你说,文学能让人得救吗?能吗?我不知道今天的见面,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我是不是太自我了?我是吗?……天呐,活着多痛苦啊!
真诚向你道歉!也期待你尽快回信。好吗?
婳婳,即日,黄昏。
另:苏童的见面会,是下月几号?礼拜几?能告诉我准确地址吗?谢谢!
D
1995年的7月20日早已模糊,我连郭婳婳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哪还记得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过,为了完成这个小说我必须强打精神,尽可能打捞细节。所有的细节。哪怕,细节早就扭曲变形了。换句话说,二十三年后的今天,身为小说家的我不敢保证我的叙述(记忆)百分之百靠谱。虚构从来是我们的天职。不是吗?
我们接着讲。郭家两室两厅,上世纪70年代的老房子,客厅有简简单单的弹簧沙发,圆桌,18吋国产电视机;桌上铺着带蓝树叶图案的白棉布;上面搁着青花瓷的茶壶茶杯。她拎起茶壶进了厨房,将暖壶里的开水倒进去,然后拎着茶壶回来,将茶杯斟满。我突然发现,她的手在发抖。水花溅出来,茶水也漫出来,白棉布洇了一大块。她赶紧找來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向我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笨手笨脚的,真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慢点,别烫着。
她偷偷打量我。镜片后的眼睛很漂亮。典型的丹凤眼。茶几上有两盘水果:橘子和柚子,都剥好了,放得整整齐齐;另一个盘子里有瓜子。她抓起一把,塞我手上:“吃啊,你吃。”又用牙签扎起橘子递给我。我一口吃了,嗑起瓜子,故意把瓜子皮吐在干干净净的水泥地板上。这样一来,气氛不那么紧张了。她笑了,也抓起瓜子,小心嗑开,取出瓜子仁,送进嘴里。
“你喜欢苏童?”我直奔主题。
“是啊,”她说,“他的小说好读些。不像别人的那么晦涩。”
“《妻妾成群》多棒啊,还有《红粉》,还有一批精致的短篇……”
“忘了告诉你,这是粮食局的房子。对,昆明粮食局。”她忽然说。
“哦……”
我有点跟不上趟。
“是我爸单位。对了,粮食局出过一个作家,写诗的。邹昆凌,听说过吗?”
“没有。”
“他在粮食局的名气太大啦。”
“我跟诗人不太熟。”
“哦,哦。”她低头看着地板。
“你也写东西?”
“……偶尔写。”她满脸通红,“你不觉得,不觉得这地方光线太强?拉起窗帘呢又太暗。很难写东西啊……”
“光线暗的话,可以开灯啊。”
“你写什么?”她明知故问。
“小说。”
“哇,天呐!”她苍白的脸上涌出红潮,“你想成为苏童?”
“想,当然想。但我更想成为马原。”
“我,我还真没好好读过马原的小说。”
我向她普及写小说的汉人马原,显然把她镇住了。聊起文学我向来滔滔不绝。我告诉她,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让他成了先锋派的带头大哥,什么苏童啦余华啦格非啦都是他的追随者,也就是俗话说的小兄弟……她出神地望着我,目光闪亮。我渐渐发现什么叙事圈套、元叙事对她来说完全对牛弹琴。我打住了,低头喝茶。她不停为我续满。她不再嗑瓜子,也不吃水果,忽然说:“你有信仰吗?”
我愣了。
“没有。暂时,还没有。”
“你有。当然有!”她很激动。
“你的意思是,文学?”
她抬起头。居然哭啦。我吓坏了。你可以想见一个二十岁小伙突然面对一个身份、年龄都相当可疑的女人的哭泣时能吓成什么样。
“对不起,对不起。杜上,对不起。”她说。“我,我想起一些事情。我自己的事情。实在对不起。和你没关系。和文学也没关系。你千万别误会。”
我找到纸巾递给她。她把眼镜抬高,背对我擦掉眼泪,又转回来,一声长叹——
“对不起。”
“不不不,没什么对不起的。不用对不起。”
“我——”她说不下去了。
“能说说吗?”我轻声说。
E
实在太热了。昆明竟然像我大学时代的武汉一样热得要命。
新家一片狼藉。装书的箱子满地都是。旧家具胡乱堆着,装修留下的臭气铺天盖地。我打开窗户,让屋里通风。暴烈的阳光扑下来,让人猝不及防。我进厨房喝了杯水,再凑到水龙头下冲了冲脑袋。总算凉快些了。我深呼吸,擦干自己,返回客厅,坐下,把刚才读过的信又读一遍。
郭婳婳。
这名字多怪啊。
我居然想出这么个名字——哦不,是信纸上的名字。它要是不在发黄的纸上出现,我早忘了。忘了那段经历,忘了那个女人。是啊,女人。她到底多大?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二?拿不准。对于女人的年龄我永远拿不准。我急于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我这小说,又该往哪写?
F
嗯,她没接我的茬儿。长长的沉默让气氛比最初的时候更紧张。我突然想起乔治·西默农的《玻璃笼子》。眼下,这个家,真像玻璃笼子。
我考虑是否该起身告辞,她说话了:“你今年,二十?”
“是。二十零五个月。你呢?”
“二十六咯。”
“看不出来,你比我大六岁。”
“乱讲,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女人过了二十,大一岁就显一岁。你看我,那么多皱纹。”
她摘下眼镜,按按眼角。我似乎看到皱纹了,又几乎什么也没看清。
“你是不是,觉得我烦?”
“哪里。”我喝一口茶。没来由的紧张。真想告辞了。天知道一个苗条的、略有姿色的女子为何让我紧张成这样。说真的,你要仔细打量会发现她长得不错,那些褐色的小雀斑瑕不掩瑜,对吹弹即破的雪白皮肤不构成任何威胁。而且她个头很高,目测不低于一米六八。三围挺棒的,你一眼就能瞧出来。她今天穿一条蓝底白花长裙,裙摆像孔雀开屏般散开;圆领,领口偏低,我的视线不时溜达过去,溜达出来——见鬼!我是因为这个紧张吗?以我二十岁的年纪,和一个大我几岁的陌生女子同处一室真不是闹着玩的。我还没那方面经验,所有知识不过是从海明威福克纳劳伦斯们那里偷来的二手货。说白了,我就是个不谙世事不懂女人的愣头青,课余写点没处发表的小说,而已。
“你看,你说得挺勉强呐。我知道,给你写信,约你见面,好像,好像太不应该啦——”
“别这么说。谢谢你给我写信。咱们聊聊马原苏童不挺好的?”
“你吃呀,吃。”她又递来一块柚子,我接过去,一口吞下。“我哭是因为……”她使劲摇头,目光闪躲,“是因为,我很久没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刚才,忽然就——”
我没吭声。
“给你看样东西吧?”不待我回答,她起身走向卧室。一阵窸窸窣窣地翻找,她抱出一本大大的黑色相册,走回来,将椅子挪向我,打开它。
上面有她单人照,也有三人的全家福。母亲年轻,秀美,鹅蛋脸,父亲头发很少,穿中山装,板着脸。当然还有父母的合影,父親不苟言笑,和母亲保持适当距离。典型的70年代照片,我家里也有类似照片和相册。她告诉我,父亲挺严肃对吧,其实呢,再也没人比他更随和更单纯啦;父亲非常爱母亲,自然也非常爱她,每个星期天带她去翠湖公园,给她买糖葫芦、巧克力,还给她讲故事。她后来喜欢文学,一定和父亲经常给她讲故事有关。她爱父亲,远甚母亲。
“但是,后来——”
我不敢吱声。
“后来,1983年7月,父亲去版纳出差,再没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的意思是?”
她低下头。
我飞快计算1983年她几岁。十四,没错。整整十二年前。她把相册交给我。它很沉,像一块石板。我继续翻看,后面全是她的照片和母亲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她的长相渐渐发生变化:穿长裙、留短发的丑小鸭出落得高挑秀气,五官越来越像父亲。奇怪的是,她和母亲不再合影。翻过三分之二,相册空了。再没照片了,全是黑魆魆的相纸。
“是自杀。”她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我的心怦怦跳。
“你这辈子,还没碰上谁自杀吧?”她说。
“……我大伯父,也就是我爸的大哥,1973年……”
“我的意思是,你经历过?”
“那倒没有。他自杀第二年,我才生呢。”
“我父亲是好人。天下第一好的好人。一辈子没干过半点出格的事情。”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越来越紧张。手心一个劲儿冒汗。
她看看我,眼中泪光闪烁:“我给你讲讲他吧,杜上。十二年啦。我该找人讲讲他啦。我想讲讲他,好吗?”
“好的,好的,你讲,我听着。”
十二年前,她的父亲和四个同事去版纳出差。一共四男一女。四个男人都成家了。女的还小,中专刚毕业,才二十岁,和我年纪一样。他们下榻当时的地委招待所,四个男人一共两间房,姑娘单独一间,在走廊尽头。当年的招待所共用厕所和浴室。是当天夜里出的事。
我莫名紧张。她喝一口茶,停下来,擦掉泪痕,眯着眼睛望向阳台。渐变的光线划过她苍白泛红的脸。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很快消失了。
当天夜里,四个男人分别上厕所,洗澡。版纳本来就热,夏天更是热得要命。那个姑娘迟迟没去隔壁女浴室。后来,几个男人,当然包括她父亲都一致认为姑娘洗过了,或者说,在他们轮流洗了澡的时候她也及时去洗了。这很正常。没什么不正常。那时候的版纳招待所还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呼呼吹一夜还是热的。父亲半夜热醒,浑身冒汗,想再冲个凉,于是轻手轻脚拿了毛巾肥皂去了男浴室。他洗完出来,发现隔壁女浴室有人。
她又停下来,问我,“你去过版纳吗?”
“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我这辈子也不会去。永远不去。”
我没说话。
“嗯,他发现,那个姑娘就在女浴室。”
“他怎么知道是她?”
我手心湿透了。
“还能有谁?”她说,“两隔壁。男女浴室,就在两隔壁。那种破招待所啊。再说,版纳傣族好像对这些东西不是太在意。”
“在意什么?”
“门,挨得太紧了。他出来的时候,女浴室的门是半掩的。我觉得,他一眼就看见女同事了,赤身裸体站在喷头下面。他看见了。当然是无意的。但他的确看见了一个二十岁大姑娘的裸体。”
我抓起杯子,又放下。
她的手也伸向杯子,中途停住了。她闭上眼睛,泪水扑簌簌掉下来。我赶紧抓起纸巾递给她。她接过去,捂着脸,捂得严严实实。我说不出一个字。
她过了很久才说:“当天晚上,我父亲就用皮带,他自己的皮带,把自己挂在男浴室的房梁上。第二天一早被同事發现……”
“天呐。”
她深深叹气,鼻尖因为哭泣而发红。
“父亲自杀前,给我母亲单位打过电话,值班室老头接的。他让转告母亲,他说,他看了不该看的。”
“可是,如果他不说,谁会知道?”
“女浴室就在男浴室后面。”她答非所问。“他不该往后走那两步。就两步。”
我无法说话。
“他看了。姑娘也知道他看了。”
“姑娘发现了?”
“发现了。”
“可是——”
“父亲死了,姑娘哭得稀里哗啦,向三个男同事说了原委。”
“后来呢?”
我无法想象这故事。我才二十啊。
G
杜上君:
你好!
请原谅我的粗心,我想确认一下,苏童见面会是下月15号,对吗?我最近睡眠很差,经常忘事。你明明说了好几遍我还是怕忘掉。哎,害怕忘掉反而容易忘掉。我经常忘了钥匙放在哪里。明明放好了的,就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怎么还是找不到呢?你说,这是不是未老先衰?
我一直记得你来我家的下午,记得你拘束羞怯的样子。只有聊起文学,你和那个卡夫卡书吧里滔滔不绝的年轻人才是同一个人——哦,请原谅,我称你年轻人,似乎我很老似的。抱歉啊,我总觉得自己比同龄人更老,经历更多。其实,我还没到三十呢。我不知道,是我的心态老了,还是这世上的事情,也就这样了。
嗯,你挺帅的,一定有不少女孩喜欢你吧?这么说太直接了。请原谅。可我至今不敢相信,你就那么来了,又那么走了……
苏童的见面会我一定要去。就算为了见你一面,也要去。
这两天我读了苏童的一批小说,他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的枫杨树系列写得真好,不过,我还是喜欢他写旧社会女性的小说。他很懂女人,那么细腻,那么温暖,他好像深深爱着他笔下的女人,你觉得呢?真想见见他。照片上的他挺帅的。从他身上,也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强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好像你们都愿为它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否则就白白爱它了,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作家了。你们的信仰就是文学。你们被文学改变,也愿意为文学付出一切,对吧?
真想当面问问你,文学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什么时候,能拜读你的小说?
那天,我跟你说的事情,你后来遭遇的那个人——你当然知道他是谁——请务必保密,好吗?算我恳求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郑重地恳求你!杜上君,我听到敲门声了。我知道,是你。你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呐。那天之后,我多么恐惧啊。我担心你太年轻,只会以猎奇的目光打量我并且用小说家的夸张将它传扬出去;我也担心,对你说了这么多会不会适得其反,让你鄙视我,厌恶我,以我的经历作为羞辱我的证据再把它变成小说?我真担心呐。恳求你,再一次恳求你,千万替我保密,好吗?
多可怕的敲门声。当时,我觉得,天都塌了。
我本就卑微,请别再将我那一点点尊严踩在脚下,好吗?
谢谢你!
苏童的活动现场再见吧。给我回信时,请务必写清楚时间、地点。拜托了。
迫切等待你的回信!
婳婳,7月21日。
H
我得去一趟三合营。
忽然觉得这些信,这个人充满疑点。它真的发生过?信千真万确。郭婳婳也千真万确。到底哪不对劲?
我从书堆里找到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集,趟过横七竖八的家具、箱子下楼开车,直奔大约二十公里外的三合营。我知道那地方,就在艺术剧院对面,从前的娱乐中心昆都背后,七八条巷子纵横交错,其中间地带俗称三合营。凡老昆明都一清二楚。
真热!我浑身冒汗,车停瓦仓巷口,大步走向105号院。绿铁皮大门半敞着,记忆中的院子和院子里的7层筒子楼却不翼而飞了——什么时候挖的?眼前只有一个巨大的深坑,四周土堆高耸;一座半拉子钢筋水泥的混合物支棱着。是从前的筒子楼,刚拆一半。
我待在门口,抽了一支烟。找到附近的小卖店主和树下纳凉的老头。没人听说什么郭婳婳。整整二十年啦。我买了一根方砖冰棍,牌子都是新的,味道也不对。我问店家,这里要盖什么,他说,还能盖什么?我往回走,把吃了一半的冰棍扔掉。回到车上,我那本《绝杀》就躺在副驾位置。我转头,105号院热浪翻腾。我明明知道答案。明明知道。我想干嘛?我重新下车,走向小卖店,将《绝杀》撂在脏兮兮的玻璃柜台上,几只绿头苍蝇嗡地飞起,声音大得吓人。
“送你。”我说。
老板吓一跳。“书?哪样书?”
“自己看。”
“讲哪样的?哪个写的?”这家伙低头哗哗翻动。
我一声不吭。
“杀人的?偷情的?还是计划生育的?咋没插图?……真的送我?不要钱?我靠,不是黄色小说坚决不看啊……”
我回到车上。这时候,时隔二十年之后,我终于感到疼了。胸口刀扎般的疼。且喘不上气。像浑身流汗流血的溺水者。我唾弃自己。要是上帝愿意惩罚,就惩罚我吧。用荆棘抽我石头打我,让人群冲我吐口水用最狠的脏话骂我诅咒我唾弃我我竟然大言不惭到处兜售自己是个作家,一个严肃的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
我流泪满面。
I
当年,我没回信。一个字也没回。
因为无法厘清几大疑点:1,如果她爸真死了,她怎么知道细节的?他同事告诉她的?作为父亲的同事,怎么可能事无巨细全告诉她?2,那个姑娘既然被偷看了,也知道自己被偷看了,那么,面对老同事的尸体,她怎么可能对其余同事一一道来?3,最关键的一点,她父亲的死,真是因为无意偷看了年轻女同事的裸体而“悔罪”自尽?说不通啊。除非姑娘大声嚷嚷起来,告他强奸之类,才可能逼死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否则,谁会因为无意的犯错就立即寻死?犯错,注意,不是犯罪。
郭婳婳撒了谎?或者,谁撒了谎?
又为什么对我撒谎?就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
二十三年前的杜上,即年方二十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J
“谢谢啊,谢谢你听我讲了这些。”
“别客气。”
“你为什么写小说?”
“不好说。就像,你喜欢某个人,你讲不清楚为什么喜欢。”
“嗯。”
“你没读过博尔赫斯?”
“读过,读不太懂。”
“博尔赫斯多棒啊。”
“是吗?”
她眼神游弋,嘴角挤出微笑。
“格非,写《褐色鸟群》的格非,是博尔赫斯最好的学生。”
“是吗?”
“是。”
沉默。气氛糟透了。我累了。说得够多了,也听得够多了。
“至于马原和海明威之间的相似性……还有余华和法国新小说的关系……”
“你每天看书?”
“每天都看。”
“什么时间写呢?”
“不一定。想写就写。”
“哦……”
她走神了。
“我该走了,都五点啦。”
她有些茫然,随我站起来。“这就走?”
“太晚了,我家挺远的。”
“好吧。那么,苏童的见面会——”
“下个月15号,吴井路昆明电影公司,下午三点。一定来。”
“好的,一定。”她努力笑着。长长的两臂垂下,两手绞在一起,似乎局促而忧伤。我们来到门口,她拽开门,轻声说,
“你家里,有电话吗?”
“有。”
“能给我号码吗?”
“没问题。”
她找来的一只白信封,我把号码写在背面。
她坚持送我下楼。我们大概在二楼遇见他的。此人穿一件皱皱巴巴的白衬衫,一条黑长裤,满头白发,脸色黝暗,像个醉鬼。但某种程度上,特别是那双三角眼里射出的狞厉目光让他更像警察。他站着,微微喘气,上下打量我。
“爸。”她说。
我蒙了。爸?十二年前就自杀了的爸?!
“去哪里?”男人大声说。
“送送他—— 一个朋友。”她满脸通红。
“回去。”
“马上就回——”
“回去!”他像呵斥一条狗。
我赶紧说不用送不用送,又认真说:“伯父好。”
他一声不吭。
我差不多是跑下楼的。郭婳婳没跟出来。我听见他凶狠的呵斥和她急速返回的脚步声。我找到车,开了锁,骑上去。心脏咚咚跳。门前,一个收破烂的家伙一面吆喝“旧衣裳旧家具找来卖”!一面推着载满废品的破单车穿过邃寂的瓦仓巷。我想了想,重新下车,锁好,沿楼道上去。湿漉漉的霉味扎我的脸。茑萝绿得发黑。我凑到门口。里面传来争执、怒斥和打骂,之后是嘤嘤哭声。再之后,我听到的声音已很难描述又昭然若揭,像所有经典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呻唤和哀鸣。我的心跳声大得离谱,长长的走廊也为之震颤。我退回来,摸了摸茑萝,像沙子一般硌手。我转身,不知哪来的胆量,凑上前狠狠敲门。砰砰,砰砰砰砰砰!没等屋内平息,我乒乒乓乓飞奔下楼直奔单车摇摇晃晃跨上去狠命踩动,箭一般射出巷口。直击胸口的憋屈、惊恐和莫名的仇恨让全昆明都暗了下来。
×你妈,我×你妈!
K
我必须告诉你,1995年8月15日,苏童来昆明了。他来了。但我没见到郭婳婳。她真忘了时间和地点?
苏童是三点一刻走入会场的,举手投足像个领袖般沉稳,比我想象的还帅。那场精彩的文学对话结束于我的最后一个提问:如何看待小说中的生与死?你对笔下女性的态度是?我记得苏童是这么回答的:“首先,作家无权决定笔下人物的生与死——不得不说,他们通常是沿着自己的命运走向生或死的。我这么说,不是故作神秘,而是真实的创作体验。至于我对女性的态度嘛……我尽可能理解她们,爱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无奈,更艰难。”
他露齿而笑。帅呆了。
L
半个月后,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告诉我,郭婳婳自杀了。
“胡扯!”我说。
她一言不发。
“怎么就——”我蒙了。
“人都走了,说这些还有卵用?你电话就写在信封上。这封信,你还看吗?”
我说不出话来。
“我早料到了。十年前我就料到了。如果前几天她去参加了什么文学活动,可能就——”她深深叹气。“我发誓我一个字没看。你要看吗?”
“请给我寄过来。有我地址?”
“有。”
“那个文学活动是我朋友组织的。婳婳很想去。她一直盼着。怎么会——”
“你叫她什么?”
我满臉通红。像被狠狠轮了一拳,耳边充满嚣叫。
她又叹口气,“她要是见了你,见了她想见的什么人——”
“是啊,是啊。”
“不说了。”
“你是她——”
对方挂了。长长的蜂鸣。我放下电话。天空白得像一小段僵死的皮。没有任何准备。我将以何种方式、用多长的时间摆脱它?事实上,此后一周我没接到郭婳婳的最后一封也就是第四封来信。大概,它送错了地址。一周后我回到武汉,升入大三。当年我那么年轻,年轻得并不认为这种事情是一个文学青年必须经历的。我选择遗忘。尽可能快地遗忘。此后寒暑假回到昆明,我再没去过瓦仓巷105号院。有时候故意绕道走。我早忘了郭婳婳长什么样了。按照小说家笔法:刻意回避之事也许从未发生。
但我记得女人那句话:如果前几天她去参加了什么见面会,可能就——
如果我回了信呢?哪怕,就一次?
哪有什么“如果”。
是啊,尽管疑点重重,二十三年之后我还是怀着无限悲伤把它写出来了。三封信,三封来自二十三年前的发黄的信就躺在我书柜里,提醒我此事绝非虚构。被我隐去的,只是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名字。
作者简介:陈鹏,当代70后小说家,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