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有力量的一根筋
2019-08-07范小天
范小天
20世纪80年代,全国几百家文学刊物,两年评一次小说奖,中篇获奖篇目20部。1981—1982年第二届,《钟山》一部获奖:王安忆的《流逝》。1983—1984年第三届,《钟山》两部获奖: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张一弓的《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1985—1986年第四届,获奖篇目由原来的20篇减到12篇,《钟山》仍有两部获奖,而且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朱小平的《桑树坪纪事》和周梅森的《军歌》。1987—1988年第五届,获奖篇目由12篇减至8篇,叶兆言的《追月楼》获奖。前一阵著名女作家林白发了一张1988年第一期的《钟山》封面,有她的早期小说《去年冬季在街上》,还有史铁生的《原罪· 宿命》,余华的《河边的错误》,高晓声的《老清阿叔》,王干的《父亲》,莫言的《玫瑰玫瑰香气扑鼻》,陈思和的评论《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话》,陈白尘的《漂泊年年》……这一期《钟山》囊括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XXX和莫言。林白不禁感慨:“给范小天看看这个,当年的《钟山》太厉害了!”

走向1990年代,《钟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顶级作家,都把自己最好的小说给《钟山》。仅长篇小说就有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米》、朱苏进的《醉太平》、刘恒的《逍遥颂》等。每一期《钟山》只能发表20多万字,这么多好小说,都舍不得放掉,我们动脑筋,开了一个栏目“三连星”,连载3部长篇小说。同时开辟了一些别的栏目,比如朱伟主持的,陈晓明、戴锦华、张颐武专门谈电影的“十批判书”;再比如,“钟山看好”,专门推出新人。
有一天,王干带了一个翩翩少年到我办公室,说:“他叫毕飞宇。”少年很有力量的样子,目光里让人感觉到他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人,我的心里咯噔一震,当然,表面上还是我一辈子改不了的既热心热情,又随意的漫不经心的自由任性的样子。毕飞宇给了我一部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小说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当时很多名家的作品,甚至超过了一些名家的代表作。我在这里必须引用一下余华当年给程永新的信:“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高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个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应该是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雨天的棉花糖》如果就这么在《钟山》上发表出来,会引起评论,却不一定能让当时的同龄作家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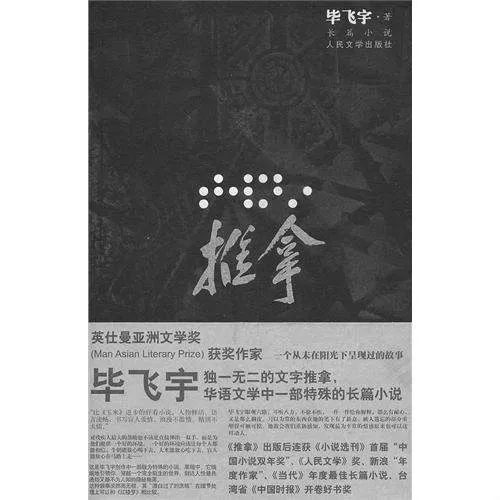
《雨天的棉花糖》在北京一个刊物上发了头条,毕飞宇拿来给我看,我替他高兴,同时还是希望他能“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
毕飞宇曾给我的作品写过一篇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小天的性格差不多集中体现在他的雄辩上。小天的脑子特别灵光,再加上自负,张口闭口的时候自然就多了一份剑气。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平时谈笑中。小天的雄辩时而中路突破,霸王硬上弓,时而一个腾挪,剑走偏锋,给你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听上去很美。当然,你最好不要是当事人。小天的口才带有彪悍的风格,有点类似于徐根宝教练所提倡的‘抢逼围’,场面上是全攻全守的。我很幸运,因为我至今没有领教过。不过我发现,小天的雄辩有一个特点,在他占着十分理的时候,他是理直气壮的,在他占着五分理的时候,他依然是理直气壮的,如果只占了三分理呢?那小天一定是理不直而气壮的。壮着壮着,他的理慢慢地又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和他辩论真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你明明觉得自己是对的,可是你架不住,在听的这一头,反而觉得他倒对了,合情合理,还丝丝入扣的,还苦口婆心的,还语重心长的。气死你。等你犯过想来,小天早已经坐到棋盘的对面了,捏起一颗子,神闲气定地拍在你的星位上;要不就是坐在了写字台上,继续写他的小说。”飞宇说我的小说不像我的辩论,说我的小说反而是“一根筋”的,“热烈,忧伤,愤懑,偏执,认死理,十万个‘为什么’最终都要变成范小天的范式‘为什么’,或者说范小天的范式‘为什么’最终都要变成十万个‘为什么’。”但是他,“喜欢这根筋,这根筋逼着我反躬自问:你怎么会过得这么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你难道从来没有发现你周围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在我眼里,飞宇也是“一根筋”的,他曾经生着病骑着自行车去离家很远的报社工作,他对创作的热爱、执着让我感动。带着这跟筋,他创作了很多作品,他的《祖宗》让我眼睛一亮。“太祖母超越了生命意义静立在时间的远方。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落差流荡在她生命的正面和背面。”冷峻而神秘。近百岁的太祖母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家族对权利的争夺和可悲,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河流几千年的悲怆和无奈。很多很多年以后,毕飞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兄弟我最爽的一次写作是写《祖宗》,晚上上手,天亮竣工。”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心飞翔”。《祖宗》就是毕飞宇的“飞翔”,我感受到他那种铆足了劲写作的姿态和对文字的热爱,这是“有力量的一根筋”。我对毕飞宇说:“你能写出来。”很多年以后,毕飞宇表示他听到这句话,“顿时就觉得曙光在前头,后背上竖起了鸡皮疙瘩,对于一个除了激情就一无所有的文学青年来说,还有哪句话比‘你能写出来’更令人振奋、更令人欢欣鼓舞的呢?”他从这句话中“得到了力量,从而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我决定给毕飞宇上“钟山看好”,同时发4个短篇。我带着“少年”毕飞宇到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费振钟家里,我请费振钟给毕飞宇的小说写评论。费振钟说:“我和飞宇是老乡,太熟了,我就不写了。”费振钟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和评论家,我们和著名编辑顾小虎、我敬重的作家朱苏进、才华横溢的评论家王干是一个围棋队的,几乎天天在围棋盘上厮杀征战。我和费振钟是非常好的朋友,没想到我竟然碰了钉子。那些年,我很少碰这样的钉子。在我的记忆里,我是很尊重费振钟的,我们都称30多岁的费振钟为“费老”。十多年以后,毕飞宇告诉我,我当时说了一句话:“你不写,以后会后悔的。”现在想来,我这句话蛮LOW的。一个好的评论家,并不一定要写每一个朋友或者每一个优秀作家的评论,更不需要通过写新人的评论来证明自己是伯乐,眼光怎么怎么好。从另一角度说,我当时自信明显不够,想通过“发现青年俊英”来证明自己。我今天能这么想,看来我在岁月流逝中慢慢成长了。哈哈,哈哈。
后来,我又带毕飞宇去了我们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著名评论家黄毓璜家里,黄毓璜很相信我,一口就答应了。我认为,毕飞宇骨子里是现实主义作家,在尝试其他手法之后,再回去写现实主义作品,也许会表达得更好,也许会更深刻。比如写过《河边的错误》的余华,后来写的《兄弟》,我就非常喜欢。这里忍不住还是要引用一下余华的话:“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现在用空洞无物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我始终认为,一个杰出作家要诞生,作品里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东西。先锋小说也好,现实主义也罢,你总是要创造,总是要直击读者心脏。我和周梅森因此提出了“新写实小说”的概念。
话跑题了,还是回来说我的朋友毕飞宇。过了不久,张艺谋的策划、编剧王斌给我打电话,希望我给张艺谋推荐年轻的编剧。王斌曾经到南京,我把南京的年轻作家都介绍过给他。我说南京作家你不是都认识了吗?包括苏童、叶兆言等。王斌说张艺谋想找更新的人。我推荐了毕飞宇,告诉他“钟山看好”上有毕飞宇的4个短篇,建议他和张艺谋都看看。他们很快就看中了毕飞宇。王斌给我来电:“艺谋希望尽早见到毕飞宇。”毕飞宇坐上了当天的火车去北京。于是,有了他们合作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乡村少年水生来到上海滩投奔六叔,被安排伺候“歌舞皇后”小金宝所引出的黑帮悲情故事。文学表达、拍摄方法和演员演技都非常好,只是到了后半段,落墨在老二睡了老大的女人引发杀戮上,比较平常,似乎还应该再思考一些东西:比如那些相互残杀的兄弟,曾经是不是质朴的“水生”,如今怎么会变得只有利益毫无道义?为什么我们民族做人做事常常没有底线?文化土壤是什么?好看的故事背后要有哲学、文化、社会、人性等等的思考。我后来听别人说,张艺谋当时碰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心乱了。我个人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应该由我尊重的殿堂级的导演张艺谋多思考,他的很多电影很好看,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影》,但是,经常停留在故事层面,或者碰到那层纸了,却没有捅破,捅破了就是伟大作品,比如电影《布拉格之恋》。
毕飞宇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天赋和他不屈不挠的努力,我只是做了一个编辑和朋友应该而且必须做的事,毕飞宇却对我重情重义。最近《钟山》40周年会上,毕飞宇是主持人,他在会上跑题说了很多和我的往事,并公开“滥用”主持人的权利,安排我提前发言。
我对飞宇的小说有一种执念,希望能由我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为了这事,我两次和飞宇喝醉,我可不是酒鬼,五年八年也不会喝醉一次。可是,我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
1990年代初,杨亚洲到南京来找我,想拍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小说讲述的是断桥镇一个父母均外出打工的小男孩啃咬一个“哺乳期的女人”惠嫂的乳房因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故事。我找到飞宇谈版权,飞宇说由你来定。我记得当时提出了一个很低的价格,还让飞宇写两稿剧本,飞宇爽快答应了。我能感受到他那种可以和朋友跨刀上战场的情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和飞宇、杨导演合作成功,还是挺遗憾的。
根据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是康红雷和陈枰执导、徐帆主演的,拿到了“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奖。我一直想把毕飞宇的《青衣》拍成电影,这部作品也是姜文和顾长卫都想拍的。我曾经和徐静蕾、梅婷都谈过,希望她们能够出演。她俩都很喜欢飞宇这部小说。我和飞宇联系《青衣》版权的时候,得知梅婷已经签走了,我只好又和梅婷联系,我们愿意作为合作者参与投资电影《青衣》。2017年,法国文化部授予毕飞宇“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不仅是对飞宇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在中法文化交流上作出贡献的表彰。
最近,我们福纳影业的策划们推荐了一批毕飞宇的小说给我,我的目光落在了《雨天的棉花糖》上,它是那么熟悉,所有的往事就像在我眼前,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这部我喜欢的却又放手的作品回到了我的眼前。我这个天生的捣乱分子突发奇想:能不能由我来把《雨天的棉花糖》拍成电影呢?“一根筋”和“有力量的一根筋”合作一次,会不会很好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