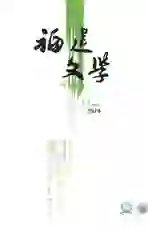张平诗歌:真诚的诗,朴素的诗
2019-08-06张作梗
张作梗
一般来说,一个诗人的写作都会有一个或隐或现的写作背景。这个背景除了与他生活的地域有关,更与他的生存状态(或方式)有关。虽说诗歌是一门“想象的艺术”,但想象也得依附在“具体物事”的刺激上,才能生长出翅膀,否则很可能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张平生活在闽北南平境内。这里的风土人情、风物习俗甚至自然气候,都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乃至左右他的用语习惯、构思生成和叙述方式。也就是说,当他将“南平”这块隶属“武夷山脉”的地方有意无意地当作他全部的写作背景,他的作品便打上了那片地方特有的印记。这种印记不仅仅只是地域性身份的凸显,更是具体的日常生活撞击心灵后所发出的带有烟火味儿的悠远回声——
在海边,我拾到了更多的
鱼骨
肉体剔除之后
身体的道路那么清楚
交叉的大海
在海边,我端详一块鱼骨
是搬动一座大海
……
我空有肉身,裸露的那一部分
骨头也钝了
这是他的一首题名为《鱼骨谣》的诗。这种非常感性而又有独特“海洋风味”的诗,不是在海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写出来。时间的严厉性在此诗中暴露无遗,它甚至会使一个“空有肉身”的人,感受到“裸露在外的骨头,也变钝了”,“一块鱼骨,成为一座干涸的大海”……很显然,这些形而上的自我感觉因为有了几可触摸的“生命经验”做印记,变得亲近起来,从而与受众构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换言之,他的这种独特的海洋生活之作,由于有了生存其中的亲身体验为读者搭建一个“阅读跳板”,而达到一种“普遍经验”的“流通体系”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这些“异域题材”的作品非但不感到“隔”,反而有一种与之呼应、融会、交响的感受的原因。
张平的诗大部分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体验里淬炼而来。他很少在一些浮泛的大而化之的感觉上逗留、徘徊。除非是首先打动了自己,他才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困扰他许久的“感受”化而为诗。因此,他的作品的品质首先是真诚的。真诚是他作品的“第一要素”。一把农村司空见惯的“草叉”,在张平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从未展开”的思想——因为“向上扬起的风”,在“这一端,被季节握得/那样紧”。在这首名为《草叉》的诗里,张平试图在对一把“草叉”的艺术化的审视中,既从生活的角度,赋予它“劳作”的朴实形象,又在“形而上”的诉求方面,挖掘出它与“劳作者”隐秘的互为生死的致密关系。这种“以点带面”的写作,无疑扩展了作品的内蕴,加大了阅读的信息储藏量,使之变得张力十足。
然而,“当我们说到生活这个词时,不应该把它理解为外部事件所认可的生活,而应理解为形式所无法触及的,脆弱而骚动的中心”(阿尔托)。阅读张平的作品,最强烈的阅读印象是他能将外景通过“智力和经验”的打磨和提炼,化为“为我所用”的内景,从而支撑起一首诗歌的骨架和容量。无论是叙写海边生活的《采石场》《谣曲:霞光》《鸥鸟吹奏》,还是涉及时间、死亡等一些终极题材的《秋千谣》《一群人坐在一截腐朽的木头上打盹》,又或是描摹日常生活的《九曲溪边》《向一棵花椒树表白》《黄昏将遇见怎样的人》,我们都会在其设置的“诗性场景”中逗留再三。这种能勾起读者“回望”并“深陷其中”的文本魅力,我以为不仅仅是“深化感知”的结果,更是诗人以一颗真诚之心,触及那物事“脆弱而骚动的中心”的表现。他在《黄昏将遇见怎样的人》一诗中写道——
旷野宽大,孤独渺小
母亲抱着柴火
不急着赶向屋内
她在暗下来的时光逗留了一会儿
惦记一件并没有悬念的事
诗里透露出的“意味”令人回味良久。“母亲”为何“抱着柴火,不急着赶向屋内”?她惦记的是一件怎样的“没有悬念的事”?这些疑惑共同构成了一首诗的主要部分,使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可能成为一次“涉险的愉悦”。
在信息化高度滚动的时代,一个诗人如果还是仅仅抱守着故土、方言、地方志不放,不及时打开他获取外界资讯的感知天线,他的写作很可能遭受搁浅的危险。正如安娜·斯懷沃所说:“诗人变成天线,获取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一种表达他自己的下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媒介。”张平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把视角从熟悉的海边生活挪移到其他领域,他的诗意一下子变得活跃、兴奋起来。这是一种新事物刺激的结果和反馈。它要求诗人更新自我的知识储备,以海风接纳大海的胸怀拥抱日新月异的世界。正是在这种相互的碰撞中,张平写出了他另外一个景象和风味的作品——
在废弃的铁轨,一朵朵草莓花
为一个留在原地的梦奔跑
那里有撕裂的痕迹
石头有变轨的某种速度
又落在同一个旋涡
这春天的假想合情合理
我无限分身
自己也是一截满载的车厢
为终结呈献
春花灿烂
再一次安葬不安的灵魂
——《春花安葬》
相比于他的地域背景之作,这样的作品更具有一种穿透人性的魅力。它们指涉的艺术空间更大,因之也使诗歌产生了更多的阅读歧义性:我们可以说这首诗是描写广义的“生命”,也可以说它是一首悼亡爱情的作品,还可以说它是感叹季节流转的悲悒之作。这倒正好印证了希尼所说的那句话,“诗人具有一种在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本质之间,建立意想不到和未经删改的沟通的本领”。这种本领,对于一个从事诗歌写作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正是这种近乎超验的本领,将区分并甄别出一个诗人成就的高下。
张平诗歌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朴素”。在当下群雄逐鹿、乱象纷呈、口水横行、语象混乱的诗坛,张平诗歌骨子里投射出的这种朴素品质尤为显得可贵。如果没有一颗能守得住寂寞的安静之心,如果没有一种坚持诗歌操守的定力,在这种风向经常变换的时代写作,是很难以朴素为创作的主动力,并将之一以贯之地落实到写作中去的。实际上,“朴素”的根子里还是真诚,“我手写我口”,不打讹,不欺心,不糊弄,不追风,一切依照写作的至高原则从事个体的艺术活动。这么多年,张平坚守着他的那一份朴素,在闽北一所小学教书之余,从容、淡定地写着他的朴素的诗歌——
父亲与我都骑着白马
群山一再低矮
村莊的烟囱拱出了天空
烟囱是另一匹马
……
父亲,我又抓住了
你的手
渐渐地,你松开了一切
——《秋千谣》
所有优秀的诗歌都不是词语大于情感的产物,也不是意象拼贴的才艺表演,而是入神走心的灵魂交流。在这首《秋千谣》里,张平将记忆与变换了的场景交接、融汇,在一种“缺失”的心境中,把压抑的思父之情,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得真切、感人。这比那种形式上求新、内容上求奇的空心化写作不知道要高妙多少。
在我看来,诗,一忌讳虚假,二反对炫技,三拒斥不知所云。优秀的诗作,从来都是从心而发,以真实、真诚为写作之本。“……诗歌在本质上是情感的,在操作上是戏剧的,是熟练地在别人身上重新创造情感。”(菲利普·拉金)从此一方面来说,我倒更相信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艺术,而并非来自浮泛的灵感。诗歌,首先要看它是否有诗的成分;如果是分行散文,或是“口水分行”,那就得另当别论。因为“一首诗的价值有多大,就看它包含的纯粹的诗的本质因素有多少”(瓦雷里),而不是看它是否出自于某个著名诗人或教授、博导之手。张平的诗歌,之所以常常给人以饱满、实在、靠谱的感觉,是因为他的朴素里包含着诸多诗性的想象和因子。他摒弃一切华而不实的装饰和卖弄,就像一个农民,一犁一铧的劳作都是实在的,都是辛苦的,绝不会玩弄什么花架子。他在一首题为《影子在弹奏世界》的诗里说:“天底下只有影子/我们各自合抱/埋藏诗歌的草叶/把嵌入诗歌的寂静/搬出来/砸响寂静/不需要发言,不需要/昨天酒杯的热烈。”是的,诗歌是草叶的寂静,而不是“酒杯的热烈”;是雷霆过后的寂静,而不是雷霆本身。
独居一个僻远的地方写作,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写作者本人来说,既是幸事,也是一种拘囿。前者我已在上文中详细展开了评论和界说;至于后者,则是说——它会限制一个写作者的眼界和视域,使其不能超越自我的地域身份,写出更为阔大、令人鼓舞的作品。这种拘囿,在张平的一些不够成熟的作品中已露出了端倪。这些作品,突出的不足是格局不大,有些生活或生命体验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现代形式而显得叙述陈旧。针对这种情况,沃尔科特曾说:“要改变语言,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在我看来,这儿所说的“改变你的生活”,倒并不是非要一个写作者抛别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和写作不可,而是提醒他,必须更改既有的生活、阅读、思考方式,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心态去接纳新的事物,迎接所有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对于我们写作的挑战。
责任编辑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