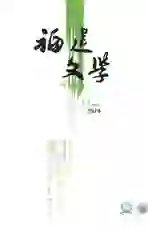我的瓷世界里有个小黑
2019-08-06吴朝烨
吴朝烨
路上的小黑
记忆里,有条路带我走向瓷厂。路上的伙伴,叫小黑。
那是我最熟悉的路,斜坡上铺着怪扎人的青草,草里藏着无数生灵,十分钟脚程,我往往走上半小时。
和我们这些慢吞吞赶路的学生不同,坡道对面,瓷厂的工人们总是匆忙。他们晚十来分钟下班,每当我走到斜坡底下的车站,正待爬坡,瓷厂就大门开了。
我有时会驻足看那些工人骑自行车从门口挤出来,洪流般,将本不宽敞的路口淹没。走得近了,看到工人们的神态,上了年纪的,大都肃穆,不发一言,他们骑得飞快,像箭般攒射而出,只剩模糊背影。
幼时我不喜欢这些背影,只喜欢年轻的工人,他们男男女女,并排走着,说说笑笑。我和这些瓷厂工人吃过饭,在快餐店、小吃店,或在没有店面的流动摊点上拼桌,一边扒拉面条,一边听他们说话。
今天多做了多少件(瓷器),能多发多少钱,想看哪个电影,什么时候要回老家……交谈内容大抵如此。在我看来,瓷厂像另一个世界,令人滋生出许多幻想。但时间一到,厂门便重重锁上,和两边的高大石墙一起,隔绝目光。
我曾无数次在脑海中演习,如何一鼓作气翻过石墙,抵达他们的世界。
带我将这想法付诸实践的,是小黑,一个大我一岁的转校生。小学四年级,许多早熟的人开始长个,一个比一个高,在班上我算矮的,可转校生比我还矮。他属猴,又矮又黑,像个瘦猴子,平日里我叫他小黑,没敢叫他猴子。小黑还真有几分猴性,会爬树,会打架,连蛇都敢抓。
直到小黑转来一个多月,我才知道我们顺路。只不过,我永远走在斜坡一边,他却爬上另一边的高大石墙,整个瓷厂尽收眼底。
每逢放学,我踩着蚂蚁,他飞檐走壁;我在小吃摊前逗留,他在高墙之上探索。
后来,我终于目睹了他的壮举。只见他穿着偏大的蓝白校服,书包斜挎,顶着寸头,脚步飞快。到了石墙边上,他手脚并用,借着石块缝隙,左右挪移,三四米高的墙,没几下就上去了。我惊得合不拢嘴,一路小跑喊住了他。
小黑竟认得我。他在墙上蹲下,小小的身躯令我觉得高大无比。
你怎么上去的?我说,快教我一下。小黑撇撇嘴,脸上却十分得意,他背过身从墙壁上下来,下到一半就往下跳,在草地上安全着陆,这一连串动作简直酷毙了。那时我着迷一切出格的举动,却只敢在心里想想,而小黑不同,他猴子附体,知行合一,敢将离经叛道贯彻到底。
我记下他踩的每个脚位,攀住的每条缝隙,临摹他一举一动,如同进行一个仪式,随他上了高墙。
终于,我如愿以偿,见到了墙内的世界。
墙内的孩子
墙内的世界,平淡无奇。
几间廠房毫无美感堆砌在一起,房子边上,是一堆堆白色“石块”,有的还显洁白,有的灰头土脸。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制作陶瓷器皿的模具。举目四顾,看不见以往成群结伴的工人们,或许他们都在这一叠豆腐似的房子里,我大失所望。
小黑也看了几眼那些厂房,脸上似有一份期待。他没看出我的失落,只顾前头奔跑,这奔跑的兴奋渐渐感染了我。两个孩子沿着墙顶前行,一路享受行人诧异的目光。
小黑是墙内的孩子,很快我就知道了这点。
石墙上原本长了许多野草,却被踩出一条路来,大概也是小黑的杰作。浮想联翩之际,小黑叫住我,说到家了,便顺着石墙里边爬下去。
那似是瓷厂工人的宿舍,一串串内衣裤迎风招展。
不知不觉跟了下去,小黑熟稔地打开房门,里面又小又黑。我没进去,看了几眼刚想离开,小黑却把书包一扔转身出来。
我说,怎么又出来了?小黑回了句没人。后来我知道他的父母都在这瓷厂打工,没到下班不能回宿舍。为了打发时间,小黑带我去玩陶泥,我鬼使神差同意了,把回家抛到脑后。
说是玩陶泥,其实和玩泥巴无异。和现在手拉坯不同,那时我们只会把泥巴捏成乱七八糟的模样。小黑一边捏,一边给我科普,说这是瓷土,看起来灰不溜秋,烧了却能变白。我不信,我打小见过的瓷器,都是花花绿绿的工艺瓷,以为全世界瓷器概莫能外。虽不知陶瓷上的诸多色彩从何而来,但并不影响我质疑小黑。
或许是年少好胜,见了小黑高墙上的身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学识上扳回一局。
小黑受不了这质疑,硬要证明给我看。他捏出一只猴子,也许应该称为“小人”的玩意,架在两块砖头间,就开始生火。
这叫烧瓷,小黑说着。
我不明所以,傻傻看着,间或也帮着捡几根木棍,共同进行着,类似烤地瓜的举动。
小黑终究是没能证明给我看。这“小人”烤了几分钟,小黑父母回来了,我和小黑共同搭起来的火堆遭了殃,被一脚踢散。我看着被火焰炙烤得已有些硬化的“小人”跌落尘埃,鼻子一酸,随即听到被拉过去的小黑的叫声。
他脸上多了个巴掌印。
“总不去读册,就造这些毋落用的物件。”小黑的长辈用方言骂着,我已不敢逗留,慌忙爬上那石墙时,终是听见了小黑的号啕大哭。
“猩猩”的孩子
德化很小。
曾经,那些瓷厂里的工人们也这么认为吧。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困顿周转于一亩三分地里。从一家瓷厂到另一家瓷厂,领着微薄薪水,渐渐活成一个个模糊背影。生活所迫,让一些年长的工人们不再认为制作陶瓷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他们以陶瓷为生,却不想让子女传承这份手艺。
这也许是十几年前德化人的“声音”。
他们梦想着,期盼着,能够不再从事那份职业,能够不再靠陶瓷吃饭,他们希望小黑这样的下一代,能够跳出这个圈子,跳出这样小的德化,去见识广阔天地。
但他们不懂得,当孩子从瓷土里捏出自己的第一件作品,用瓷土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时,陶瓷早已成为孩子的广阔天地。
德化,绝不仅是这一座座瓷厂高墙内那一亩三分地,它更应该因陶瓷而大。
大学毕业回来,我有幸与小黑重逢。
那时他长得五大三粗,我笑称“猴子”长成了“黑猩猩”。小黑告诉我,他终究读不好书,辜负了父母期待,后来他决定听从内心想法,去工艺美院,也就是曾经的陶瓷学院学习创作。再后来小黑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作品也价格不菲,经济独立后依旧每日钻研,活得充实快乐。
在小黑授课的陶艺班里,我见到了许多如他小时候那般捏着泥巴、玩着瓷土的孩子。一双双小手灰扑扑,脸上却挂满笑容。有个孩子眼睛贼兮兮,玩起泥巴来有股疯劲,他捏出一只乌龟,背上却是蜗牛壳。小黑忍俊不禁告诉我,那是他的孩子。
原来是“小小黑”啊!
回过头来再看小黑创作,一把篾刀,一块瓷泥,捏、雕、刻、削、贴……巧手挥动间,一尊猴子悄然成型,再细看,竟是活脱脱一个“齐天大圣”。
看着大圣威风凛凛,我却想起小时候他想证明给我看的,那连猴子都不像的“小人”,心中无限感慨。
交谈中,小黑说到,他父母早已从瓷厂退休,而那家瓷厂现在也快关门了。十几年间,德化的陶瓷产业迅猛发展,传统瓷厂渐渐转型,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有的专注于机器代工和“3D打印”,搞数字化生产,有的乘“一带一路”东风,成为出口海外的领头羊,这几年还听说德化陶瓷茶具销量占了全国百分八十,难以想象这仅是一县的生产力。
德化真的不小了。
也许因为生存,一些老一辈工人们曾对这古老的陶瓷业产生过不满,但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在新一代陶瓷新秀身上得到了继承。德化陶瓷的明天该怎么走,我想,像小黑这般的年轻人心里或许早已有了答案。
依旧走在那条熟悉的坡道,耳边却回响着与小黑临别时的对话。
这“齐天大圣”还烧吗?
烧。
责任编辑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