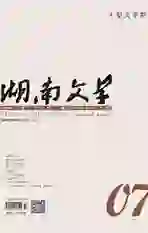宁可,文学陕军第四代之突围进行时
2019-07-30阿探
阿探
一
十多年来“断代论”的叫嚣尘上中,陕西文学迎来了一个多元纷呈的全新时代,文学陕军第四代作家群不断发力,在逆袭的蓄势中暗自构建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版图。生于西府并长久工作在西府的宁可,以近年来的稳健突进,构筑了自己千变万化的文本。
宁可,大约在很多年前就倾心文学,然而生活并没有给予他这样的机会。上帝曾暂时关闭了他的文学大门,同时又为他打开了体察社会、人性的窗口。得益于在这扇窗里长久的凝望、审视与思索,后来宁可如一匹黑马,一路狂飙,留下了令人心魂荡漾的风景。这些年来,他先后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五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并出版长篇《日月河》与小说集《明天是今天的药》,甚至曾经一年发表了十三个中短篇。陕西文学的根性在于乡土,乡土文学几乎湮没了文学创作现代进程中如此鲜活的身影。
读他每一篇作品,有种活在当下的感觉,文本植入了现代意识,而小说人物最本质的精神状态,则体现在小说人物鲜明的传统意识、观念里。这样,宁可的作品有了时代的鲜性,深为读者和刊物所喜爱。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充盈著人性的幽默、饱满和温暖,审视人世的智慧,同时打破了题材、地域性等陕西老一代作家遗留在时代进程中的种种局限。著名作家、评论家邱华栋认为,宁可“打破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魔咒,在柳青、陈忠实、贾平凹、杨争光等小说大家开辟的地域文化小说之外,又找到了一条新路,而在这条路上奔走的,一定有宁可的身影”。
二
文学是一种艺术的表达,重点在于写什么和如何写,如何与时代的脉象息息相通。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观念的巨变,新旧交织、碰撞,人的坚守与蜕变等等,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资源。对于作家来说,越是病象丛生的时代,越是文学繁荣的时代。只不过这个时代也给作家带来了浮躁,而文学是人学、心学,是对人类心灵的审视与体察,是拒绝喧嚣的。在如此之时代的声光迷影中,有没有更好的角度和视点,去触及我们身处的时代?
宁可选取了时代之下社会人心的断面,以社会生活的广阔、丰富视点的变化漂移以及视野高远的作品作了肯定答复。他的创作,从宏观上讲,是社会生活,人性文学;从更微观的层面说,是充满着激变意味的各阶层生命的焦灼、困境、困顿,以及对焦灼、困境、困顿的调适与解脱。
有直击商战惨烈惊心的,如《三角债》等;直击大企业的人事内耗、角逐的,如《三角关系及变化趋势》《较量》《祸》等;聚焦个人奋斗的得与失的,如《裂隙》《尊严问题》等;涉及劳资困局与权力冲突的,如《不服我就灭了你》《我有病我没病》等;直面欲望与人性回归的劝世作品,如《资本的游戏》《春光也风流》《遗嘱》等;关注金融危机下的企业生态的,如《生存实验》《一日四餐》等;关于底层生存压力和安全感的,如《谁是我的天堂》《明天》《碗》等;罪恶与正义的抉择,如《门里门外》;经济与爱情的辩证关系,如《迷失》等等。
宁可的创作取材十分广泛,而且常常有着随意性撷取的意味,所以学院派以“工业文学”定性其创作,是含混的,更是缺乏准性的,不足以概括宁可作品的张力和核心价值。
文学作品如何呈现、表现现代意识?贾平凹把现代意识归结为“人类意识”,“这个地球上大多数人都在想什么,干什么,我们也该想什么干什么。”
中篇小说《三角债》中,宁可以三角债务构建了引发人性失衡的关系错乱、突变的社会乱象,并留下的深深悲哀:早知今日,人生又何必初见?一笔三角债务中,梅茹芳和雷一鸣,贪欲炽旺,利用楚彬的多情、重情、位高权重等多种经济优势、性情劣势,炮制了用心良苦、计划周密的阴险陷阱,企图转嫁债务危机,并造势、借势一举夺取楚莎的公司,陷楚彬于不仁不义、不生不死中。
经济社会,大多数人的贪欲复苏,他们在想什么?掠夺、占有等,是梅茹芳、雷一鸣的意识最真实的一面。而楚彬作为权力、资源的占有者,在想什么?经济、权力充盈充沛,他的意识就落在了左右迷离的情感上。楚莎的意识在于对楚彬的感情期待,赵二宝则是一个以爱情为生命的人。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切卑劣的计划因赵二宝对楚莎真诚的爱而选择竞聘国企老总试图击垮楚彬,导致整个阴谋破产。贪欲膨胀得不到满足,反使自身处于破产的危机中,怒而生狂,梅、雷二人将所有不满发泄给赵二宝,致使赵成植物人。对于这样步步算计、处处陷阱的巨大阴谋,作为确定的被害人的楚莎何以能全身而退,出任国企老总?这是宁可的有意之为还是情节发展使然?抑或某种深意的提示?作品没有说明,没有暗示,不做暗示便是最大的暗示。
宁可以现代感质地的叙事语言和速率,以场景的变换交错,展现了现代商战真切的社会画面。对于“我们该想什么干什么”,宁可是借助楚莎这个敢爱敢恨、醋意和嫉妒心很强的性情女人来实现的。在这场债务纠纷中,楚莎的目的很单纯很明确,夺回楚彬的心,不让其受算计。她是一个满足于自己创造的人,对别人也没有非分之想。是她因爱生恨,以身体诱惑赵二宝去竞聘国企老总,赵二宝因爱坚决执行,楚莎又似有悔意。楚彬的短信,令她对自己与赵二宝的身体交流感到罪恶、羞耻。结尾处楚莎想到需要照顾的两个深爱自己的男人时的羞涩,着力刻画了人物的心灵之美,心境的平静、和谐。作品完成价值意识的导向,至此达到了一种文本内在的平衡。作品的内涵有了质的升华,楚莎这个人物具有了文化意义的承载。
这个中篇是宁可优秀作品之一,小说内在的平衡与实现,依赖于其创作的控制力。《三角债》以时间、空间的转换,形成强大的社会气场;以人物的自我思量,凌乱思绪的梳理等等营造了人的心灵气场;以三角经济债及三角孽缘为背景,突出了经济社会改革的大视野、国家体制的世相大气场;以楚莎从三角经济及情债孽缘的乱象漩涡中全身而退,进而成功竞聘国企老总,力现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人性道德修养的德行气场。作品主要体现在情节推进神速有力,节奏感增强,紧扣读者心弦,大有隐忍未发的张力。就覆盖力而言,作品以精妙的构思统筹结构,形成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联动机制,使作品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断面。
三
宁可的创作,可视为纯粹的人性精神寻根——时代背景下的人的心灵动态的触及。
人性的最高狀态应该是灵魂的动态,在文本构建中,好的表达就是清晰、明确、真性,艺术地再现人的多种灵魂动态。相对于一个承袭了数千年有着自成体系思想的相对保守的农耕社会而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阵痛”,是需要强大的心理适应力来化解的,会给不同阶层的人打上程度不同的烙印,会使人们在特定的生存、生活环境下,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真正的作家眼中,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而作家的责任在于捕捉人性这一最为灵动、复杂的心灵动态,解构人性的种种心灵动态,并给予灵魂困顿中的人类以出路,以解脱。
宁可的创作,就是抓住了社会大背景下的各个阶层的焦虑、困惑、困顿,并深深触及心灵特定时段的真切动影,在审视人性,甚至调侃生活、戏说人生中,给人以解脱之道的昭示,完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
《三角关系及变化趋势》中新成立的公司老总杨左右处在行政领导国企老总龚一和公司董事长施山之间,每一项决策都左右为难,作品真切描述了在两位顶头上司构筑的夹缝中举步维艰的心灵煎熬;《马二宝治厂》中“四大动物”之一的“马”被任为领导,在国家利益与兄弟情义之间,不得不使手段使兄弟“就范”,内心斗争的激烈,人性最真最善的隐藏等种种心灵动态在小说中得以直击;《裂隙》中邱杰为给妻子梅一一和自己一个美好的生活,付出种种努力,包括接受诱惑,随着职位的晋升,对妻子的感恩换作了对其不贞的质疑,人性的裂变中暗藏着多少对最真最善最传统意义品质的放弃和颠覆,这种惨烈不禁让人有种“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千古感慨,但是人往往臣服于欲望的脚下;《谁是我的天堂》以进城民工难以与城市融合,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天堂”,直击了农民工单纯、质朴的灵魂动态;《较量》中的老总王志刚身处潜藏的种种斗争之中,终没有逃脱被算计的命运,勾画了经济权力高层高处不胜寒的心灵苦涩等等。
对于生命在时代大背景下的种种困顿,宁可是如何给予解脱之道的呢?这正是宁可开给这个时代的处方。这个处方依旧是意识态,即人的自我救赎,颇有有些“佛不度人,人贵自度”禅意。
如中篇小说《资本的游戏》中安妮这个年轻女孩,就是雷一鸣一家三口紧张关系、矛盾冲突的化解、终结点,是和谐、福音的使者。雷一鸣对现实生活和家庭的回归是作品中所有生命纠结的终结;《三角关系及变化趋势》以杨左右和他的创业骨干没有去出席公司的“庆功宴”,昭示了生命的解脱——以对权力和利益的不屑,彰显了生命更高贵的境界;《裂隙》以邱杰对车间主任老庞头的宽容和对妻子人性的回归,完成生命纠结的消解、融化;短篇小说《碗》中,在李二水的大度中工艺员心中涌起的愧疚,是生命欲望的解脱;只有三千三百多字的《春光也风流》中,舒凡和水中笑这对都市中寂寞无聊的男女,在欲望的迷失中觉醒,恢复正常的朋友关系,是生命终悟;《较量》中公司老总王志刚失去权力的释然与“对手”张闯的和解,是心灵的放下,是人性更高境界的展现;《尊严问题》中徐小安举报了车间主任,主任却在被撤职前推荐他继任,徐小安对自己心灵的拷问中,人生的眼界、心胸延伸向广远等等。
在激变的社会大背景下的我们,都病了,这是生命的迷离与困顿,走出这种迷离与困顿,靠不得他人,我们自己才是最好的最后的医治者。人生一切在于心境,在于一心一念间。生命是否能够走向美丽新世界,在乎于此。生命困境的解脱,其实是宁可对中华文化核心之道——中庸的理解、活化运用,这种不偏不倚的状态,也构成了小说文本艺术逻辑上的一种圆满,人生和谐的构建。
刘再复认为,“文学是心灵的事业。文学所有要素中,心灵属第一要素。因此,不能切入心灵的文字,不是最好的文学。”宁可以自身对文学的领悟,使作品切入了人物和读者的心灵。
四
宁可的创作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写实主义,体现着扎实的创作功底;二是探索性创作,充满着强烈的创作开拓、突进意识。这种探索性创作,是一种更空灵的表达,使作品的篇幅更为凝练,思想性、涵盖力、突破性更倾向于深邃、广远、犀利。在文本形态上,淡化了故事情节,甚至有些跨文体、无意识、去中心,多种手法运用的活化,强力提升了作品的知觉层次,使作品获得了经典的意味。
如《哥哥》中,小说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出现过“哥哥”这个人物,“哥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物”、意识的存在。所谓“哥哥”,本质上只是娘心中恒久不变的恋人,娘的“情哥哥”和“父亲”,是同一个人物,一个很有担当的好男人,小虎的人生楷模。以娘的刚强,应对着生活的悲哀和命运的玩笑。宁可在艺术构思中娴熟地运用了“人物分解”的手法,将“娘”分解为其他四个人物来写:以小虎成长刻画出娘的孤儿寡母的艰难生活;以“姐姐一样的女老师”还原娘年轻时漂亮、善良、多情、果敢的性格和青春状态、情态;以小虎意识中的完美的“哥哥”形象勾勒出娘当年恋人的动人情态,“那个人”永存在娘遥远的记忆里,已成为娘对小虎的某种期望;以父亲的点滴补叙,将娘的心灵的寄托逐步抖落——因爱被众人群殴致死的父亲——那个公家人的坟头。如此这般,娘的形象清晰可见,娘的情感如红楼女儿般感天动地——真爱,天荒不老,可穿破岁月的沧桑和逝去不复的冷酷。
人物刻画精到入微,重在内心感受和体验,体味;如描摹五岁的小虎的天性,被娘教训的心灵感受,到位、出彩。意象联结人物,强化了叙事的集中度和关注度,小说中的“坟地”,成为联结小虎、娘、父亲的纽带,亦是牢牢掌控作品延伸的中枢神经。“那个人”“哥哥”,在娘的心中,是何等地位,尽在不言中。庄严如宗教般的“认爹”仪式,是娘的情感寄托的移位与承接,是因高速路平坟导致的娘的心灵重创的缓冲、人性化交接。娘完成了灵魂寄托的交接,也就迎来了生命的终结。而“我”却始终没能喊出“爹”。生命从来不是完美的,生命里有遗憾,才显得完美。
如果说《哥哥》只是宁可对成长中美好情感的寄托、艺术抒发的话,那么《春夏秋冬》则是击穿全部人生意义的抽象表达;《天病》则是艺术境地的一种创造。短篇小说《春夏秋冬》以一个女人人生四季的裂变,直至生命的凋零,清晰勾画出人生不同状态、情态。爱情如春,是生命最真的意义;物欲如夏,权欲似秋,生命蜕变为一种虚荣;完美终如冬,生命凋零,意识本真顿悟。开篇写生命的坠落,既是肉体的坠落,又是意识的延伸,坠落过程的意识流,使作品与维昂的《回忆》、狄诺·布扎蒂的《坠落中的少女》中的坠落有了相通的经典意义,不同的是宁可重点在于精神层面的表达。小说结尾还将这种经济繁荣下的虚荣生活的过程和意义推广到女性的另一面——男人。探索至短篇《天病》时,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一是将不可琢磨难以描状的天气进行物质化、准性化的艺术表达,呈现了一种艺术力的原创性;二是将对环保意识淡漠的批判潜隐在小说人物身上;三是由对小说人物、环保意识的批判升华为对人类自身陋根的批判。小说涉及了二〇一三年度热词“雾霾”,以失真手法直击了环保副处长的“病变”及复原过程,借“老天”之手对环保副处长进行了“惩戒”,作品始终荡漾着调侃、诙谐的意趣。对于雾霾形象描绘的文字既类似塞万提斯式如梦如幻的情思,又类似于其如梦如幻式的表达,是宁可无意间的艺术创造。“天病”在现实中又常常体现为“人病”,小说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以环保副处长复原后的蠢蠢欲动,昭示人类的陋根——好了伤疤忘记痛,从而使作品延伸意义提至更高层面。
五
以传统为底蕴,以现代为技法并完成二者融通,是宁可近两年来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小说人物甚至故事最终几乎都从文本中退场,文学表达的探索进入纵深与广远,升华为对人类意识的某种寓意。
海德格尔曾断言,当今人类已不能与本身相逢。宁可的短篇小说《左右》《明天是今天的药》却让我们与真实的自己相逢。
《左右》中“我”或“阿左”或“阿右”,不是人的本体,而是变体之一种。人性在《左右》里,集中体现为一种悖论或相对立的存在,这恰恰是人性最真实的状态,失真状态。宁可在这个短篇中再一次采用了“裂像”技法,一个人分裂为淳朴的“阿右”和有些强势的“我”,而“我”后来又幻化为同质体的“阿左”。最终以第四人出现的虚幻人影,注视着“阿左”和“阿右”并肩和谐地坐在护城河边上。究竟是一裂为二,还是一裂为三?抑或二合为一?“一”和“二”之间,是以一个美丽的女性小月联结,这个女性带给“阿右”和“我”或者“阿左”的似乎只是冲突,然而在表面的冲突下面,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不弃不离的中和。这是人性复杂抽象的艺术想象化,中国式美感的完美呈现:一个人的“阿右”可视为太极图中的“阳鱼”,“我”或“阿左”可视为太极图中“阴鱼”,小月自然是阴、阳鱼之间的“S”形对流线,达成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本源性阐述,也就是人性本真的阐述。在短篇《左右》类似迷宫的设置中,宁可为读者留下了钥匙,前文“咬脸”,后文“咬手”,这把钥匙,让读者顺利进入小说的深层。
《明天是今天的药》是青春与中国青年本身的相逢,是外在物质与人之本质性精神交错交织的对峙性存在的相逢,它再次阐述了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生命认知: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作为一个“有主见”的九〇后女孩,“我”的爱情选择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却时时处处承受着闺蜜赵小兰的现实性真切的刺激。正如赵小兰遵从了物质,意识里依旧不放弃对林峰真切渴望,赵大怀抱着赵小兰依旧不放弃对“我”的物质引诱与精神意淫。在这种三角情感纠结与对峙中,真实的林峰成了现实中的虚幻存在。婚纱影楼,处于浮虚中女性的真实的惊艳,成为人性本真与世道浮迷的一种对抗存在。宁可借化妆师的暖心及扩大战果性话语,暗自有力地奏响了人之本真最终胜出的序曲。合影时对象的互换,是宁可宽广胸怀包容的一笔。以“我”对身边男人赵大内心由衷的赞赏,化解了对这个时代富豪及土豪的精神对峙和仇视。而站在林峰身边的赵小兰的一丝羞涩,传达了她人之为人的本真情怀。无论“我”还是“赵小兰”都是这个时代真切存在,都是这个浮迷浮虚的时代雾霾下弥足珍贵的一缕金色的阳光。笔锋一转,又打破了“我”短暂的迷梦。穿上质地相同的婚纱,“我”和赵小兰处在同一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褪下婚纱,依旧是天壤之别的生存处境。紧接着,这种比对进入升级版。从赵大赵小兰的奢华别墅出来,当再次面对宝马与摩托的选择时,“我”和林峰一致拒绝了赵大赵小兰的宝马车。赵大、赵小兰退出文本,成为一种符号,即“我”及林峰之虚荣心的化成。甚至“我”和林峰,也只是人世间坚守本真本我的一种存在之凝结。“我”与林峰在出租屋中奋力追逐赵大赵小兰,一步之遥依旧追不到,乃是宁可对时代之人性的整体性寓意高妙之笔。迷梦追不到,最终“我”和林峰在彼此的眼中找到自己,回归到青春本身。赵大赵小兰只是我们平凡社会个体的“他者”生活,只是凡人生活的切实比照与强力刺激,问题是赵大赵小兰的生活真是我们所苦苦追求的吗?物质终归是实在性的虚设,但却有着强大的导引力,把我们导向没有情怀的生活,于是在灵魂失衡的迷离中,坚守成为坚守者的精神灾难。明天究竟是什么?是对美好生活生生不息的热望,是冰释和化解今天所有负担的药。一番曲折的反复,文本回归了青春的质朴与初心本念,唯有明天才是医治今天精神苦疾之药。文本整体就是实与虚,真与假的转换及消弭,一种多层次立体感的成功营建,看似不着色调的叙事中蕴含着逐层递进与深入的张力,最终至高点飞流直下三千尺,从人间直达宇宙亘古之不变:世界在一心一念间。以坚守到底之曲折,断然阻击了物质社会对人之精神的无限压制、压榨,是谓捍卫人心质朴之作。
短篇《东西》重书了经典之终极印象:虚无的存在,即于有限之空间建筑一种无限之意蕴,引发人类之严肃思考。《东西》彰显沉静之气,于诗性极度缺失的时代,信手拈来,收放自然,伸展之间力道强劲而无形,小说大象渐现。文本无异于人类向本体本初的一次回归,亦是艺术向古典境地的回歸。变了的东西,我们已经记不起它原本的样子,没有变的东西,数千年来一直就在那里。
《东西》之意蕴丰富丰满丰沛,扎实入微。主人公男人小东与美女小西,可以东西方人之情感交流为意义,凝视人类的前世情缘。然而小说人物,只不过是人类意识的符号而已。若以文化为内蕴,《东西》则是东西文化的前世、今生的写照,动影之定格,则小东是东方含蓄、内敛文化的象征,小西则是西方直接、奔放文化的象征。文本中预伏了些许的蛛丝马迹,并重返了东西文明的本初存在状态——一次理想而短暂的交汇。文本的演绎是打破时空观念的,于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实中如艄公般随处可见的荒诞不经,艄公的歌声则是人类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声响。热玉米棒亦是两种文化文明冲破藩篱、擎起古今共性的和谐。春天西斜的阳光下,无论小东还是小西,凝结为最纯粹无瑕的美。梦境亦幻亦真,完美之中有缺憾,这缺憾不过千古不变的常态而已。虚境虽美,不过海市蜃楼之一刹那闪现,意识之唯美的奔袭被惊回会场。“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鲍照《拟行路难·其四》),东西有别,人生有定,或许有和谐之交汇,但依旧是各奔东西。那么文本确定寓意的就是文化吗?依旧是确定之中的不确定。以人性,命运之宿命,人伦交际,对外关系等等为说辞亦通顺如常,每一位聪慧的读者都可读出自己心仪的无形之意义。这篇《东西》之中,宁可设置了串结古今广远的视野,游刃于一种唯美、优雅的气场,以淡然承载丰富的语言,探究和延伸了人类存在性的思考。他的语言,是从来不做无心之举,需要我们去体味再体味,甚至用全部生命乃至历史、文化去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