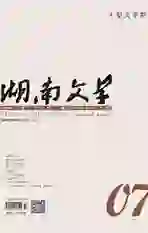雨一直下
2019-07-30张运涛
张运涛
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老罗正在乡政府。县扶贫办要给他一个处分,因为田常林贫困户材料作假的事。
王畈是“软弱涣散”村,换届时老支书那一班落选,老隗以微弱优势当选。因为告状的太多,原来的五十九家贫困户重新甄别,只剩下三十三户。上周督查组来查一个信访件,查出田常林肺气肿有假,医院能查出来的病历只有肺炎,输液吃药花了还不到两千块钱。老罗当时也没在意,反正责任不在他,他这个驻村第一书记是半年前临时从沈红伟手里接过来的,那时候新甄别的三十三户已经上报,老罗只是做了最后的建档立卡工作。局长哄他说,驻村回来能解决他的副科级。老罗在政府大楼干了二十多年还是一个股级干部,出来总觉得矮人半截。
初到王畈的时候,老罗不知道田常林是支书老隗的内弟。第一次开村委会,老隗说田常林明天出院,狗日的要求村里派人去把他的账给结了。老罗问,不是给过他三千块钱了吗?一屋人都不吭声。田常林说他的腿属工伤——年后村里栽树,贫困户都参与,算公益岗位,有补助。栽完树,田常林骑电动车回去,掉到沟里,摔断了胳膊。住院期间村里已拿去三千块钱做慰问金,但他不满足,出院时还要村里去给他结住院费。这还不算,后来收麦时,田常林吵着说他胳膊疼动不了,四亩地麦硬是村里帮他收的。
老罗去过田常林家,很光鲜的两层小楼,但屋里乱糟糟的,沙发上纸箱子上到处都是衣服。田常林说他是寡汉条子,老罗笑,说听说你有老婆,老婆失踪了(老罗没敢说他老婆跟人跑了)。田常林也笑,你都知道啊?我老婆孬种,把我的钱都卷走不说,还不让我见我闺女。你知道我以前多挣钱不?我一个月工资七千,前儿个人家还打电话让我回去上班呢。老隗也介绍过,说他以前在一个造船厂工作。造船厂在海上,一年到头也就春节回来一次。老罗问,工资那么高,你回来干吗?田常林讪讪的,收回眼里的光。老隗说田常林那个婆娘长得可水灵了,就是有点骚。她跟老隗的老婆说,一年到头见不到男人,我要钱有啥用?
趁着回城送材料,老罗先去了弟弟家。母亲电话里似乎很镇定,有事儿,想跟你说说。老罗知道肯定是大事——母亲是那种越是有事表现得越镇定的人。果然,他刚进门,母亲就迎头一句话,老虎在搞传销。老罗怔了一下,并不多意外。过年老虎回来,说是在广西做,一个月五千,他马上就联想到传销——十多年前他就听说北海南宁那儿搞传销的多。老虎前几年在深圳当保安,一个月工资三千多,他一没技术二没文化,突然拿五千,着实让人怀疑。但老虎不承认,说是跟北庄的一个朋友在南宁搞工程。人家凭什么给你五千?老罗当时还问过他。老虎说他过去带班。老罗问母亲听谁说的,母亲说是来福的一个姨夫,不太亲的姨夫。上个月老虎回来,带了两个人走,其中一个就是他。老罗安慰母亲,不一定,我问过老虎,他说不是。我再问问看。母亲说,他听你的,你让他赶紧回来吧。
雨就是这个时候下的,打在铁皮做的护窗上,噼噼啪啪的,像经过了一个大功率的扩音器。母亲去关窗户,老罗说不用关,雨小,屋里可以进点凉气。母亲折回来,说下了好,稻子要水,花生也要水。老罗说,人也要水。连续十几天三十九度的高温,一天得洗好几次澡。村部没洗浴设施,老罗只好天天烧点水撩着洗。
回去的路上,老罗找了个僻静处,打了几个电话,辗转找到来福姨夫的手机号码。起初对方不愿说,老罗说我只是想从你这里证实一下,前天这边有人见到老虎了,说是在搞傳销。人家还是不肯说,说他发过誓。老罗其实已经听明白了,不敢相信,非要对方来句准话。你以为不说是帮他?等他钱花光了,将来肯定会怨你!你们这样的亲戚又不是三天两天。来福姨夫这才说,他是司机,想跟着老虎去找个开车的活儿。老虎带他在南宁转了两天,才说让他买个产品,然后就坐等着赚钱。来福姨夫断定是传销,坚决要回。老虎并不是那种心狠的人,说你坚持回去也行,但这边的事你得发誓不讲出来……
挂了电话,老罗心里空落落的——不是因为老虎去搞传销,而是因为老虎竟然跟他这个亲哥都不说实话。南宁,一个月五千,其实到处都是疑点,他怎么就没拦他呢?幸亏十万的货款没批下来——年前老虎回来,说想入朋友的股,把那个工程包下来,申请了一笔十万的贷款。老罗当时只是隐约怀疑,十万块钱在建筑工程里算什么?即使能起作用,能分红的事怎么会轮到老虎这样的人头上?但他还是做了担保,亲兄弟嘛,他有机会了还能不帮他?银行将老罗的身份证输入电脑,老罗之前替朋友担保过的一笔贷款还没还,没有担保资格。老罗当时还有点愧疚,没能帮上弟弟。再怎么样也不能骗自己的哥哥啊,他想。这十几年,老虎家里的事儿都是老罗替他照应,老虎在城里的房子,两个侄子来城里上学,包括弟妹在城里的工作。
老罗定下心,决定过两天去一趟南宁。走之前,他得先把那个假贫困户的事儿弄干净。老罗跟局长汇报,局长说他也听说了。老罗问怎么办,局长说尽量做督查局的工作,做不下来再说。
督查局是临时机构,从各局委抽的人。老罗打听到情况,说是通报批评基本确定,最迟下周一公布。老罗急了,给局长打电话,被挂断,回复正在开会,稍后联系。老罗又发微信,把打听到的情况仔细说了一遍,请局长抓紧活动。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局长才回话,通报批评不影响什么,一年后一切如前。老罗拿着手机看了好久,才明白局长的意思是让他顶这个处分。凭什么啊?老罗不同意,田常林的贫困户又不是我甄别的。局长发来一个咖啡的符号,意思是请他喝杯咖啡。然后又说,志远啊,沈红伟刚刚搞了个“十佳驻村第一书记”,现在再给他一个通报批评,不是打咱的脸吗?老罗心里有所松动,可让我背这个处分也太冤了吧。局长说你得有全局意识,沈红伟推上去了,下一个不就是你吗?
老罗想了大半夜,还是觉得别扭。第二天上班,他直接去督查局,找到分管副局长——副局长他认识,是比他低一届的大学同学。人家倒是推心置腹,说这是领导定下的,说是我们研究,其实还不是走过场?还劝他,这样的事儿多了,领导挪用资金,让分管副职签字,出事了都是分管副职顶。你没看新闻吗,无论什么事,处理的都是临时工或副职——他们哪有拍板的权力?还说,你也别找这个找那个了,讲不下来不说,要是你们局长知道了,对你更不好。老罗想好了,不怕。以前我太猥琐了,这次明显占着理,我得搞到底。不行的话,我想到市里。副局长笑,你是我学兄,我就明说吧,人生难得糊涂,千万别太认真。你敢说你没责任?建档立卡工作人员必须清楚建档立卡户的基本情况,你说你不清楚不是失职吗?
从督查局出来,老罗才发现伞忘在副局长办公室里了。反正下得也不大,老罗就从路边树底下慢慢朝回走。树是法国梧桐,枝繁叶茂,像墩在地上的伞。走到公交站台——县城刚刚开通公交车——干脆坐下不走了。老罗想静静,捋捋心思。手机振动了一下,QQ空间里有新动静——他好久都不用QQ了。一个叫安的人给他发来一句话,可与人言无二三。像是个文艺青年。老罗一时没明白那句话的意思,随手就进了对方的空间。多是转发的文章,看不出主人身份,老罗胡乱点了个赞,退了出来。他想起来了,“可与人言无二三”是一首诗的下一句,上一句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他又打开微信,除了群聊天,没有新信息。正无聊,一个瘦老汉也进了站台,往公交站牌上贴了张纸,又匆匆走了。老罗凑过去看,是寻人启事。唐李宣,男,七岁,留平头,上身穿警服,下身穿黑色牛仔裤。二十一日在县城走失,知情者请打下面电话,定重谢。寻人启事遮住了几个站点名字,老罗揭下来,贴到座位后面的广告牌上。唐李宣可能是瘦老头的孙子或外孙,父母在外打工,孩子留给他照管。又想,父亲也说不定,农村人显老,瘦老头也许并不老。无论是谁,丢了孩子,那老头肯定安宁不了……正胡思乱想,手机又有动静。还是那个安,QQ里又发来一个笑脸。
老罗也回了个笑脸,然后接出上半句,不如意事常八九。
捡能与人言的说。
刚跟领导吵了一架。老罗其实喜欢跟陌生人说话,肆无忌惮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敢跟领导吵,不想好了?
谁不想好?主要是心里烦。
烦什么?
我弟弟进了传销窝。
啊?
过了好大一会儿,安发过来一段文字。我亲侄子,大学刚毕业,去年被骗到巢湖搞传销。我哥知道大概位置,去了,在那儿待了七天,我那个侄子硬是不出来见面。
老罗心里一沉,良久才问,最后呢?
最后?最后我哥回来了,侄子半年后也回来了,花了十几万。
老罗紧张起来,老虎过年从他这儿要回了他那三万块钱,是不是都拿去“投资”了?买了房子之后,老虎打工又攒了三万块钱,都打到老罗卡上。过年回来,老虎突然来要钱,说是老婆要用。老罗心里纳闷,问他用途吧,好像自己多不情愿似的。人家的钱,他凭什么一直拿着?
安在网上自言自语。那边让他从手机上贷款,还有找亲朋好友借的。人家知道我哥有钱,不怕还不上。
一滴水从站台的棚子上落到老罗脖子里。老罗被激了一下,站起来。他得给老虎打电话——实在忍不住了。你到底在那儿做啥啊?
带工,不是跟你说过吗?
老罗有点不耐烦弟弟的语气。你的工资呢?
老板说,先压压,工地上资金周转不开。
房地产项目,没听说靠工人工资周转的。现在的大城市,谁还敢欠农民工的工资?
老虎不吭声。
知不知道,来福前天感冒输液还在找人借钱?你一个男人,大半年不朝屋里拿一分钱,咋解释?你把你那个北庄朋友的电话给我。
好,我发给你。
挂了电话,老罗等了会儿,微信和短信一直没有动静。他重拨老虎的电话,想提醒他不要跟其他任何人——当然是指他那个传销组织里的人,只不过那时还没扯明——透露他们之间的通话。老虎的电话一直占线。
老罗反复重拨,愈加怀疑老虎是在向上线汇报。老罗的心被气愤和失望占满,这个时候,老虎竟然连自己的亲哥都不信任!电话终于通了,老虎上来就说,我现在没跟人家干了,电话不能给你。
没跟人家干了你刚才咋不说?
老虎不吭声。
你刚才是不是跟你的上线在通话?汇报?老罗还是没忍住,用了上线这个与传销紧密相连的词。
啥上线?老虎装着不明白。
老罗索性不遮不掩了。我傻啊,你跟人打了这么久的电话,现在突然又说没跟人家干了,手机号不能给我了。真要没跟人家干了,刚才为啥不说?老虎啊,你还没聪明到能想出这个理由的程度……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想想这个世界上谁最不会骗你?
说完,老罗兀自摁断电话,气得浑身觳觫。他决定现在去南宁,马上就走,他要老虎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话。老虎要还这样说,他非上去打他几个耳光不可。
通报就通报吧,不就是一个副科嗎,一辈子做一个股级干部又如何?老虎的家不能散了——钱要是败完了,家不就散了?他跟局长请了两天假,加上周末,四天应该够了。五天也无所谓,老罗其实不怕多耽搁一天——他现在一点儿也不担心工作的问题了。
取票机上显示老罗的身份信息已过期。他把身份证翻了个面,还是一样。消磁了?他记得听谁说过,身份证消了磁电脑就无法读取信息。他到柜台上问,售票员说是你晚点了。老罗这才想起来,他当时心神不定,可能点错了车次。
可以改签,但当天的高铁票全部售罄。老罗说站票也行,人家说高铁没站票。老罗只得改签晚上九点多的火车,二十三个小时,还是硬座。
坐公交车摇到火车站,还不到三点。老罗没心在外面逛,天又热。他递上火车票和身份证,人家又还给他。你来得太早,提前两小时才能进站。老罗问,我进去上个厕所好不?对方不耐烦地摇了摇手,不再理他。老罗出来找肯德基,他记得火车站附近有个肯德基。
从肯德基的厕所出来,老罗找了个偏僻的座位坐下。他旁边那个桌围了三个老太太,每人面前一个大茶杯(杯壁上满是棕黑色的茶垢),像是这里的常客。听她们聒噪了一会儿,才知道都是给旁边长途汽车拉客的,中午来肯德基小憩。再远一点儿的座位,旁边竖着两个大拉杆箱,应该和老罗一样,也是早到的乘客。老罗想在朋友圈发条微信,为什么火车站不把乘客当人?还不如人家外资肯德基。但一想到老虎会看到,会警觉,又作罢。
老罗跟母亲和弟妹都打过招呼,不要跟老虎透露消息,他想打他个措手不及。依他的想象,现在的传销肯定也在与时俱进,就像病毒,经常更新,破绽越来越少。比如,他们会用实体做幌子,绝不承认自己是传销。
老罗渐渐静下来。他从包里拿出一本书,《一个人的县城》,本县作家的作品——儿子买回来的,说是写得接地气,建议他认真学习。先看与书同题的那篇,很长,写作家在县城的经历,还说到有人花一百二十万买一顶官帽……
老罗突然想到上午那个电话还没问到那三万块钱呢。他收起书,从肯德基出来,站在屋檐下——家丑,老罗怕人家听到——给老虎打电话。
没人接。
肯定在開会,在洗脑。老罗想象着,老虎和十几甚至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屋里,手机都集中到一处,都设置了静音,谁都不许接。他越想越气,重拨,重拨,再重拨……
没办法,老罗只得在微信上给他留言,先是急不可耐地质问,然后是无奈地劝说:
老虎,你要走那三万块钱干啥用了?能跟我说说不?
知不知道你的话漏洞百出?还在狡辩。我真伤心啊,你竟然不相信我却去相信你的上线。
老虎啊,谁都有短板。马云什么都会吗?肯定不是。马云厉害就厉害在他知道自己不是万能的,所以靠一个团队作战。你初中都没毕业,见识也少,上一回当很正常,但你得知道好歹啊,至少你该知道我不会骗你吧?
世界上最笨的不是笨人,而是不知道自己笨的人。老虎,赶紧醒醒吧。
……
你知道耶稣不?一个传道者蹲到老罗面前,一只手抚着他的膝盖。耶稣让我来通知你,神一直在关注你,保佑你……
对方是个女人,透过眼镜传递出的眼神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她说她在荷兰十多年,这次因为火车晚点顺便来向大家传福音。
老罗没有拒绝。要搁以前,他会调侃对方几句,甚至会居高临下地反问她一些问题。这次他没有,他接过传道者递来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永生的祷告》,楴罗勃牧师。
信神的人有永生;不信神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你对基督的态度决定你永恒的未来;相信他,就得永生;拒绝他,受到永恒的处罚。
……
他把那个小册子塞进双肩包的外兜里,想着在车上还要待一整天,不急,终会明白的。
传道者转到对面那排椅子前,手抚在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背上。老罗进来找座位时就注意那个妇女了,她身边还有一个男人,脸上是庄稼人惯有的那种棕红色。两个人应该是夫妻。不知道是传道者把她说哭了还是她在向她倾诉,老罗看到妇女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头几乎伏到传道者的怀里。那个男人像个陌生人,伸着脖子,东看看西看看,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也可能是装的。
车站真是布道的好地方,老罗想。这里有多少人心怀绝望啊,去探望生了绝症的亲人,或者自己正前往医院等待手术,再不济也是被生活所迫出来谋生……还有老罗这样的,去挽救一个身陷囫囵的人。
老罗差不多有十年没坐过硬座火车了,年龄大了,身体不经熬了。不过,这一夜比老罗预料的要好。他先是头靠着椅背靠睡了一会儿,后来又趴到座位上。六点多,卖早餐的吵醒了他。营养早餐,咸菜馒头鸡蛋稀饭。
多少钱?对面有人问。
十五。
问的人笑笑,挥挥手,餐车又推走了。
不用急,挨着老罗坐的男人像是安慰对面的人,说等他再转回来,十块钱就能买一份。
听口音,老罗以为他们俩是朋友。一个略显粗壮,另一个相对瘦小,但两人都五十多岁,面容黝黑,像是经常在外作业。老罗发了会儿呆,才去洗脸。回来发现邻居手腕上方有几处烫伤,像是烟火烫的。再往上一点,还纹了一条蛇,吐着灰色的信子。对方问他去哪儿,老罗说南宁,你呢?纹蛇的男人说,也南宁。你去旅游?老罗说不是。对方又问,在南宁工作?老罗想了想,说算是旅游吧。纹蛇的男人很得意于自己的判断,一看你就不像打工的。老罗脸上挤出一点笑意,谁不是打工?公务员为政府打工。南宁的治安还好吧?老罗把话题扯开,他其实一直想找个人说说传销,说说南宁的传销,排遣一下心里郁积的情绪,说不定还能有益于解决弟弟的问题。
到处都是摄像头,能不好?对面那个瘦一些的插话。他其实只是相对瘦一些,跟老罗比起来壮实多了。身上的T恤衫偏大,左胸部印着一个显赫的商标——应该是地摊上买的冒牌货。他们都是农民工,典型的农民工,虽然穿戴不一样,说话也不一样,但一眼就能看出来。
以前可不好,纹蛇的男人说,以前广西最乱了。
我在这儿待了十二年,没听说过乱啊,瘦点的男人说。
能有我清楚?纹蛇的男人头一硬,我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一年到头都在外面跑。广西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乱,山上隔不多久就有一具尸体。
瘦男人坐回去,不反驳,也没有被反驳的尴尬表情。中庸,老罗突然想这个词,瘦男人长得真是太中庸了。
去年,我还见南宁两班人打架,纹蛇的男人一点儿也不在乎中庸的反应——他也不是那种在乎别人情绪的人。他们拿着钢管棍棒……
你做什么工作?老罗打断他的话,他其实更偏向相信中庸的话。乱呗,纹蛇的男人还用了两个特别,老罗觉得他习惯夸夸其谈。
搞建筑,纹蛇的男人说。我儿子是包工头。
包工头挣钱。
纹蛇的男人问,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四千多,老罗说。
不会吧?他装出很惊讶的表情。还没有我高?我一天两百块钱。
你工资六千多也不如人家四千多的,中庸插话,你盖宾馆你住过吗?宾馆盖好后还是人家去住。
老罗笑,也不辩解,想着借此打压一下纹蛇的男人。他问中庸,你呢?你做啥?
我在防城港,给人看果园。
老罗不知道防城港在哪儿。
靠近越南,中庸说。
那儿是不是很穷?老罗问。
比河南富多了。以前他们靠走私,从越南带东西过来,从广西带东西过去……
现在不行了?
现在架了铁丝网。不过,还是有人翻过去——趁哨兵不注意。
你经常见越南人?
经常见。果园雇了很多越南人,他们的护照都在我手里。中庸打开手机,让老罗看他拍的越南人。
越南人好偷东西,纹蛇的男人说。
哪儿都有小偷,中庸一直是平淡的语调,但明显在和纹蛇的男人较劲。越南人也有不偷东西的。
偷东西的多。纹蛇的男人为了向老罗证明自己的论断,从兜里掏出一把钱。看,我还有越南人的钱。有一年我在防城港打工,工地上有几个越南人,今儿个把老板的切割机偷走了,明儿个又把老板的发电机偷走了……
那么大的东西,偷走放哪儿?老罗问得很礼貌,但他越来越不相信纹蛇的男人了,连他儿子是不是包工头都值得怀疑。
越南人这边亲戚多,中庸反过来替纹蛇的男人解释,偷了东西先放在亲戚那里。
餐车又过来了。最后一次早餐了,营养早餐,咸菜馒头鸡蛋稀饭。
多少钱?纹蛇的男人问。
十五。
纹蛇的男人没趣,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十块处理了?
人家没理他,嘴里吆喝着“最后一趟了,咸菜馒头鸡蛋稀饭”,走了。
听说,老罗清了清嗓子,南宁搞传销的多。
现在谁还上那个当啊,中庸说。
我以前房东的弟弟,被传销骗走了几十万。纹蛇的男人并不感激中庸替他圆场。
几十万?老罗侧身看着纹蛇的男人,怎么那么多?
几十万。
他哪来那么多钱?老罗不相信。
拆迁啊。房东说,他把人家补偿的拆迁款全部投进去了,谁的话都不听。
中庸说得对,老罗重又郁闷起来,那么明显的套路,老虎竟然上套了。老罗从没上过这样的套,只要别幻想着天上掉馅饼,就不会上当。上世纪九十年代,老罗跟同事一起去郑州开会,同事被路边的免费抽奖诱惑,上去抽了个一等奖。人家簇拥着他先去交了税,回来才把奖品交给他。一条毛巾被,商店才卖一百二十,税就交了一百六十。还有一次,单位评两个先进,几个最有竞争力的同事都打了招呼,最后老罗能胜出,全靠他的聪明。老罗反复跟自己的铁哥们儿安排,不但要投他,另一票还要投给最没可能的那个人——这样老罗才能和竞争对手拉大距离。有时候老罗也反省,可能正是因为太聪明,自己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飞机!一个孩子大声喊。
车窗外,一架飞机几乎与火车平行。中庸看了会儿,说比高铁快不了多少啊。纹蛇的男人嘁了一声,五个高铁也不一定能撵上它。老罗没坐过飞机,但他更相信中庸的话,中庸的判断就像他说话的样子,踏实,认真。老羅靠回到椅背上,笃定地说,飞机每小时不过三四百公里。纹蛇的男人说你说的是起飞和降落时的速度,中间可以飞一千多公里。中庸不急不缓地反驳,高铁可以跑三百五十公里。飞机要是能快那么多,城里人咋更愿意坐高铁?老罗的手在空中快速划了一下,你知道一千多公里什么概念不?就这样,唰的一声看不到了。纹蛇的男人说,我敢跟你打赌,飞机绝对能飞一千多公里……
老罗轻笑了一下,站起来,从纹蛇的男人前面挪出去。他不想跟他这样的人争,无知又自大。他把双肩包取下来,想接杯水凉着。两边的网兜里没见水杯。包里也没有。老罗仔细回忆了头天晚上在候车室的一举一动,他想起来了,那个传道者过来布道时,老罗顺手把它放到座位底下了。
火车到站之前,老罗接到电话,他的通报批评下文了,老隗的村支书也被免了,暂由乡里副书记兼着。老罗没有发牢骚,好像人家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南宁也在下雨。老罗有点恍惚,要不是不远处的热带植物提醒着,他以为还在老家。出站之后,老罗一直靠着沿街门店的墙走。雨不大,天又早,老罗不急,反正今天不打算见老虎了,先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再找个酒店住下,美美地补一觉。养足精神了,明天再与老虎见面。
走了差不多两公里,路边有家“粉之都”,老罗想着既然来广西了,就吃粉吧。有一年他去南京,老同学热情接待,点了一大桌菜,喝的是茅台酒。如今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第二天早晨吃的鸭血粉丝汤,真是极暖胃的小吃啊。老罗坐下点了一种粉——他心里有预案,不好吃也罢,总算吃了一顿广西本土的热饭吧。等粉的过程中,老罗打开店里的免费网络。
九百公里。竟然是九百公里。也有一千公里的。老罗在百度上搜到了飞机的速度,他的脸热起来,怎么可能呢?看看周围,好像每个人都像那个纹蛇的男人。吧台叫了两遍他的号,老罗才听到。他要的粉好了。老罗小口尝了一下,不错。再扒两下,真不错。老罗的心情顿时好起来。
吃过饭,天还没黑,顺风车把老罗带到东方广场——老虎曾经说过,他们晚饭后经常去东方广场逛一会儿。那里有点儿像郊区,周围都是小市场,里面夹着一些小宾馆。老罗想看看房间,老板从柜台后站起来,递给他一张门卡。老罗接过门卡,干净不?问罢又后悔了,明显是句废话,就像问人家卖的瓜甜不甜一样。他最终没有上去看房,觉得这个老板太像火车上纹蛇男人说的那个房东了。就是这里了,洗个澡下来再跟他好好聊聊。
老罗那天晚上没有下来和老板聊天。他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多。简单洗漱之后,他想下去吃点早餐,顺便和老板聊聊他那个搞传销的老弟。下了楼,柜台后面换成了女人。换班了?换了老板娘?老罗在外面转了转,早餐又点了粉,却索然无味。
他给老虎打电话。还好,老虎接了。他说他在东方广场某某酒店门口——老罗没敢说他住的宾馆,怕老虎的同伙来控制他——老虎并不惊讶,好像早知道了似的,答应一会儿就过来。
老虎是步行过来的,应该不远。老罗躲在旁边的门店里,暗中观察。他穿着白衬衣,黑裤子,右手撑着一把小伞——伞布是那种透明材料做的,不像男人用的,更不像农民工用的。期间并没有人与他同行,他也没跟谁说过话或者打过电话。老罗闪出来时,老虎也没有意外的表情。他问他住哪儿——本来是见面时常见的寒暄,老虎却警觉起来,说你要想去我就带你过去看看。老罗不想在街上和他吵,说到我房间去吧。
老罗坐在床上,老虎坐在对面的椅子里。椅子比床矮多了,老罗看老虎时,有种俯视的感觉。
你不知道你的话漏洞百出?
啥漏洞?老虎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
前一秒你还说给我你那个上线的号,打了一通电话你又说没跟他干了,电话不能给我——既然没跟他干了,为啥电话里不早说?
老虎重新抬起头,看着老罗。我不是传销,你得相信我。
相信你?来福的姨夫跟你有仇,故意编排你?搞传销的人没一个承认自己做的是传销。老虎啊,你得知道,这世界上最不可能骗你的是谁。你说是谁?你亲哥难道还不如你的上线?你跟我通完话,又汇报给你的上线,真让人寒心。我为你买房子,怕你来回跑挣不到钱还替你装修,你两个小孩转城里来上学没让你花一分钱,我这都是为啥啊?你心里想过没有?
我知道,我心里清楚,你为我……
你别好嘴,我不喜欢听这样的好话。我就问你,你是相信你的上线还是相信我?
哪有上线啊,不信你跟我去看看。
老罗突然觉得很滑稽,他们俩离得这么近,看起来很亲密——至少形式上是亲密的——心却隔着大江大河。
老虎大多时间都是低着头,说话时也是。他的头洗得很干净,连头皮屑都没有。白衬衣也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他身上有在工地上带班的痕迹。我问你,你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七个月。七个月零几天。
往屋里寄过多少钱?
工资没给全,先給生活费。
来福前儿个去医院看病你家里连五百块钱都拿不出,你知道不?
……
你一个大男人,半年不往屋里拿一分钱,你就不急?
……
对了,过年你从我手里要走的三万块钱都花哪儿了?
借给来福姨夫一万,咱爹一万。
还有一万呢?
花了。
花在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
老罗忍住气,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外面一男一女正站在屋檐下躲雨。老虎啊,那可是一万块钱啊,又不是一千两千,花了不知道花哪儿了,鬼信啊?你过个年能花那么多?老罗边说边打开手机的订票软件,回程的高铁一周内都没票。
你不相信我,可以跟我去看看。
他越让他去看,他越不去——既然不怕看,肯定是早准备好了,用一个实体来掩护。传销可能都这样。
老虎看老罗不说话,以为被他说动了。我真是在做工程,不信你去看看。顿了顿,又补充一句,这对我是一个机会。
机会?老罗心里想笑,你真相信天上掉馅饼?
富人眼里都是机会,穷人眼里都是陷阱。
这话肯定不是老虎自己的。老虎初中都没毕业,说不出这么有哲理的话,肯定是人家给他洗脑时的励志口号。老罗一时无语,他成穷人了,弟弟老虎成了富人。窗外躲雨的那个男的像是说了句什么,女的气鼓鼓地走进雨里,同时把手里的塑料袋扔了出去。男人跟出来,捡起从塑料袋里滚出来的番茄,青菜。老罗转过身,我问你,你是有资金啊还是有技术?让你入股,老板脑子进水了……你前年在家里是不是输了一万块钱?是不是借来福舅的钱还上的?
借了他一万块钱不假,不是还债。
来福舅说你是还赌博账。
我故意那样说。
老罗转过身,不是赌博输了你借一万块钱干啥?
我不能有自己的事儿?你——,老虎脸上挤出一丝笑,试图抵消话语中的坚硬,你们,就喜欢自以为是。
老罗怔了一下,你们?他想了想,老虎可能指的是他和他老婆。自以为是,老虎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老罗眼睛定在老虎裤子左兜下面一点的一个小洞上。洞有小手指甲大小,像是烟烧的。白衬衣,黑裤子,黑皮鞋,老虎显然是照城里人的标准穿的——搞传销的人肯定得比打工仔讲究。老罗一时有点心酸,老虎的裤子和皮鞋都太厚实了,与这个季节明显不搭。他想了想老虎的年龄,他应该是七三年的,四十六岁。老罗坐回到床边,你们,自以为是,老虎可能是指责他们平日里太高高在上。他想拍拍老虎的肩膀,又觉得这动作于他们兄弟太生疏——弯不能拐得太突然,怪难为情的。他又站了起来,老虎便又矮了一截。
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老罗实在是没词了,该说的都说了——他以为见了面就能说服老虎的。他安慰自己,别跟老虎一般见识,老虎的脑袋肯定是被洗过了,像他身上的衣服一样,洗得干干净净。确切地说,他已经不是老虎了,他只是披着老虎的皮囊,像科幻电影里的未来人,换了大脑。老罗在手机上找回程的火车票,座位票没了,卧铺更没有——一周内的卧铺都没有。
你到底愿不愿意回去?老罗的语气重新温和起来。
过几天吧,我这样咋回去?
你哪样了?
你们都说我在搞传销。老虎用的还是你们。
老罗顾不上老虎了,订票软件里突然出现一张当天下午的座位票,他得抢过来——最近一周的座位票都没有了。他想回去,越快越好。是的,老虎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即使走错路,老罗也不能强迫他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作为兄长,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老罗心里安慰自己。
母亲打来电话,老罗拿起手机再次走到窗户旁。雨下大了,还有风。玻璃上淋了雨,看不清外面的物景。母亲电话里问这边的情况,老罗不想让旁边的老虎听到,语焉不详地嗯了几声。母亲问,你跟老虎在一起?老罗说是。家里怎么样?想想不对,刚出来两天,家里能怎么样?紧接着又问了句,还在下雨?母亲也嗯了一声,一直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