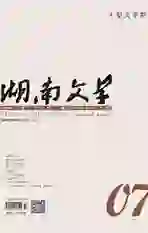我看你的山外青山(外一篇)
2019-07-30彭澎
彭澎
A面
风吹在远处,东一丝,西一缕,纹理曲曲弯弯,也时不时飘过身边来,轻轻贴一下,又远远飞离。阳光当然是好阳光,净洁透亮,照亮新旧交替的江河,不低不高。此时我一个人端坐纳雍河边,是三岔河的交汇处,岩壁高危,静水深流,山间的青葱与水面的幽绿,实实嵌在一处,山水的清妙抬眼便见,岩崖间的皱褶与皲裂,构成丰饶而沉厚的色谱,勾勒披皴,点点滴滴,在阳光的反衬中,汇聚成静美画轴。河从容着在面前流过,除了看到风吹过时的轻浅纹路,我看不清河流前行的方向,一点都看不清楚。其实,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并不重要,河流依然还是老样子,一如既往,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如同此时,它默不作声,一往直前地静静流淌。
在更多的地方,河流是大地的经络,是兄弟,是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割,历史见证着它,它也见证着历史。河流不言,却也能自然分出疆域,眼前的地方,是三县交界的所在,分属两个地区。我脚下隶属纳雍地界,对面为织金,右边则为六枝。天高,云却不淡,四下明亮澄明,环望或者俯仰,周遭的点滴,大事小物都看得清清楚楚。河唤作纳雍河,到底是因河得县名,还是因县名而得河名,我没有问过。只是后来,从百度地图上查看此河流向时,推测纳雍河当是后来当地的命名,应该特指纳雍一段。因为这条河在地图上,起止皆称三岔河,即从发源地赫章大韭菜坪附近开始,到汇入东风水库止。其流向大致为,三岔河辗转至赫章兴发、松林坡一带后,进入水城,之后分别流经纳雍、六枝、普定、织金、平坝、清镇、黔西等县区,一直到汇入黔西的东风水库化屋基,即乌江南源与北源的交汇处。之后乌江经安顺、贵阳、遵义、铜仁,入重庆黔江、涪陵,最后进入长江。顺江而下的文化,尽管地域之间相隔千里,但内里的文化,却是一脉相承。河流带给我们的,就不只是农业文明的浅层灌溉。
纳雍河所在的乌江流域,也当是拓展西黔文化的生命之源。一条河边的文化生态,往往是从源流开始,便也一直贯通始终,包括语言、习俗、风物等等,无不带着浓郁的共通标识。而这条河流之外不远的邻近地段,却多是与之大相径庭的别样天地。三岔河向西不远的六枝地界上,有河牂牁江,却是珠江流域、北盘江水系。虽说相隔不远,语言习俗这些却仿佛两个天地。一看牂牁这样的古老地名,知道其历史实在有些久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经写到过:“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纳雍河原本没有如此宏瀚,不过是一条大水,从远远的地方来,偶然地流经此地,转个弯或是在河道两侧贴一下,再竟自远去。只是前些年,下游筑了坝,建成重要的水利枢纽,水积起来,才有如此气象。绕山绕水过来,我们的车顺着这浩渺的大河边上走了不少的路程,才到得这三县交界的地方。
穿过路沿两边林木掩映的村庄,还有村庄外面的苞谷林,汽车载着我们,一路驰行。前面曲曲弯弯的流线,错落在村舍或是林木间,让来路和去途时现时隐,若有若无,有意无意间,添增了些长远的想象,右侧的纳雍河也就时不时要从右边冒出来,峰回路转,河流浩荡,静卧在数列大山之间的世界,仿佛与我们平素的日子,隔了几个区间。苞谷林地在我们眼里,习以为常,但从河北来的一敏大姐不一样,她看上去有些兴奋,说多年没见到过这样阵势的苞谷林,高大,密集,且又是如此的平静安宁,它们长在这样雄阔的大江大河边,却也并无半点张扬的模样,真是好,本本分分的,像极了抬头便见的村民。汽车继续在苞谷林间穿越,苞谷已然掰下,余下空空的秸秆,和渐次枯萎的谷穗,没有了沉重感的苞谷毕竟是孤独的,无奈的,尽管它们一棵紧挨一棵地挤着。因为头顶的天空高远而又明亮,村舍浅灰而本色,这就使得远远近近的江河水碧透无边,让人说不出一句成形的话来。
自然而然,车上的大家,之于眼前的景致,也是欣然的。舒适与愉悦,有些人现在脸上,更多的,则是在内心里激荡着,太多的风云,一些给眼里的河山,一些给远逝的旧事。面前的景致实在是好,水予人的静美,予人的清秀,予人的空灵,实在是别处给不了的。峰峦叠嶂,千山万水,佐以村舍阡陌纵横,如此完美的配搭,就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滇黔地区,惯看起伏山川的人,此时眼见着如此的风物至景,也是不能不为之动容。素来安静的黄斌兄从湖南来,大美山河自然见得多,看看眼前的世界,他还是在心下里溅射出一团一团的光焰来,说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好,堪为净土,不可方物,仿佛西藏的那些远山远水。实在地说,有这样的想法,也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單是他们,甚至于我这个本土生长的人,眼前的风光也都有太多的诱引,让我为之气爽,为之神清,有着太多的联想,一切也就再正常不过。
何况多是些来自山外的作家,平日里看惯的河山一马平川,与眼前所在,实在有些大相径庭。心下的弦被无端激荡起来,一时半会也不好停歇下去,眼里仿佛火光烛天,满目轻灵曼妙。只是把这些美妙念想,一一说与当地人,人家便有些莫名其妙,不理解,以为这样景致,实在寻常,用如此多的好辞去褒奖,实在不必要,附带讲了一句,你们说的,不外是些无中生有的东西,食指横横一指,说这些,不过是平素里天南地北涌来的水,歇在这群山间的一波闲流,如此而已,实在没必要去大惊小怪。至于好看不好看,美妙不美妙,在他们习以为常的世界里,实在值不得说。故而有外地作家说起你们生活在如此的美景里面几多幸福的话题,村人更是有些漠然,甚至觉着有几分稀奇的古怪,说那是你们不久住的缘由,你长年住下来试试。作家们当然不必过多在意如此话语里的内容,止步下来,想想村人所念,细细思忖,仿佛说得也不是不得道理。
事实上,平时虽则久居这高天后土下的纳雍河边,只是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看到的,或者说看得多的,不过是景物的外相,内里的东西,灵魂的东西,要么想得原本不多,要么连想都不曾有过,对一些内核深处的理解,实则比这些偶或到来的外人还要浅陋。这世界的内核,距离他们更为遥远,更为陌生。说来这有些残酷了,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景致进入他们,还是他们进入景致,有些人疾驰,有些人缓慢,有些人,则只是一辈子都驻足于景致外边。为物所役,为景所缚,原本不是他们的愿望,却在有意无意间,固有的步履套实了村人的眼光,圈牢了村人的向往。
一个人要真正把自己看得明白,只有走出自己;一个人要从心底深爱自己的故土,也多半是从离开故土的那一时刻,才有了开始。无数次的相守,无数次的别离,再后是无数次的撕扯与靠近,历经无数的黑暗与空白,敞亮与宏阔,才会明白,原来无数的美与好,苦与乐,不过如此。有些看去遥不可及的东西,走到后来,才知道,原本和自己竟然是如此的朝夕相候。你看到的,是一种美好,别人看到的,又是别样的美好,你说出的美好,和不说出的美好,到底哪个才留存到最后,才成為真正的美好,事实上,我们已经不能完好地知晓了。知晓不知晓,有些时候,当然也是不重要的,只要有那么一个时段,你感悟到一点,也就足够。
现在不是看纳雍河最好的时节,除了一川江水有点看头,别的,也都找不到说的了。村人的说法和我们,实在不一样。再问,说的是要春天才好。哪里好呢?说哪里都好。当然这是常人的念想,毕竟艳丽的本性是最讨人欢喜的事体。以我的眼光,倒觉着眼前的世界实在大好不过,河水清洌,村舍静安,河水绿得碧玉般透彻,天也蓝得不见底板。和远远近近的山岭融在一起,偶或罩笼些薄雾,或浮游水面,或划破云山,炊烟袅袅,和风吹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有仙山琼阁的感觉,当是心静神闲的最好去处。
春天里的纳雍河虽然不曾来过,但照片却看得不少。一河两岸,满满地都种了油菜,一色纯正的黄,错落在青绿山水间,铺天盖地,袭面而来。因为一川河水的掩映,这大片的纯黄里,便透出空灵明静,透出妩媚风情,透出自然大美,手机随手一拍,都堪称大片。那样的时候,世界诚然是美好得不可细说,这也是自然中的事情。彼时山川,才从风雪中蹚过,万般的娇柔都等着层层释解开来,切切渴盼中展开,正是物事最美的时辰。抬眼,便多是温煦春风,天舒地展,面颜葱郁,看哪哪好,大地自带光芒,透出活活的气来。冬日是紧锁的,春天却是打开的,一张一弛间,世界换了崭新模样。青天与绿树,相携着,一步一步走将出来,眼里所在,尽是光华展颜的态势,上下左右,从哪里看去,都有看头,不像其他季候,只能看得到一个面,这边是有些样范,翻过来,却是寡淡无味,让人不忍卒读。
静谧间舒展的,还有大地的筋骨。
自然,此时的我仿若依旧坐在河边,整块平整的山石,方正完好地歇下我有些疲累的身子,屁股贴近石头,感觉整个心魂都扎进大地,和这周围的大山大水,仿佛已是千年的融通。大地是安稳的,心灵是安稳的,岁月也是安稳的。四下里寂然的天地,和你静静地相与对望,静静地化为一体。躲过热闹的人群,说来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是群居生物,要真躲进一个人生地荒之地,时间久了,又止不住要想回到那个世界里来,如此进进出出,如此出出进进,便也成就了人的一生。等闲半日浮生,回首已是千秋万代。
偏安一隅的净土,断然不好找得,除非你的心底,已展现出万般清明。心静,万物才可安宁,心若不宁,到了哪里,都一样左右不是。就像此时,天上的云层叠加着,变幻着,有那么一个时段,诸物静美,云朵安详,仿佛这大千的婆娑世界,原本就是如许的妙好安康。风一吹,云朵自个就不住要变换模样,飘逸着,荡漾着,转旋着,渐渐叠成一座七彩琉璃宝塔,不高不矮,中中正正,现在目前。座基倚着山棱,天空却也占去大半,与河流、山崖却是无隙地融通着,梵音袅绕,清香横溢,明晰天光刚好透亮其间,端端正正照着河滩上走来走去的人们。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知道自己离群索居只能是暂时的事情,野地闲坐,歇息片刻,便得快快回到热闹的人群里去。
祥夫先生的身子隐在一片热闹的交谈中,此刻,那些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实在有些抢眼,一个一个,沿着河滩并列着展开,把原本有些淡暗的身影,一下子从这平畴或是起伏的山水间分别出来。自然帐篷里面众人坐满,虽则是秋月,但阳光上好,直直晒上半时,脸颊也多会生疼。看到我慢慢靠近,谈话声音仿佛突然安歇下来,静谧的四周,我看到我的脚步变得充满激情。祥夫先生看我走近,起身,说我们画画儿去,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人家安排得这么周到热忱,给画个画儿,也算得一份答谢。我说那当然好啰,你的墨宝于他们,这是天大的礼物。一敏大姐在一旁,竖了大拇指,说祥夫是重情意的人,大情怀的人,了不得!祥夫先生来自山西,是作家,也是画家,书画同道,相得益彰。在我的拙眼看去,能把书画与文学都做得达到祥夫先生境界的,国内实在鲜见,其书画一脉,家学渊源,童子功扎实,中有旧学的传统,也有之后以文化人的明心彻悟。
用于书画的台子,在上一个阶梯间,我们轻松地跃了上去。适时,散文诗杂志社主编冯明德老师正好准备收笔歇息,冯老师一手汉隶写得雄放洒脱,结体秀逸,清雅端庄。尤其擅画各色蚂蚁,千姿百态,飞花流云,楚楚动人。取下墨镜放好,祥夫先生看了远处一眼,这边我也给他铺好宣纸,轻稳下笔,峰回路转间,看得出祥夫先生画的是梅花,虬枝旋舞,花蕊清幽,万般风雷隐藏在平实的笔意里。动作有些洒脱,剑走龙蛇,意纵神横,起承转合之间透出的,不只是笔墨功夫,更多的,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丰厚学养。只是材料准备有限,有墨汁,并无国画颜料,画笔下的梅花,便只能是水墨效果。祥夫先生说,这大山大水间画下的东西,理当得天地性灵,水墨笔意实在不能真正传神,致知于内里。见边上有茶,说好在有茶,祥夫先生的意思,是以茶汁替代颜料。这一点,我一下子明白过来,遂起身捉茶,加水,少顷,酽酽泡出一杯好茶过来。祥夫先生说,这样的茶汤作画,轻重淡湿更有讲究,说来,比颜料画去还难,不能太实,也不能可太虚,力度尤其讲究。边说边动,笔锋走过,仿佛只有浅浅水印。祥夫先生一边画,一边说不急的,只等装裱上墙,这些隐藏在水印间的花瓣,立时便会鲜美弥散,透纸而出。围在四周的人,当然只能是一脸茫然。
祥夫先生有些不自觉地,环顾四周,仿佛一切还是老样,只是黄昏一下子就来到眼前,天边的云彩是无边的宽阔,早时明艳的大河之水却也沉静在暗影里去。我们走下台阶,音乐响了起来,这时河岸边的篝火已经点燃,火光冲天腾起,好像是要追着还有些残留在天际边丝丝缕缕的霞光。只几步,我们到得篝火边上,接过那边伸过来的手,融进了绕火而舞的队伍里去。乐音柔婉,我们都有些不能自已,跳转起来,神情是有些夸张随性,步履却是轻灵欢畅,回头看去,一束束亮光映红大家的脸,动作都有些相仿,脸侧仰,眼微闭,沉浸在这无边的欢乐里。我顺着看过去,文清丽、唐涓、蒋蓝、刘照进、甫跃辉、孟小书等等,全都在这个队伍里,我们和他们,两两相忘,全都不去想及这个世界,原本是如此的俊美。柴火在夜空里燃烧的声音是净洁的,脆爽的,火星飘荡的地方却是遥远的,深邃的。篝火是不知道停歇的,除非燃尽;我们也是不知道停歇的,除非离开。
我们大都知道,黔地的文明,在现代交通不曾通畅的时代,主要是仰仗河流运输,借助河海,打开与外面世界的往来,和域外的文明才真正接轨。这样说来,河流在农业文明时期起着的作用,不只是生命之源,还是他们对外交流与联络的动脉血管。单说西黔毕节,明清以前,当为贵州最是发达地区,盖因她的辖地范围,多有大河环绕,溪涧纵横。西黔说来本是福地,赤水河与乌江,环绕左右,再不必说它们的支流,毛细血管一样横贯全境。越过赤水河,毗邻的四川,便到得脚下,西黔自来多受川地文明影响,近朱者赤,一切说来也就有些理所当然。赤水河分开两省,语言习俗、人情世态却是一脉相承,更多浸润过来的,当然不只这些,而更为根本的,当是域外文明对蛮荒之地启蒙的肇始。有了阳光,土质也好,西黔这片化外之地,自然而然富裕丰厚起来。
B面
雾是有些重了,清寒阵阵,杂带冷雨吹落。幸好是秋天,要是季候再往后些,风自会刮脸,生疼,一阵紧过一阵。山高,鲜有人至,现成的路仿佛没有。越过十米外的视野,高山植物的低落与瘦矮,隐约可见,再远的地方,除了茫茫雾霭,我们再也看不到别的。眼前的雾全然不像戈乐坝子里的模样,七七八八横在半山,轻柔,通透,空灵,时不时也罩在村舍边缘。远处的农人安然走在路间,随心所欲,屋舍的安置,当然也更是随心所欲。于当地村民言,有雾霭或者雨水,再平常不过,全然不像域外的人家说像是仙境这般玄幻奇异。在他们眼里,如许说法,多少有点少见多怪,犯不着的。阡陌纵横间,阳光就要在东山边线上移出来,照亮眼前已经灿烂着的苦荞花开。
一路前行,阳光一点一点隐进坝子里,遗落在雾雨绵绵中,绕至大山的台地,坝子里夏秋的景致完全变成冬日的情形。平眼环望,此时的海拔已然超过两千米,很快接近这金蟾大山最高峰的二千四百七十六米的海拔。順着一线的草坡望过去,远处是赫章的二台坡,现在称为阿西里西大草原,再远,便是贵州最高峰的小韭菜坪,和满山长满韭菜花的大韭菜坪。近处尚有丝丝轮廓,青灰一片,再想远望,雨雾加厚,却是心力不逮,再如何使劲,看进眼里的,除了雾,还是雾。
眼前的草坡高低散乱,绿草葱蕤,错落着划向看不到的山间。想想,如果有阳光的日子,静卧向天,或是在草丛间奔走,也都是舒心事情。天高地远,风物清净,除了予人美好,可观可玩,也适合养羊养牛,成全一个牧人平实的梦想。有着这样的念头,转眼,便看到真有牧人顺坡走了过来,披了高原人欢喜用着的披毡,脸油黑,声音洪朗,身手轻捷。牧人跟在众羊后面,不近不远地跟随,不说话,默默地走,行走过程不疾不徐,从山坡的阴面走向山坡的阳面,再去到更为迢遥的地方。其实他要说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说给羊听,说给风听。山太大,风也太大,说的话声调纵然再猛,此刻也是小的,天地太大,还没传出多远,就又自个拆散开去,或是让雾挡了,重新环绕在自己身边。次数一多,便觉是说给自己听,还更要好些,不累人。
山势渐高,草坡去远,眼里看到的,全是铅灰色调,山势一如既往起伏着,一波一波隐约在雾色里。半山铺满细瘦山竹,风贴地吹来,竹枝轻柔曼妙,招摇在万千的波澜里。好在山竹是聚群而居,一簇紧挨一簇,在荒清的山间,倒也感受不到独处的无奈与惶恐。风吹向山竹,他们有些情不自禁,晃荡来,晃荡去,看上去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因为冷寒,为着取暖,总是要相互推搡和挤拥,几个回合,身子里便也充满暖意,冷都去了一边。风从东边来,他们便齐齐倒往西边,风再从南边来,他们便齐齐地倒往北边,向来无人违拗规则,简直就是一群听话的孩子。
问边上的纳雍朋友,知道本地人称这种山竹叫做滑竹,平常并无他用,多数时候,只是一任他们生生息息,终老远山,为这荒清山地,添增些绿色。仿佛他的存在,与低处的村舍并无半点关联,与更远的山外青山,更是毫无半点联系了。说他没有半点关联也不确切,说起早些年,他们是有大用处的,只是那些,都封存在一代人心底,慢慢被村人,或者乡村遗忘。那时的乡村,物资并不如现今富足,少砖石木料,滑竹可以作为山墙的充体,细细密密编织成墙,时值大夏,清风透墙而过,杂带的滋味里面,有了清竹养心的成分。天气再冷些,滑竹也慢慢干透,面上就得再敷上一层牛粪或是五色稀泥,北风渐进,次日可见两者均已死死粘连,如此即可挡风避雨,屋里的煤火或者炭火的暖度,也轻易不好散失。彼时行走西黔山间,农家的屋舍,也多是如此建构。这样品类的滑竹,附近的大山也多,近的在二台坡一带,再远些,威宁的百草坪四处都有,据说,素以滑竹为食的当地山羊,肉味鲜美,少有膻味。后来查资料,知道滑竹又叫作箭竹,大熊猫的特有食品,这就高端了,就有了些许精妙的联想,止都止不住。
这海拔是一点一点高去,眼里的植物品类也零落稀疏,到得山顶,看到的,就只有伏地的山草,也杂一些开满花的灌木。火棘蓼、续断之类,开得铺天盖地,山是青苍的,白色或是紫色的花,也就愈发耀眼,眼前一应铺得满满当当。雾气实在厚重,只是这山间,天高地阔,不染尘埃,万物都是养人的,轻轻吸一口,神清气爽,纵然翻山过岭,一路奔劳,长长吐纳一气,力量重又回到皮肉和筋骨里来。天地终于通透,攀上高高的山顶,雾气荡开,现于眼前的,却又有了另外一重山的巍峨,一重一重。穷尽这无边的万重青山,能否有了心间的远方,而那样的所在,又当是如何的境地,能否容我们歇下这七尺之躯?想想,答案是也不是,左右摇摆,多想几回,思绪里面有了些异样,索性把一切放回心里去。不去想,也不念,定定看向迢遥的天外,一言不发。
这伏地的巨蟾也真是形神体貌皆备,首尾安好俱全,背脊呈三十度的斜面,让人可以轻缓而上,头部上扬,沉稳厚实,如此方位看去,比起在半山或者山脚看到的,又多了些具象的本真。金蟾即蟾蜍,有招财进宝之美意。在本地,此物称赖疙宝,早先,本地人对此山的称呼,也都叫着赖疙宝大山,后来因为宣传一类的想法,方才有了如今的名字。我们从万山之间走过,峰峦叠嶂间,上了这金蟾大山的峰顶,众峦之巅,一览山小。朝向峰顶的路是没有的,从一蓬蓬安宁的植物间走过,到了顶部,所见便只有灌木和草丛,长势也还茂密,青葱一片。慢慢上去,在金蟾的头部,忽然之间四下里燥热着,感觉少了适才的安静,热闹起来,有一种状如蚂蚁的蚊子飞旋着,时而歇在草间,时而腾空飞扬,飞落我们衣服上,密密麻麻,让人不寒而栗。并不噬人,只是绕在你身边,飞或爬,有些让人不自觉地心生烦躁。据随行的羊场民族乡党委书记郝庆说,此处的蚊子,无论天热天冷,无论晴天雨天,包括雪凝天,也都一样多。据当地人说法,因为金蟾平素里皆以蚊虫为食,这些飞蚂蚁自然也就是为着供养他,而安静地生活在这大山一隅,陪伴金蟾这神来之物。说来也真是奇怪,等我们下到平地,刚才纷繁的闹热早已消弭隐遁,四下里只有众山清寂的安宁。
斜斜走下山去,悠长的一段路是穿林而过,头顶上的树枝参差交叠,中间是前些年砍出的通道,里许路程。偶或阳光耀照,树缝间落下筛点一般的几许光泽,眼里的世界愈发幽深、玄幻,仿佛时光隧道。因着常年温润湿软,今年的落叶盖住了去年的光阴,一层一叠,紧相依存在一处,不分彼此。这样的地方,是极易滋生诸多另类物种的,诚然,衍生别样的婆娑妙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时的山间,已然远离红尘,清雅安适,多有合抱之树,树身一应青苔缀满,虬枝纵横,听闻丛林之外不远,还有一林稀世的珙桐。随眼可见的枫树,或者杜鹃,或者栎树,也都按着自己的念想,长成自己的样范。只是空间逼仄了些,也就齐齐拥挤在一起,把原本广大的天空,掩映得只余下树影和风声。仿佛历经了一次曼妙的极地探幽,我们走出这长长的通道,眼前洞开的世界,实在美好,不能一一言说。花开一地,朝天罐、龙胆草、旋覆花、紫荆花等等,目不暇接,接踵而至,次第现在眼前,引我们走将过来。
恰是一湾清流去远
大湾苗寨我是第二次来。
两次去的时间,都是午后。阳光轻,众山青翠,依旧是水洗过的天空,依旧是清浅的米酒,连同浓郁人情。一杯一杯喝下,有些醺醺然,云里雾里,不必知道身在何处。原路回程,之前的印记了无痕迹,唯觉路道弯扭,东倒西晃,比全车的人醉得多,人醉酒了,感觉车也是醉的。好在是万物浸于暗夜,看不分明,优哉游哉,须臾回到住处去,也就觉得,万般的好,还在酒里。两次的场景,大同小异,有些相像,也有些不同,起初是会有些分别,酒一杯一杯喝下,细节零乱开去,自然分不清楚哪些是前次的,哪些是后面一次的。分不清楚也没问题,有些东西,原本就不必清楚,脉络太过明晓,神情过于清明,看到的,便也多是枯枝残屑,横七竖八,反倒没了原本滋味。
翻过山的垭口,众山腾越,地脉逶迤,左右看过,皆是青绿山水。像上次一样,中巴车照例斜斜停歇下来,让我们下车,看看天空,看看远近山水,还有,就是山脚古树掩映、一弯河水环绕着的寨子。俯视的角度真是好,整个画面的组构天然自成,房屋错落有致,龙脊轻扬。眼光轻扫,形如半阙八卦的摆布,安然停歇在安然的大地深处。蜿蜒去了别外的半阙,陷隐青山,仿佛在,仿佛也不在。寨子隐约,屋宇幽亮,雨水天的寨子会有些潮潮的水雾,大约和环绕寨子的一湾河水有着太大的关联。雨后,正好有阳光从别处铺陈过来,寨子看上去会更养眼些,天光环照,一点一点,让看得到的天地透亮起来,看不到的地方,当然也是透亮的,只是我们眼力不够,看不分明。想来,万般物事都是有趣的,有些迷离,也有些清幽。我慢慢走向远处,移开这沉重的肉身,又一道光照过来,亮处更亮,暗处更暗了。在这样的千山万壑之间,说来,有这样的配搭,当是好的画图,画画写字者欢喜,山水也是欢喜的。
雨水是有些随意,刚刚进得寨门,稀里哗啦下了起来,并无半点章法,乱七八糟的。山寨里的雨水不像城里,会沾满过多尘土和喧嚣,落到哪里,都要留下些印痕,花一块黑一块的,雨水原本的样子,掩得深,輕易不好见到本相。眼前的雨水还没走样,除了自身,再没有别的成分,清亮,纯美,孩子一样,落到树上、屋檐,或者地上,安安静静的。从里到外,干净,也纯粹,落在身上,是干净的,落在脸上,也是干净的。大湾的雨有趣,进得寨子,急急地来,追在我们后边,像是赶路。我们跑到别人家的屋檐下面,雨住了,止歇的速度让我们有些赫然,措手不及。雨脚还没落定,太阳破开薄云,晃荡着,钻了出来,万丈光芒,像是一下子打开了整个雨水洗过的世界,敞亮、净洁。阳光此时是温顺的,悠缓的,从满山的树影间穿透过来,浅浅地,照见青绿的木草,丝丝缕缕,明晰着它们生命中的暗纹。阳光再偏一些,斜斜落满峡谷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生灵们,随即重新换回原色。
阳光从别人家的屋檐下照过来,随随便便,就和邻家搭在一起,这样的光,起初是一点两点,慢慢地,就哗啦一下铺开,整个寨子俨然悉数打开,展现在众人面前。又一阵阳光照来,亮的地方暗了,暗的地方,却是明亮得让我们说不出话来。倘若航拍,角度也好,侧光逆光相宜,便有了大片的滋味。黄昏伴随敬酒歌一起到来,一起到来的,还有高悬的银制头饰,鲜艳的服饰,连同一张张纯厚的笑颜,寨子里的苗家女子,手里捧酒碗,唱着酒歌,袅袅而至,歌声还没到得眼前,酒碗已然递到唇边,想躲都无法找到去处。
劝酒的阵势,进寨子门口时已经领教过,装在牛角里的酒,顺着笑容一起递将过来,喝也要喝,不喝也得喝,架势是饱满的,热忱的,强劲的。酒量大者,张口随灌,任酒水从嘴角边泄出,也不计较,一博众人的喝彩,图个好耍,也省得多耗口舌。反正这样的酒,须臾也醉不得人。嘴早让牛角卡紧,轻易也不好挪移,酒量小或者不知道酒力劲道的,只能用舌头抵住,尽量不让酒入喉咙,如是者三,别人见到此般行为,也不好再作勉强,悻悻然,把酒递向下一个客人。
酒是自己家酿造的米酒,微甜,酒精度低,类似我们西黔的水花酒,不同于烧酒做法,是将粮食蒸煮后,加入酒曲,发酵蒸馏而成。水花酒的做法,少了蒸馏工序,直接将米糟与酒曲装入陶罐,密闭三两月即可。色泽多为乳白,略微浑浊,间或漂一两朵米花,表明着它的来头纯正,不杂假。酒的味感绵长,入口湿润,舒适,不像白酒辣烈,躁心乱神。只是像人一样,再温顺的人也有脾性,诚然,再顺口的酒也会醉人。大湾米酒的醉人,我上次就见识过了,感觉有些像行走晚夜里的丛林,远远看到灯光,细细地透着迷茫,一点一点靠近,却也是老是走不拢,但也不能说停就停,就一直往前走去,去到哪里,没人会问,当然也问不出结果来。酒意是慢慢到来的,从远及近,由左右而至心间。缓缓悠悠,身子无端轻柔起来,脚步飘荡,云里雾里。酒不醉则个,实实醉倒,三两天酒意都会缠身不离,纵是心有万念,却是手脚无力,动弹不起,把个稀奇摆你面前,你也无法消用,无法。
歌声四起时,我发觉自己是有些酒醉,整个世界也是酒醉的,抬眼四顾,一切变得轻轻悄悄,世界虚幻,伴有率性的晃荡,频率不高,却不曾有着半宿的停歇。绕着村庄环行的河水声,不时传来,恰是一湾清流,竟自向远。天光暗下来,眼里所见,是一叠紧跟一叠的屋脊,不时涌来,不时涌来,尘世静安,有迷醉的美好。身体时有异样感觉,仿佛在不同的维度,来回变幻,有时是自己的,有时又觉着不是。远处的人,突然向我走近,还没到得眼前,又急急去了别处。思绪停歇下来,酒又让人端到唇边。早省了推却,唯余下豪情,手起杯尽,落得四处一片叫好,早忘记诸般禁忌,纯粹的随心所欲。
酒量有些透支,欢喜于酒场的时段,心志上也错过了,平日里能躲开的酒事,一应主动让开,再不敢凑近。偶或遇着,也只是撤在一边,坐看别人的闹热。我现在是爱说一句话,早先酒量大,经常醉着,时今酒量小了,也就难得醉上一回。说的也真是实情。早时,自恃有量,加之年少轻狂,有人挑战,每每便也主动迎击,单挑十来个回合,算得轻松事情。胆气在,豪情饱满,从来不曾惧场,彼时,不只是酒量大,醉量更大。不酒醉沙场,仿佛对不住自己。想来也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又能有几个全身而退?醉酒,成了常态,也自然而然。
年齿渐长,历事繁复,身子也日渐与酒精相忤,时日稍久,酒量自个小了下来。于酒之态度,早少了旧时的横冲直撞,多是躲,是退,是让,是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如此心境,想醉也多是不太可能。情致上的抽身,行为上的远离,在时常往来的友朋里面,时今大都把我定义在不事烟酒之流,烟我是没抽过的,记事以来,从来没有吸过。但就在此时的大湾,我已经少了早先时候的念想,不曾沉醉在苗家米酒里,哪里对得住如此美好的夜晚。把自己生生地往酒事里推,一推,再推,推我的,除了自己,自然还有祥夫先生。他推我,我也推他,两三回合下来,酒还没走远,歌声就落在跟前,醉意便也泛开,东奔西突,直直地把我们导入一个别致的景地里,不醉也都不太可能。
心是异样的,步子也是异样的,心火四处流窜,让人丝毫不可安坐在临河的长椅,好生吃完一杯米酒,或是搛一箸野菜。身边的祥夫先生也喝得不少,他的心里,定然也不安宁,回头看到的,是一张酒红的笑脸,我以为,此时才是本真的祥夫先生。祥夫先生是平和的,是安逸的,不装模作样,唱歌,也唱戏,唱作也不似早时的板正,手眼相随,率性,夸张,透出文化人的真性真情。也大口喝酒,自己喝,对不时递过来的敬酒,更是来者不拒,真真切切喝出一份爽气来,全然少了适才在老滕家临河的书屋里,写字画画时的谨严和沉静。
雨水过后,寨子里的灼热又慢慢回来,雜着水雾清凉,在河风里吹过来,再吹过去。顺着河水吹去吹来,好纵是好,只是时间久了,也是会累。好在阳光适时从寨子的屋檐边跌落,仿佛有了牵引,有了由头,那些吹累了的风,径直去往寨子上空。一起来的十多个人,一一坐在老滕家河边的回廊间,喝茶或者说闲话,阳光有时照在大家的脸上,有时照在回廊的影子里。有时是直照,有时又多是横斜。其实这些,于此间的人,都不要紧,甚至可以说成是阳光照或不照,有阳光没阳光,并没有太多的人在意。他们已然拥有了各自的一己世界,不再理料别人,只在意自家,说来这也好理解。谁也不管谁,喝茶的继续喝茶,说闲话的继续说闲话。那边有人过来,说宣纸和笔墨都准备好了,祥夫先生说,走,我们写字去。
是一个典型的书房,不大,收拾得却也规整,老滕在城里工作,整个格局也就有了城里的模样。笔墨和案桌都是新的,看上去,闲摆的时间定然比用的时间要长,整个境地,是还有些生硬,平日里少有侍弄,欠缺人的气息,不够温润,有一道无形的影,横在那里。祥夫先生把宣纸铺好,抬头四顾,随即慢慢默下头来。捉笔蘸墨时,嬉笑收住,一脸的正经,神色便和平日里有了差别。始终不离的墨镜,顺屋外透进的阳光间看去,愈发黝黑,也就无法看清他的眼神和心念。
祥夫先生的文字好,吃饭的活路,自然不消多说;国画是童子功,家学深厚,功课经年不辍,当然也好。从我的理解上,觉着他是作家中最好的画家,画家中最好的作家,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说法,他当是作家中最好的作家,画家中最好的画家。所见作品,多为国画,花鸟草虫或者人物山水,布局多有八大之风,笔墨得宾虹精髓。他笔墨之间的滋味,比好多所谓的专业画家还要精妙,还要让人沉迷。大抵是因了文养的缘故,不只是手上功夫得行,心上功夫更是少有人跟踵。多的是文化意味,少了匠心雕琢的痕迹。祥夫先生环顾左右,笔墨荡开,便也画将起来。那样的时刻,除了翰墨清香,再无别样。
午后的阳光慢慢矮下来,四处的绿树高出视野。我走出门来,一湾流水依旧如常,兀自去远。清水是安静的,阳光是安静的,整个寨子也是安静的,自然,我也是安静的。只是我不知道,再过一个小时,我会被这安静的清水酿造的安静米酒醉得不再安宁,分不出南北,分不出东西,闹腾着,一点一点,忘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