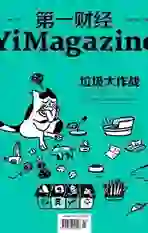拍完《人间世》才知道活着就是幸运
2019-07-25郑晶敏
郑晶敏
2019年6月14日晚,站在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颁奖舞台上,范士广接过了奖杯,他导演的纪录片《人间世》第二季获得了最佳系列纪录片奖,这部将镜头聚焦在医院的纪录片是他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至今在豆瓣上依然保持着9.6的高分。
与他一同担任这部纪录片的导演的,是他相识已久的搭档秦博—曾经的同窗,如今的同事。
在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广播电视艺术专业读研究生时,秦博没有想到那个早晨爱在宿舍阳台背古诗词的室友会成为自己职业生涯里的重要搭档。两人的身上有很多共性,比如都来自河南,也都曾因为高考失利而选择复读,只不过相比范士广在第二年就考进自己理想的大学,秦博算是经历了一些坎坷。
复读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局,秦博考入了一所航空院校。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对文字和影像的敏感终于在大学里获得了释放。整个大学期间,秦博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看电影。“我的阅片量基本都是在大学时积累的。”于是大四那年,秦博决定考研,报考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专业基础是秦博的软肋,直接导致了他第一次考研的失败,但他没有放弃,毕业后,他一边在东方航空工作,一边准备“二次参战”。在航空公司,秦博的工作是结构维修,通俗点来说就是修飞机。在机场工作一年,让秦博更加确定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既定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不多,所以工作的成就感很小。”这也加深了秦博想要考研的决心。他的想法得到了车间主任的支持,即便看出他的心思不在工作上,也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他分配了更轻松的任务,好让他有更多精力学习,“他说人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才能做好。”这句话秦博一直放在心里。

第二年,秦博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大学电影学院。范士广的名字出现在秦博的后面,两人从此有了交集。毕业后,两人一同进入上海电视台,范士广在纪实频道做编导,秦博则成了新闻中心的一名调查记者。直到2015年《人间世》剧组成立,两人重聚,一同在第一季里担任编导,到了第二季,他们又同时成为导演。
《人间世》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研究生时期,秦博和范士广就拍过一部记录养老院老年人生活的纪录片《一个人老了》。现在重看,他们依然觉得这部片子虽然拍摄手法稚嫩,质感略显粗糙,但捕捉到的生活细节是动人的。
“当时有一个老伯伯要出去玩,儿子就用三轮车带着他,老人一直说‘我害怕,你拉着我的手。我跟范士广就骑了电动车跟在后面。”时隔多年,秦博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的画面。这部片子不仅让他们从技术上知道拍纪录片是怎么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拍摄和剪辑之外,学会了观察。现在,秦博仍不会回味这部片子里的片段,是反思,也是找回初心的一种方式,“那时候虽然很稚嫩,但我们能关注到生活琐碎中只言片语的温馨。”

这部早期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同样让范士广记忆犹新。“当时有个老人,太太去打牌了,他就等她回来,一边跟我讲他们的往事,一边叫我看着表,说还有十分钟她就来了,我说真的吗?过会他说还有五分钟就来了,还有一分钟就来了,到了那个点,他太太就真的进来了。”这些平淡生活中的细小温馨始终打动着范士广。
多年后,他们将这种对生活最平淡的捕捉带到了《人间世》第二季的拍摄中。在讲述认知障碍老人的《往事只能回味》一集中,秦博和范士广补全了拍摄《一个人老了》时的遗憾部分。“早先不知道,那时候的老人其实认知有问题,现在经过系统性的调研再去拍阿尔兹海默症就会有更多感触。”秦博说。《往事只能回味》采用了和《一个人老了》相同的分段叙事手法,讲述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与儿女、老伴和病友之间的故事,算是对他俩早期纪录片的一种弥补。
相比《人间世》第一季,秦博与范士广导演的第二季在记录的同时加入了更多电影化的表达方式。比如在讲述医患关系的《命运交响曲》中,让坐在医院办公室门口投诉的家属和送锦旗的家属同框,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出对于医患关系的无奈。而在讲述精神病人现状的《笼中鸟》中,摄制组发现其中一位病人写的一篇标题为《三等公民》的日记,并决定让他朗诵出来。这个画面最终被用在视频开头,一位精神病人的形象立刻呈现在观众眼前—他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
摄制组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故事的冲突感和戏剧性,但秦博始终会提醒自己要把握好这个度。纪录片拍摄的首要原则就是保持真实,和拍电影不同,纪录片里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拍摄结束了,但人物的命运还在继续。9个摄制组,50名工作人员,200多个拍摄对象构成了一部《人间世》,每拍一集就会产生10万字的场记,一季素材超过100万字。每一段素材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背后,都牵连着家人、爱人、朋友……一张由情感交织而成的细密的网。
拍摄者常常处于双重角色的转换中—作为朋友无法不动情,但作为记录者必须保持冷静。
正式拍摄之前,秦博和范士广都在医院体验了将近一年。每天进进出出,熟到连医院的保洁阿姨见到他们都会打招呼。前期调研并不是拍摄中最难的环节。最难的工作永远是和人打交道。

与患者建立信任是个漫长的过程。“人家凭什么要理解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义务配合你,拍10个故事有9个拒绝的,但你要不断敲门。”范士广说。在拍摄第一集中那个患骨癌的孩子时,孩子母亲一开始不同意,范士广与剧组和这一家人相處了两个月之后才最终获得理解。但在拍摄过程中,范士广也有不忍心的时候,只要家属要求不拍,他就会立刻放下摄影机。“人家最悲伤的时候,哭着说你别拍了,那你还拍吗?没必要,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为了增加一点煽情元素吗?太功利了!”
尽管见证了很多苦难,在拍摄现场,秦博和范士广都很少有流泪的时候。作为记录者,秦博和范士广在说服别人的同时,也在说服自己。就像主刀医生不能带着情绪进入手术室,他们也要时刻保持冷静才能捕捉到动人的细节。
“我没有哭,我们不是观众,观众才会感动、才会有同情心,如果我们感动得哭了,片子就做不了。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人在日常生活里一直哭。”范士广说。
秦博为数不多的几次流泪,是在后期整理素材的时候。一位癌症患者在拍摄期间为家人录制了告别视频,最后对着镜头对向组表达了感谢。秦博在剪辑室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很多时候,感动人的往往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们在经历苦难时还能保持善良。“你的摄像机是打扰人的,他们没有从你这获得什么,而你是三番两次在打扰,记录的素材越多,片子拍得越好,打扰的程度就越深。看素材的时候能看到他们的体谅和对我们的善意,那个时候尤其觉得难受。”
接受采访前几天,曾参与拍摄的一位小朋友去世了,为了完成她母亲的愿望,整个剧组都在整理她的素材。秦博内心是矛盾的。没有人喜欢悲剧,谁都想患者能痊愈,但现实中总是会有人离去,而在这个时候,他又必须去记录。
遗憾无可避免,某种意义上,《人间世》就是一部记录遗憾的作品。人无法掌控生死,为了展现真实,记录者必须冷静。但在镜头之外,秦博和范士广都在尽力表达善意和温情。导演《人间世》为他们带来了名声、荣誉和关注,但更重要的改变在于,镜头中记录的每一个人都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时刻提醒着他们:活着就是幸运。
因为争取到了进入手术室的机会,在《人间世》的成片里,你可以看到大量直观的手术镜头,跳动的心脏、取出后等待移植的肺、浸满血的纱布……但在范士广的回忆里,回想起手术室的拍摄,他想到的不是血腥的画面,而是类似头发丝烧着的气味,那是高温手术电刀割破皮肤后,蛋白质燃烧的味道。
对生命的领悟往往不是波澜壮阔的,而是在生活的细流里慢慢显现。接受采访前,范士广刚刚陪妻子做完产检,他珍惜这一刻。与爱人一起迎接新生命,是他此刻生活中最美好的事。
Yi YiMagazine Q Qin Bo
Yi 《人间世》第三季打算拍摄什么题材?
Q 第三季正在筹备。但我们希望我们的纪录片跟别的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就是新闻气质。所以即便不是做医疗,肯定也会碰触社会敏感话题,这是我们坚持的。
Yi 拍摄《人间世》第二季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Q 拍完之后需要充电,一直在往外掏。越来越感受到非虚构写作是个综合性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经过系统性的文学培养,不能一直靠耍小聪明,还是要看大师的作品。
Yi 做调查记者的那几年对你拍摄纪录片有什么帮助?
Q 我最想做的其实是影视。以后不拍纪录片也说不准。这是个过程,也是个财富。我经常觉得自己是曲线救国,你以后做的事情肯定跟你过往的经历有关,这些经历就是财富。为什么是枝裕和可以写出《无人知晓》,那就是一个刊登在报刊上的很小的新闻。所以影视和新闻、社会现实是相关的。
Yi YiMagazine F Fan Shiguang
Yi 拍摄《人间世》第二季对你来说有遗憾吗?
F 没有遗憾。第一,倾尽全力了。第二,我们拍的都是真的生活,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种遗憾。我拍那么多故事,哪个故事没遗憾?儿子拼命劝说父亲换肺,最后换好了,人死了,遗憾吧?妈妈有了先天性心脏病,一定要生孩子,医生说你不能生,孩子生下来她死了,遗憾吧?记录了很多遗憾,我们的遗憾算什么。
Yi 作品播出后受到很多评价,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
F 别人都说我们是医疗类纪录片,我很反对,我们只是披了医疗的外衣,讲的还是中国人的情感维系,说白了我们就是一个情感类纪录片。医疗不是我们想表达的重点,发生在医院里是跟医疗相关,但一定不是说这个医疗器械多厉害,不是单纯说这个医生经历了多少困难把病人救活了,这样讲太片面了。第二季最后一集我们讲一个儿科医生,表现更多的是她把人救活了,但愧对自己的孩子。她9岁的孩子马上要考试,她没有时间管,但在病人的生命面前她只能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