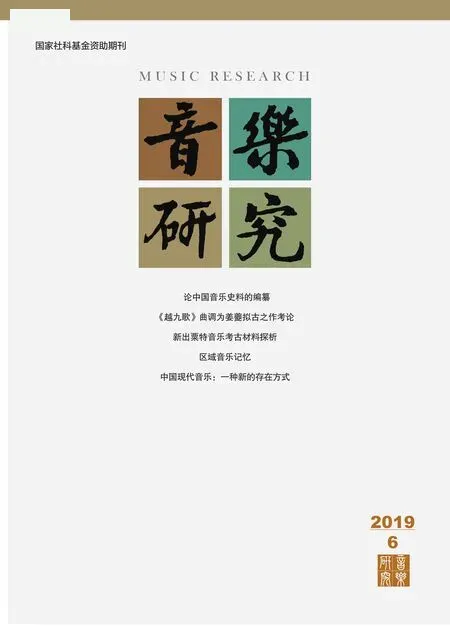新出粟特音乐考古材料探析
2019-07-21文◎吴洁
文◎吴 洁
一、对新材料的初步认识
卡菲尔-卡拉(Kafir Kala)是近年国际考古学界尤为关注的一座丝绸之路城市遗址,它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南部,达尔古姆运河左岸,距阿弗拉西阿卜东南方向约18 公里。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5—6 世纪。2017 年,日本帝塚山大学—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对卡菲尔-卡拉城堡北部建筑群进行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近方形的装饰木板、木质拱门残件,以及数块木板残片。木板的房间位于宫殿的正中央,可能是一处具有接待功能的大厅,这些装饰木雕发现于房间内拱门背后的土层下。其中,方形的装饰木板原本挂在墙上,经焚烧后脱落,木板上的图案经修复后主体部分已大致可以分辨,所表现的音乐图像尤为引人注目。2018 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对这件材料的基本信息做了简要介绍。①关于木雕装饰板,简报描述如下:“长141 厘米,宽124 厘米,由两块厚度不到0.5 厘米的木板以铁箍固定、拼接而成。木板表面雕刻的图像内容完整。46 位不同的人物分列四层,展现神祇崇拜的主题。”Amriddin Berdimuradov,Gennady Bogomolov,Alisher Begmatov,Uno Takao,“Уникальные находки с городища Кафиркала”,Фан ва турмуш,2018,pp.9.以下,就图像的题材、主题和未涉及的细节略加申说。
这是一幅展现琐罗亚斯德教题材的图像(图1)。娜娜女神位于上两层的中心位置,体型明显大于周边人物。这种构图形式在粟特地区十分常见,在邻近的片治肯特遗址发现的多幅壁画上,娜娜女神的大小比例和出现位置也是如此,反映了该地区对于娜娜女神的尊崇。进一步观察这例娜娜女神图像,她右手握束发带,左手持权杖,头戴羽翼王冠,带头光,两肩冒有火焰,这些都是粟特神祇的符号性元素。她身穿的紧身连衣长袍、边饰连珠纹、双臂间缠绕帔帛等,也都是典型的粟特服饰标识。两侧祭祀者二十人,分列两层,均为男性,剪发,身穿中世纪粟特服饰,腰部束带,未悬挂武器,足蹬软靴,他们面向女神站立,手持火坛、祭台、银盘等器物。女神右侧正面站立一位男性,他手持权杖,装束明显区别于其他人物,他的身份可能是王或贵族。第三层的奏乐场景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粟特音乐图像材料,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对其重点展开考释。第四层展现的祭祀场景共有十二人组成:他们以祭台为中心对称排列,每侧六人,大多单膝跪地,手持各类器物作敬献状。这些器物包括铜镜、银盘、花环,以及细颈高罐、盘口圆瓶、双耳高足杯等各种造型的器皿。显然,这件装饰木板是以祭祀娜娜女神为主题的图像学珍贵资料。
二、乐器图像考释
装饰木板的第三层传递了丰富的音乐信息。该层共有十三人,右侧六人中,有的手持花环、火坛等器物,有的吹奏角。靠近火坛位置的一人高举右臂,身体微曲,可能是歌者或乐队指挥。左侧七人中,有演奏角形竖琴、琉特琴、潘笛和短笛。两侧外端各有一位听众,双手交叉于胸前。下文将逐一对这些乐器图像进行分析,继而探讨它们在粟特和周边地区的分布。
(一)角形竖琴
竖琴发源于两河流域,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传播伴随着不同的文明而展开。以往学界对此类乐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地区,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古代粟特遗址提供了竖琴研究的新材料,表明其在中亚的地位不容忽视。
装饰木板上的角形竖琴基本延续了两河流域垂直角形竖琴的结构和形制。共鸣箱与弦杆的夹角为锐角,琴弦与弦杆垂直,共鸣箱的上部呈弧状弯曲,演奏者呈站姿竖抱乐器于怀中,乐器的底边与演奏者的腰部齐平,主要用于行进中演奏。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此类垂直式角形竖琴大约从公元1 世纪开始出现在粟特地区。例如,古撒马尔干城遗址阿弗拉西阿卜发现的奏乐雕像(图2,约公元1—3 世纪)。该图显示,竖琴的共鸣箱上部略有弯曲,顶端尖锐,内侧刻有共鸣槽,系弦杆与共鸣箱的夹角为锐角,演奏者站立,左臂抱持乐器,将共鸣箱的顶部靠在肩部,脚柱抵于腰间,双手呈拨弹状。这幅图像向我们展示了早期粟特地区角形竖琴的形制结构和演奏特征。
此类垂直式角形竖琴在粟特地区频繁出现,公元5—8 世纪使用纳骨器的葬俗相沿成风,在沙赫里萨布兹锡瓦兹遗址、玉玛拉卡特佩发现的纳骨器上都有角形竖琴图像(图3,约公元5—6 世纪)。它们形制相近,共鸣箱上部弯曲,顶端尖锐或圆润。有些细节不同于装饰木板上的角形竖琴:弦杆与共鸣箱、琴弦呈直角,底部系有坠饰,弦数不等。演奏者通常呈跪姿,将竖琴挟于臂下,底边接近演奏者的腹部,双手作拨弹状,这些纳骨器大多属于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粟特人,画面对应不同的葬仪场景。天神以奏乐的方式示意亡灵升入天国,由此可知角形竖琴具有特定的宗教功能和属性。
除了祭祀和丧葬仪式以外,这类角形竖琴也出现在世俗场合。例如,乌什鲁沙那的卡拉-伊-卡赫卡哈I 宫殿壁画(图4,约公元6—8 世纪),画面描绘了一幅宫廷奏乐场景。其中,角形竖琴共鸣箱宽阔,弯曲弧度较大,顶部尖锐,共鸣箱与弦杆的夹角,琴弦与弦杆的内角都呈锐角。有别于上述小型角形竖琴,这件大型角形竖琴弦数明显增多,共鸣箱外侧有系弦的痕迹,底部增设脚柱等细节。演奏姿势也有所不同,演奏者盘腿而坐,脚柱抵在地上,双手拨弹琴弦。此外,壁画上还有残缺的琉特琴和角形竖琴的图像,形成弦鸣乐器的组合。
综合以上图像材料来看,这类共鸣箱弯曲的垂直角形竖琴与两河流域的竖琴有着不解的渊源。乐器的形制结构和演奏姿势也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了不同的样式、演奏方式、乐器组合和功能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粟特地区发现的垂直式角形竖琴还有一类共鸣箱平直的样式。例如,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发现的奏乐浮雕(图5,约公元5—8 世纪)。这件雕像人物颧骨突出,眼睛呈杏形,左肩抵着一件角形竖琴,共鸣箱呈长方形,弦数不详,共鸣箱和弦杆的夹角呈钝角,演奏时竖置于胸前拨弹。在邻近的巴克特里亚地区也发现了此类角形竖琴。例如,埃尔塔姆遗址发现的一组希腊化柱头装饰上,就有这样一例角形竖琴(图6,约公元2—3 世纪),共鸣箱呈上宽下窄的梯形,边缘棱角分明,共鸣箱与弦杆的连接角度不详,琴弦位于斜边的位置。它与琉特琴、双面鼓等乐器进行合奏。
综观粟特地区的垂直式角形竖琴图像,共鸣箱的样式有平直形和曲形两种,新出粟特音乐考古材料中的角形竖琴属于后者。这类源于两河流域的角形竖琴,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形制多样。从图像来看,共鸣箱的弯曲弧度不一,顶部有圆润和尖利等形态,弦数在五至十余根之间不等,小型和大型角形竖琴都有出现,脚柱和坠饰等细节逐渐丰富。总的来说,垂直角形竖琴仍以双手弹拨,坐姿、站姿、跪姿皆有,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祀、丧葬仪式及宫廷宴会等不同的场合中演奏,承担不同的功能。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装饰木板上的这类角形竖琴是当时粟特地区最普遍的一种样式,反映了该地区竖琴的主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样式的角形竖琴在两河流域、北非、西亚等地早已有迹可循,以此为线索可以勾勒出古代粟特人的乐器传播及其文化流动的图景。
(二)琉特琴
琉特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的弦鸣乐器,它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说,它的传播是在两河流域、古希腊、古波斯、犍陀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互动中进行的。过去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学界对于中亚段的研究始终没有展开。近年来,新出的一些粟特音乐考古材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也使我们对于该地区的音乐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装饰木板上的两件琉特琴(图1 第三层左三、左六),琴身为梨形,琴颈修长,琴身与琴颈连接处线条圆滑,琴头平直。其中,左三这件弦轴信息明确,琴头两侧各有两枚弦轴。演奏者水平横抱乐器,左手按弦,右手拨弦,在行进中演奏。
接下来将视线延伸至粟特地区的其他考古材料。位于撒马尔干的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雕像(图7,约公元1—3 世纪)是目前可见年代较早的琉特琴图像。这件琉特琴为直项,共鸣箱圆润,刻有四根琴弦和覆手。从乐器的形制和演奏姿势来看,与卡菲尔- 卡拉遗址发现的琉特琴图像较为近似。
此类形制的琉特琴在粟特地区比比皆是。例如,卡什卡达里亚河流域发现一组公元1—3 世纪的奏乐雕像,这组琉特琴的形制和演奏方式基本一致。琴身圆润,短颈,直项,弦数有二弦、四弦。演奏时,横抱乐器于胸前,执拨和手弹皆有。另外,从乐器和人物的比例来看,早期粟特地区的短颈琉特琴尺寸不一。
再如,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发现的一组泥塑(图8,约公元5—8 世纪),其年代稍晚,尽管有的琉特琴雕刻简易,仅见共鸣箱和琴颈部分,但也展示了该地区短颈琉特琴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图8之(3)这件琉特琴,它的形制较为特殊,共鸣箱呈棒状,直项,面板上刻有四弦和覆手,与中国于阗地区留下的四弦琵琶图像及音乐文物十分接近,它体现了琉特琴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变迁。
除了直项以外,曲项短颈琉特琴也在粟特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图像(图9,约公元5—6 世纪)。锡瓦兹遗址出土的纳骨器上,左侧天神演奏的琉特琴共鸣箱为梨形,琴颈弯折呈直角,演奏者以跪姿斜抱乐器,琴头朝上。在卡拉-伊-卡赫卡哈I 宫殿壁画中,左侧乐师演奏时以坐姿斜抱琉特琴,琴头向下倾斜。
此外,位于塔什干的坎卡(Kanka)遗址也有相关发现。浮雕上的这件琉特琴(图10,约6—8 世纪),琴颈和琴头已经损毁,琴身与琴颈的连接线条流畅,面板上有两个对称的圆形音孔,刻弦两根,琴弦延伸至琴身底部。演奏者横抱乐器于胸前,琴头向下倾斜,演奏时执拨弹奏,拨子通体呈扁平状,头部尖锐。乐器形制和演奏方式与同时期的短颈琉特琴基本无异。
上述两例短颈曲项琉特琴图像中,其形制和演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持琴的角度不再是早期的水平式横抱。从这些特征中也可看出,粟特地区曲项短颈琉特琴与波斯的乌德、中国的曲项琵琶之间具有密切的渊源联系。
以上这些材料反映了短颈琉特琴在粟特地区的主流地位。这件乐器与古代粟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都是在丧葬、宴饮等不同场合中使用。公元6—8 世纪是其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胡风盛行的历史时期。大量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进一步带动了乐器的传播和发展。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葬具上就有多例执拨弹奏琵琶的图像,例如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图像。在园林宴饮场面中(图11,公元6 世纪),乐人们分别演奏曲项琵琶、直项琵琶、唢呐、竖箜篌等乐器。两位琵琶演奏者(左一、左二)均左手持拨,拨子手柄呈长条形,拨面呈扇形。
值得关注的还有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北墙上壁画——武则天泛龙舟图(图12,约公元7 世纪),描绘了盛唐时期中国宫廷的生活场景。船尾处两位女性乐人头梳椎髻,身穿唐朝服饰,分别持筝和琵琶。尽管琵琶的琴体被前排人物遮挡,但是琴头位置的五枚琴轸清晰可辨。中国俗乐器筝的出现表明了胡、俗乐的融合及中国音乐文化在粟特地区的渗透。
在历史的变迁中,粟特地区的直项和曲项短颈琉特琴衍生出了不同的样式和奏法。共鸣箱有圆形、梨形,演奏方式有拨奏和指弹。持琴的角度从水平横置发展为向下倾斜。演奏姿势中坐奏和立奏皆有,但基本为横抱,右手拨弦,左手按弦,主要用在宗教和世俗场合。除了独奏以外,比较常见的是与角形竖琴的组合。由此可知,装饰木板上的琉特琴融合了犍陀罗和波斯的特征,是当时粟特较为典型的类型,反映出该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性。
(三)潘笛
装饰木板上的潘笛由近十支长短一致的音管排成一列,以两道篾箍固定连接而成。演奏者呈站姿,双手握持潘笛两端,水平置于胸前,吹口朝向上方,与嘴部垂直。这种形制的潘笛,在粟特的中心地区片治肯特也留下了相关图像。位于6 号建筑群13 号房间北壁的这幅壁画(图13,约公元7 世纪),画面描绘了三位乐师奏乐的场景,其中,潘笛的形制和演奏方式与卡菲尔-卡拉装饰木板上的呈现基本一致。在它的两侧还有琉特琴和弓形竖琴进行合奏。
潘笛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神话,因此,早期潘笛的图像主要出现在一些神话人物的雕塑中。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遗址发现的潘与达弗涅斯雕像、希腊化时期小亚细亚发现的阿提斯雕像上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据考古材料显示,这件乐器在中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 世纪的北巴克特里亚。历史上该地区曾经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卡普尔特佩(图14,约公元前2 世纪—公元前1 世纪)、扎尔特佩(图15,约公元3—5 世纪)出土的这两件潘笛雕像年代虽然不同,但形制基本相同,均由五至七根长度一致的音管组成,以两道篾箍固定连接。乐器的形状近长方形,音管较长,底部已接近吹奏者胸腹之间的位置。演奏时双手持握笛身下方第二道篾箍,将其水平地置于身前。吹口正对嘴唇做吹奏状,这两幅图像是研究早期中亚地区潘笛的重要材料,也是希腊音乐文化在巴克特里亚的直接反映。
上述潘笛均属于笔直潘笛,它们形制单一,音管长度一致,制作简易,是早期潘笛的典型样式。在实际演奏时通常会在笛管内填充腊类材料改变音管的长度,从而演奏不同的音高。公元前2 世纪以后,潘笛的形制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长短不一的音管,即今天常见的圆弧形潘笛。综观上述,潘笛图像可大致勾勒出这件乐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分布区域与传播路径。
(四)角
装饰木板上出现的角这件乐器(图1第三层右五),传递了非常特殊的信息。一般来说,角的演奏方式主要有两种:当角体较小时,以双手持角吹奏;当角体较大时,则以左手托抱角底,右手持角身吹奏。另外,由于音色粗犷、音量较大,角通常运用于行军征战和狩猎活动,鲜少在宗教场合出现。这件图像上,角用于与竖琴、琉特等乐器合奏,并且以单手握持,情况实为罕见。新发现的这件材料增补了该类乐器在粟特地区的图像材料。
这种类型的角,在中国境内的粟特葬具中也有反映,例如山西太原发现北周虞弘墓。石椁底座刻绘的数组奏乐舞蹈人物中就有一人吹奏角(图16,公元6 世纪)。这件角的角身较短,管口呈椭圆喇叭形,细端为浅杯形吹口。它的形制和演奏方式与装饰木板上的角接近。演奏者高鼻深目,留络腮胡,身穿窄袖长衫,腰间系带,足蹬短靴,是典型的胡人形象。至于发掘简报中提到的短笛(左四),由于乐器形制并不明确,故不在此作讨论。
装饰木板第三层乐器有弦鸣和气鸣两类。弦鸣乐器方面,角形竖琴和琉特琴均成双使用。这两件乐器的音色优美,富有歌唱性,深受粟特人的青睐,是乐队中必不可少的配置。气鸣乐器方面,潘笛和短笛的音色空灵飘逸,角富有召唤力。这些乐器音色和谐,轻巧便携,经常在宗教场合使用,具有渲染气氛和颂神的功能。在已知的祭祀娜娜女神的图像中,这是粟特地区所独有的一幅奏乐祭祀图。这些乐器的组合构成了粟特地区音乐的鲜明特征。
关于粟特地区的音乐,文献中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据《魏书》卷一〇二“西域 传”载康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⑪魏收《魏书》卷102,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281 页。从这里也可以知道,琵琶和箜篌是粟特地区代表性的乐器。
公元6 世纪前后,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将粟特音乐大规模地带进中原,并逐渐形成一种风尚。据《隋书》卷十四载:“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⑫魏征《隋书》卷14,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331 页。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应该是善弹琵琶等乐器的粟特人,他们随着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进入到中原。
除了史料记载,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一些图像材料上也有反映,集中在宴饮和祭祀场景。其中,由角形竖琴发展而来的竖箜篌和由琉特琴演变而来的琵琶,仍然在乐队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安伽墓门额上表现琐罗亚斯德教祭仪的图像中,上部有两位飞天,各持竖箜篌和琵琶。又如在史君墓石棺上刻画的园林宴饮场景中(图17,公元6 世纪),竖箜篌和琵琶与横笛、腰鼓、曲项琵琶进行合奏。
三、琐罗亚斯德教祭祀仪式中的音乐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随着入华粟特人墓葬的陆续发现,学者们开始关注粟特音乐的研究,主要对葬具上的音乐图像进行考释,代表性的文论有陈海涛《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对安伽墓与虞弘墓中舞蹈归属的浅析》⑬载《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3 期。;黄云《隋唐粟特乐器研究——以西安地区6—8 世纪墓葬为例》⑭河北师范大学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林春、李金梅《古代中亚的胡腾舞考释》⑮载《敦煌学辑刊》2010 年第1 期。;周伟洲《6—7 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⑯载《文物》2012 年第4 期。;任方冰《中古入华粟特乐舞及其影响》⑰载《音乐研究》2016 年第4 期。;刘晓伟《粟特乐舞入华及其成因》⑱载《音乐研究》2016 年第4 期。;王红蕾《安伽墓乐舞图像考》⑲陕西师范大学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 陈文革《粟特人与唐乐署供奉曲般涉调部分曲目传播考——兼及中古乐伎中的粟特人成分》⑳载《音乐研究》2016 年第6 期。等。以上研究就入华粟特乐舞及其对隋唐音乐的影响做了初步探讨。另外,姜伯勤、荣新江、张庆捷、孙武军、单海澜、齐东方等一批学者也对葬具上的图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入华粟特人图像的研究相比,粟特本土的音乐图像研究还比较少。卡菲尔-卡拉遗址发现的这件材料无疑为粟特音乐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图像不仅提供丰富的音乐信息,也蕴含特定的宗教内涵。以下,本文试图对琐罗亚斯德教祭祀仪式中的音乐场景做进一步的解读。
这幅关于娜娜女神的祭祀奏乐图像共有四层,每层用纹饰带隔开,形成独立的单元。第一层以主神娜娜为中心,参与祭祀仪式的人员中有一位身份尊贵的王或贵族。其余人物服饰统一,面朝娜娜女神,手持各种造型的火坛。画面展现了一个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仪式场景。第二层的祭祀人员形象与第一层接近,但是手持的器物更加丰富,有铜镜、银盘、缎带等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用具。第三层的人物形象多样,体态舒展放松。他们以火坛为中心分列两侧,左侧主要演奏粟特地区的各种乐器,右侧手持花环、器皿等祭品,从而构成奏乐和祭祀同步进行的场景。第四层的人物地位最低,大多数呈跪姿,执各类胡瓶作敬献状。画面的整体布局规整有序,不仅突显出娜娜女神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表明了神祇和人物之间的尊卑关系,暗示琐罗亚斯德教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这是一个比较庄严的祭祀仪式。乐队出现在第三层,即神祇和人物之间的位置,是人和神之间沟通的媒介。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发现的粟特葬具上也有一幅祭祀乐舞图像,即日本美秀美术馆藏公元6 世纪石棺床上的娜娜神祠图(图18,公元6 世纪)。画面分为三个部分,上方是一位四臂娜娜女神,中间有两位伎乐天人,分别演奏琵琶和竖箜篌。其中琵琶的音箱呈葫芦形,竖箜篌的音箱瘦窄。它们在此寓意天国之声,具有特定的宗教含义。下方则有一组乐舞图像,表现了在神殿或殿前跳舞祭祀的情形。中间的一位女性舞伎身穿中原样式的长袖宽袍,甩袖起舞。两侧的伴奏乐队共十人,演奏曲项琵琶、直项琵琶、竖箜篌、铜钹、横笛、筚篥、笙等乐器。乐器配置以弦鸣乐器(直项琵琶、曲项琵琶、竖箜篌)和气鸣乐器(横笛、筚篥、笙)为主。体鸣乐器(铜钹)的加入使乐队编制渐趋完备。中国乐器笙的出现则反映了粟特音乐进入中原后汉化的迹象。关于画面的布局,朱安耐与乐仲迪认为:“上面表现的是天国,下面表现的是人间。”㉑㉑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9 页。笔者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上方的神像和天人直指祭祀主题,下方乐人演绎的世俗性乐舞具有娱神的功能。
卡菲尔-卡拉遗址出土的装饰木板和美秀美术馆藏石棺床上的两幅图像(图1和图18)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祭祀娜娜女神的情形,但两者之间有些细微差别,前者突出的是奏乐祭神的主题,后者强调的是乐舞娱神的主题。这可能反映了这些粟特本土的乐器及仪式随着入华粟特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融入了当时的社会风俗,突显了娱神的性质。
事实上,除了能够在图像上看到祭神的场景,我们也能从文献中找到相关的线索,但主要是民间祭祀活动。相关记载如下:
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㉒㉒ 魏征等《隋书》卷7“礼仪志2” ,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49 页。㉓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 页。㉔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64—65 页。㉕ A.L.Juliano,J.A.Lerner,"No.125. Eleven panels and two gate towers with relief carving from a funerary couch",Miho Museum,South Wing,Shigaraki,Miho Museum,1997,pp.247-257.
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㉓㉒ 魏征等《隋书》卷7“礼仪志2” ,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49 页。㉓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 页。㉔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64—65 页。㉕ A.L.Juliano,J.A.Lerner,"No.125. Eleven panels and two gate towers with relief carving from a funerary couch",Miho Museum,South Wing,Shigaraki,Miho Museum,1997,pp.247-257.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㉔㉒ 魏征等《隋书》卷7“礼仪志2” ,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49 页。㉓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 页。㉔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64—65 页。㉕ A.L.Juliano,J.A.Lerner,"No.125. Eleven panels and two gate towers with relief carving from a funerary couch",Miho Museum,South Wing,Shigaraki,Miho Museum,1997,pp.247-257.
以上三段文字内容记述了在琐罗亚斯德教祭神、祭天、祈福仪式中击鼓、歌舞、奏乐的情景,反映了音乐、舞蹈和仪式有着紧密的关联。
综合这些图像和史料,我们能够更加完整地看到粟特地区的乐舞祭祀情况及其进入中原之后的流变图景。
四、余 论
首先,关于粟特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位于亚欧大陆中心的粟特,宗教面貌异彩纷呈,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都在此占据一席之地。宗教上的多元性、复杂性使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并不明确。近年来,随着卡菲尔-卡拉遗址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逐渐勾勒出公元5—6 世纪,粟特人以撒马尔罕绿洲为中心的活动轨迹。他们留下的文物遗存反映出该区域的粟特人主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
其次,关于娜娜女神。她源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中亚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到了粟特地区成为主神。“不仅是片治肯特的城市守护女神”㉕㉒ 魏征等《隋书》卷7“礼仪志2” ,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49 页。㉓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 页。㉔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64—65 页。㉕ A.L.Juliano,J.A.Lerner,"No.125. Eleven panels and two gate towers with relief carving from a funerary couch",Miho Museum,South Wing,Shigaraki,Miho Museum,1997,pp.247-257.,也是撒马尔干、布哈拉等城市最受尊崇的女神。这类神祇图像的主题基本一致,但是细节有所差异,并没有形成严格的仪轨。即便如此,它仍然成为当时粟特艺术中最为流行的元素。
最后,有关音乐和宗教仪式。综观粟特本土的图像材料,音乐往往出现在琐罗亚斯德教的葬礼、祭祀仪式中。这件新发现的材料则增补了音乐在祭神仪式中的信息。并且,显现出角形竖琴、琉特琴、潘笛等乐器在粟特地区的使用情况。再观中国的粟特音乐图像材料,在正式的祭祀仪式和普通的祭祀活动中,都可以看到音乐和舞蹈的存在。笙、排箫等中国乐器的加入,乐舞娱神功能的衍生,揭示了粟特系统图像中,音乐与宗教仪式的传播与变迁。
然而,由于粟特人在前伊斯兰时代的宗教图像还远未完整,因此,以上对于图像材料的分析和解读也只是管中窥豹,具体的细节将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充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