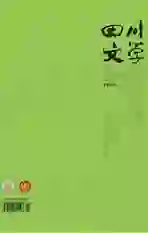这一天,我在赛场上记录失败
2019-07-19李不言
李不言
当我提笔写这篇文章时,10月20日已经过去了40天。
即使我从来没有刻意去回忆,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那个学妹。人潮中,她披散着波浪一样的长发快步走远。10月20日那天,她是第一个进入我镜头的新生辩手。
校里的杂志计划出一期采访稿,采访对象是那年“新生杯”辩论赛的落败选手,要突出“新生”“落败”“瞬间”这一系列关键词。而我身在杂志图片部,任务就是用相机记录选手落败的那一瞬间。
“抓拍!就是尽量抓他们失落的微表情,给特写!”主编再三向摄影们强调。主编的意思已经很明白,这天下午,我挎上相机就向举办辩论赛的教室走去。
临时用于辩论赛的小教室非常逼仄,中间仅有的空地被辩手的桌子占据。桌子被摆成一个“八”字,一撇是正方,一捺是反方,教室的墙沿挤满了观众,并不强烈的阳光从淡灰色的窗户漫进室内。在这样的环境下,拍出好的面部特写并不简单。这“八”字的一撇一捺上,分别坐着四个新生辩手,他们身着正装,都熨烫得板板正正。有的同学开学报到时就从老家带来了正装,其他的同学则是比赛前临时在学生服务中心定制的,在这里定制正装会比校外便宜不少。
我在拥挤的赛场边缘挪动,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这时她闯进了我的镜头。
她并不是以一个正方四辩的身份出现,她只是一个陌生的大一学妹。镜头和这位学妹的距离很近,因而我并不能看到标有她名字和院系的桌牌。
她显得很清醒,挺胸抬头,正装黑白分明。镜头上移,我看见她长着圆脸,未经修剪的长发垂在身后。她显得干练,上半部分的头发高高扎起,但我也看见,头发的路子歪歪扭扭,手法生疏。同样未经任何修饰的,她的脸,是典型的新生脸。这一点尤其明显——我在校园里一年,已经习惯了身边女孩用浓淡各异的粉底修饰脸庞,使得肌肤平整得缺少光线变化,即便不化妆,也必然是细细修过眉毛,并把脸捂得白嫩。而眼前这个女孩,顶着一张小麦色的脸,眉毛长而杂乱,根根分明,她大睁着眼睛,犀利的目光直直盯向正在发言的对方辩手,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可畏。
我立即按下快门,在离她不到一米的地方给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特写。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模特,我查看相机里的特写,她的情绪能够直接装在眼睛里。如果最后她成为我今天正式拍摄的对象,我的照片定会入选最终的文章插图。人们会惊叹这野生的眉毛如何流露出失败时的不甘,惊叹她麦色的脸庞如何被迫收敛目前的盛气——总之,惊叹一个生机蓬勃得有些盛气凌人的新生辩手竟然如此失意和落魄。
但愿这只是一个年轻摄影者的自私。
假如没有手中沉重的单反,我绝不希望这个朴素得独特的女生被宣告失败。
2016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面试,那是清华大学的一次选拔性冬令营。
北京的寒冷打得我措手不及,妈妈准备的羽绒服和毛裤根本抵不住狂暴的冰风,而室内暖气强劲,我像火烧一样浑身滚烫。正打算脱下羽绒服时,我却看见其他同学露出了外套下漂亮的衬衫西裤。我又退却了——我里面穿的是纯黑的毛衣毛裤……我默默地把拉到胸前的拉链拉了回去。
我直接穿着红羽绒服走进了面试室,就像一团火,浮躁、浮夸。闷热的房间里,缺乏面试经验的我一个人面对三位清华老师,应付着那些我根本不能掌控的刁钻问题。我分不清了,背心里一股一股的热汗是因为暖气还是紧张。漫长的面试结束后,我终于从压抑的教室逃出来,从那三位老师没有任何情绪的目光中逃出来。我站定在面试楼前大口呼吸,滚烫的后背和被风刮疼的脸似乎在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嘲笑着我这个弃甲曳兵的可怜人。楼前空地,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女孩在家人的簇拥下离开,她是那么的骄傲,正在高声向父母还原面试场上的漂亮作答。
我走到一个避风的角落,想打一个电话给妈妈。妈妈或许正忙,只有“看山看水看四川”的彩铃声在耳边循环,大风刮得眼睛酸涩,不过也可能是我想哭的缘故。
所以我知道,做一个朴素的失败者并不好受,因为除了要面对失败,你还会无止境地揣摩自己过分的朴素与这次失败的微妙关系。
辩论赛进入评委点评环节,写有评委们意见的纸条已经递到了负责人手中。胜负事实上已经落定,只是场上的选手和观众仍毫不知情。
“反方输,摄影准备。”摄影群里发来消息。
我举起相机,对准了反方的四张脸庞,离我最近的正方四辩就在镜头最前方。我碰巧得到了自己中意的“模特”,却并没有以往等待抓拍的高度兴奋。
漫长的点评中,场上的评委一致性肯定反方,并时不时点出正方的不足。正方四辩把眉头慢慢拧了起来,她仍然坐得笔直,在纸稿上奋笔疾书,不时抬眼,专注地盯向评委一就像每一个中学时代的好学生那样。
好学生们总是如此,当班主任批评其他同学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地聆听,并写下反省性的笔记,仿佛是自己受批评,脸上写满虔敬的悔改;而当班主任象征性地批评他们时,他们也会认真地聆听,不时在记下要点,仿佛是别人被批评,脸上写满超然的专注。
这就是优秀者的表现,不会有人不對这样的优秀者表示赞服。
不过在这狭窄的赛场上,谁会留意到一个失败的优秀者呢?
她抿起嘴的同时嘴角轻轻上扬。我不知道这于她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竞选失败时我为胜出者鼓掌,会这样抿起嘴角礼貌性地微笑。不妨在此假设她也如此,那么她也许早就明白己方败下阵了。说不定在来回的辩驳中,她早就感到己方难以自圆其说,难以对付对方辩手的咄咄逼人。说不定,她在辩论赛开始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双方外表上的差距:这就像是中学与大学辩论队的友谊赛,一方素面朝天,一方描眉画眼。
总之,她应该已经预料到自己的落败。
不过如果一个辩手在还未被宣判失败时就露出了失败后的样子,例如低眉下眼,例如垂头驼背,例如不经意地将写满点子的稿纸过早地揉成团,或将签字笔过早地揣进衣兜,那么即使这个辩手最后被宣布在获胜的一方,他的脸上必定也是毫不光彩的。普遍的舆论是,一个过早自认失败的人并不很有资格获得成功,当然这种观点只适用于普通人,成功者的自认失败人们另有一词来形容:谦逊。
她自然是一个普通人,尽管她是曾经的应试成功者。因此她还在维持一个辩手的骄傲,一个尚未被宣判失败的新生辩手的骄傲。她以曾经的优秀学生的方式,即超然地在稿纸上记下评委的批评意见,有意无意地维持着体面。我当然很心疼,因为我也明白,在即将被宣告失败的时候表现得达观甚至乐观是多么自我委屈,尤其是在黑压压的观众和黑洞洞的镜头面前。因而我是有责的,我托着沉重的单反并将镜头对着她们这一方,且其中起码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是只对准她一个人,我的一个镜头抵得上几十间屋子的观众,对她的曝光量和打击量是惊人的。
我忽然想起,她应该已经提前知道挎着相机的我是来这间教室干什么的,因为杂志编辑部事先跟他们沟通过关于采访失败辩手的事。如此,她已明白我一直将镜头对准她的用意。
于是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不适,那感觉可以被形容为被自己欺骗、将自己背叛,我正在进行的任务根本不是抓拍辩手被宣判失败的瞬间。事实是,一个已经被告知胜负的摄影记者,和一个已经预感并证实己方会失败的辩手,在进行一场心照不宣的摆拍。
她自然不是本来的她了,她很清楚自己暴露在一个镜头前,这个镜头会将她被宣判失败那一瞬间的形象,说得更细致一点, “微表情”,暴露在全校的读者面前,这其中有她的新老师、新同学,或许还有她倾慕的某个男孩。一个好的失败者(在这里她很明白是指一个好的“她”),不能是垂头丧气的,不能是恼羞成怒的,而应该是理性承认自己不足、非常乐意为对手鼓掌的。于是她在其他三位队友已经开始明显泄气之时,保持着辩论时的紧绷坐姿,那么认真地记下评委的批评,那么勉强地翘起嘴角似乎是在为对手微笑。我也那么努力地拍她的样子:不曾疲倦的手的特写、挺直的脊背的特写、充满平静和理性的眼神的特写,微微上翘的嘴角的特写……
这是一次默契十足的抓拍,如果用自信得有些傲慢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一场精致的合谋。
最终她的照片没有出现在杂志文章里。文章的插图都是一些被认为真正属于失败者的照片,或许是光线,或许是场合,照片里的辩手们显得或憔悴,或懊恼,或不甘,或烦躁。独独没有这个表现得理智而大度的正方四辩。
因为,她不符合主题设定的“落败”。
那篇文章推出以后受到了多方质疑,包括选题缺乏正能量、照片与院系错位、某些照片未经过许可等等,而我作为一个与这些问题没有太多关联的一个摄影,只是在网络舆论的边缘静静看着,想着,想着那个与我合谋的正方四辩在发现没有她的照片之后是失落还是轻松。文章自然是正能量的,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意在传达失败是成功之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可被选上的那些插图分明都是比较负面的情绪表达。目前编辑部的规則如是,上一层的文章编排我没有渠道参与,只能和其他普通读者一样接受最终的图文成品,这次的成品告诉我,我和正方四辩的精心合谋被宣告失败。
但这样的失败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她没有像其他辩手一样垂头丧气,因而她的肖像、她朴素的自尊都避免了这次备受争议的曝光,她可以像一个从未被大众传媒绑架过的人一样,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最近几次见到她,她都在那个特定的位置自习,头发已被烫成大波浪,也着了淡妆。曾经镜头前的那个朴素的正方四辩,不再与她有任何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