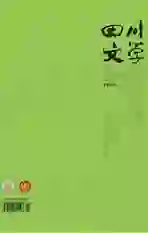深渊
2019-07-19阿微木依萝
阿微木依萝
我得下山找我的朋友曾小旺,五年前他下山去了。我的朋友曾小旺比我小几岁,那时候他的腿脚突然好了,原本重病起不了床,在床上躺了十年。
我记得白露刚过两日,他来敲我的门,他问我,你走吗?我说不走,天气有点冷了。他就自己扛着一个包袱摸黑走了。那当几天还没有亮。
我的狗送了他一程。现在我的狗都死两年了。
我一个人住在山上,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我自己的房子像树一样长在林子里。我和这儿许多鸟都相识,它们常来我的房顶叫唤。
如果曾小旺不走的话这儿不远就是他的宅院。也不知道那房子还在不在,我也很久没去看。
曾小旺说他不超过四年就回来,他只是想下山见见世面。
我等了他五年。
现在我要下山去找他。现在也是白露刚过两天。
听说山下有个小镇,整个镇上的人都是瞎子。他们是后来才瞎的,起先只瞎了一个人,后面一个接一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如今那儿一个看得见的人都没有。他们一年四季手里拿棍子探路,凡是他们能走到的地方,路面都是大大小小的眼子。镇子旁边是一条河,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却很灵敏,那些人就摸索着打渔为生。
曾小旺可能在那个镇上。不。我确定他在那个镇上。也不,我其实不确定。我不知道。
我锁好门窗,跟我的鸟友们道别。我扛着一个包袱,不知道包袱里装的什么。昨天晚上收拾的。
路上起了一层露水,也可能是雨水吧,夜里下了一场雨,天快亮的时候雨还没有完全停止,我走在路上几次滑倒,几次将草叶上的水滴赶下来洗手。我是天快亮的時候起身的,天边冷清清,灰黑色的云像鸟的翅膀。
我不确定有没有走对路。曾小旺可能不是从这条路下山。林子越来越深,越走越透不过气,常年埋在阴暗里的树叶腐烂了。
倒大霉的!我咒了一句。摔了一筋斗。我的耳朵可能蹭破皮。我是侧面摔下去的,听见体内咔嚓一声,我以为我断了。
我遇见一个人,这个人瘦得跟鬼样。
你去哪里?他问我。
去……我说不下去,我才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个镇子的名。
我去找我的朋友曾小旺。我对他说。
他低头想了一下说,那也总得有个去处呀?
我低头想了一下,我该怎么告诉他我并不知道那个镇子的名呢?
你总该想起点什么吧?寒梅先生?
他嘁我寒梅先生。这大概是我从前的名字。我就说嘛,不,是曾小旺说的,他说是我自己不想要从前的名字,我并非是没有名字的人。这个人嘁出“寒梅先生”的时候,我对这个名字感到熟悉,我感觉并确定它就是我从前的名字。
你认识我的朋友曾小旺吗?我问他。
不认识。他说。
我就往前走了几步,既然不认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人赶紧跑到我跟前,他倒是一脸操心的模样,他说,你总得说个去处呀?寒梅先生,你还要去哪儿?
我去一个镇子,那儿的人全都看不见路。我猜曾小旺是去那个地方了。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寒梅镇。他很高兴自己知道了我的去处。
原来那个地方叫寒梅镇。这个地名和我的名字—样啊。
我劝你不要去了,寒梅先生,那儿全是死人,没有活的。他说得如此认真,额头都皱起来了。
可不能瞎说,我说,你怎么乱讲话呢?那儿只是住着一群眼睛生病的人,他们看不见路,不是死人。
他就不高兴了,一脸苦闷地望着我。
你不要挡我的路。我推开他。
我就是从那儿出来的,我会不清楚吗?他一种悲伤的语气。他其实很不想戳穿自己的来历似的。
我对他摇摇头。不信他的话。
你不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你没法忍受他们的行为,你努力了很久根本劝不了他们,所以你就走了,走得远远的,听说你连名字都不愿意跟人提,我打听了很多地方那些人都不知道寒梅先生,你把从前的名字刷掉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干的。是我也会这么干。现在寒梅镇的人彻底看不见路也好,这样他们就不会四处抢夺东西了。
你现在要回去干什么?他又问我。
不知道。我说。
我根本记不起从前的事情,我怎么会住在寒梅镇呢?我一直住在山上。
你不是要去找你的朋友曾小旺吗?他微笑,是在笑我的坏记性。
啊,是的,我是要去找曾小旺。我说。
我就和这个人道别了。他劝不住我。他钻入树林就不见影子。他说他要去做另一个寒梅先生,他是不会回到寒梅镇的,不会跟那死家伙昆在一起。他很决绝。
寒梅镇就在山脚下,我知道。我也不懂为何对它的位置如此清楚。
我走了很久,穿过一大片红薯地,穿过一大片玉米地,穿过一大片青绿的葱地,我看见前方最远的地方有灯火。这时候天刚擦黑,那是最先亮起的一盏灯。我估摸着行走的时间和地形,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寒梅镇了。而这些庄稼是谁种的我就搞不清楚了。我隐约觉得这个地方从前是荒凉的,连草也不会生得齐整,几乎是沙石遍地,废弃的一片土地。
我加快脚步。很快就走到那盏灯的门前。我举手准备敲门。
进来吧。里面有人说。
我推门进屋。屋子最里面的窗户下坐着—个人,那人背对着我。
对……对不起,打扰您了。我说。
那人转过身,一张笑脸。我通过点燃的油灯看见他就是曾小旺。
曾小旺!我差点跑过去。
来了就好嘛。他从凳子上起身朝我走近。
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我说着便四周看了看,看见一根凳子。
你早晚要来的嘛。他说。
请坐。他说。
我就坐到凳子上。
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他变得很客气让我有点不习惯。
白露一来天气就凉了,寒梅镇就是这种样子。他说。
你准备留下来还是去哪儿?他说。
我来找你,我来看看你出了什么事,你说不超过四年就回山上。我说完盯着他,看他怎么回答。
啊,我忘记了,我这么说过吗?他犹豫了一下说。
他喝了一口热水,然后拿着锄头去忙活,他让我自己在房间里呆着,如果没有别的事就不要出去乱走,寒梅镇的晚上并不安宁。
我不知道他这么晚出去干啥,既然寒梅镇的晚上并不安宁。
我听他的话整个晚上都呆在房间,外面吵吵闹闹,有很多人仿佛在房顶上跑来跳去但我始终闭门不出。也許我在山上一个人住惯了,我的房顶经常有鸟儿跑来跳去,这些声音丝毫不能影响我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呆。窗户的缝隙有月光透进来,过一会儿月光熄灭后,有雨水透进来。曾小旺是在雨停后回来的,天已经放亮,有一丝薄薄的阳光照在窗缝上。
你整晚没有睡觉吗?他问我。
是的。我说。
你也一样嘛,整晚没有睡觉。我说。
他打个哈欠走到床边倒下就睡着了,那样子像个死人,睡觉连呼吸都感觉不到。我放了一根手指在他的鼻孔上始终没有探到气息。
原来是这个缘故不回山上。我自言自语。
也不全是。他说。他居然还醒着。
我有点惭愧,往后退了一步才跟他解释,我并无恶意,我只是想知道寒梅镇是不是真的像路上遇到的那个人说的—样。
就是和他说的一样。曾小旺边说边斜眼瞅着窗外。
那你?我不晓得往下怎么说。我有点难过。
你回来做什么?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可发誓再也不回来。曾小旺转头看我。
我不记得了。我一直住在山上。你怎么和那个人一种口气?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发抖,仿佛刚刚哭完,嗓子还不顺畅。
曾小旺对我的话有点不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给我甩脸色。接下来我们谁都找不到合适的话说。
第三天,也是晚上,曾小旺又拿着锄头出去忙活了。连续三个晚上他都拿着锄头出去干活。他说这五年他就是这么过的,每天都要劳动,每天晚上都出去跟寒梅镇的人说话,他说那些人其实都不错,他们只是暂时因为眼睛看不清东西而焦躁,跟人说话的语气不太中听,其实他们为人很好,至少会慢慢变好,他们从来不阻碍任何一个进入寒梅镇的人,这儿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来去自由的。寒梅镇远郊的那片庄稼地就是他开垦出来,原本那儿寸草不生实在荒凉,大风一阵一阵把那儿吹成了沙漠。他用了五年时间将那片土地改造了。 “人定胜天。”他很骄傲地跟我说。他要用那些庄稼把人们去其他地方抢夺食物的习惯改掉。这个镇子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曾小旺十分有底气也仿佛是在实现他的理想似的跟我说,他不会像我一样选择放弃,他会坚持到底,寒梅镇的人一天不改变他就一天不离开。
我确实看到他的庄稼地(当时不知道是他的地)。三天前我从那儿经过。
曾小旺从窗户底下的箱子里掏出一件衣服,这件衣服他没有穿在身上,而是拿到我的眼前说,熟悉吗?我接过来看了看便直接穿到身上了。
熟悉吗?他又问。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说不清怎么一下子想起从前的事。也许因为这件衣服披着我所有的过去,我把它穿在身上就等于把过去穿在了身上。这听上去很神经质。我说不清。
你想起了什么?曾小旺很着急的样子。
所有,差不多是所有。我说。
那你还走吗?曾小旺背转身问我。仿佛他害怕听到我说走。
我需要休息几天。我跟他说。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几乎不怎么说话,没机会说话。他白天很困晚上出去干活,我白天出去瞎逛晚上睡大觉。我们的时间错开的。
寒梅镇的人和从前没有两样。除了他们以前眼睛看得见现在眼睛看不见以外,没有改变。他们还是那种性格,还是一年四季从寒梅镇周边带回许多别人的粮食。“抢什么?为什么要抢?”这是我从前跟他们说的话,现在他们看不见我,也没听说我回来,这种话也就不用再说。从前有段时间我的嗓子一直哑着,是跟他们吵哑的。他们骂我伪君子,怯懦,毫无斗性,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蚂蚁都不如,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要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也配!他们是这么抱怨的。我就和他们使劲吵,嗓子都嘁坏了。
眼下我不会这么干了。我去山上之后从来不用大声讲话。曾小旺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们两个一到冬天就在栅栏围着的院子里烧一堆火,喝酒。
现在谁求我给寒梅镇人讲什么道理我都不干。这些人是不会为了谁的话改变的。我觉得曾小旺要白费心机了。我看他那些庄稼还不如收拾起来喂鸟呢。
寒梅镇的人也跟曾小旺一样,晚上出动,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连续好几天夜里听见曾小旺的房顶被人狂踩。也许他们知道我回来了?
我是被赶出寒梅镇的。这个事情只有我清楚。想到这件事觉得胸口很痛,就好像那只曾经踩在我胸口的脚一直没有松开。
曾小旺把玉米收回来了,他要我负责看粮食。他有三间卧室,我没来的时候一间睡觉两间用来做粮仓。现在只有一间粮仓。
要睁大点眼睛看好啊。曾小旺叮嘱我。他是被吓坏了,五年来,他的粮食都是被抢光的。我劝他不要在这儿耗着,回山上过清静日子。以我从前的经验,他就是在这儿住上五十年,寒梅镇的人也不会改变。他们从来不会对人说“请”、“谢谢”之类的话。他们的性格里只有掠夺和霸占,他们恨不得自己整个人就是一把刀子或者无数的芒刺,谁也靠不近,谁也欺不了,许多待人处事的基本礼节在这儿已经感受不着。 “我们要有狼性!”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也是这么跟他们的孩子说。
也只有你还愿意留在这个鬼地方。我对曾小旺说。
那又怎么样?他一脸的不屑。这种冲劲儿看起来像十七八岁的热血少年。
我觉得很困,一边给曾小旺守粮仓一边打瞌睡。曾小旺跟我说,眼睛睁大一点,慢慢地就不会觉得困了。他准备收完玉米立刻翻地,撒上豌豆种子,撒上韭菜,栽葱和蒜。不过眼前最要紧的是将粮仓加固。
仅仅—道门是不够的。曾小旺说。
我们两个抬了一扇石磨,将它堵在粮仓门口。
我可以松一口气了吧?我说。
行吧。就这样吧。曾小旺看了看屋顶。
白露过了半个月,加上连续几天小雨,早晨的空气中都是雨水的味道。曾小旺的房子被几颗树木包围,好在树下有一小片菊花开得正旺,前几天我醒来就会到树下看看菊花又开了多少,这天早上觉得疲乏就一直躺在床上。曾小旺的枕头是用书本做的,他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我不行了。我的眼睛看什么都不太明亮。正当我想挪一下书本将枕头垫高,听见外面有人小声小气说话。
求求你们了!我听到有人說。说话的人含着哭腔,听不准是谁。我垫着脚尖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去看…一是曾小旺!他像狗一样跪在地上。
求求你们!他又说。
我看见他的一张侧脸,那脸色很着急很可怜很伤心。他前面站着一大群人,我估摸着所有寒梅镇的人都在了,包括老人和小孩。
我前天晚上还带他们出去干活,他们刚有了改变,你们不能再这样教他们了。曾小旺说。
为什么不能?你想让我们过从前那种日子吗?曾小旺,你把我们的土地都霸占了,你让寒梅镇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你,你和从前那些人是一样的,不,更坏!你现在准备跟他们学个彻底,连吃的也不给我们吗?你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熬过那段黑暗日子的人脑子可是很清醒呐,我们再也不会糊涂了,不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了,我们就是要将孩子养得像一只虎狼,这样他们才不会被人欺凌,被人坑害……曾小旺,我不想说那些伤心的事了,我们从前失去了什么,你去问问你的好友寒梅先生,他会全部告诉你的。现在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只要我们想看见,只要我们愿意再睁开眼睛,我们的眼睛就会像刺一样把你这个仇人挑出来。你可别想着走那些人的老路。我们寒梅镇的人——肚子里陈年的怒火还没有消呢!
不是这样的,马老先生,您误会我的好意了,我只是想让大家不去过那种……那种日子,我们自己有手有脚,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就能…..
别废话了曾小旺,你跪在地上学圣人的样子跟从前那帮人一样可恶,你这样所谓“能屈能伸”的人站起来就是恶魔。
我看见马老先生说完就绕开跪在地上的曾小旺,带着他身后一群人走到曾小旺的粮仓门口,他们根本没有动一根手指头,只用身子的一侧轻轻撞了一下门,门就开了,不,门就倒了。
我想起那个路人跟我说的,寒梅镇没有活着的人,一个也没有。也许他说得不错,这些人身上确实没有一丁点鲜活的气味。而且他们也不讲什么情面,我来了这么久,他们明明知道我来了这么久,竟然没有一个人戳破事实,就算曾小旺有一天清清楚楚在他们跟前叫出“寒梅老头”这个名字,他们也装作不听见。
我推开门,走到曾小旺身后站着。
你全都看到了。曾小旺说。
我点头。望着对面昨晚我们加固的粮仓,看着那些人将曾小旺收回来的玉米全都扛走。
你为什么要笑?曾小旺吃惊地瞪着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
那些人走完之后,我们走进空荡荡的粮仓。
我就知道守不住。曾小旺有点泄气,望着满屋被翻腾起来的尘灰,手在鼻子跟前扫扫,打个喷嚏。然后他就进屋休息了。“反正粮仓已经空了。”他对我说。
第二天晚上,我决定跟曾小旺一起去他的庄稼地看看。但是曾小旺不去。连续好几天,他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不起来。
你不要那些庄稼吗?我问他。
他们说你什么都知道。他疑问的眼睛望着我。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急忙闪开他的话。
从前他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呢?马老先生说,你并不是看不惯他们现在这种生存方式,你只是不知道作为人….-不,说仔细一点,作为寒梅镇的人,懦弱和凶狠到底哪个更适合这片土地。从前被欺凌的人突然变狠了,而从前凶狠的人被赶出寒梅镇,他们在寒梅镇旁边建立了新的居住地,没日没夜遭到寒梅镇人的掠夺,“抢走他们的全部,就是抢回我们曾经失去的。”这是寒梅镇人的口号。马老先生说,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寒梅镇的人即便全都做了鬼魂,也要将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曾小旺说完就一直盯着我。他希望我给他回答。
从前的事情我都记不清了。我说。
曾小旺不信。
立冬之后,寒梅镇冷得不像话。我住在山上都没这么糟糕。早晨起来裹着厚厚的被子,晚上睡觉脱衣服冷不脱衣服睡不暖和。总之我感觉在这儿呆不下去。从前寒梅镇的冬天没这么难熬。我对曾小旺透露自己要离开的心思,他只是听着,什么话也不说。
自从那次粮仓被抢,曾小旺就像霜打的茄子每天没有精神。
也许找陕要死了。曾小旺说。
不。我早就死了。曾小旺说。
我不懂怎么接他的话。沉默。
我准备在下雪之前离开寒梅镇。
寒梅镇下雪了。比我预期的早。这场雪将我的行程延后,只好多留几日。
我不知道曾小旺什么时候把地里剩下的玉米收进粮仓的。我是有一天半夜,听见门口有脚步声,开门看见一大群老人和孩子趴在地上,蚯蚓一样向曾小旺的粮仓挪动,才知道他把剩下的玉米收回来了。我以为他从此一蹶不振呢。
曾小旺就站在墙脚,他手里抱着好大一根木棍。这天晚上地上雪有多厚月光就有多厚,把所有人身上都照亮了。
求求您,给点儿吃的吧……
趴在地上的老人说。
求求您,给点儿吃的吧……
趴在地上的孩子们学着老人们的话说。
您就是老天爷,老天爷啊,求您给点儿吃的吧!这是马老先生说的,他嗓门微弱,不像前一阵子跟曾小旺说话那种响亮。他最老,爬得最慢,他身后老人和孩子们挺尊敬和照顾他,一直让他保持在最前面的位置。
马老先生说完就死了。我是真真的看见他咽了气。然后他后面的那些人叫唤着爬到他跟前,由于饿得没有力气哭,就干巴巴坐在月亮底下,一些人将马老先生的头发整理整理,一些人将马老先生的衣服整理整理,一些人看见马老先生的嘴里居然咬着两颗玉米籽,他们互相看了看,就把马老先生的嘴巴撬开了。
孩子们往前挪了挪,挪到曾小旺脚前两步的地方,望着离他们五步左右的粮仓—一求求您!他们说。
我感觉眼睛很疼,我才发觉自己在淌眼泪。
曾小旺放下棍子弯腰使劲呕吐,原来他昨夜喝酒了,拿着棍子就是为了撑住自己摇摇晃晃的身体。他吃了肉。我看见有肉粒混合在他呕吐的那些废物中。
恶心。我心想。
好香啊!我看见孩子们眼巴巴望着曾小旺面前那些废物说。他们又往前挪了半步。然后他们就挪不动了,嘴边惨淡的喜悦尚未消失,他们就咽了气。我是看见他们咽气的。
曾小旺!我使劲这么一喊,才发觉自己早就站在人群里,站在馬老先生跟前,那孩子死在我旁边四五步距离,原本我刚才还躲在门背后呢。
我准备去摇醒曾小旺,却看见马老先生从地上站起来。
马老先生对曾小旺说:
看见了吧,现在你知道了吧?我们从前就是这么软弱可怜,我们用我们的性命相信那帮人的鬼话,他们像你一样也很勤劳,也很会说话,他们表示每一滴汗水都是为我们流,寒梅镇起初那几年,我们确实尝到了甜头,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就像看见了老天爷,不,就像看见我们亲爹,世上只有亲爹才会这么爱护他的孩子们。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他们建造了粮仓,把我们的土地上种满他们的粮食, “终归都是你们的!”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就相信了,可是一到冬天,我们的日子特别难熬,他们粮仓的大门却总是锁着。寒梅镇的人都是讲良心的,也相信别人的良心,我们一天一天等待,等待粮仓大门向我们敞开,可是没有,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身体逐渐吃不消。他们设定的规则是我们曾经举双手赞成,后面怎么能轻易反悔?我们不是出尔反尔的人。“我们可以饿死,但不能失了气节。”我是这么跟寒梅镇的亲朋说的,我在寒梅镇辈分最高,他们向来听从我的话,和我一起忍受寒冷和饥饿,就仿佛我们面临的并非人祸,而是老天爷降下来的天灾。曾小旺,你刚才配合得不错,那天晚上那个酒鬼就是撑着一根大棍子站在粮仓门口,我对着他一边喊救命一边咽了气。我说实话吧,我当时真的害怕那个醉鬼,我害怕他手里的棍子,他们就是拿棍子将我的骨头打断,我只能趴在地上,寒梅镇很多人都没有完整的骨头,有骨头的人也只能为了保护他的骨头不受重创而趴在地上,就这样,你看到了,哦不,你的朋友寒梅先生曾看到了,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学会站起来走路,他们看到的是一群永远趴在地上的亲人,我们眼里都是恐惧,我们把这种恐惧和“爬行经验”像传染病一样传给他们。他们以为这就是行走,以为每个人都要在恐惧中走完自己的一生。曾小旺,你现在明白我的话了吗?你到这儿做的事情并非好事,你在盘算什么?
不,我什么都没有盘算,我纯粹……
曾小旺的话没有说完就被马老先生打断了。
马老先生又接着先前的话说:
我们的孩子都是饿死的——哦不,不只爬到粮仓门口的孩子,有许多病弱的幼子已经死在半路。那天晚上,寒梅镇的风里都是饥饿的味道。我还知道有人将孩子丢弃了,丢在山沟里,他们觉得山中虽然有野兽,但或许还能找到可吃的树皮?或许老天爷会让山林的野兽白天黑夜的沉睡。他们太天真了!当我知道他们这么干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绝望,你觉得那些孩子会活着吗?曾小旺,我想起来就绝望。
马老先生说完咳嗽几声,他的喉咙像被人丢进一把沙子。
曾小旺低着头,突然又将脑袋抬起来,他露出真诚的样子跟马老先生说,我不是那人,我是曾小旺,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样的。马老先生一口咬定。
不一样。曾小旺丢开手里的棍子。
我走到马老先生旁边,我对他说,马老先生,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他转身对我说,是有好久不见,难得你还记挂着。你都看见了?我们把从前所有的真相都给你的朋友曾小旺好好“看”了一遍。
我看见了。我说。我又问他,您的眼睛看得见了吗? 一直看得见。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继续跟我说:
你现在应该想明白了,我们眼下这种办法才是对的,你曾亲眼见到他们将棍子戳进寒梅镇人的心脏,他们挖出的深坑之中到现在仍然有寒梅镇人在那儿叫唤,在那儿受苦,他们永远处于暗无天日中,永远出不了那个坑害他们的地方。
马老先生语气沉重地将这些说给我听。他盯着我,又问,你回来是想明白了吗?想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吗?那些人就住在寒梅镇旁边,他们所有的劳碌都将是白费,你应该为他们这个下场叫好,比起他们的手段我们算是仁慈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只是拿走曾经属于寒梅镇土地上的东西。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对付他们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
你会知道的。马老先生总算对我笑了一下。然后他就带着老人跟孩子们撞开曾小旺的粮仓大门,抢走了剩下的玉米。
曾小旺瘫坐在地上。垂着头。有意思吗?这算什么呢?他说。他望着自己脚尖说话。我只能凭语气知道那话里的无奈和伤心。
寒梅镇的人现在活得确实凶狠。我安慰曾小旺。
他们身怀旧恨。曾小旺说。
是的。我说。
他们不相信我。曾小旺说。
是的。我说。
我不是那些人,我纯粹……
你纯粹为了他们好。
嗯。
那些人也这么说。每一个想要在寒梅镇实现抱负的人,他们最初的决心都接近于理想主义,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就只剩他们管控一切的野心。
我像个野心家吗?曾小旺盯着我,他用自己想要发誓的眼神盯着我。
这时候还看不出来。我说。
我是个单纯的理想主义。曾小旺保证的语气。
没有这样的人,曾小旺,理想主义也是一种野心,只要你想要实现你的某种想法,它就变形了。它会变成一块跳板,你站到这个跳板上就会想别的事情,也可以说它是一颗种子,种子发芽就想长成大树,成了大树还想开花结果,开花结果还想让自己的果子们落地生根。
照你这么说,我该如何?
你不该下山。曾小旺,作为朋友,我可以用我浅薄的经验告诉你,在我的想象中,真正的理想主义是顺风而行,从不想开花结果的事情,从来像河流,流到悬崖是高山流水,流到浅滩是平静湖水,流到芦苇荡,那就是苍茫的海。曾小旺,你懂我的意思,对吧?
你说的这种东西不是人,是懒蛇,还是快死的那种。曾小旺说。
我知道曾小旺懂我的话。但我也知道他不甘心。从他的行动就可以看出来,在他的心思中,理想主义是创造和争取,不是我说的顺其自然。我这种理想主义是懦弱的,和当初跪在地上的寒梅镇人一样,是无能的一种。要不然我也不会轻易就离开这儿,隐姓埋名。
你不用多说了。反正你很快就要离开这儿。曾小旺说。他好像早就发现我打点好了行李。
等这场雪停。我说。
曾小旺看看天,天上又开始落雪。月亮隐了下去。小片的雪花飘在我们脸上。
我对曾小旺说,你该知道世上许多事由不得你一个人。我也是后来才明白。
他们会相信我。曾小旺的话里很多不服气。他就是这种人,越挫越勇,越失败越要证明他的能力,这种性格我从前只在那些人身上看到过。
我对他的话很难过。我跟他说,你跟我一起回山顶吧,现在我完全相信那个路人的话,他作为从寒梅镇逃走的…..我不确定他是否也是一个鬼魂…..他比我们更了解现在的寒梅镇。你刚才也说了,他们怀着旧恨,这是无法解开的,你留下来有什么用,难道你还想再用从前那些人用过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立足吗?不行的,曾小旺,马老先生明确地跟你挑明了,他们这些熬过了黑暗日子的人头脑不再糊涂,你的方式只会引人怀疑,即使你确实想让他们恢复自在的日子,没有一丁点儿坏心,他们也不会并且不敢相信,你要知道一个从井里逃出的人是怎么也不愿呆在井边的,他只会逃离,只会对井保持终生的警惕和恐惧,你所做的一切都太晚了,自从那些人到了这里,就什么都不能挽回。曾小旺,你的用心在这儿根本使不上,住下去毫无意义。
我只是想让他们恢复正常的日子,总得有人拿脑袋去撞钟啊?哪怕他的头骨会碎掉。曾小旺这些话把我说得无地自容。他像个英雄,而我像只蛤蟆。
雪又加重了,当我收拾完行李准备离开,发现大门完全打不开。
不用着急走。曾小旺对我说。
我又放下行李暂时住下来。
腊月二十七,我听到有老人在外面喊——都准备好了吗?
腊月二十八,我听到有中年人在外面嘁—都准备好了吗?
腊月二十九,我听到有小孩在外面嘁——都准备好了吗?
腊月三十,我听到所有人都在寒梅镇的街道上嚷嚷,都在说话,都不知说些什么。我原本打算一直关着门,反正我的门被大雪堵了。但是我從窗户里跳出来,站到大院门口看到寒梅镇所有的老少都双手捧着什么,向河边的一栋大房子走去。 我跟上去。 大房子门口站着两个看守,他们见到马老先生的时候对马老先生说,我们可以换岗了吗?站了一年了,我们想去活动一下筋骨。
马老先生说,去吧。
两个看守推开大门,各自走了。
马老先生带着所有人走进房子。我也悄悄跟上去。
房子里冲出的霉臭味把我熏得难受。
你也来了?马老先生说。他说着就走到我的面前。我只好点头说,是,我来看看。
你早就应该来看看,寒梅,逃避是没有用的,你得加入我们的队伍像个硬汉的样子,抢回属于我们的东西。难道你不是因为忘不掉你的孩子和夫人才回到寒梅镇吗?那时候你的儿子刚出生,你的夫人被强加了罪名,她是被逼着跳进那个深坑,她最后在坑边喂饱了孩子,然后抱着孩子跳下去,那原本是全新的一天,太阳刚刚从山边冒出来。她当时连头也没有回一下。寒梅,我不得不说,你夫人是个人物,这样的女人在我们寒梅镇也是少有的。只有她敢站出来指责那些人,她是第一个清醒起来的寒梅镇人,她不愿意让她的儿子生来就趴在地上,她说,她只差每家每户的敲门去说: “我们要站起来走路,我们的骨头没有断,你们摸一下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好好的呀!”她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遇到谁就跟谁说,但是谁也不敢听她的话,更不敢像她那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记得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吞葬你妻儿的洞口,你悲痛的样子让我们当时在场的人都有点难过。真是抱歉,那时候我们还不像现在这么团结,那时候我们是散沙,是一粒一粒,我们被一粒一粒摧毁的时候并未觉得难过,只有我们身边大片大片倒下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感到恐惧和祸害难逃。
马老先生羞愧的样子,说完前面那番话,他的眼睛就落到墙脚那个洞口,一直盯着洞口。
后来,他又转头跟我继续说道:
是你夫人带着孩子跳下去,她连最后一眼都不肯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才醒悟。你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离开这儿的。说到底,你憎恨我们这儿的每一个人,甚至憎恨这片土地。你走的那天甚至把身上穿的衣服裤子脱下来扔在这片土地上,你是赤条条离开寒梅镇的。他们都说你疯了。寒梅,我是非常希望你回来的。现在跟你说这些,我也是放下了所有的负担。你要原谅我之前对你的态度,不,原谅寒梅镇人的态度,他们不是故意在你离开那天还动手打你,不是故意踩伤你,他们只是害怕,他们只是和我一样觉得羞愧,觉得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在你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愿睁开眼睛生活。
我不记得了。我对马老先生说,我忘记我曾有过妻儿。他上上下下看了我几眼,眼里有泪水滚出来。
我觉得抱歉。我又对马老先生解释,这段时间我总是睡不着,可能这影响我的记忆。
他后来把我带到洞口。我望着洞口。我望着洞口的时候眼泪止也止不住。我什么都记不起,但眼泪却一直往下落。
我听到他们在念,不,是在唱:
我们建立了房子,我们保护洞口
我们抢回了粮食,我们填进洞口
我们是凄惶的魂魄,我们不需要粮食
我们早已腐朽,我们不需要房子
我们昨天没有耳朵,我们今天长出来
我们昨天没有眼睛,我们今天长出来
然而一切太晚了啊,一切太晚了
他们在唱。我的眼泪止也止不住。马老先生蹲在洞口,后来他就跪在洞口了。所有人都跪下去。等他们完全从悲伤的情绪出来,我也止住眼泪的时候,他们又将大房子的另一道门打开,我看见这是一个更大的粮仓,里面放着许多腐烂的玉米和别的作物。
马老先生说,他们看着这些腐烂的粮食就仿佛看到也正在腐烂的那些人。即使那些人现在也做了鬼魂,他们也要每天去他们的土地上掠夺,在他们死去安身的家园里,让他们不得安身。
我摇头。我说我忘记了。除了记得自己也是寒梅镇人,记得一些算不上重大疼痛的回忆(当然我没跟他说,自从回到寒梅镇我的心就一直没有安宁,每天晚上梦见自己掉入深渊,却总是落不到底,一直处于下落的恐惧中,我的耳边不断有婴儿哭声,每晚从噩梦里醒来),其他都想不起来。我只是记得我曾让他们别再抢夺那些东西,反正都用不成了,都失去了,都太晚而没有意义了。
马老先生听完叹了一口气,他并没有责怪我,他只说理解我的处境,毕竟我光秃秃离开寒梅镇,这样决绝是发了狠的要将自己的心掏空。不过我还是从他的眼中看到一些失望,就像曾小旺曾经嘲笑我是个无能而软弱的人。曾小旺说,我是个被人拔了牙齿就把牙齿吐掉,觉得跟人打一架也长不出新的牙齿来,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可以讓对方也没有牙齿。 “你活得像个‘松毛蛋,谁抓开你软绵绵的防护,你都只会睁大眼睛看着他。”曾小旺就是这么说我的。
他说得不错。我可能就是这种人。我现在期待的是大雪停止,这样才能早些回去。
正月初一晚上,这是新一年的第一天,寒梅镇所有人都出去了,他们带回来更多的粮食。一些放进粮仓,一些作为种子丢进洞口,说是要让洞子里那些寒梅镇的人——最重要是我的妻儿——到了春天能亲眼见到小麦发芽,菜籽开花,到了秋天能亲眼目睹玉米抽穗。
曾小旺已经不种庄稼了,不过,马老先生让他教孩子们读书。马老先生说,虽然这些孩子一生都只能呆在寒梅镇,但读书还是需要的,毕竟曾小旺是从外面来的人,他会带给孩子们一些新的见识。
我每日在等大雪停止。每日大雪不停。
曾小旺说,大雪永远不会停止了。
马老先生说,我和他们一样了。作为一个活着离开寒梅镇的人,我可以丢掉衣物,丢掉记忆,赤条条光秃秃,但死后作为魂魄我也只能回到寒梅镇。
我不信。我作为魂魄也可以离开寒梅镇。我每日都在等待大雪停止。
曾小旺仍然劝我,大雪不会停止,我既然到了寒梅镇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他最后才说,那深洞之中也埋葬有他心爱的妻儿。
后来,曾小旺的房子被大雪压塌了,我们两个干脆搬到河边的大房子居住,这也是马老先生和所有寒梅镇人的意思,有我们住在房子里省去专门派人看守。自从住进这所房子,每日面对墙脚的洞口,才没有整夜在梦里的深渊中下落,我能一觉睡到天明。
寒梅镇的天亮得很晚,在这个地方,白天总是很短,夜晚来得很快。大雪就和曾小旺说的—样,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