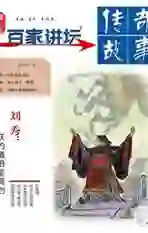腹有诗书我为大
2019-07-16安木
安木
《资治通鉴》的主要修撰者之一刘恕,18岁那年就考上进士,并因善讲经义而被皇帝特别关注,钦赐及第。这一番轰轰烈烈后,朝廷才给他巨鹿主簿的官职。主簿不过是从八品小官,估计是朝廷嫌他太年轻,想让他历练几年。
刘恕本着不怕上司、不怕顽吏、不怕积习的原则,在这个岗位上打黑除恶,很快营造了一派新局面。但他风头太劲,做事又不留余地,无论同僚还是上司都对他暗中侧目。就在刘恕的仕途岌岌可危时,一张宰相府的传帖为他打开了局面。原来年近花甲的老宰相晏殊请他进京讲学。
晏殊怎会对刘恕青眼有加呢?刘恕13岁时曾以布衣的身份拜访晏殊,把晏殊问得哑口无言。五年后,晏殊主导的庆历革新开展得如火如荼,需要大量的储备人才,于是想起了刘恕。可惜庆历革新后劲不足,晏殊很快罢相,刘恕也离开京城,到山西利川当了几年县令。
是金子总要发光。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皇帝问他需要何人相助,司马光想也没想就推荐了刘恕,“精通史学者,满朝仅刘恕一人而已。”要知道,当时翰林院中可有不少学术大咖。
事实证明,司马光的眼光不错。《资治通鉴》中魏晋以下、隋唐以上的部分多出于刘恕之手,司马光乐得逢人便说:“我得刘恕,如同盲人得相扶!”
但面对恩主,刘恕绝不会在学术上做丝毫让步。他特别反感司马光从周威烈王时“三家分晋”写起的断代法,觉得应该从西周共和元年開始。这比司马光版多了420年历史,几乎是另起炉灶了。他没通知司马光便毅然重写,写完后才让儿子送一份清样给司马光看。
学问方面如此傲岸,在政事上,刘恕是否会向权臣低头呢?
王安石没发达时和刘恕是好友,好到什么地步呢?王安石常拿他开玩笑,说他“精于史而不通于经”。而刘恕也毫不客气地宣称王安石赖以立身的“新经学”是胡说八道,满纸“妖气”,还会传染人。
王安石功成名就后,也没忘提携当日的损友,请刘恕出山主抓新政的核心部分——“三司”工作。如此美差近在咫尺,刘恕却丝毫不感兴趣,当着王安石和满朝大佬的面怼了回去,“谢谢,干不了。”接着还不留情面地指责新政中违反常情、变乱祖制的地方。
王安石的涵养比不上晏殊,更比不上司马光。据史书记载,他听后目光凛凛、脸色如铁,很不平静了一回。旁人见他发了火,或顾左右而言他,或掩耳抱头作鸵鸟状。要不是王安石没发话,他们定会夹了尾巴逃跑。而刘恕却谈笑自若。
那么,在生活之中,刘恕是否也能保持与众不同的本色呢?
熙宁四年(1071年),因得罪王安石而被贬往南康军的刘恕,前往洛阳拜见同样得罪王安石、被排挤为分司留守的司马光。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司马光主持的“史学会议”,商定《资治通鉴》的编纂事宜。司马光见刘恕衣被单寒,就把一些旧貂皮被褥送给他。刘恕不想当众拂逆老人的好意,但走到半道就让人送回去了。
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刘恕为何能成为孟子口中的大丈夫?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