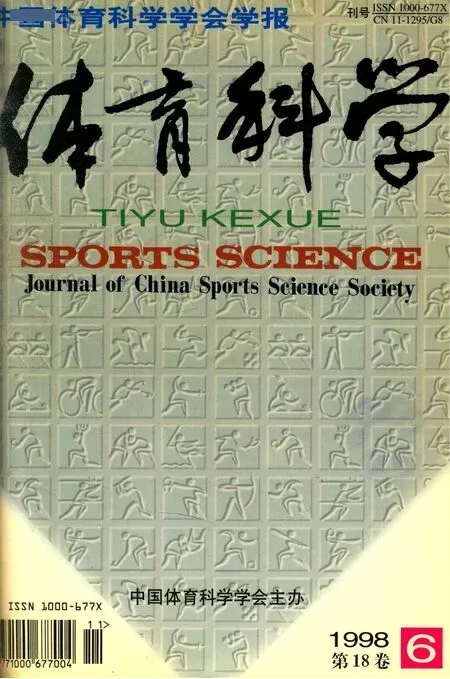辨误与厘正: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理论立足点检视
2019-07-13熊文
熊 文
辨误与厘正: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理论立足点检视
熊 文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我国学校体育以“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或核心理念是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呼应,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1)“健康第一”在学校体育中凸显,而其学校教育背景则相对被忽略;2)“健康第一”展开中缺乏对健康内涵演变的考察;3)对“健康第一”的理解存在“主次”排序的误读;4)(学校)体育与健康关系定位不当导致学校体育对健康的僭越。针对以上问题,研究认为:1)“健康第一”作为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具有衍生性、同质化、自上而下导出和放大化的取向,应与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做出必要的区分;2)新中国成立后,“健康第一”经历了不同时期,其健康内涵在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为医学健康和身体素质主导,当前践行中则呈现突出生理负荷等趋向,新时期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需要寻求新的外在支持和内在学理;3)毛泽东同志提出“健康第一”的语境为“学生减负”,其重要启示在于揭示健康的基础、根本意义。基于此,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的重要着力点应为当健康与那些影响、损及健康的因素冲突时以健康为重,而非对体育内含各价值、功能排序中把健康列为第一;4)应在大健康观的视域下审视学校体育“健康第一”,而非仅局限于体育的有限“健康”功能,以及囿于运动量和强度的规定;5)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应与学校教育及体育多维育人价值同构。
学校体育;学校教育;健康;身体素质
“健康第一”作为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或核心理念已广泛、深入地渗透于学校体育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如各版本《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包括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竞赛等方面)的宣示、校运会(或校园体育文化节)的口号等。“健康第一”无疑是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呼应,展现了特定时期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主题和特色,然而其在提出和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随着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化,需要对此予以回应、反思与破解。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基本-元理论和内在逻辑;2)健康追求与(学校)体育内在规定、价值之间的关系处理,又涉及竞技体育及其文化介入学校体育的议题;3)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局限和问题。本研究主要涉及第1个方面,具体包括:1)“健康第一”凸显于学校体育,其学校教育背景则相对被忽略,存在政策、体制色彩,而学理探讨不足;2)不同时期“健康第一”中健康的内涵并不相同,需要对当下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的依据进行再审视;3)对“健康第一”的理解存在“主次”排序的误读;4)(学校)体育与健康关系的定位不当,造成学校体育对健康的僭越或学校体育健康化。这些不仅为考量学校体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理论立足点,也体现其“思想”或理论的内在逻辑,具有基本-元理论意蕴。对此,已有学者从某些点、面进行了关注和思考,但研究视角切入、系统性和深度等方面尚存不足。并且,对于本议题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当前呈现的新动向,鲜有文献反映和揭示。本文将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或缺失,从哲学(逻辑、元理论)、人体-健康科学、价值-人文向度及学校教育和大健康观参照下对相关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和思辨。本研究旨在厘清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相关认识误区和理论困境,明确学校体育健康追求的合理定位。
本文所提出的“学校体育‘健康第一’”既是基于当前学校体育以“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或核心理念的现实,也指学校体育贯彻或推行“健康第一”。
1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溯源及“健康”内涵演变
1.1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相关文本溯源与澄清
1.1.1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衍生及同质化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这一提法主要从领袖语录(毛泽东,1987)及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衍变和抽取而来。其中,两份文件更是当下学校体育倡导和推行“健康第一”的主要政策和文本依据。然而,对两份文件进行解析,可以发现:
1)两份文件分别在学校教育和基础教育语境下提出“健康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贯彻‘健康第一’的思想,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和健康水平……”。其中,前者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和标志性意义,后者可认为是对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贯彻。
2)两份文件中,在“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下,学校教育和基础教育开展的事项,除了体育还有其他方面,如学校管理、各级政府行为及具体举措,如“培养学生的良好卫生习惯,了解科学营养知识”“加强传染病预防工作和学校饮食卫生管理,防止传染病流行和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等。由此可知,即便在两份文件的条文中,学校教育或基础教育“健康第一”相关事项所涉及的范畴也并不仅限于学校体育。
与“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类似的表述还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其他相关文件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如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及“健康第一”: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习近平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新华网,2018)。其中“健康第一”被置于“学校教育”或“教育”背景之下。
除了对上级文件精神的跟进,学校体育“健康第一”概念的另一来源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校教育的指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对学校(教育)提出“健康第一”的要求,并从学生减负、营养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可见,学校体育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并非相关标志性文本(文件或语录)的原始表达,而是由学校教育指导思想或指示衍生而来,或说是对学校教育指导思想或指示的直接沿袭和借用。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不仅在纵向上因循学校教育“健康第一”,从而流于部分与整体的趋同,在横向上还遭遇其他领域“健康第一”的比照和混同。这在相关文件或文献中也较为常见,如学校卫生工作、幼儿园工作、医学、药物学、营养学,以至在与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有关的行文中,“健康第一”均被普遍使用。
1.1.2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导出及彰显
对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或核心理念的确立,这实则为对学校体育意义、价值的定位。其确立或引入的依据涉及体育人文价值、文化本质、生物学意义、学校教育目的和背景、哲学思想、社会发展主题等方面。其中,尤以对体育人文价值和文化本质的认识最具根本意义。不同时期,中外体育实践及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诸多论述在重视体育的健身、健康价值的同时,也倡导体育的人文价值,甚至更为强调后者。如柏拉图指出,身体锻炼和心灵锻炼相结合,不认同体育只是身体锻炼这种片面观点。希腊人重视体育不完全是为了健康,更多的是为了培养勇敢的品质,甚至认为这才是体育的核心所在(李力研,2003)。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健康的精神[1]高于健康的身体(辛利,2013)。近现代以来,竞技体育作为体育文化最为主流和典型的形式,其发生、发展的动因并不主要在于“健康”。学校体育引入体育文化,显然不应忽略这一体育文化的实质,不能忽略体育的人文价值考察。鉴于长期以来我国学校体育生物体育观所受的诟病,对当下学校体育价值的相关认识及定位,更应在其生物学基础及人文认可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与此相映衬,当下我国学校体育把“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认识和实践中更是把“健康”作为学校体育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并赋予其统一规定性。这种规定的起点源自领袖语录及有关文件和政策,具有某种由上至下导出及体制性推动的特点。
由学校教育“健康第一”衍生为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如果说二者的同质化还仅是有损“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学理性,其背后则可能催化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放大,以及“学校教育”在学校健康体系中的淡出。学校教育以“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意味着该指导思想应面向学校教育的各个学科、部门和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如语文、数学等)一样,对“健康第一”的贯彻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一面,且“健康第一”的落实乃是牵涉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环境等综合体系)各个方面的系统和整体,而不应是学校体育的专属或专职。学校体育单一领域、系统及其实践活动(即便加上一些健康知识和技能等构成《体育与健康课程》)是否能担当健康的主角需要足够的理论支撑。
学校体育在学校健康体系中的定位既依赖于学校系统的统筹和协调,也取决于学校体育自身的价值和功能,而不能一枝独放地彰显,否则势必掩盖和削弱学校教育其他部门和环节在贯彻“健康第一”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也即,当“健康第一”在学校体育中被过于强化,无疑会造成其在学校教育其他领域中的弱化。
“健康第一”这种自上而下的导出,并在学校体育的彰显、放大,乃至误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学校体育“健康第一”遭遇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症结所在。
1.2 从“健康”内涵的演变到当前学校体育“健康第一”依据的审视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提出以领导人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作为标志,分别经历了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其“健康”的内涵也各不相同。
1.2.1 第1阶段:医学健康阶段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0年就提出“健康第一”,这一时期,健康主要与防治疾病联系在一起:受长期战乱的影响,我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和指标极其低下。各种疫病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无数人因此丧失劳动力,甚至失去了生命。1950年春,北京各大高校进行了一次体检,发现学生健康状况很差,患肺病、胃病和神经衰弱的不在少数。很多大学生反映他们感到“精力不济,学习效率不高”(鹿璐,2014)。同时,北京市青年工作委员会也对北京市男二中、女一中等七所中学的学生健康状况开展调查,显示学校在营养、卫生条件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学生的健康状况不佳(鹿璐,2014)。这一系列调查报告正是促使毛泽东同志致信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的直接原因。又如1951年5月,研究人员对多所学校在校学生进行了调查,北京大学有10%的调查对象患有肺病,中国医科大学因患各种疾病休学的学生比例达到14%,长春机械工业学校患各种疾病的学生比例达到76%(熊晓正 等,2010)。由此可见,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所提出“健康第一”中的健康主要是基于医学意义,即健康就是不患有疾病。
1.2.2 第2阶段:身体素质或体能主导阶段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和医学卫生事业已得到巨大的发展,国民及学生中的疾病人口、疾病率大幅下降。第2阶段“健康第一”的提出主要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标志,是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时,学生健康问题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这更多反映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及后来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所体现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测验项目,以及学生的近视率、肥胖率等方面。如同年(1999年),时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的杨贵仁在《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一文中指出,我国中小学生在耐力素质、柔韧性素质、肺活量等体质健康指标停滞或下降,肥胖儿童及超体重儿童比率增长较快,近视率居高不下,并提出,“研究制定针对学校和学生个体的体质健康评价标准,标准的内容和测试项目要充分体现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杨贵仁, 1999)。这也与中共中央国务院2007年颁布的《意见》相呼应,该《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青少年体育问题最高级别的文件,文中先后两次出现“健康第一”。其在开篇指出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存在的问题:青少年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城市超重和肥胖青少年的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年营养状况亟待改善。并在文中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把健康素质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健康第一”在学校体育的体现很大程度与身体素质(或体能、健康素质)相联系,其部分内容也被称为“健康体适能”。
可见,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两个阶段中健康的内涵并不相同:第1阶段“健康第一”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学生发病率高,基本和体育无关——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体育锻炼一直被作为“增强体质”的重要手段而加以倡导;第2阶段“健康第一”则主要由与体育相关的“体质健康”所引发(学生耐力、力量、速度等身体素质指标的持续下降),其在学校体育的践行也主要体现于这些指标。两个时期的“健康”虽然在诸多官方和学术文献中均指“体质(健康)”,但前者是“医学”体质,后者主要是“体能”性体质。
从健康的内涵来看,第1阶段“健康第一”主要基于“疾病”的背景已不复存在,从而不再作为当前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展开的依据和动因。那么,当下学校体育是否仍延续第2阶段“健康第一”的逻辑和惯性?毕竟,从第2阶段“健康第一”的提出到现在已经有20年(距离2007年《意见》颁布也已有12年),学生“健康”状况及相关认识、实践也呈现某些新的取向。比如:1)当前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号称在健康的3个维度演绎和展开,这与第1、2阶段“健康第一”所指的医学、生物学健康,尤其身体为主的健康相区别。尽管在相关文本中也提及身心健康或心理健康,但并未突显。实际上,关于健康的多维取义可以追溯到1948年,而后又有三维(苏静静 等,2016),甚至四维说(辛利,2013; 曾承志,2007),然其在我国被作为社会、政策认识和实践则相对较晚。2)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学校体育“健康第一”除了继续注重身体素质指标,相关实践还试图借助于医学研究的某些结果,提高心血管循环系统机能(作为健康体适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服务于慢性病防治等医学健康效应,从而呈现出突出和强调生理负荷的导向和趋势。
此外,第2阶段“健康第一”的时代主题为“素质教育”(1999年),当前“健康第一”是否需要寻求新的时代着力点?另一方面,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在展开过程中又面临来自体育内在规定、人文价值等多方面的审问。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困境也由此而来,故寻求新的外在支持和内在学理是当下学校体育继续高扬“健康第一”大旗所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
2 从“健康第一”提出语境到学校体育实现“健康第一”
“健康第一”作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与学校教育指导思想雷同,且源自毛泽东同志“健康第一”教育思想及置于相关政策背景之下。因此,对毛泽东同志提出“健康第一”的语境以及对当前学校教育政策树立“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实质进行考察,对于学校体育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1 毛泽东同志提出“健康第一”的语境:“学习第二”和“减负”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体育运动,除了身体力行,还在早期专门撰文《体育之研究》,对体育提出很多精辟的论断,倡导在学校三育并重,新中国成立后也多次指示发展体育运动,以期增强国民体质(健康)。然而,他多次提出的“健康第一”以及关注学生的健康问题则主要与“学生减负”联系在一起,而与体育本身关系不大。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校教育的有关指示和言论中,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1950年6月19日,针对当时学生负担过重,身体健康水平下降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写信给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同志就学生健康问题再次致信给马叙伦:“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并做出决定:“要注意青年健康。对大、中学学生要增加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克服忙乱现象。”
1953年6月30日指示:“14~25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他认为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跳跳蹦蹦”,教育教学工作要“适合青年的特点”,要充分兼顾“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也太多,也应当减少”。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同志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16~17年,20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由以上文献可见,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学生的健康问题,多次批评学校教育“不照顾青少年的身体”,并提出改进意见。但是,他对学生健康问题的关心更多是与“学生减负”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学生学习和工作的负担太重,应兼顾娱乐、休息、睡眠,包括“多玩一点,要跳跳蹦蹦”。此外,还应加强营养、搞好卫生等。总体来说,在毛泽东同志针对学校(及学生)提出“健康第一”及论述健康问题的语境下,未直接提及与体育的关系。
换言之,毛泽东同志对于学校教育工作提出“健康第一”,主要与学习相对而言,即“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当前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所提的“健康第一”一脉相承,也是学校教育以人为本,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虽然如前所述,当前“健康第一”中健康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总体来看,学校教育中学生健康与学习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似乎有加重的趋势,提出这一口号仍具有现实价值。
2.2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实现:冲突下的取舍而非主次排序
在健康与学习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学生减负”实则从另一个角度辩证地揭示了二者的关系,即把握“健康第一”(和“学习第一”),对健康和学习的关系不宜简单地视为主、次权重分配,不是规定和强调健康要比(文化)学习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及更多的资金、设备,也并非在诸如语文、数学等科目中把健康作为第一习得性的追求目标。“健康第一”更多的是对矛盾、冲突关系的把握和取舍,其遵循合理兼顾和“不损害”底线原则。“健康第一”是指健康和学习在投入度方面保持某种合理的比重和张力,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学习应以不损害学生的健康为最低的底线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在关注健康问题时,不断强调学生减负其实就是反对学习负担太重而损害学生身体健康。
就主要方面来看,“健康第一”隐含着“学生减负”,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健康第一”的初衷,也符合当前学校教育工作的实际考量,应作为理解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各学科、领域,应合理兼顾学习和健康,学习应以不损害学生健康作为底线。这可谓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实质,也应成为体育教学及其他学校体育工作贯彻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应有之义或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学校体育的各种学习、练习等活动不应损害学生健康。如年少学生不宜使用成人训练的体育场地、器械、时间或规则,因这可能会有损学生健康(如造成伤病),学生不应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过度练习或训练等。当然,应虑及体育所具有的特定健康价值或功效并适度引入学校体育,但同时也不应忽略体育内在的特质与规定。
实际上,学校教育“健康第一”这一冲突——多种权衡下的取舍,主要是基于物质、生物体存在(身体)与意识、精神存在相对、相参照的意义,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陶行知先生被视为国内“健康第一”最早的提出者,诚如他在《每天四问》第一问所言,“……因为‘健康第一’。没有身体,一切都完了!”他认为,物质生命的存在是生命的第一要旨,健康是人生命的基础,没有健康,个人的生命也就失却了保障(朱小蔓 等,2019)。在此,“健康第一”与“安全第一”一样,更多的体现为基础、根本意义和保障作用。也因为此,“健康第一”在各领域、行业被广泛地提出和应用,乃至被作为人生、生活哲学。
反观当下学校体育所提出的“健康第一”显然游离于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思想,主要不是上述涵义与意旨,其已演化为学校体育以追求健康为第一要旨,已经成为对学校体育的各项价值、功能进行轻重、主次权重的排序(把健康列为“第一”),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通过考察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实质,我们也可以发现学校体育把“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缺陷和模糊之处,即其在提出和践行“健康第一”的同时,对于“第二”(或“第三”等)是什么,或是回避或是语焉不详。这可能让其避免了理论自身的两难境地,而这“第二”、“第三”或被回避的可能正是学校体育所不应忽视的核心价值。这或许是该提法或“理论”的“高明”之处,但也是其虚幻和薄弱之处。
体育具有独特的健康促进价值,但学校体育是否应把“健康第一”列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还需要遵循体育及学校体育自身的逻辑和功能,需要考察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以及学校教育环境下学校体育的定位。这种考量既包括人文哲学意义,也包括自然(生物、人体)科学方面。
3 大健康观参照下的学校体育“健康第一”
随着大众健身热的出现,健康追求似乎已与体育锻炼成为某种因果关联,这可以说与学校体育“健康第一”遥相呼应。当前,学校体育某种意义正成为学校教育中健康及所引发问题的主要承担者。除了学校体育相关文件和表述把“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和首要任务,由于对“健康第一”的误读和认识偏差,学校和社会也常把学生健康问题归咎为学校体育,如把体质与健康关联并作为学校体育工作效果的检验标准。这很大程度与人们对(学校)体育(及其运动量和强度)在学生健康影响体系中不恰当的定位有关。在此,对学生健康的各种影响因素,尤其是对环境、社会因素加以全面、综合把握即为大健康观。
以下主要在大健康观之下对体育、学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涉及学校体育践行“健康第一”的能力、可能和方式等问题,也即学校体育能多大程度及如何正确地肩负起学校-学生健康的重任。因此,这也是考察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合理性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理论问题。
3.1 (学校)体育何以达成健康
3.1.1 健康涉及多维影响因素,并主要受制于学校环境及社会系统
随着对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认知的不断深化,在国际上,提出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的概念,认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很大部分起因于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的环境(赵驰 等,2015)。2014年至今,Bircher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健康模式——迈基希健康模式(meikirch health model)。该模式认为,健康是一种个体潜能、生命需要、社会和环境因素良性互动的状态(朱素蓉 等,2018)。有学者认为,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健康的维护更需要医疗制度、健康教育、社会扶持等制度安排(傅虹桥,2015)。世界卫生组织经研究指出,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生物学因素(与遗传有关)占15%,环境因素(含社会条件)占17%,保健设施(如医疗条件)占8%,生活方式占60%(谭广 等,2009)。有学者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提出青少年儿童体质下降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行为和生活方式是青少年儿童体质下降的核心因素(叶茂盛 等,2017)。在这些影响人健康的因素中,体育及锻炼(严格意义是身体活动或体力活动)并没有单独显现出来,而是隐藏其中,与生命需要、生活方式、环境等相联系和互动,发挥着有限健康促进的作用。
有文献指出,影响中小学生健康的主要因素为课业负担过重、升学压力过大、睡眠不足、膳食不合理、缺乏体育锻炼、网络成瘾等;影响大学生健康的主要因素为过度熬夜、睡眠不足、抽烟喝酒嗜好、就业与考研压力、不按时吃早餐、没有养成体育锻炼习惯等(王志敏 等,2005)。由此可见,对在校学生健康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尤为突出的是学业压力过大。回顾毛泽东同志对于学生健康问题的担忧和指示,表明他已认识到,在没有大规模疾病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学校环境下,过重的学习负担是影响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健康的主要因素。这显然超出了学校体育的职责范围,需要学校管理和社会支持的介入。
学生的健康处于由社会、学校和家庭所构建的系统(即广义的社会系统)之中,对于那些影响学生健康的体制性、社会性问题,学校体育实则无能为力,仅在学校体育范畴下动员、组织,只借助学校体育的形式一味予以“加强、提高”,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面对当前学生不堪重负的课业压力,如果不注重合理安排体育锻炼,反而使体育本身成为一种新的负担,从而影响学生的健康。
3.1.2 (学校)体育与健康关联的向度及局限
就身体健康而言,相比医疗、药物等学科领域对健康的治疗效用,环境、营养对健康的保障和支持意义,体育对健康的作用体现为促进、改进、预防和辅助性(如降低某些疾病风险)以及体质、体能等。如美国不同版本《国家体育教育标准》关于健康的内容主要指向与健康相关的体能,包括心血管循环系统耐力、肌肉力量和耐力等。
从健康的心理和社会维度(社会适应)来看:首先,不同心理品质、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善和发展与不同或特定体育项目有关,这些项目具有不同的运动量、强度和身体活动等特征。片面突出特定生理、体能指标,会抑制某些心理、社会适应发展目标。其次,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发展或培养更多体现为目的性(需有意识地贯彻与渗透)、内隐性、过程性和潜移默化性,对于体育教学等过程如何达成相应目标,如何评价还难以界分及缺乏操作性。再次,体育对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介入价值或促进作用还较为有限,甚至未得到充分认可。从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未提到体育的作用便可见一斑,这反映出即便是教育管理部门也没有认识到体育对心理健康介入的价值。另外,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也是其他课程和实践活动(如心理教育和矫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等)的内容,学校体育在把健康作为“第一”任务时,也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其他课程是否应让渡这种作用和地位?)。
3.1.3 “健康”与(学校)体育关联的实质为其体力活动
学校体育蕴含多种教育价值,从各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来看,鲜见把健康作为首要考量的表述。如美、英、德、日等国学校体育提出的多维价值目标中,健康只是其一,甚至更为强调其他教育价值(李茂堂,2002; 董翠香 等,2013)。其中,美国2013版《K-12国家体育教育标准》中提出了5项标准,对健康的表述体现在“标准3”中 “有通过知识和技能达到并保持一个增进健康的体育活动和体适能的能力(张大超 等,2017)。”其他4项标准则与体育运动相关知识、能力及体育精神、社会性等有关。在此,学校体育开展的依据还须在健康效益与体育特质及其他价值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也提示体育与运动、身体活动、体力活动应做出必要的区分: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提出“生命在于运动”,认可运动对健康的意义,这种“运动”不仅有体育(项目),还包括其他身体、体力性活动(含日常体力活动)。也因为此,诸多文献和组织、机构更多提出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而非体育)与健康相关。而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则不仅是运动或体力活动,更是寓意丰富的文化-价值体。
3.2 学校体育的运动量和强度
学生的健康获得和学校体育的开展必须从健康的各种影响因素来考量,尤其是学校环境下可能影响学生健康的因素以及健康的机理,应树立大健康系统观,而不能仅局限于学校体育范畴和体育运动的维度。
如前所述,就一般意义而言,当前对学生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学习压力和负担,在此前提下,只要减轻学习压力和负担,改善作息时间,辅之以其他方面的举措(如卫生、营养、课外活动——包括一定的体力活动),即便不硬性要求特定量和强度的体育活动,也可以从源头或根本上减缓或解决学生的健康问题。
由此也推论,在不过多改变目前学业负担的情况下,如果只是简单地加强体育活动,不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合理安排运动量和强度,包括为追求体育成绩而导致过多、过强的运动,体育活动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尤其对于那些体质较差、身体虚弱的学生来说,更可能造成对身体的损害。
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活动即便与健康有关,但在学校环境下也不应一味照搬和追求基于生理负荷而提出并强调的对运动量和强度的要求。因为在大健康观下,在学习之外的有限时间内,达到健康效果的可能因素包括休息、睡眠、文娱活动、其他社会性活动等,也包括各种身体(体力)活动,比如散步、爬山、课外体力劳动,或不同节奏、不同运动负荷的专门性体育活动。其健康机理并不仅与心率(强度)和体能等相关,也包括体力活动与心理的有机结合、生活-学习节奏的变换、注意力的转移、睡眠状态下的疲劳恢复、安静状态下的心理调整、社交活动带来的心理愉悦……仅以体育活动的运动量和强度这类生理-物理性指标作为健康锻炼的要求,忽略了人体是一个由生理、心理、精神等构成的统一体,忽略了学生所处的外在环境不只是生物体的体育-锻炼环境,还有复杂的学校和社会环境,甚至忽略了诸多低强度体育项目所具有的锻炼价值。即,通过低强度运动及心理的调节达到与注重强度和量的生理性锻炼相同或不同的健康效果。
美国、加拿大中小学普遍安排了类似课外自由活动时间,在此时间,学生集中在室外或体育馆内,自由运动、嬉闹、休闲(很多情况下老师的职责只是“看管”)。这某种意义契合“减负”的要求,未尝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反观当前学校体育健康至上或对学生健康关注的研究或理论模式,其所沿用的“健康”概念多源于医学模式[2],其视角和理论基础为人体科学或量化生理-心理学,基本逻辑是自然人和社群的健康理论,典型参照是运动量、强度及健康体适能等维度和指标(且主要是生理相关),而脱离学校、学校体育的教学、教育语境及人文科学和价值考量。在干预实验中过于关注运动负荷,其理论依据为特定强度及持续时间的运动可导致某些生理健康指标(或可量化的心理指标)的改善,而没有考虑和纳入大健康观下影响学生健康的各种因素,包括没有基于环境-身心和谐统一的健身观(如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体育观),没有把学习负担作为考察因素。此外,也没有考虑除健康之外学校体育的自身规定与多维发展价值。从而造成研究结果、结论与真实学校环境之间的偏差。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考虑(文化)学习及相关学校、社会因素,把“健康”仅限于健康体适能,为提高学生的健康体适能,在一般意义提出学生每天应参与一定量“中等至剧烈强度”的体育活动(如前述更为准确的表述是“体力活动”)。这种“参与”也应在规定性(管理和组织下)与自主性(学生自发参与),校内与校外,体育课内与课外,教学、训练与锻炼以及不同运动项目(如东西方体育项目)之间做出区分,而不应把其作为学校体育管理的统一要求。如这种负荷是否应衍变为体育教学中对强度和密度的统一规定就值得商榷。
4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推行:与学校教育及体育多维育人价值同构
4.1 从学校体育健康化到学校教育“健康第一”
体育或学校体育与健康的关联程度实则有限,而学校体育在表述上直接沿袭学校教育“健康第一”这一指导思想,且学校教育领域下没有其他领域、部门或科目(课程)提出“健康第一”,这很容易导致体育或学校体育的健康价值被放大。种种迹象表明,学校体育大有揽下学校和青少年学生“健康”这个重任的趋势,或学校体育表现出向健康看齐的取向——姑且谓之“学校体育健康化”。从理论向度来看,体育内涵的三维(即三维体育)与健康的3维完全等同,即身体(生物)、心理和社会3个维度,学校体育追求的3个维度也直指健康的三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从外在实践看,体育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体育对健康具有怎样的价值,如何通过体育干预学生的健康;体育主管部门及各级领导反复强调学校体育对健康的重要作用。无疑,学校体育占据健康的制高点,对提升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具有鲜明的“旗帜”效应。然而,学校体育与健康这种近似绑架式的关系也成为学校体育难以承受之重。
首先,容易导致学生健康问题与学校体育工作失职划上等号。目前有关学生健康的构成除了例行的体质测试指标,还涉及健康的其他问题,如身高、体重不达标、龋齿、贫血、近视、肥胖、心理障碍、营养不良等。如前述,对于这些健康问题,体育或是不能改善或是难以改变,或是促进作用有限。实际上,即便体质测试的某些指标与(学校)体育的关联也极为有限。而对青少年体质指标持续下降的归因中,学校体育往往被率先问责。
在学校环境下,学生健康首先受到来自学习负担太重的威胁,而具体来看,影响学生健康的原因复杂而多维。在不改变其他外在环境和条件的情况下,学校体育工作开展得再好,也并非必然改变学校(学生)健康的面貌。实际上,“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等体育制度性规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减负”、休闲等功效,不应只视为体育相关,或仅考虑其与体育相关的健康价值或功效。
其次,过分拔高学校体育对健康的地位和作用,过多将健康大任揽于学校体育自身容易导致社会和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体育寄予过高的期望,提出过当的要求,加重学校体育的压力,不利于社会和学校其他各方面一起推进学生的健康工作。
可见的事实是,借助国家基础教育课改背景和平台,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这或许为部分体育人喜闻乐见,但由此也留下学校体育僭越学校教育作为学校健康的主体甚而第一责任承担者的假象和隐患。
因此,从学校教育层面的意义,需要把学生的健康管理从目前“只见学校体育,不见学校教育”的局面中解脱出来,把当前学校健康工作从聚焦于学校体育上移和回归到学校教育的广阔视野——这也是前后两个阶段“健康第一”提出的初衷及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具体来看,这不仅涉及教育理念、管理部门、管理制度和方式,也包括有关学生健康的直接管理,如对学业、休闲、营养、体育锻炼及医疗、卫生条件等的安排,以及各门课程的协调、配合,领导、教师观念的转变,考核和评价制度的完善等。而不再停留和局限于学校体育系统内部的挖掘和“发挥潜能”,如把体育运动打造成健康优先的手段,驱使体育教师参加健康培训及开设健康教育课程等。
4.2 从生理负荷和“健康”取向到学校体育多维育人价值
理论上,体育课及各项体育活动可以基于健康的某些指标而提出特定生理负荷的量和强度的要求,与健康的心理、社会维度及体育的其他价值结合或统一起来。如通过运动项目的教学、练习、竞赛等形式和过程,培养学生的价值精神、道德品质及社会适应能力,实现学校体育“育体”与“育人”的同构。这种结合和统一,包括兼顾运动技术形成的规律(如过程性和阶段性)、项目本身的规定和特征(如比赛的节奏),渗透各种育人方法和手段(如讲述性引导、榜样、鼓励等),形成张弛得当、动静结合,量和强度合理搭配的最佳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免因强调特定“健康”或“健身”水平的生理负荷量和强度,而让学校体育陷入某种固定量化的模式,并避免让体育运动沦为单纯的医学健康手段,而失去其在学校教育环境下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与此同时,单纯强调持续特定(中高)运动负荷,无形中会忽略甚至抑制某些价值、品德的形成。因为个体的各种价值、品德在特定运动量和强度之下自动形成的假定并不正确,且过多安排特定负荷的运动必然会挤压德育渗透的其他形式、机会或时段。因此,如何在运动量、强度与学校体育的多维价值、目标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使学校体育的健康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相得益彰,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及全面、和谐发展,是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不可或缺的要义。
作为对医学模式和生物体育取向的超越,学校体育需要重温、回归体育的实质或真谛,即把学校体育视为体育——作为教育意义丰富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社会实践在学校的投射或教材化,体育有何种价值、功能,都可以在学校教育语境下百花齐放或择其重点,其生物性、社会性、人文性都应该可以兼容,各得其所。健康如果视为一,也是学校体育的当然构成,而不应把其各价值、功能分出主次,并固化地对学校体育活动(尤其是体育课)做出规定或要求。如此才能释放体育,回归体育,让学校体育不再背负不能的包袱。在此,关键是走出学校体育对学校教育“健康第一”误读下的局限:必须树立学校教育和大健康系统下的“健康第一”观,而非把健康确定为学校体育的首要追求并碾压其他价值和目标。
5 结语
1.从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文本溯源来看,“健康第一”作为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具有衍生性、同质化、自上而下导出及放大化的取向。其中的重要症结为“健康第一”在学校体育的彰显和放大,并某种程度导致其在学校教育其他领域的弱化。基于此,学校体育贯彻“健康第一”应置于学校教育语境下,其提法以“学校体育贯彻(或落实、推行等)(学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为宜。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的依据不宜拘于自上而下的文本或政策导出,而需更多引入体育人文价值理性和思考。
2.新中国成立后“健康第一”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其健康内涵分别为医学健康和身体素质主导,当前践行中则呈现突出生理负荷等趋向。这提示新时期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应寻求新的外在支持和内在学理。
3.毛泽东同志提出教育“健康第一”对理解当下学校体育贯彻和落实“健康第一”具有现实意义:1)“健康第一”的参照为“学生减负”。2)“健康第一”在于揭示健康的基础、根本意义。由此推出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重要着力点,其是矛盾冲突时的取舍原则而非体育各价值、功能的排序:是当健康与那些影响、损及健康的因素冲突时以健康为重,而不是对体育内含各价值、功能排序中把健康列为第一。
4.应在大健康观的视域下审视学校体育“健康第一”,而非仅局限于体育的有限“健康”功能,以及纠结于运动量和强度的规定。
5.学校体育推行“健康第一”应走出学校体育健康化的局限,同时把学生的健康管理更多回归于学校教育。运动的生理负荷指标应与学校体育的其他价值、目标保持合理的张力,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及全面、和谐发展。
学校体育倡导和推行“健康第一”既是与学校教育的同构,也是与体育多维育人价值的同构。
董翠香,苏朋,季浏,2013.美英日中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12):81-85.
傅虹桥,2015.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J].现代哲学,(5):44-50.
李力研,2003.体育:“培养人的勇敢”:亚里士多德体育思想解析[J].中国体育科技,39(5):2-6.
李茂堂,2002.德、日两国体育教学指导思想模式比较[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6(5):35-37.
鹿璐,2014.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的背后[N].中国档案报,2014-7-3.
毛泽东,19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413.
苏静静,张大庆,2016.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的历史源流探究[J].中国科技史杂志,37(4):485-499.
谭广,谭红,马卫平,2009.关于健康第一基本理念的思考[J].体育学刊,16(1):46-49.
王志敏,杨旭东,蔡宝忠,2005.解读“健康”与“健康第一”思想[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8(7):967-969.
辛利,2013.对学校体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思考[J].体育学刊,20(5):8-11.
新华网,2018.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2018-09-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0/c_1123408400. htm.
熊晓正,钟秉枢,2010.新中国体育60年[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44.
杨贵仁,1999.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J].中国学校体育,(6):6-7.
叶茂盛,陶永纯,郝阳阳,等,2017.美俄日英澳5国体育课程标准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0(9):81-87,95.
曾承志,2007.健康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解读[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0(5):618-619,62.
张大超,杨娟,2017.美国3版《K-12国家体育教育标准》演变对学校体育影响的比较研究及启示[J].体育科学,37(10):21-31.
赵驰,任苒,2015.健康观的再认识[J].医学与哲学,36(12A):15-18.
朱素蓉,王娟娟,卢伟,2018.再谈健康定义的演变及认识[J].中国卫生资源,21(2):180-184.
朱小蔓,王平,2019.陶行知的生命教育思想与实践[J].江海学刊,(1): 224-232.
Corrigendum and Correction: Reflection on the Theoretical Standing Points of “Health First”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XIONG Wen
“Health first”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or the core idea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is guiding ideology is the echo of national macro-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exposes man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ts theoretical foothold faces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1) “Health first” is too prominent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but its school education background is ignored to some extent, the practice of “health first” lacks an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health connotation; 2) The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first” has the misreading of the orde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3) The improper positio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leads to the viol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o health. Therefore, we should point out that: 1)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Health first” has the orientation of derivation, homogeneity, top-down derivation and magnif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Health first” in school education. 2)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alth first”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meanings of health were respectively dominated by medical health and physical quality. At presen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tress physiological load in practi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first”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needs to seek new external support and intern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3) President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 first” as “reducing the burden”. It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lies in revealing the basis and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health. Based on the above, the key point of implementing “health first”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as follows: When health conflicts with those factors that affect health, heal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not the first one in the ranking of the values and functions of sports. 4) Examining the “health first”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health concept, rather than the limited health function of sport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of the amount and intensity of exercise. 5)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first”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value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
2018-10-10;
2019-05-16
上海市教育科学重点课题(2015A1502)
熊文(1972-),男,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学基本理论、体育伦理、体育教学与训练等, E-mail: xiong2001wen@sina.com。
G807
A
1000-677X(2019)06-0089-09
10.16469/j.css.201906011
[1]“健康的精神”为价值理性,不同于“健康的心理”中的心理指标。
[2]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所提出的有关健康的权威概念均基于医学模式(苏静静等,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