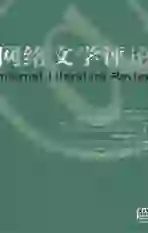网络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2019-07-13张丽凤曾琪琪
张丽凤 曾琪琪
摘要:网络文学天然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天然性的联系不但没有凸显城市的相关问题,反而使得城市像是空气一般在时空中失去了它的主体性,成为没有文化内涵的代码。人与城市的关系也由共存互生的关系变成了生存背景的简单介绍,城市中的人不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外部问题,而更加关心自我情感及存在。网络文学中呈现的城市书写展现了网络时代人的生存体验及文学想象,是一种新的现实关系的发现。
关键词:网络文学 城市书写 代码 世界性关联 自我存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文学的书写与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逐渐走出长期以来的弱势格局,并初步形成了“他者化”的城市书写、以新生代作家为主的迷乱城市书写、以‘80后为代表的青涩城市书写以及网络文学中的世俗狂欢式的城市书写这一基本格局”①。诚如网络文学借助的媒介网络一样,网络文学中的城市也天然地带有了媒介城市的样态。网络文学的城市书写呈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及情感诉求,它超越了传统的城市问题,以强大又无限的网络建构了媒介都市的新内涵。无中心、碎片化、流动性的特点成为别于传统文学城市书写的重要表现。网络的虚拟与无边界性使得在现实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城乡关系变成世界化的城市关联,作家在小说中不再关注人与城市的关系,转而更加关注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的情感变化与展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此时,城市成为简单的代码,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内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城市书写无效,尤其是当我们将网络文学的城市书写看成一个过程时,网络文学对城市书写的价值将更加凸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商业化外表背后折射的网络时代的生存体验与文学想象是中国网络文学重要的潜在新质”②。
城市成为没有文化内涵的代码
20世纪的传统文学中,不管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地方性一直是小说中最为鲜明的特征。正如老舍笔下的北京、茅盾笔下的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鲁迅笔下的鲁镇一样,人与地方是一种共存互生的关系,不管是小说中的人物角色还是空间建筑,都带有鲜明的城市文化特征。王朔笔下的北京大院的生活,王安忆笔下上海的弄堂巷子,杨克笔下的天河城广场,无不是其生活中最为深入的部分,因而散发出该城市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基于此,人与城市的关联往往成为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对象。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就曾明确地表示要寻求城与人之间多种形式的精神联系和多种精神联系的形式,“我越来越期望借助于文学材料探究这城,这城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在其居民中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期望“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经由人——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和那些以特殊方式与城联系,即把城作为审美对象的人们——搜寻城”③。但在网络文学中,当城市成为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代码之后,人与城市之间就缺少了一种生成关系,城市只不过是故事发生的背景。
在网络作家笔下,城市固然还是人物的生存空间,但所有的人物于这个城市来讲不过是附着于上面的一个点,所以城市就成为一个没有其自身文化性格的所在,而成为一个代码。美国作家乔依斯·卡罗尔·欧茨曾说,“城市作为人类想象的原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天堂之城、地域之城、神之城、人之城、死亡之城、旷野之城——存在了几千年,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城市吸收了圣城与世俗之城的对立形象,表现了在一个失去了宗教的时代人的心理需要。④”到了网络文学,城市则成为超越以往任何时候的一种空间定义,而成为个体情感精神空间的一个表征。表面上看城市依然是故事发生的空间,实际上人的情感与精神都不再与其发生关联,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内涵也不再是作家关注的部分,于是C市、G市等代码随处可见。
在网络文学中,由于城市自身内容的流逝,城市开始失去其自身的主体性,只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符号性的空间。在较早的城市网络文学中,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对成都的书写,具有转折性的标志意义。在这部小说中,成都貌似是一个与“我”紧密相关的主体,实际上不过是一個背景,城市的文化并没有融进人物的生命之中,所以小说不仅在开头无意介绍这座城市,即便后面介绍的时候也更像在介绍一个与自我生命不太关联的客体一般,贴切全面却缺乏“即在”感。如小说将成都比喻成“不求上进的流浪汉,无所事事,看上去却很快乐”,成都话“软得黏耳朵,说起来让人火气顿消”,成都人闲散,“跷脚端着茶杯,在藤椅上、在麻将桌边,一生就像一个短短的黄昏”。而如城市名牌一样的历史古迹,青羊宫、武侯祠、杜甫草堂等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空间没有历史文化的差异,真正展现这个城市性格的人物不再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正如“花五块钱买一杯茶坐上一天”的成都人,他们的悠闲自得在作家那里不过是无所事事。背景性的城市介绍在后来的网络小说中变得更加鲜明。以人海中的网络写作为例,虽然她写的故事也多发生在上海,但却极少像传统作家那样去描述、建构上海这个城市。与程乃珊在《上海的探戈》里凭借着“老上海后裔”的身份,信心十足地挖掘和“复活”着一个被历史的尘烟掩埋的“如假包换”的“真上海”⑤不同,人海中同样作为老上海的后裔,对上海几十年的历史叙述则是“冷眼旁观”。如在《我和我的经济适用男》中,何小君家的公寓楼作为20世纪三十年代的产物,其黄金地段的优越位置及几十年的历史沧桑本可以大书特书,但是作家写起来却轻描淡写,房子的历史与人的历史被没有任何障碍地斩断,留下的不过是现实中的一段白描:“她家虽然在上海的黄金地段,但却是最老式的三层公寓楼,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产物。说得好听是历史保护性建筑,其实那里面根本是千疮百孔,一栋楼住满了七十二家房客,厨卫全设在走廊里,烧饭的时候一家一家挤在一起,吃什么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过她妈妈倒是这栋楼第一代主人的后裔。也不知为什么,解放前外公没跟其他人一起走掉,独自留下来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在自家的这栋公寓楼里被赶出去,接受改造。老外公撒手西归的时候,倒是允许她们家住回这里了,但只有西北朝向的小半套属于她家。从那间屋推窗就能看到纵横交错的晾衣架,晒满了十几家人家的被褥床单。她妈妈记忆里那个清脆葱茏的小花园早已成为历史,连带着那一点点对往昔富贵生活的追忆,一起烟消云散。”在这里,城市作为主体的经历被彻底架空,人在被架空的城市中成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家族记忆、城市的沧桑没有像基因一样潜藏在后辈人的身体内,因此,此时居住于其中的人既没有探求城市历史隐秘的兴趣,也没有置身其中的之中牵绊。
当城市作为一个符号性的空间被描述和表达时,城市自身的生命被彻底抽离,城市在他们笔下就开始直接以字母代号的形式出现,以往城市的“即在性”被“即时性”替代,更强调人物感官的表面感知。如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浮世浮城》《我们》等这些校园青春小说和都市情感小说都发生在G市,然而在不同小说中被反复书写的G市并没有给读者留下特有的城市印记,我们对它依然是一无所知。即便有来自G市附近郊县的人物,我们从她的身上也丝毫看不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正如小说中的何绿芽,“是个老实本分的姑娘,大家赞同的事她不会反对,别人开心她也开心”。至于离G市4个多小时城际列车的S市,离G市两个多小时的B市,就更是一个空间代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涵。这一点在晴空蓝兮的都市情感小说中有着相似的表现,如晴空蓝兮在小说《良辰讵可待》中对故事发生地城市给予介绍时,描述的依然是人物对这个城市极为表面的感知,不涉及城市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大学坐在的城市,以夏炎冬冷闻名,同时也是典型的无辣不欢”,无论是“夏炎冬冷”还是“典型的无辣不欢”,都是富有体感的描述词,是与人的身体的部分发生即时感知的部分,既不涉及纵深的历史,也不涉及城市空间的变迁。《一霎风雨我爱过你》中故事则发生在B市、C市,C市是个名副其实的娱乐之都,城区里最不缺少的便是吃喝玩乐的场所,奢华的酒店与夜店极大地丰富并满足了城里人们的业余生活,而B市是珊珊生活的地方,但城市自身依然是一个代码。作者即便明确写出了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对城市中人的影响也极少被考察,如骈四俪六在小说《名利场》中明确交代了故事发生在澳门、香港,但它们也不过是萧、盛两大家族权益相交的空间而已,丝毫没有传统文学中对城市生存与精神的描写。当城市作为代码出现的时候,城市也就可以被其他“即时性”符号所代表。
在网络文学中,人不仅不能代表某个城市,而且城市也从不曾滋养、限制人,人与城市之间也就缺少一种现实普遍性的反映,人观察城市的视角也就不自觉地停留于自我发现的表面,城市的内涵与生命表现也因此变得表面化、碎片化、个体化。如《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当“我”在夜晚寻欢作乐之后,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那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这个坟墓一般的城市里,谁可以为我的青春作证?”显然,人在这个城市中的生命,只与自我有关,与那个与“我”发生关系的姑娘有关。同样地,《一霎风雨我爱过你》中的舒昀“不想回到C市”,只“因为那里少了一个人”。柳下挥的《天才医生》,当让一个外来者认识并走进燕京这座城市时,再也不是去浏览城市的名胜古迹,不是踏进城市的历史深处,亦不是走到城市的现实,而是去品尝城市的食物:“中午你们就别回来吃饭了。秦洛肯定没吃过全聚德的烤鸭吧?你就带他去尝尝这个。青云阁小吃城的小肠陈、爆肚冯也不错,你们晚上如果不回来,也可以去试试——那个叫什么三里屯的酒吧街挺出名的吧?”虽然吃饭的安排从故事情节上讲是为了促成恋爱,但是因为情感发生的毫无逻辑性,使得故事与城市之间只能考这种暂时性的关系维持,而没有更深层的精神联系。柳下挥对燕京的认知就像人海中小说里的张江男,这些符号属于这个城市,但又是片面而肤浅的,很难说可以代表这个城市。而在《你好,旧时光》中住在城郊平房里的余周周,面对潮湿发霉惨不忍睹的屋子,不仅没有被杂乱的生存环境压制,反而借助想象完成了超越,正所谓“优秀的雅典娜女神是不会在乎恶劣环境的”“她也可以不开灯啊——漆黑一片的时候,连房间都不再有边界”。显然,这与传统作家书写人与城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对现实生活及生存境况的关注是传统作家批判和反思城市的一个重要维度,如迟子建、格非、贾平凹、铁凝等都将目光投注到底层人物身上,关注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城市作为一个生存空间将其生活紧紧地包裹起来,人与人之间、人与城市运行的规则之间都发生着关联。所以即便像徐则臣试图让人物在心灵上以张扬的姿势超越城市的限制,“跑步”穿过中关村,但依然要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正如小说中那个叫敦煌的说的“我跑,不信两条腿也能被偷去”,所以虽然“他一路跑得意气风发”,实际上却已经违反了城市的既定规则,“闯了三次红灯,两辆车为他紧急刹车”。如果说闯红灯与紧急刹车还属于现实中的具体规则,那么他这种疯跑还触犯了城市人生活的情感与精神状态而成为另类,“很多人盯着他看。在拥挤繁华的中关村,很难看到狂跑不止的疯子”⑥,精神世界的张扬终究在跌落在现实的城市中。
滞重的城乡关系转化为世界化的城市关联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乡土文学,甚至在21世纪,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还是千丝万缕,这从一年又一年的春运大潮中依然能感受到现实中乡村对城市的那份牵绊。2017年,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打造的《春节自救指南》神曲迅速火遍网络,更是以极为搞笑的形式揭示了无论人们在城市生活了多久,在人们内心深处,从情感到思想无不受到乡村特有的宗法制文化的压制,七大姑八大姨们表面上的嘘寒问暖正透漏出现实生活中個体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在网络小说中,因网络媒介的虚拟性使得乡土文化对人的牵绊却极少呈现,甚至城市也犹如网络一样,将世界连接到一起而呈现世界化的特征,主人公穿梭于世界各地。但作家们却无意于表达城市对人的影响,而不过是将城市作为主人公生命行程中的一个驻点或驿站。因特网的链接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网络中的城市之间的联系触手可及,各个城市之间不再有中心与边缘,一改传统文学中城市与乡村、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的分别。“无论在何种层面上,网络文学都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城市文学。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它所描绘的生活,都完全属于城市世界。⑦”与城市相对应的是更远的城市,是世界各地,而不再是乡土。即便是涉及城乡关系,也早已没有了城乡文化带给人的不同思维及影响,而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关系介绍性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代表着先进,“上城”一度成为人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姿态描述,高加林们拼尽全力也依然未能顺利地敲开城市的大门,而陈焕生们则在世人的嬉笑中完成了一次上城展览。到了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进城市,城市以其张开的怀抱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城市的自由与欲望同时生长,当打工者们终于与城市亲密接触之时,城市也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斑斑伤痕,郑小琼笔下的女工们的命运,正是这个城市最为冰冷一面的显现,而“铁”的意象更显示出繁华城市的另一个面向。《跑步穿过中关村》的徐则臣,一路上的红绿灯及汽车的鸣声无不揭示着人置身于城市中,城市对人的一种束缚与限制,同时也预示着人的身体虽然完成了进城,但是精神上依然徘徊在城乡之间,徐则臣的《啊,北京》写的正是人们虽然日常生活与工作在城市,但情感与思想深处依然停留在乡土。正如小说中的边红旗说的“北京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希望,有我的丹丹,我是绝不会放弃的,你还怕什么?”甚至小唐也领悟到必须与乡村的妻子离婚才能真正地融入北京,他认为“不彻底解决后顾之忧,怎么在北京混?你只有产生了家的意识和感觉,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地方的创业中”。然而,人的理智与情感向来不同步,人的身体可以瞬间跨入城市,但是人的情感与思想却可能永远无法斩断与乡村的联系。正如“我”作为旁观者审视边红旗的生活时所感觉到的,“打完电话我开始难过,因为我在听到边嫂的声音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边红旗其实还是属于苏北的那个小镇的,那里有他的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他的家,有永远也不会放弃他的生活,那些东西,应该才是最终能让他心安的东西。”而边嫂那句“明天我就要他跟我回去”更是以无可置疑的语气写出了乡土所具有的巨大威力。所以当边红旗不得不跟着糟糠之妻回家的时候,他看着城市里的太阳与天空,“眼泪哗哗地下来了”。此时的眼泪不是屈辱,而是不甘中的无奈,是融入城市的艰难与离开城市的简单,他的那首“啊,北京/我刚爬到你的腰上/就成了蚂蚁”,正是对自我的渺小与城市的庞大之间的强烈对比,也是“进城”之艰难的形象表达。
在传统的小说中,城乡之间的关系依然是紧张而滞重的,城与乡之间有一种进入与容纳的关系,城乡关系一直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借助戏剧《城市启示录》将城市与乡村难以剥离的关系非常形象地表达出来。海归导演余松坡认为中国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北京依然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北京,我们无法把北京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格,这些都只是浮华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尽管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像打了鸡血一路狂奔,但是城市化远未完成。显然,小说中对城市的认知充满了现实观照。然而,与徐则臣执着地描写城乡关系不同,网络文学中人与城市之间再也没有进入的困难,人天然地生活在城市之中,就像维希留(Virilio)在著名的论文《过度曝光的城市》(The Over-exposed City)中强调交通与传播科技在城市变迁过程所扮演的角色那样,“进去城里”(to go into town)已取代十九世纪的“进城”(to go to town),由此,我们就“不再只是站在城市前,而是永远地居留在里面”⑧。此时,城市与人成为一个整体,城市会随着人的出场而现身。即便涉及现实中城乡关系,其表现也脱离了城乡的文化情感羁绊,而成为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介绍。如辛夷坞的《浮世浮城》中,唯一涉及城乡关系的是曾毓谈了一个农村的男朋友,结果该男子同时交往多个女孩,并对每个女孩子说年底结婚,实际上却是他在老家有一个明媒正娶务农的老婆,但无论是务农的老婆还是该男子都沒有展现城乡不同所带来的矛盾与摩擦。可以说,这里的城乡关系仅仅是一个关系,并未有人物情感与思想的牵连。
所以,在网络作家们的笔下,城市超越了中心与边缘,城与乡、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立,而更表现出一种世界性的关联性。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就像各个网点之间的关联一样,虽然身处世界两端,但却没有实际的距离感,人可以任意穿梭其中。国外的城市不仅是他们生命经历的一部分,同时还关联着个人的友情、亲情甚至爱情。如辛夷坞的小说《我们》中,周瓒曾在加拿大留学,有乌克兰的同学,公司“年终总结”,公司中层以上负责人和骨干精英飞往三亚,而冯嘉楠则前往香港过圣诞,国内外的城市于作家来说,并没有文化和距离上的差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周渠被公司惩罚后下定决心和妻子一起移民加拿大。柳下挥的《天才医生》中,林浣溪大学毕业后曾被推荐进入哈佛医学院学习药物学和免疫学。骈四俪六的《名利场》中,盛家分家后,七姑娘杀回去,将家里的老老少少一个个折戟沉沙,结果七姑娘的三个哥哥,两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巴西。八月长安在《你好,旧时光》中,会不经意地写余周周忽然很想告诉正在新加坡读书的温淼,“你知道吗,其实如果我们足够勇敢,东京真的不远”。晴空蓝兮的《良辰讵可待》中,凌亦风前往美国治疗并成为传媒大亨。人海中的《我和我的经济适用男》,故事虽然发生在上海,但是冯志豪的父母都在洛杉矶,他不仅要经常往返两地,同时家里又有一个大型投资项目要在泰国进行;陈启中的父母和姐姐又都在加拿大。由上述文本可以看出,网络小说中表现的城市都带有一种世界性,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的进入与表达都没有隔阂。
网络文学的作家们无意探究各城市之间的差异,他们之所以写到某个城市只是因为某个人与这个城市有关联。这种连接在故事中以情感为线,在现实中以网络或电话为媒介,然而无论是情感的线索还是电子媒介,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都出现普遍重组,“那些曾经是(或至少被认为是)壁垒分明的前线或边疆地带,包括家庭、地方、城市、地区、国家、国际等,如今似乎已无可避免地彼此重叠”⑨,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外间公共空间的关系与个人空间重叠,城市间的关联因个人的关系而展现,因此变得偶然而脆弱。正如《我和我的经济适用男》中,冯志豪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街头与地球这端的何小君的通话,当她许久没有等来一个字的回答时,“‘啪的一声就合上了电话,他也不再打来”。此时,洛杉矶与上海的联系随着电话的挂断而失去;而在《良辰讵可待》中C城与美国之间也因为凌亦风近乎固执地想回来而发生了关联。
人与城的关系变为对城市中自我存在的关注
综观中国20世纪城市文学,城市特征鲜明的作家都与个体情感相关。当人远离了土地与城市朝夕相处时,个体的情感就毫不例外地被突现出来,不管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还是张欣笔下的系列小说,都难以摆脱对个人情感的触摸。李欧塔(Lyotard 1984)提出,“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危机是后现代的基本情境,至少大叙事的危机多多少少可理解为受疆界、参照与空间危机所影响。我们如何划分内与外?如何协调近与远?如果“此地”与“彼方”不再有区别,而是即将融合为一,这将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过去的地理问题是:“你的家在哪?”如今已被新的问题取代:“家的意义为何”⑩?当我们将“家”这样一个概念从地理位置上抽离而更关注它的意义时,本身就说明了可以赋予意义的主体的重要性。“虚拟社会的身份嗜好,基本是主体性世界的延续”?,主体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建构理想的自我,生活失意的现代人可在其中体验别样人生、弥补现实缺憾”?。但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续, 还是现实社会是虚拟社会的延续有时候很难说清,然而非常明确的是当我们面对网络这一虚拟空间时,人的思想与情感获得空前的解放,人终于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在虚拟的“网络”上言说表达自我,而超越了现实生活“网”对个体的限制。因此,当网络作家借助网络媒介书写城市生活时,眼光会超越现实生活而更加关注自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我和我的经济适用男》《一霎风雨我爱过你》等小说对“我”的凸显,无不显示出城市网络小说的旨归。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小说是向内看的,看的是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份欲望,而传统小说更多的是看向外部的,作家往往怀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他们更多的时候并不直接袒露自我的生活,而是将目光投注到他者身上,形成一种审视。同样写城市中的白领情感故事,传统作家如张欣会写出“微笑抑郁者”,症候般地揭示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境况,但网络作家则更关注自我内心是否幸福。可以说,在传统书写者那里,无论城市获得了怎样的发展,他们总是将目光投射到城市的底部,透过繁华的表相中悲悯地书写城市人内心的伤痛,所表达的仍多是城市的滞重,关注的是人与城市的关系;而在网络作家那里,任何人与城市的关系归根结底仍然是自我情感的安放,人回到某个城市不是因为城,而是因为某个人。
网络的虚幻性彻彻底底地将人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相应地,人与城的关系就变成了人与人关系的书写,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的情感关系成为网络小说书写城市的重要部分。城市的快速发展往往带给人诸多焦虑,在变幻不居的城市街头,人们既不能像以往那样遥望故乡寄托乡愁,同时又必须在各种社会角色中担起自己的责任,单面又多功能地活着。关注自我情感是人绝对地掌握世界失败后期望把握自我的一种努力。在生活中,家庭、工作都变成了附带性的介绍,而生活中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指向了自我情感。如王齐君的《昌盛街》,本来写的是东北吉林的老城,但是小说的题记却明确说是写爱情,小说正文第一句则是“你们玩过刨幺吗?又是否到过昌盛街呢?”昌盛街作为一个破败的城市,作者已不关心它的改造与升级,也不再期望城里的男待业青年们有怎样的改变,于是将所有的问题悬置,就写一群天天无所事事玩刨幺的人,以及这群人中有些心酸有些朦胧的故事。《钱多多嫁人记》中的钱多多和依依作为上海本地人,从小在上海这个城市长大,看着这个城市变化,但是她们却无意探究这个城市,而是更沉浸于自己的情感世界,城市不过是一个存在却没有性格的空间。在这个拥挤的空间中虽然挤着各样的人,但这些人不过是生活的背景一样,虽每时每刻的人并不相同,但总体的氛围和感觉却丝毫没有差异,三十年如一日。正如周六的咖啡厅里,“人来人往,这氛围都好像没有变过”,而唯一变化的是年龄,“不不,还是有变化的,转眼她们两个都要三十了”。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也曾写道咖啡厅,但是他并不将目光一下子落到咖啡厅,而是将之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空间,展现出由此及彼的过程性,以及此与彼的相关性,如“按照初恋情人的指示,穿过一片贴满各种租赁广告、办假证广告和稀奇古怪的留言纸条的低矮破旧的筒子楼和老平房,来到河边的一家咖啡馆里”。可以说,后者的咖啡馆和前面的咖啡厅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从情感表达上,都差异极大,前者对现实的超脱与后者沉到现实之中的努力显示出作家书写城市过程中的不同。与跳出城市的现实空间相联系,网络文学对个人生存环境影响极大的家庭、工作也极少触及。正如钱多多和依依名为闺蜜,但多多甚至都不知道朋友依依的家庭情况,亦不会想家庭的成长对她带来的个人影响,“其实她(依依)也想解释,她妈妈原本出身富贵,当年为了嫁给一个工人的儿子而放弃跟父母离开中国,最后却被人抛弃,沦落到只能在棚户区里跟她相依为命”。同样地,工作中的变动也不能成为叙述的重点,一个“后来”就将所有的惊涛骇浪和腥风血雨打捞进去,不留任何痕迹:“后来……山田集团在这次投资中损失惨重,当然的,山田惠子也从UVL车底消失了。许飞上任后,李卫立提前退休。这世上每分钟都有人出生,有人死去,不过是公司内的新旧交替,一天之后这些名字便成为历史,再也没人提起”。即便是被知青们无限怀念甚至痛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也被简化为简单的个人情感,“前一段时间,单位组织去婺源旅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鬼使神差地就一个人走回了李庄,那棵老槐树还在。我做梦也想不到竟然会在那里看见了你林伯伯,年轻时候以为眨眼间便会过去的事情,原来是一辈子的。那天,我和他都哭了,后来,你林伯伯就在树下跪在我面前,说下半生一定会给我幸福”。
然而,人对环境的想象与脱离,并不是简单地活在一个虚幻的世间之中,相反,是自我努力改变现状的一种努力。就像《你好,旧时光》中的余周周,时常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妈妈和外婆早已见惯不怪,以至于当妈妈看到她在房间里自导自演的时候,虽然认为是“正在犯病”却并不给予干涉。余周周自己虽然通过幻想躲避外在的世界,但是她并没有成为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如“她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爱情是很恐怖很难缠的——即使她并不知道爱情到底是什么。”面对三教九流的大世界,“她学会了乖巧地跟大人打交道,该讲话的时候讲话,该沉默的时候沉默”。在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正是内心的造像,人真正地为自己的情感与生命活着,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有时间谈恋爱,更有机会长情。因此,与其说这些都市情感小说是虚幻想象,不如说是人作为一个主体,试图超越一切历史、现实束缚的真切诉求。正如较早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夜晚的隐喻一样,在夜晚的掩盖下,人内心的躁动和欲望赤裸裸地展现,就算是常被人讴歌的爱情与友情,在夜幕的掩盖下也往往崭露出它们令人心寒的一面来。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它就像夜晚一样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肉体隔离在外,使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当人隐身到网络空间之后,自我诉求就得以凸显,主体期望将一切固定的秩序和价值打破。这似乎预示了人在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里认知自我所要经历的路径,从隐到显,从打破价值秩序到建构自我。
真正的自我建构不是制造幻象,而是直面现实并建构新的关系。正如辛夷坞的《浮世浮城》,她表达既不是“世”也不是“城”,而是“浮”。现实生活中的赵旬旬,从未追求怦然心动、惊心动魄的爱,而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为目标,“只是再简单不过的生活,他不需要如痴如醉地爱我,也不需要为我赴汤蹈火,只要给我一个家”,能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万一哪天急病发作,还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提高生存概率。“我就是受够了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生活!”“你说我卖给谢凭宁也好,打自己的小算盘也好,我最大的愿望只是每天醒过来,发现今天的一切还和昨天一样,什么都还在,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一心爱着她的池澄则表示“你把我当成这个城市里最能信任的人,我会很珍惜这份信任,与情欲无关”。在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中,無论男人和女人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某种不安,他们都在或放纵或保守的行动中找寻着内心的一份慰藉。《我和我的经济适用男》中向来生活不羁的冯志豪,并不是一个长情的人,交往过很多女朋友,“从纯情稚嫩到风情万种,什么样的都有,唯独对何小君,两年来总不觉得厌倦,也算异数”。《一霎风雨我爱过你》中曾有无数个女朋友向来有轻微神经衰弱的周子衡,只要抱着自己的情人舒昀,“再大的压力都会统统化为无形,漫长的黑夜似乎变得极其好打发”,而此时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不再在物质的诱惑下委曲求全,她们期望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取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从身体到精神,都真正地独立。“作为一个成年女性,在单调的生活里加入这么一个角色,对她来讲并没有任何坏处”,面对位高权重的企业家情人,“她向来底气够足,只因为她并不亏欠他什么,甚至连一块钱都没有伸手拿过他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单纯,没有牵扯到利益或感情。所以无须小心翼翼地伺候对方”。这种自足而自我的诉求与20世纪30年代张爱玲笔下与男性斗智斗勇的白流苏的形象迥异,也与90年代初期张欣笔下的那些都市女性在欲望中迷失自己的情形极为不同。其实,当慕容雪村在《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由男性说出“两清了,我们互不相欠”时,就已经表明女性已拥有了与男性乃至整个社会对抗的能力。性与爱的分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易,某种程度上恰是人试图完全掌控自我的一种努力。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提出,“发现陌生的事实和关系使我们觉得增长了知识,尤其是当它们最后与我们的首要目的、生存及各种生存手段、我们的幸福或者各种各样彼此冲突的需求的满足相关时更是如此——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都是为了成为这些”?。因此,当我们看到网络文学中对自我情感的追求与梦幻般的大团圆结局设计时,除了批评它的简单,更应该看到心里深处所隐含的那份自我追求。曾经一直在心中打架的两个小人因为没有了现实世界关系的考验,可以无比放松地借助网络在内心做出选择,正如“敌人就隐藏在我们中间,或者我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所以当人在符号的空间里无限地变异狂欢之后,“通过交流这近乎饕餮的嗜好,才能自我清洗,自我诊断”?。
然而,网络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自我情感的张扬,实际上也因为网络的表层化,使得都市中的人对自我的痛苦认知和残忍剖析几乎不存在。大家在一切梦想皆可编制的网络世界里不断地寻找形式上的填补,而不会触及内心的自我更新与成长以及心智的蜕变,有的只是情境的变化。正所谓“网络成了社会实验室,我们可以在那里尝试塑造一个新的身份,那么这个自我更新的欲望结构是怎么样运作的,厌弃那个旧自我的理由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在充分看到网络文学的开放性的时候,我们却在网络文学的城市书写中看到一种自我的囚禁。以往我们强调城市中的人是因为社区的划分,人与人之间是单面性的交往。在网络文学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超越了现实生活“网”的限制,当城市成为没有内涵的代码,城市之间成为一种没有生命连接的关联之后,关乎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城乡问题也就被悬置起来。正如“赛博空间将如何影响我们, 并没有刻入其技术特性之中, 相反, 它是以社会——符号性关系网络为转移的, 而这个网络总是已经过度决定了赛博空间影响我们的方式”?。
班纳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讲道,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构建出来?。但是,当人们在小说中不再强调有效的时空,城市作为没有内涵的代码而存在时,小说的建构也就没有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存在,于是城市、民族与社会理所当然地难以成为关注的重点。王朔曾在《网络之星丛书》跋中认为:“这之后一切将变。”“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使每一个才子都不会被埋没,今后的伟大作家就将出现在这其中”。是否能产生伟大的作家当下还难以定论,但从当前网络文学对城市的书写可以看出,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正在借助网络媒介,超脱现实中滞重的关系束缚,他们越来越切近个体的感受与存在,这本身就预示着新的社会文化心理。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所有人借助网络获得完全自我的张扬后,有关城市的书写会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徐从辉.网络视野下的新世纪城市文学地图.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7).
③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
④转引自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
⑤陈慧芬.“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文学评论,2003(3).
⑥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64.
⑦蒋述卓.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2000(4).
⑧⑨⑩Scott McQuire.媒介城市:媒介、建筑与都市空间.赵伟妏,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1:10、29、12.
张念.网络媒介:符号的极乐世界.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黎杨全.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1).
[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M],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6.
[斯]齊则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99.
[美]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
张丽凤,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曾琪琪,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2017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