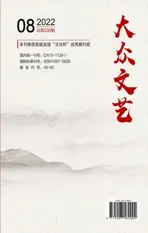汉代赋盛诗衰现象刍议
2019-07-12江苏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221116
(江苏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 221116)
自屈宋骚体聿兴,荀卿作“赋篇”命名,辞赋开始以一种独特的姿态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然而汉初之际,刘邦《大风歌》、贾谊《鵩鸟赋》等依旧承绍楚辞体例,至枚乘《七发》出现之后,汉代大赋体制方才得以确立。从此班张扬马之辈各骋才能,两汉巍巍然成为大赋纵横的王朝。虽然汉代的辨体意识尚未系统形成,然而终汉一代,文学发生的趋势是辞赋鼎盛而诗艺式微。尤其到了王国维明确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主张之后,赋学研究中以汉赋为中心的观念更是进一步被强化。那么,是什么铸就了汉赋的蓊郁之美?又是什么造成了汉诗的整体消沉?(案,此处不将建安文学包括在内)兹以为,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时代精神的“赋”化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王朝,汉朝不仅拥有着“大赋”一般的国势威容,其国力与气象也均是短命之秦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讲,完全可以把汉代视作中国第一个张扬出民族特征的大一统帝国。如莫砺锋即说道:“从暂时的结局来看,确实是秦国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如果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其实是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才真正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1公元前202年,高祖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尔后灭诸侯,营未央,议定礼制,终于将秦末以来的颓废局面重新收拾起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文景二代的苦心经营,西汉已然实现物阜民丰的愿景,成为盛极一时的东方帝国。试看:
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西京赋》
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西都赋》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到汉武帝时代,汉朝已经实现了空前强盛:南收百越,北定匈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培养政治人才;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种种恢弘的气象,本身即如大赋一般铺张扬厉,毋庸说为汉大赋的聿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汉代的赋家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抒情咏志的歌者,而更像是着力于描绘帝国气象的画师。
首先看作品题材。在两汉时期,大到都城、宫殿,小到一屏一鹤,都是赋所涉猎的对象,而在汉大赋之中,所涉及之对象更是细大不捐,包罗万象,以至于后人有“赋代类书”之说。萧统在《文选》中大致将赋分成了邑居,畋猎,纪事,咏物四类,而在两汉时期,这一雏形已经基本完备。如邑居则有两都、二京;畋猎则有子虚、上林;纪事则有北征、长门;咏物则有洞箫、长笛等等。其次,在作品风格上,无论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还是扬雄的甘泉、羽猎、河东、长杨,甚至于《梁王菟园赋》、《舞赋》这样再一等的赋作,都颇为气度不凡,蔚为壮丽。有人如此总结道,“苞括宇宙”的赋家,他们所追求的正是宇宙间一切大的东西,所企图创造的正是能令人拜倒的大的形象,所要夸扬的正是事物奇妙无穷的大的美点。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赋的气象便是王朝的气象,王朝的气象便是赋的气象,不但帝国成为了赋家笔下的骄傲,同时汉赋也成为了帝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二者彼此交融,彼此影响,使得赋体文学的繁荣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
二、文学理念的缺位
通过对汉朝时代特色的观察,我们大略了解到了汉赋兴盛的社会基础。那么从作家主体来看,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自觉选择了赋体的创作呢?这里以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彼时文人的侍从地位。
据班固《两都赋序》所言,“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 ……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汉赋的兴盛,固然与帝国气象息息相关,但统治者的喜好与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豢养文人在武帝时期形成了一个高峰,不啻帝王如此,连藩王亦多有此癖好。如:
(梁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史记·梁孝王世家》
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汉书·严助传》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这一时期,朝廷大量招致言语文学侍从,献赋作颂,既有积月成篇的司马相如,也有援笔立成的枚皋之辈。而考察汉代赋家身份,多属中朝官系的郎官,兼具参政与娱戏的双重功能。3然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往往更重视赋家的后一种身份,以至于扬雄发出了“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喟叹。
自觉抑或被动?功利抑或无功利?这是我们在讨论文学发展时不可避免的重要议题。毫无疑问,汉代赋家尽管有着汪洋恣肆的才思与深厚的文学积累,他们的创作是非自觉的,同时又是功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如许结以为,赋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固然源于文学或文辞的发展,但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完型,则显然与汉代礼乐制度的构建相关。4这就无怪乎在《史记》和《汉书》中,“文学”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而被书写出来,直到范晔《后汉书》的出现,方才专门为文学家们列了一篇文苑列传。再倘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侍从的作家们既没有在文学领域获得觉醒,文学也没有成为文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因此对他们而言,“缘情”或“言志”的诗歌自然不会成为他们探索的对象,而铺张扬厉、体国经野的大赋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们的心理趋从。
三、宗经意识的影响
经学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建立以来,渐次经历了黄老昌盛到儒学独尊的递变过程,伴随着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儒学典籍上升了到“经”的地位,从此经学便逐渐成为中国学术延续的一大血脉。著名学者徐复观即以为,“经学是两汉学术的骨干”。而于此同时,私家著史的习惯也于斯诞生。所以,经、史气质便一并构成了汉代文学的两大传统。有人即如此说道:“汉代赋论载于史书,赋论主张不免印上史家的痕迹,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皆为儒生,赋论思想自当蕴含汉儒经学思想。”5在这种情况下,“赋”的创作与批评自然也难逃宗经意识的禁锢。
秦火之后,天下文坛哑然。至武帝即位,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尔后今古文经相与颉颃,并有石渠、白虎之议。于此之际,田何之《易》、伏生之《书》、高堂生之《礼》、《诗经》四派、《春秋》三家,均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而史迁、班固先后撰写的《史记》、《汉书》,则并为中国历史学谋定了两种新的格局。基于这样一种背景,汉代辞赋家除了兼有他种身份之外,自身也多具学者气质。例如,司马相如为文字学家,扬雄为学者,班固为史家,张衡又是地理学家与科学家,除了辞赋写作之外,他们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建树。可以想见,没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与考据学的功夫,是断然难以写出一篇篇骋词大赋来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汉代文人理性远远大于诗性。在周国平译介的《悲剧的诞生》中,他将尼采的主张如是总结道:艺术家与批评家是资质相反的两种类型,前者从事创造,后者从事接受。6在尼采看来,理性的批评力必然损害感性的创造力。这样的见解,用于汉代文人的身上恰恰再合适不过了。
可以说,宗经意识就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为汉赋提供了大放异彩的养料,另一方面则遏制了汉代文人的诗性。故无论是扬马班张之辈,还是王褒、傅毅之流,在诗歌领域毫无疑问是一无建树,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但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囿于经学的汉代文人虽然在诗艺上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却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新文体——赋。
注释:
1.莫砺锋.诗意人生[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4.
2.何新文.辞赋散论[M].东方出版社,2000:55.
3.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M].中华书局,2005:23-36.
4.许结.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J].南京大学学报,2006(04):90.
5.马言.从用到体:赋体的自觉与变迁[J].中国韵文学刊,2018(02):100.
6.[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