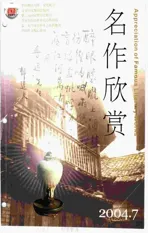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两只蝴蝶》及新诗
2019-07-12北京刘琼
北京|刘琼
《两只蝴蝶》是胡适1916年8月23日写的一首诗,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文诗。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从诗体本身,这首诗都被认为是平平之作。但它在文学史的地位以及它传达、传播的信息,一直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是珍贵的。
先说写作当时。有史家说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革命活动是在异国他乡酝酿成熟,比如辛亥革命,比如新文化运动。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环境有关。一方面,封建制度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形成严重阻碍,另一方面,整个世界发展出现高地,先进强大地区(包括文化)势必对落后贫弱地区(包括文化)形成压迫,东西方列强在用武力敲开中国大门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入侵战略,比如庚子赔款留学计划。庚子赔款留学计划,从始作俑者的美国角度,本质上是一项长期的文化战略,但客观上,让少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从盲目自信的封建老大意识里清醒过来。“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辛亥革命前一部分中国社会精英分子的普遍共识。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与同盟会、兴中会元老在日本东京、长崎等地酝酿,新文化运动是由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胡适等人率先举旗。写《两只蝴蝶》时的胡适,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已经从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钻研哲学。
可以看看当时的留学规定。根据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的派遣留美学生规程,有些规定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这一项是总体目标,应该基本实现了。比如,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此外,他们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这一项是对留学生的考核要求和学业要求。有意味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留学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学生,申请农林理工专业,还是远比申请文科专业容易。换句话说,美国在对待中国留学生政策上,一百年几乎没变。跟今天的留学环境差不多,能够获得庚子赔款留学机会的学生,一则要有文学、历史和英语学业基础,二则家境不错,能够负担起一些生活用费。此外,庚子赔款留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起初申请的专业跟最后学成的专业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一则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学习期间允许转专业,二则一些留学生申请理工科是权宜之计,他们真正的兴趣还是人文学科。胡适便是一例。胡适最初申请的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来转到文理学院,最后又考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庚子赔款留学除了美国之外,后来英、法、荷、比等增加进来。庚子赔款留学总数不详,但这批借由庚子赔款留学海外的学生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精英。推断其因,大概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家世不错的少爷和小姐,在国内接受过较好的人文教育,经由庚子赔款项目,又有机会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眼界和功底都不错,回到国内,只要他们能够踏踏实实在某个领域耕耘,基本都属于开天辟地,能建创业之功。
新文化运动是经由文字革命开始,最先开始的是早期留美的青年学生。1915年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该研究部的文学委员。这期间,有感于旧有的语言方式对思考和表达的严重桎梏,胡适大力提倡简易文体和对话体写作。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当年的思想。在1914年到1916年这三年的日记里,胡适记载了对于文字、文体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写了不少白话诗,对古人诗歌也做了评论。我粗略地数了一下,这一段时间涉及诗歌的文章大约有三十来篇,如《诗贵有真》《三句转韵体诗》《秦少游词》《诗乃词之进化》《陈同甫词》《刘过词不拘音韵》《山谷词带土音》《杨、任诗句》《答梅觐庄——白话诗》《答觐庄白话诗之起因》《杂诗二首》《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杜甫白话诗》《打油诗寄元任》《宋人白话诗》《改旧诗》《白话律诗》《打油诗一束》《打油诗又一束》《写景一首》《打油诗》等。顾名思义,这些文章的主题内容从题目几见端倪。
显然,力主白话文写作并率先用白话文写诗的胡适,对于古诗并非不喜欢,更不是不懂。从胡适对宋诗的研究就能看出,胡适的古典诗文功底深厚。中国是个出诗人的国家,甚至是诗教国家,这就好比有的民族是歌舞民族,但凡开始说话走路,就开始唱歌跳舞。感时伤怀,生离死别,场合应酬,抒怀言志,无一不用到诗。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宋词较之唐诗,偏重理趣。胡适喜欢宋诗,可能也与其性情爱好有关。本质上,胡适不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是一个理性随和的学者,这在许多人关于胡适的印象记中也能看出。胡适性格中的学者气大于其文人气,这也是胡适文学创作上成就并不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说,这也不是他的追求。这一点是他跟鲁迅的区别。鲁迅的前面尽管有革命家、思想家等定语,但终其一生,鲁迅作为一个作家的实践始终没有停止。而胡适公开地说文学只是他的爱好,他的职业是哲学。相对而言,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这段时间,也是胡适文学创作较多的时期。期间,胡适写了许多打油诗,既出于“拨乱反正”、文体探索的需要,也是天性使然。胡适广交朋友,擅长演讲,性格幽默平和,人又聪明,写打油诗体现了其对于语言使用的一个原则:晓畅明白。
在日记中,胡适主张,写诗第一贵真——真切、真实、真情;第二畅白,畅白涉及文字形式,也涉及内容,他认为写作要平易近人;第三讲韵律。
第一点最好理解。在此插播一下,《两只蝴蝶》最打动我的,恰恰就是一种石破天惊的“真”。今天,我们男女相爱互相表白是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刚刚从皇帝的龙袍下解放出来的中国社会,前一刻还男女授受不亲,后一刻则公然用语言来表情示爱,这是文字的革命,更是观念的革命,冲破的不只是文字本身的束缚,更是理学观念的重重枷锁。言之有物,不做无病呻吟,这也是“真”所要提倡的文学主张。继续联想到今天的白话诗,许多诗反倒越写越复杂,越来越看不懂了,白话还是白话,诗却不是原来的诗,所指和能指缺乏严密的逻辑关联。
第二点是文字革命的具体表达。提出这一点,从中国文字的传承来看,是有基础的。中华文明之所以在民族和国家变动不居中依然根脉不断,文字和文化始终一脉相承很重要。胡适认为白话文革命不是空穴来风,从宋诗开始就有“白话诗”之说,说明白话的基础很扎实。胡适这个观念,在东部留学生中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这让胡适感到孤独。这些留学生因为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国古典诗词难以忘怀,这一点是正常的,毕竟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它在高峰时期的美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字——这是就具体形式而言,到了晚清和民国,科举八股文以及各种形式主义化文字,无论作为公文文体,还是作为诗文写作,已经严重不适应时代生活剧烈的变化。
前两点好理解。第三点关于韵律的主张,这一点往往被后来的我们忽略。我想多说几句。胡适不是反对死气沉沉的旧体诗,主张用白话文写诗吗?韵律不是旧体诗的遗产吗?与有韵律的古诗相比,白话文写诗要不要押韵,怎么构造意境,是大家感到困惑的地方。这些问题特别重要,解决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新诗出不出成果。
第一,用白话文写诗,并不代表不要韵律。新诗与古诗之别,以及优劣之分,是一百年来长盛不衰的议题。其中最直接的问题是,新诗到底要不要韵律?近年来新诗的诗味越写越淡,什么原因?回过头来看新文化运动,会发现哪怕是写打油诗,也不会认为韵律是个问题,即诗歌自然是要关注节奏的。胡适的《两只蝴蝶》,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鲁迅的《我的失恋》、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女神》系列,这些白话诗的第一批成员,都具有较强的节奏和音乐性。郭沫若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特别推崇纯情感流露的无任何矫饰的诗歌写作,认为优秀诗歌的节奏应该是内在情绪的涨落,而认知是情绪内核的扩展和升华。虽然郭沫若后期的诗受到非议很多,但其诗歌理论及其前期的诗歌实践在中国新诗史上拥有重要地位。古诗词特别讲究音韵合辙,到了胡适、鲁迅,即便用白话写诗,也基本押韵。“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著名的《两只蝴蝶》全文不过40字,除了“也无心上天”这一句,“天”“还”“怜”“单”都合韵,朗朗上口,易懂好记。中国是诗歌大国,早期人类似乎会说话就会咏诗,比如大家都知道《诗经》里的“国风”是朝廷采诗官摇着铃从民间采集而来。看《诗经》以及唐诗也会发现,比起技巧,从发生学的角度,诗歌写作重在言志抒怀,而把诗写得好看,让人能唱能诵,志和怀才能尽其意走得远。这也是当年白居易等写诗提倡翁妪能颂的思想基础。再从文字发展史看,中国普通百姓受教育面普遍不广,许多文学形式是通过口头流传,才能起到作用。口头流传,对于文字的语言性、音乐性要求较高。今天能够流传下来的唐诗宋词,并不是所有唐诗宋词的总量,经由漫长的时间能够流传下来,与宋以后印刷术的发达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诗歌本身的音韵节奏有助于口口相传。
第二,用白话文写诗,也要讲究意境构造。《两只蝴蝶》便是实践成果。就文本而言,这是一首小型叙事诗,用动作和细节描写两只蝴蝶的合与分,“双双飞”“忽飞还”“怪可怜”“太孤单”,这些富有鲜明情感色彩的语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期的诗歌,比如汉乐府《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里方位词的变化,映衬着不变的坚持的“鱼戏”这个场景,强化和放大了现场。没有人因此觉得它写得单调,反而被这种情绪感染。今天我们的诸多流行歌曲和民谣也是用这种旋律和意境的重复来“叠景”。到了鲁迅写《我的失恋》这首诗,因是故意调笑张衡的《四愁诗》,故此步其韵而写,使用的全是白话文。《四愁诗》写相思之苦,原诗四段,每段七句,在每段第四句相继出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崐报之英琼瑶”“美人赠我琴朗轩,何以报之双玉盘”“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美人赠我锦绣锻,何以报之青玉案”。鲁迅写《我的失恋》,把第四句改成:“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葫芦。”“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百蝶巾”对“猫头鹰”,“双燕图”对“冰糖葫芦”,“金表索”对“发汗药”,等于是诗意有情之物对干巴甚至恐怖的实物,这种错位的意象使用,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忍俊不禁,达到讽刺效果。
第三,白话文写诗,要有趣味。现在,我们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两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和《我的失恋》都是大师之作。胡适和鲁迅两个大师被广泛打趣,原因在于大家觉得这两首诗超越了大师的平常“文格”,写得滑稽、有趣。没错,滑稽有趣,是美学的一种趣味。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在《民国最美的情诗》一文中,大赞胡适这首诗写得“浅畅明白,通俗感人”。“晓畅明白”“通俗感人”,正是早期白话诗提倡的美学趣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诗歌这种趣味的变革。不仅当时就有人表示批评,比如学衡派教授胡先彇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批评文章,言其“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今天,同样也有许多人对胡适的诗歌不以为然,比如台湾诗人余光中就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余光中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后来人对于胡适早期白话诗歌成就的认知。唐诗以其意象意境隽永深致被大家喜欢,到了白话诗的时候,仍然需要用白话文构造意境并达到美感目的。诗人用白话文写诗,构造意境的本事倘若丢了,诗歌光剩下浅白,也就没有诗味了。
胡适不仅提出了用白话文写诗这个主张,并身体力行。与胡适同时代的鲁迅与胡适的侧重点不同,鲁迅是纯粹意义上的作家,是文体学大家,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无一不精,因此后来在白话文创作上的成就要远远大于胡适。鲁迅对于诗歌,无论古体还是新诗,都写,并相当有水准。关于如何用白话文写诗,鲁迅有很多理论思考。就以打油诗《我的失恋》为例,用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文序》里的话,是“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啊呀阿育,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首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了”。由这段话,不仅知道鲁迅写这首诗的心理历程,而且一个活泼幽默充满情趣的鲁迅跃然纸上。这与后来被刻板化和严肃化的鲁迅形象迥然不同。没错,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言,鲁迅有其严肃、庄重、“横眉冷对”的一面,也有其平易、诙谐、“孺子牛”的一面。“创作新诗有没有句式?有。句式不变,调韵甚至也不变。诗情,诗心,都为之一变”,关于这首《我的失恋》的评论,真是太到位了。
今天,我们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谈什么?当然首先是谈它的思想文化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宗明义,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中国大门,中国旧有制度和文化已经完全阻碍社会发展进步和领土安全之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思想文化革命为圭皋,最大成果是“开天辟地”,建立新社会、新制度和新政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或者说完成了的工作,是文化和思想的启蒙。因此,今天我们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充分认识它已经结束的使命和尚未完成的使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对于民族成长和国家建设不是一蹴而就,当然也就不是阶段性和短期的工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新,是毫无疑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一面大旗,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从历史的漫长的坐标来看,新和旧都是相对而言的。但是在历史的转折点和转型期,新和旧会表现为突变和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新文学的大幕,中国现代文学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旧文学和新文学之别,首先表现为语言形式之别即白话文和文言文之别。这是断裂式的差别。对于写作来说,语言是一种形式。但是在语言与语言之间,语言本身就是思想、文化、观念,也即内容。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情感习惯和逻辑习惯,甚至思考习惯。比如同样是小说,曾朴的文言文小说《孽海花》等,虽然开启了近代小说写作的先河,但我们也不会称之为新文学。新文学要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算起。语言的这个变革在明面上,容易辨析。用白话文写作,形成新的文体,比如新诗。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文学样式,新诗即便不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那颗钻石,也是最富有含义的那朵玫瑰。
因此,如何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条相对缩小的线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