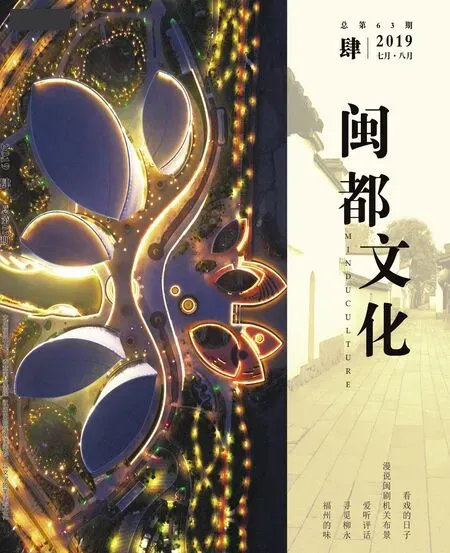看戏的日子
2019-07-06刘小敏
刘小敏
1
1949年4月,苏州观前街附近的开明大戏院,上座颇佳,“尽管炮声隆隆,但戏迷们似乎听而不闻,看戏的豪兴丝毫不减……”几十年以后,当我读到李盛斌先生的回忆,仍不免惊讶于百姓们兵临城下的淡定。或者因为胜败大局已定?更何况,富连成社“盛”字科中的“武生三杰”之一李盛斌,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儿,正在舞台上叱咤风云。
渡过长江的大军势不可当,几天之后苏州解放,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慰问,剧院也为之演出,戏码中就有李盛斌的拿手戏《伐子都》。大军与百姓一样,都爱看戏且不乏戏迷。其时先后任十兵团28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刘培善(后任福州军区副政委),观剧后亲下指示,动员艺人尤其名艺人参军。6月间,李盛斌带领一双儿女还有全部行头参军入伍,被委任为三野十兵团政治部京剧团艺术委员会主任。之后一路随军南下。8月20日,福州解放仅仅3天,京剧团紧跟着便进了城……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看过李盛斌的戏,但从前常听父亲提到他。少年时代,跟着父亲看了许多戏,见我没心没肺啥剧种都喜欢,他便恨铁不成钢地劝导:京剧是国剧,最博大精深;省京剧团地李盛斌,演得那叫一个好啊——1953年十兵团京剧团集体转业成立省京剧团,当时称福建京剧院。

京剧《伐子都》剧照,李盛斌先生饰公孙阏
父亲素爱京剧,高兴时也常哼唱几句。我猜想,当年在苏州,父亲是不是就见识过大武生李盛斌的飒爽英姿?1949年7月10日,从胶东大众报社选调到华东支队新闻中队的父亲,随省委从上海到苏州集中,同城之际或者有机会瞧见十兵团京剧团闻名遐迩新来的名角儿?3天之后新闻中队开拔南下,中途与十兵团京剧团又都曾在闽北的建瓯逗留。新闻中队8月22日从西门进入福州,比京剧团迟了两天。
假如当年有卫星,假如卫星留存下搜寻影像,定会看到那支浩浩荡荡的南下队伍,人流中不仅有扛枪的军人,而且如影随形同行着文化的潺潺溪涧。场面是一下子就铺开。8月25日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正式出版。京腔京调亦为闽都增添了别样选择,每一出新戏诸如《闯王进京》《九件衣》什么的推出,总被挤破了门。军队轮流看,其热情自不待言,听惯了闽剧的群众也争着先睹为快,据说有夜里排队到天亮买票的,甚至有观众带着油布睡在剧场门口等候开门……当然啦,倘若本地居民更多出自于新鲜感,那儿京剧的主要观众应还是南下的大军与干部群体。

林浦村,闽剧表演南宋末代君臣“行乡”
对于偏居东南一隅的闽都来说,世世代代,所有迁徙而来者几乎皆为南渡。所有南渡的移民,在闽都多彩的文化织锦中都留下或多或少的经纬。传说林浦的安南伬,就是南宋末年赵罡逃至此地登基称帝,随队乐师传授给当地民间艺人演变而成,如今已位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遑论,1949年的革命大迁徙,那是一个强有力新政权的建立,越过武夷山脉的南下洪流中,十兵团所辖第28、29、31军至少10万人左右(次年32军约2.9万人亦从青岛南下福建),还有山东、山西等地抽调的干部以及上海南下服务团的学生们约万余人。人类对于文化的渴求在此又一次显现,新时代以初生的芬芳绽放着花儿朵朵。不仅仅京剧,20世纪50年代相继成立的省话剧团、省歌舞团等,追溯前身,总可以窥见南下洪流中随军文工团的形影,留存着历史不可抹却的踪迹。
也或多或少,留存在我们的脑海心田。
2
多年前姥姥在世时,曾在我面前数落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说小妹出生没几天,母亲就撂下小婴儿溜出家门,只为看京剧——梅兰芳的戏。小妹出生于1954年3月,近日我查了查,梅先生果然于1954年来过福州,但在6月。虽说姥姥夸大其词了,但与父亲一样来自胶东的母亲,爱看京剧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梅大师的戏呢!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兰芳第一次来福建,唱的是“断桥”。年届60的梅先生此前是否曾涉足闽地不得而知,但京剧大师们足迹罕见的原因应该比较好理解:方言复杂的八闽居民,早年间怕没多少人欣赏京腔京调吧?1949年翻山越岭跋涉而来的十余万“两个声”们,成为京剧观众的天然基础;普通话的渐渐推广普及,应该也是京剧等渐渐扎根的因素。梅先生终于来了,还不止一次。
根据采购申请、需求合并、采购计划、确定货源、询价报价等多个环节的处理后产生采购订单,向《合格供应目录》内的供应商购买物料;供应商生产备货,发到工厂仓库后进行采购收货质检,并接收供应商开具的采购发票进行合同核销;最后转到存货系统进行存货核算以及转到应付系统进行付款结算。各个功能可相互参照,也可手工录入,减少人工操作的工作量。
梅兰芳再次来福建,是1958年。
海峡两岸的对峙,使闽地成为前线,尤其8•23炮击金门后,福建骤成焦点,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慰问团赴闽“慰问前线三军”。读得回忆文章《全国人民慰问福建前线——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作者庄正时任福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在纷繁的接待事务中,他曾以日记细细记录下当年那些迎来送往:从1958年9月至1960年12月,全国有100多个慰问团和文艺团体来福建前线慰问。国家级的团体就有好些,各省地方剧团也接踵而至,京剧、粤剧、潮剧、赣剧、采茶剧、邵阳花鼓戏、湘剧、山西梆子、汉剧、秦腔、碗碗腔、黄梅戏、庐剧、泗州戏、越剧、吕剧、河北梆子、东北二人转等,都是一流的剧团、顶尖的名角儿,诸如侯宝林、常香玉、袁雪芬、严凤英、周信芳……
来来往往,省城自然也都演上几场,那盛况堪称空前绝后。仿佛不经意间,历史老人撒落下一串沉甸甸的麦穗儿,那么饱满、芳香,飘荡在闽都的坊巷间。
正是逢上那年代,小学二年级的我,开始有了徜徉戏曲百花园的机缘。报社是宣传单位,戏票少不了,又总是很人性化地一人给两张票,作为长女的我,便也跟着父亲看了好些剧目,狂轰般被普及了戏曲。但年纪还小,懵懵懂懂,又或者一下子贪多嚼不烂,便没对哪个剧种特别着迷。回味起来,就好像现如今欣赏那乐坛,一个个歌手轮番上场。自然也有印象特别深的,比如沪剧《罗汉钱》。庄正的回忆文章罗列了一大堆,不知怎的没有提到沪剧,偏偏《罗汉钱》女主角丁是娥我最是喜欢,那唱腔婉转细腻,如行云流水,令人舒坦。
梅先生是10月间,随首都文艺界慰问团前来的,团长是田汉,他是副团长。仅仅这一个慰问团,福州9天、厦门2个星期,共演出78场,观众61152人次。梅大师在榕演出了《宇宙锋》等戏,还为省京剧团演员做指导。“梅兰芳在几次慰问演出完毕后,不下妆就走下台来把观众送到大门外,而且亲自到前沿阵地和坑道给战士们清唱,没有琴师就请战士伴奏,这样的事是他以前少有的……”当年的慰问团工作总结报告如是说。
当然啦,梅大师的演出一票难求,我自是无缘得见。即便父亲能得两张票也没我的份,肯定被母亲抢先一步啦。
3
之所以不确定是否看过李盛斌的戏,是因为1958年,47岁的他全心投入创办省京剧学校,演艺事业难免有所牺牲,正值盛年却唱得很少了。但当年省京剧团阵势大名角儿多,好些戏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女孩子嘛,珠环翠绕的旦角自然喜欢,最令我久久仰慕的却是一位武生。也是无意间着了迷。那天在人民剧场看折子戏,《伐子都》开场时,武戏原不在兴趣之列,便溜到末排闲逛,锣鼓声中猛一抬头,只见从叠着的三四张桌子上,有一扮相英俊的武生翻跟斗下来,稳稳站立。须知他扎靠披蟒、头戴帅盔,两根长长的雉翎飘忽悠荡,如此这般的“云里翻”着实不易。一打听,武生名唤景惠生,是李盛斌的徒弟,武戏好,唱功也好。后来的年月《伐子都》是不能演了,只靠样板戏过把瘾。省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也是景惠生主演。“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回旋跌宕的唱腔从幕后悠悠传来,随即打虎上山的主角飒爽英姿登场亮相——在我眼里景惠生扮演的杨子荣,着实比京剧电影中的童祥苓更棒!
芳华越剧团的戏,当年那是百看不厌。《红楼梦》只是其一,《盘妻索妻》《沙漠王子》等,更是芳华越剧团屡屡上演的拿手剧目。扮相俊朗、唱腔醇厚的尹桂芳自不必说,常与她搭档的旦角李金凤亦沉静秀美、清丽婉转,一对才子佳人,蝴蝶般总是在我心中蹁跹起舞。
曾经在温泉路的大众澡堂,偶遇李金凤。当年的女汤池,需用木盆从热气腾腾的温泉池子舀了水,在外边先洗头。若洗淋浴也可免去这一道,只是常常要排队。那天我正洗着头呢,忽听得叽叽喳喳“阿拉”声起,涌进一群亮眼的女浴客,其中一位因将衣服搭在门框占位与人有所争执,直到迟来的伙伴走进。那个款款而来者,似曾相识,猛地认出正是芳华越剧团的李金凤,与台上一般娴静优雅……顿时有一点很奇怪的感觉:舞台上的女神,也需食人间烟火啊。

1962年芳华越剧团演出《盘妻索妻》,尹桂芳饰梁玉书,李金凤饰谢云霞
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芳华越剧团曾在沪上数一数二,小生尹桂芳更是“越剧皇帝”、“尹派”创始人;不知道李金凤们是1959年随尹桂芳支援福建而来,抛下原本熟悉的观众、舞台以及安逸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初,从知青到南平纺织厂分配在针织部——原是内迁而来的上海勤余针织厂,师傅们对沪上深切的眷恋之情,让我蓦然间体味到芳华女子们南下的不易。满口上海话的师傅们倔强地试图保留往昔生活,丁字鞋、格花呢外套、一字领两用衫……探亲往返中所有沪上流行被一一传送到南平安丰大沟,讲究的甚至连酱油也从上海带过来。
这一南来,就是多少年就是一辈子。2000年2月28日,弥留之际的尹桂芳要外甥女找来原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题词展示给她看:“越剧奇葩”。京剧武生李盛斌1990年9月病逝于福州,他好几次有机会去北京、去上海,却没有离开。一路走来的艰辛,猝不及防的“文革”带来的深重磨难,都没有夺走他们的爱——爱戏剧,爱这个浸润着他们心血的地方。
4
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省会城市居住的好处之一就在于,看戏的机会,真的很多很多。省一级剧团自不必说,逢年过节遇大事总归得演上几场。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学校组织观看,流浪儿彼佳出场时哼唱的“你是我的爱人,溜溜地嘎……”在男孩们中间流行一时,每每还特别加重“爱人”二字。各地县剧团时不时会演,诸如高甲戏《连升三级》、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等名剧,都曾在闽都的舞台大放光彩。《团圆之后》简直就是我此生看过的最悲催的戏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还能嗅到缕缕忧伤,如此浓郁。
闽剧却看得不多——父亲不热衷,我自然就缺少机会。但毕竟在福州,闽剧的主场地,自当见识过。最记得的一出就是《贻顺哥烛蒂》,林务夏主演,那端着算盘活灵活现的模样儿,真把一个吝啬之人演绝了。观看此剧是学校组织的,一拨孩子在表演结束后上台献花。从时间推算,很可能在1962年,或者就是老舍、曹禺、田汉、张庚、阳翰深等北京“五老”来闽观看《贻顺哥烛蒂》那一次?当年老舍先生观剧后,曾与林务夏在鼓山座谈并赋诗一首:“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漾春波。”
令老舍先生“十年尚忆”的《钗头凤》,主演是闽剧名角李铭玉与郭西珠。1952年《钗头凤》赴京参加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观看者中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此剧,但“郭西珠”三字却是早早就烙下印记。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读小学四五年级,走过学校操场老榕树下,忽听得两个老师低声议论:瞧,那就是郭西珠的女儿!视线前方有一女孩,走路颇有弹性,两条马尾辫随着脚步一甩一甩。何等重要人物,连女儿都让老师注目?惊讶之余便对女孩留上了心,方知郭西珠乃闽剧名角,假如没有记错,女孩随母姓,名叫郭小玲。

京剧电影《大闹天宫》剧照
隐约记得似乎是在光荣剧场观看的《贻顺哥烛蒂》。光荣剧场在八一七路东侧,原亨得利钟表店旁边,似乎比较多上演闽剧。当年最繁华的老城中心东街口附近,汇聚了人民剧场、光荣剧场、八一剧场、人民影院等好些影剧院,都是我们常去之处。1954年竣工的人民剧场,廊沿4根罗马柱,气派十足,是当年榕城最“高大上”的场地,但凡有影响力的演出多在此间。我所居住的报社宿舍与人民剧场仅一墙之隔,晚间常常可以听见演出结束散场时若隐若现的乐曲声……
如今人民剧场倒是还在,但早已不是重要的演出场所。省里几个主要剧团都有了自己的专属场地,前些年曾在白马河边的芳华剧院看过一场演出,似乎是团庆纪念,折子戏、清唱什么的,很是多姿多彩。2008年越剧(尹派)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尹桂芳的嫡传弟子王君安成为越剧(尹派)非遗传承人。潺潺流淌的白马河水,想必早已将喜讯传递给九泉之下的尹先生。
京剧是好些年没看了。前些日子倒是读到一则消息:福建省承担创拍京剧电影《大闹天宫》,福建京剧院牵头全国11家院团的精兵强将,已经开拍。京剧电影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大闹天宫》是迄今唯一一部武戏。我看到了一个名字:李幼斌。这个当年与父亲李盛斌一道参军,跋山涉水走进闽都的10岁小武生,如今已位列专家指导委员会名单。
既居福州,在街角拐个弯有时也会与闽剧相逢。家住东门,三天两头走过琯尾街,那地方至今仍留存着浓浓的乡俗民情,三岔口榕荫遮盖的古戏台,农历年节时有草台班子唱闽剧,居民们总是早早排下凳子等候。土的有洋的也有。前些日子在三坊七巷中瑞剧坊,一台高科技文化影音秀讲述着福州故事,闽剧自然也被融入剧情。
戏曲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渐渐远去,时代的发展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但在这个躁动的岁月,有时真是挺怀念那些婉转曲折、百转千绕的腔调,剪不断理还乱的悠悠情怀……
还有那些,看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