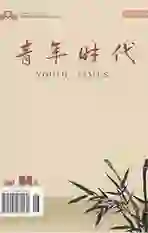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异议裁定的实证分析
2019-06-25黄于芯
黄于芯



摘 要:通过对三项裁定书进行对比分析得知,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异议的裁定,各地不同的法院根据自由裁量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裁判结果也不同。而解决网络纠纷的首要环节是确定协议管辖是否有效。只有确定了有效性,才能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由此需要从普通协议管辖的有效性及效力方面来看清该程序的“真容”,故结合普通协议管辖的理解和域外的经验确定我国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统一适用,比如“协议条款能够记录保存且位置清晰”、“限制适用弱者保护”、“明确界定网络合同纠纷当事人”等。
关键词:网络合同纠纷;普通协议管辖;有效性规定;当事人界定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的跨地域性无法适用传统理论中的连接点,故协议管辖制度的灵活性和快速确定网络案件的管辖权归属等优势,可以很好的平衡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网络合同有着完美的契合点,故我国的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制度应运而生。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34条①规定了协议管辖制度,为了应对日益上升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②对其作了补充规定。在网络购物过程中,一般会出现三方主体,即消费者、店家和平台运营者。平台运营者在新用户注册时,通常会通过格式条款的形式与消费者订立协议管辖,并以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即达成平台运营者与消费者发生争议时由协议约定的法院管辖。但是,当纠纷涉及到非协议管辖签署一方的店家时,法院是否会对其适用协议管辖呢?对此,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网站搜索裁判文书,对浙江、湖北、广东三地部分法院有关“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处理情况的观察发现,各地法院对于协议管辖有效性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在以店家为被告和以店家与平台运营者为共同被告的两种不同情况下,法院对于协议管辖的适用存在司法态度差异。处理结果的混乱与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制度立法本意相去甚远。因而,上述问题亟需理论上的回应。因此,本文通过裁定书分析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问题,透视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确立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统一适用,从而为法院如何统一适法提供些许参考。
二、基于三种网购合同管辖协议异议裁定书的现状检视
同样是卖家提前拟定的协议管辖的条款,法院在认定该条款效力时却出现不同的裁定结果,并且在以店家为被告和以店家与平台运营者为共同被告的两种不同情况下,法院对于协议管辖的适用态度也有所不同。在此,选择以下三地法院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
(一)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即案例一)③
苏宁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心因与周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中,苏宁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心上诉称,本案争议发生于上诉人开设经营的网络销售平台,而淘宝注册协议有所规定,在使用淘宝平台服务产生及与淘宝平台服务有关的争议,由淘宝与消费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周某在淘宝注册,即应受该协议约束,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浙江省衢州中院并未采纳上诉人的观点,裁定如下:天猫注册协议第十条第二款约定的管辖协议,属淘宝平台与注册人就服务产生争议而作出的管辖约定,而本案系买卖合同双方产生管辖争议,不受该管辖约定约束,应当按照《民诉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二)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即案例二)④
刘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中,上诉人刘某称其在手机上注册的淘宝账户,注册页面上没有提示注意管辖条款,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关于协议管辖的格式条款应当无效。并且本案有三个被告,只有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和上诉人之间对协议管辖有过约定。应当依据《民诉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依照其收货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确定管辖法院。湖北省黄石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刘某在注册淘宝网时同意淘宝平台的《服务协议》中的约定:发生争议,由淘宝平台与消费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管辖条款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并注以黑体以特别提示,应为有效。故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即案例三)⑤
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称,本案应为产品责任纠纷,并非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张某作为天猫会员与淘宝交易平台签署的《服务协议》已确定发生纠纷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广东省广州中院依据《民诉法解释》第20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系由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天猫店铺购买姜黄粉引起纠纷,因此,本案定性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涉案产品的收货地为广州市荔湾区,应认定广州市荔湾区为合同履行地,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至于上诉人主张淘宝平台已与被上诉人约定发生纠纷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问题,法院认为,《服务协议》中管辖条款参杂在大量的繁琐资讯中间,使被上诉人难以注意到该格式条款的具体内容,不能认定采取了合理方式提请注意的措施,即便有加粗提醒,但仍然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以此认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从上述三个裁定书主文可以得知,三地法院对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浙江衢州中院的裁判结果认为店家与消费者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不适用协议管辖的约定,明确了店家的地位,其裁定书主文的句子主干为“买卖合同双方不适用协议管辖”;湖北黄石中院裁判消费者、店家、经营平台均适用协议管辖的约定,对店家和和经营平台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界定,裁定书主文的句子主干为“网络合同纠纷适用协议管辖”,而“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作为“协议管辖”的定语;广东广州中院裁判认为预先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直接不适用协议管辖,对于店家和经营平台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界定,裁定书主文的句子主干为“网络合同纠纷适用买卖合同糾纷管辖规定”,“协议管辖条款无效”则作为状语修饰“买卖合同纠纷管辖规定”。
从立法上看,设立网络购物合同协议管辖制度是为了消费者能过通过合法的方式顺利维权,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实现诉讼机会均等,但是,在实践中预先约定的协议管辖恰恰违背了立法的本意,平台运营者主动提供网络合同的出发点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消费者为了能够在网上购物就必须接受所有条款才能完成注册,纠纷发生时还会增加消费者的诉讼成本。
三、“不同裁判结果”现象出现的认识归因
通过对上述三个案例的裁定书裁定主文进行句子成分分析发现,实践中法院处理结果的混乱归根结底是对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有效性问题没有一致认识以及对当事人的界定不清。
(一)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是否有效缺乏统一标准
上述案例二与案例三中,均以店家和平台运营者为共同被告,但是两地不同的法院根据自由裁量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导致相同类型的案件在不同法院得出不同的判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有效性问题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下面将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展开:(1)实践层面。通过对三项裁判文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一个共性的问题,即案例的裁判文书对预先订立的格式条款的效力要么缺少说理部分,要么被法院概括了之,意味着法院审理标准的模糊,故可推知司法实践中法院在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认定上出现混乱。(2)理论层面。从协议管辖条款认定的角度出发,实务操作中协议管辖条款“有效性”的统一标准是什么;对“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又如何去界定;订立条款时商家是否履行注意义务也会因为出现各种因素作出不同的判断,故理论上缺乏统一的标准作指引。
(二)网络合同纠纷对当事人没有明确界定
在前述案例一与案例二中,分别以店家为被告和以店家与平台运营者为共同被告,法院对于协议管辖的适用态度存在差异,裁判结果的混乱使消费者无所适从。究其原因在于对当事人界定不明,忽略非管辖协议签署方的被告店家,应当如何确定管辖?分析上述问题,必须先明确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模式,如下图:
我国的电子商务平台分为B2C模式与C2C模式,前者是企业对消费者,也叫“平台自营”模式,平台自行决定商业主体及发货主体,自己面向大众消费者,例如当当、亚马逊、携程网;后者是消费者对消费者,也叫“第三方经营”模式,平台只是作为店家与消费者沟通的渠道,例如淘宝。在“第三方经营”模式之下就会出现店家与平台运营者、消费者与店家的关系界定。
1.店家与平台运营者之间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界定
店家签署协议进驻平台运营者的平台,该协议由平台运营者提供,某种程度上是否与网络购物合同的格式条款相类似?平台运营者利用其强势之处,谋取利益最大化,同时,最大程度的将责任推卸至店家身上,最终导致在网络虚拟世界,平台运营者无限盈利,不断压榨消费者和店家。是否可以制定法律,直接对二者间关系进行规制,划清权利义务的边界,明确责任分配?
2.消费者与店家之间是否适用协议管辖
在“第三方经营”模式下,因店家信息不准确、地址难确定,一般情况下,消费者更愿意起诉平台运营者,也会有消费者与平台运营者协商,通过其告知,直接起诉店家的情况,那此种情形下平台运营者与消费者签署的协议管辖约定是否对店家产生约束力呢?店家与消费者签署的合同是否属于买卖合同?
四、普通协议管辖的有效性标准
要看清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真实面目,需要从普通协议管辖的有效性及效力方面来看清该程序的“真容”,以此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在实践中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会出现混乱。
(一)普通协议管辖的有效认定审查
“普通协议管辖,又称约定管辖、合意管辖,是指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以协议的方式约定案件的管辖法院。”我国法院对于普通协议管辖的审查不仅在立案受理阶段,在受理后也会依职权审查管辖问题。不过,依职权审查不等于依职权探知,原告仍需要说明法院的管辖权,在法院对是否有管辖权存在疑虑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普通协议管辖原告应当对管辖协议之存在、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等承担证明责任。法院审查管辖协议的有效性不仅要依照实体法律的相关规定,还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总而言之,普通协议审查的有效认定条件包括:(1)管辖协议成立;(2)管辖协议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适用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4)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管辖法院,如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5)必须采用书面形式;(6)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7)当事人具有诉讼行为能力。
(二)普通协议管辖的效力
普通协议管辖的效力是指有效订立的管辖协议对当事人和法院产生怎样的影响,一般而言,协议管辖的效力可分为排他性的效力和竞合性效力。“前者又称为专属性合意,即当事人在约定管辖法院的同时,对法定管辖范围中的法院予以排除。后者又被称为任意性协议、附加性合意或积极的合意管辖,即在法定管辖范围之外增加额外的备选法院,但并不排除法定管辖。”竞合性协议管辖可以避免占有优势的一方滥用协议管辖的约定,防止店家打着意思自治的旗号限制消费者的起诉权,这是与专属性协议管辖的区别所在。
对普通协议管辖的效力,各国有不同的认定模式:“在日本,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其他法定范围以外的法院接受裁判时,就是附加性合意;否则就是专属性合意。”而在德国,“联邦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十分尊重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要求各级法院先综合了解当事人双方的意志,再根据协议内容对案件作出解释。”而美国法院认为,“管辖协议只有出现唯一、专属等词汇,才被认为属于排他性管辖,只是约定了某一法院的,不能认定该协议具有排他性的效力。”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普通协议管辖的作出规定,但是能够从《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看出,立法者还是希望当事人积极订立竞合的协议管辖,而不仅仅排除某个法院的管辖,竞合性效力与排他性效力结合使用。此外还可以結合德国的模式,赋予法官解释协议内容的协议内容的权力,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三)与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比较分析
随着网络交易合同使用率的升高,给民事管辖规则带去冲击,对普通协议管辖制度适用于新兴的网络合同纠纷案件提出了新的要求。下文将要对普通协议管辖与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进行比较分析:
在实践中,协议管辖制度越来越多以格式化的形式出现。这种格式化的协议管辖条款在网络合同中大量使用,网络交易平台在服务协议中大都写明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间接排除了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的管辖,而服务协议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例如: 淘宝平台管辖协议规定:消费者与淘宝平台服务有关的争议,由淘宝与消费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支付宝管辖协议则放在最后一条,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苏宁会员章程规定因使用苏宁平台发生纠纷(包括与苏宁平台中入驻商家的纠纷),将由平台运营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在《民诉法解释》出台之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只规定了普通协议管辖的有效要件,并没有涉及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条款的有效性问题。因此对于网络合同案件协议管辖的审查往往参照实体法规范,主要集中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以及《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41条等。⑥随着《民诉法解释》的出台,虽然对网络合同协议管辖作了些许规定,无须援引实体法规范,但在实际案件中情况复杂,这种规定只能就个案逐一解决不具有普适性,因此,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有效与否的确定权要依赖法官自由裁量,才会导致司法裁定的不一致。
五、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统一适用
上文对普通协议管辖的成立标准进行了厘清,这为裁定书中处理有关法律问题提供依据和奠定基础。不过,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异议裁定书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处理应当如何统一,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已有深度探索,仍需从比较法的角度入手展开分析。
(一)确定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形式有效性标准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40条⑦对协议管辖制度作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此外,德国协议管辖对法院选择没有太大的限制,当事人一方在国内法院有管辖权,那么双方可任意约定管辖法院,更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协议管辖的有效性规定方面,“德国将一般交易条款划分为一般条款、无裁量余地的条款及有裁量余地的条款。一般条款依据公平原则进行判断;无裁量余地的条款即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法官不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无意义条款;有裁量余地的条款即在普通认定中无效,但基于部分具体情况而允许法官适用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性条款。”因此,德国在实践中常常将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的条款判定为无效。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1条⑧是关于管辖合意的规定,其中合意管辖规定必须以书面形式确立;“合意管辖的法院因为日本一审法院的特殊性,仅限于在简易裁判所或地方裁判所这两种法院中作出确定或选择”;适用的时间在纠纷前后均认可。
“对于格式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问题,我国立法缺少明确的规定。”在网络合同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通常根据自由裁量给出不同的解释,裁判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涉网案件协议管辖的形式有效性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
1.条款内容能够记录保存
传统协议管辖条款以纸质文件的形式订立,但是基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使网络合同协议管辖的条款超越纸质文件的形式,均采用电子化的形式订立。为了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协议管辖条款形式上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纸质文件或者电子化形式,还应对涉网案件协议管辖条款进行形式审查。“在协议管辖条款往往是在线形成的情况下,协议的内容以及达成协议的记录保存以及将来的查询和引用,都将成为涉网案件中协议管辖条款形式有效性审查的重点。只要能够供将来查询和引用,就可认为符合涉网案件协议管辖条款的形式要求。”此时,网络平台负有证明协议管辖条款存在的举证责任,因为该条款由网络平台事先拟定,其有义务证实服务条款中的法院选择条款及其内容。
2.条款位置清晰突出
協议管辖条款的有效,必须要达到消费者明确知悉该条款的内容的标准。例如,美国DeJohn v.TV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et al.⑨一案中, 法院认可了原被告双方所达成的协议管辖条款。法院认为:原告点击“同意”键就等于接受与被告之间订立协议管辖条款,而消费者在进行用户登记时,协议管辖条款就在“同意”键的上方,清晰明了。我国的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条款在形式上也应进行这方面的考虑,管辖条款位置放置突出、清晰。
(二)限制适用弱者保护原则
“目前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采取有利于消费者的管辖规则,消费者原地管辖⑩便是最主要的一种。”2000年欧盟通过了《布鲁塞尔条例》,为网络购物合同的消费者提供保护。条例中规定,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的住所地或卖方住所地起诉卖方,该条例扩大了协议管辖的范围,为后来各国的电子商务立法提供了参考。但是消费者原地管辖也有局限性,其仅保障消费者一方的诉权,当消费者诉权过大时,商家的利益必然遭受损失,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商家,必然会打击其信心。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不能盲目适用消费者原地管辖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保护弱者这一出发点本身是好的,我国的网络合同纠纷协议管辖可以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有限的适用消费者原地管辖。
笔者对当当、亚马逊等B2C模式以及淘宝等C2C模式下的平台的注册协议进行比较后发现,除京东规定“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应向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外,其他网站无一例外规定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从协议管辖的内容可知,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域外各个国家均加强对弱者的保护,我国在立法上未对弱者保护原则加以明确。“对于坚持协议管辖的诉讼契约性质的法官来说,通常会运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来审查协议管辖的效力问题。而对于坚持协议管辖的程序性质的法官而言,当事人的协议管辖具有程序性质的效果,弱者保护的观念则很难获得认可,当事人实际地位的差异并不会对协议管辖的效力问题产生实质的影响。”因此在适用弱者保护原则上司法实践中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一方当事人的权利过大就会就会导致权利的滥用,应该限制适用弱者保护原则,例如,设立纠纷发生后订立协议管辖条款制度。一方面,更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加强对弱者的保护,通过对域外制度的借鉴,循序渐进,不完全加以肯定。
(三)明确界定网络合同纠纷当事人
消费者、店家与平台三方之间实则存在两个合同:第一个是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的服务合同,第二个则是消费者与店家的买卖合同。而前述协议管辖条款是消费者与平台的服务合同之中达成的,那么对于店家是否适用呢?前文所述,我国的电子商务平台分为B2C模式与C2C模式,根据这两种模式对网络合同纠纷的当事人进行分类:
第一,在B2C模式下,平台运营者就是商品经营者,此时就是消费者和平台运营者的直接纠纷。对于此种类型的纠纷解决:平台积极介入解决纠纷→建立积极的协商机制→协商不成,运用法律手段,直接适用协议管辖条款。
第二,在C2C模式下,平台运营者不是商品经营者,而仅是网络服务的提供方。对于此种类型的纠纷解决:首先,“平台运营者相当于消费者和店家之间沟通的桥梁,应该最先积极介入协商解决二者的纠纷。”当纠纷发生时,消费者可以先点击客服小蜜,打开后会有几项提前设定好的纠纷类型,消费者可以按照指示自行解决;其次,认为解决的不满意或者无法解决的,由人工客服介入处理,与消费者进行协商,人工客服作为中间者,让店家与消费者分别提供证据;然后,成立大众评审团进行审定,得出处理意见,如果是店家的责任,那么由平台运营者垫付,再向店家追偿;最后,消费者认为纠纷仍未解决的,运用司法救济手段。至于责任承担方面,应该增加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明确平台运营者与店家定位,消费者可以起诉店家,也可以起诉平台,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这时的关系主体就是消费者、店家和平台运营者之间的纠纷,适用协议管辖条款。在消费者只起诉店家而不起诉平台时,则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适用《民诉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收货地法院享有管辖权。如此一来,既减少平台运营者的诉累,又起到保护消费者的作用。
注释:
①《民事诉讼法》第34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第31条:“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③(2018)浙08民辖终27号裁定书。
④(2017)鄂02民终1781号裁定书。
⑤(2017)粤01民辖终1902号裁定书。
⑥《合同法》第39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需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并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0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无效”;第41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一)本来没有管辖权的第一审法院,可以因当事人间明示的或默示的合意而取得管辖权;(二)当事人一方在国内有普通审判籍时,就只能选择该当事人在国内有普通审判籍或有一种特别审判籍的法院;(三)此外,对法院管辖的合意,只在合于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以用明示的和书面的方式订立:1.争议发生后订立的2.在诉讼中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契约后将其住所或居住地迁出本法施行地区以外,或在起诉其住所或居住地不明者。”第40条:“(一)关于管辖的合意,如非就一定的法律关系以及由此法律关系而生的诉讼而为者,不生法律上的效力;(二)诉讼所涉及的为非财产权的请求,或对诉讼定有专属审判籍者,不得成立管辖的合意。此种情形,也不得由于不责问地进行本案辩论而发生管辖权。”
⑧《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1条:“(一)当事人可合意确定一审管辖法院;(二)前款的合意如果与基于一定法律关系发生的诉讼无关,并且不以书面形式协议时无效。”
⑨DeJohn v.TV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et al,245F.Supp.2d 913 (C.D.Ill.2003)
⑩消費者原地管辖原则,是指消费者与店家因合同发生纠纷后,消费者可以选择在其住所地或者对方当事人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而店家只能选择消费者住所地法院管辖。
参考文献:
[1]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1.
[2]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9.
[3]段文波.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5.
[4]王吉文.我国统一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256.
[5]田平安等.民事诉讼法原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169.
[6]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0.
[7]参加[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5.
[8]周翠.协议管辖问题研究—对<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127条 第2款的解释[J],中外法学,2014(2):460.
[9][美]罗伯特·L·霍格,克里斯托夫· P·博姆.因特网与其管辖权——国际原则已经出现但对抗也隐约可见[J],何乃刚译,环球法律评论,2001(1):49.
[10]参见王全弟,陈倩.德国法上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一般交易条件法>及其变迁[J],比较法研究,2004(1):68.
[11]李智.协议管辖在互联网案件中的合理适用[J],法学,2006(9):107.
[12]朱方强.论网络购物合同中管辖格式条款的效力与解决争议[J],知与行,2018(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