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凌的声响中行走和写作
2019-06-21霹雳贝贝
霹雳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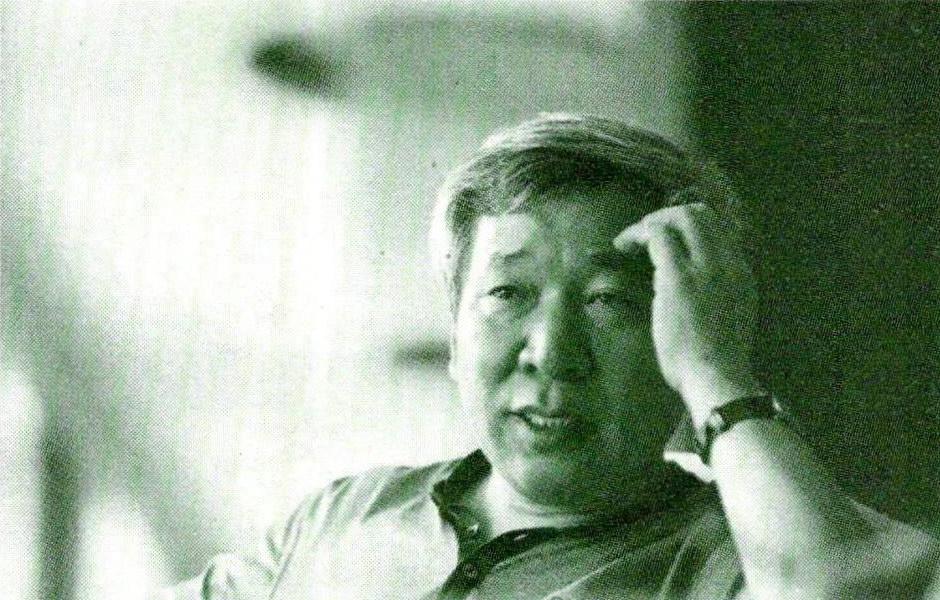
永远想要逃离土地
1958年,阎连科出生于中原的一个偏穷的村落,河南嵩县田湖村。在这个情感紧密的家庭里,有他的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他的哥哥。
父母是农民,这让阎连科从童年时期起就体会着乡村和土地带来的滋味,那是无趣与疲惫,单调与乏味。上学之余,他下田割草、喂猪、放牛,生活中的一部分被“永不间断的饥饿和疲惫”缠绕。
但阎连科又庆幸,田湖村比更偏远的山区好,因为这里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集市中心。处于这样的“中间地带”,他既能体会到乡下人对田湖的向往,又能亲历着自己对三十里外的县城的向往。至于县城的人,他们想去的是百里外的古都洛阳。
从读小学起,阎连科就体会着这种细节具体的城乡差距。同班来过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其中一个洛阳来的女孩胖胖的,“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在她面前,阎连科“乡下男孩的自尊”变得清晰而强烈,他开始暗自在学习上追赶女孩。
和城乡差距一样给阎连科带来“冲击”的,是书籍的世界。他一边追赶着洛阳女孩的成绩,一边开始了对阅读的痴迷追尋。
大姐的床头被他称为“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阎连科小时候,大姐身体不好辍学在家,躺在床上读了那时候她能在乡村找到的所有印刷品。大姐的床头有革命文学,他就跟着读。
于是,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阅读与劳作成为阎连科生活里并行的两条线。因为要给大姐挣钱治病,他和二姐去过十几里外的山沟,从那里运送石料进他们村的县水泥厂,也给修公路的承包队运送过鹅卵石子。诸如此类的体力活,让阎连科“累得如同多病的牛马”。
贫穷和城乡差距在心理上拉扯着阎连科。但它们却没有让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有所减损。因为有了大姐床头的那个“图书馆”,阎连科在散文集《我与父辈》中表达过对大姐的感恩。“那种无可比拟的姐弟情谊,就会以潮润的形式,湿润在我的眼角。”他写道。
关于父亲和母亲,他则描述道:“父亲的勤劳和忍耐,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
这样的情感,被阎连科视为“一生的巨大财富”和“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只是,洛阳来的女孩仍旧尖锐地“提醒”着阎连科的自卑,他无法忽视城乡之间那“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阎连科说,那是他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那些情感上的激荡迫使他开始“日日地瞪着寻找机遇的双眼”,直到有一天——这个故事他讲过很多次了——
有一天,阎连科在大姐的床头拿到了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很多年以后,他早已记不清那本书讲了什么故事,但那本书的封底的内容提要却至关重要。
那上面写着,知青张抗抗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因为去了哈尔滨出版社改书稿,张抗抗在小说出版之后离开北大荒。留在了哈尔滨。
这个“命运转折”的故事让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
1975年前后,阎连科写作的念头“萌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去出版,调进城里,他就可以离开土地了。
一直都在冰凌的声响中行走和写作
1978年,阎连科应征入伍。入伍之前,“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加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需要有人去挣回一份维持油盐药物和零用的钱来”,他从高二退学了。不到17岁,阎连科到了河南新乡,开始打工。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是阎连科的“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他跟着他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搬运工人.“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一千公斤”,把火车上卸下来的煤或沙子,运到水泥厂里。“六十多里路,能挣到四五元”。
后来他们又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去做临时工人。每个月领到薪水,阎连科寄钱回家,从邮局出来看着天空和行人,“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温暖,感到了自己已经是个大人,可以为父母和家庭尽下一份情谊和责任”。
这段打工的日子。因为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而中断了。阎连科从河南新乡回了家,去参加高考。但他没有考上大学,县里也没有人考上。1978年底,阎连科另寻出路,决定去当兵。
离家的前夜,阎连科在村里深冬的寒夜间一夜未眠,家门口那条小河的结冰声“刺骨地响在耳边和村落上空的寂静里”。
在这个声音里,他起床到父亲的床前去道别:“爹,我走了……”在他“文学钻石”一般的《我与父辈》中,阎连科记录道:“父亲从被窝里伸出他枯黄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里,喘喘吁吁嘱托道:‘走吧你……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从此,他就开始了他一生的写作和奋斗。
他的第一个短篇,发表于1979年。拿到“让人激动和兴奋”的8元稿酬,他用其中的2元买了糖和香烟送给了部队的连长、排长和战友们。剩下的6元,被他和三个月的津贴凑在一起,一共20元,寄回了家里,让生病的父亲买药吃。
阎连科作为一名作家的道路,隐约就从这里开始了。
1985年,军队的《昆仑》杂志刊登了他的第一个中篇。
24岁,阎连科提了干。当官,走仕途,是他想做的事。此后他还真的直接从排长当了指导员,正连级。
但就是此时,他也从未放弃过写作。写作是他骨子里的爱好。“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7000、8000字,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天天如此。”当年有人这样描写他的写作,由此我们可以想像他的创作激情和才华。
成为作家和一心仕途,两种想法一直在阎连科的身上纠结和博弈。最后,“成名成家”的理想占了上风。1989年,他最终决定要从事文学,便毅然去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上学了。
1991年从军艺毕业,因为长期伏案写作,随之而来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颈椎病,从此他开始“四处求医,数年不休,每天连吃饭都要老婆端到床边去”。
躺在床上,阎连科极其伤感。生病让他联想到死亡。姐姐从小身体不好,父亲也因为疾病走得过早,因此他为疾病会时常落泪。在伤感中他再次开始阅读卡夫卡、胡安·鲁尔福等作家的作品。
这次崭新的阅读体验击中了阎连科,他的小说“一下子从某一种现实生活,走进了某一种生命和想像”。接着,他就趴在床上和仰躺在一家残联工厂为他特殊设计的写作椅和写作架上写出了中篇小说《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从此,他的文学开始了另外一片湛蓝的天空。
接着是那两部为他赢得更大的声誉也为他赢得更大争论的长篇小说《受活》和《坚硬如水》,继而是《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从此,他的写作从湛蓝的天空一下跌入了“黑暗的深渊”。
之后经过调整和思考,他写出了让人惊愕的“神实主义”之作《四书》《炸裂志》和《日熄》等,让他在国际上蹿红的速度快如流星样。
而且各大国际文学奖,也接连不断出现他的名字和作品,使得他成为了被国外真正接受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也成为了在社会和读者中仅有的争论最多的作家。
虽说如此,阎连科的生活和写作都仍在继续。
在香港教书
四年前,阎连科开始了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的生活。
最早的时候是去科技大学驻校,他和余华在那儿待了两三个月。后来,作家刘再复的女儿刘剑梅希望找一个作家去教书,每周备课和讲课,答应下来的作家就少了。因此,阎连科决定去科大当客座教授。
在香港,第一年他讲的是十九世纪的文学写作,第二年是二十世纪的文学。2019年,他想在中外文学中各选15部作品,开设“中外写作对读”课。
阎连科是科大校园里颇有自己特色的一位老师,用他的话讲,可能他是唯一讲中文的老师吧。然而,他的课却相当受欢迎,不仅教室满座,而且还常有外校、香港、内地和台湾的学生、听众去听讲。
两年前,有名法国的留学生选了他的课,听到第三节,她让同学帮忙问阎说,为什么你一句英语也不讲?
当得知他完全不能讲英语时,又问学校会不会给他的课堂配翻译?当看到阎连科摇头时,法国留学生泪都要急出来了。因为她在法国看到科大有阎连科的课,当时选了课后一直都为能听到他的课兴奋激动着。
还有一个大三的香港学生听了一学期阎连科的课,学期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她告诉他,如果她能早一年听到他的课,她就会换专业到人文中心来。她说:“她在香港的大学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有趣的课。”
而阎连科则又一次重申:“我想她不一定爱文学,但她至少觉得文学是非常有趣了,从此爱好业余时间读文学作品了,这就足够了。”
教书之余,作家更重要的任务是写作和读书。
在北京,早上7时起床吃饭,8时之前坐下写作,2个到2个半小时,写2000来字。如果是NBA开赛季,再看半场NBA,中午休息,下午如果不是出去见朋友,就看一会儿书。而在香港,阎连科一周半天课,三个小时。不上课的时候,上午写作,下午没有应酬,“就完全坐在那儿看书了”。
阎连科每天都在寻找那些超出他写作能力的书,一边嫉妒,一边学习。一年能遇到一两本这样的书,他就很开心。他提到鲁西迪的《午夜之子》,说这位小说家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才华,让他非常羡慕。
去年他又讀了《简短,但完整的故事》,其中里面的中篇《在磨坊在磨坊》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超现实写作可以摆脱“夸张性”,而走向庄重、肃严的方向,这给他许多提醒和启悟。同时,他还提到李敬泽、李修文、李娟的“散文三李”。
迥异于他对别的作家的作品的欣喜之情,阎连科对自己的作品却没有怀着相同的感情。在课堂上,如果需要讲到写作失败的事例。他永远讲的是自己。
“就是在人大作家班的课堂上。我也永远在讲自己写作的失败。失败是我最爱和人讨论的文学话题。我想我的好,就是能面对和接受我写作的失败。任何人说我的小说不好,我都可以接受。”阎连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