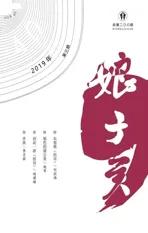春天里
2019-06-19王今
王今
春天里的意向,令人浮想绵延;春天里的物事,令人神采勃发;春天里的色彩,令人满目生情;春天里的气息,令人心旌摇荡。
春天的美好,满满的,似乎要溢出来;浓浓的,化也化不开。
早市印象
早市上,最抢眼的,莫过于那些蔬菜水果了。
瞧那颜色,绿得纯粹,红得深沉,白得晶莹,紫得高贵;再瞧那仪态,豆角们齐刷刷的,是整装的士兵;葱韭们衣袂翩翩,像飘逸的才俊;西红柿一脸绯红,如娇羞的嫁娘。更有那白白胖胖的萝卜,愣头愣脑的洋葱,憨态可掬的土豆,堆积如山,气势夺人。南方的稀罕物也来凑趣儿,只是流落北地,入乡随俗,失却不少灵秀之姿,添了许多拙朴之态。那所谓的春笋,想象中应是鲜如葱指,嫩如香腮。可眼前这物事,却粗笨丑陋得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灰头土脸地躺在地上,真真一个土疙瘩。要不是旁边的“告示牌”,谁信那就是被文人墨客奉为高洁之君的竹笋呢?至于莲藕,也没有了远道而来的尊贵,横七竖八地躺在筐子里,一张大花脸,实难看出“出淤泥不染”的清高。
再看水果,草莓的娇小玲珑自不必说,那白里泛红的小脸蛋,婆婆娑娑的绿纱裙,吹弹可破的嫩皮肤,活脱脱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浑身散发着美好与快乐。火龙果形如其名,张牙舞爪,热烈奔放。如此泼辣之性,却经不得浩荡春风,需穿件塑料“风衣”御侵。橙类水果满身尽带黄金甲,充满十足的贵气和盛气凌人的霸气。最不起眼的要属猕猴桃了,不明白它是如何混入水果行列的,一副粗糙面皮,与水何干?据说营养还蛮丰富,倒也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的老话。本地的苹果梨子倒也干眉净眼,只因不合时令,被冷落在一边,鲜有人问津。
春天,本是花的季节。自然,早市上也少不了花的影子。茂盛的绿植,可爱的肉肉,婀娜的月季,自是风流旖旎。它们分立于早市入口两侧,如窈窕的迎宾,招揽着过往的行人。
早市的物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早市的人们更是千奇百怪,别有生趣。
一个枣摊铺排在人行道边。枣的品相不错,红得透亮,大得惊人。卖枣人一头卷发拢在脑后,肩上斜挎一个帆布包,操着一口东北腔,不住地叫卖。一对男女有意买枣,双方讨价还价,最终成交。买者如愿以偿,卖者连喊赔本。末了,卖枣人指着女顾客对男顾客说,“我认识她。她常来,老顾客了,照顾你们!”然后又凑到女顾客耳畔低声叮嘱:“别和别人说这个价啊!”买者愕然,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光顾这个早市。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地上,面前摆着几把香菜。她的目光随着川流不息的人流左顾右盼,似在“搜寻”着垂青香菜的主顾,嘴里还不停地大声喊:“香菜——香菜——,一块一堆,便宜了!”人们从她身边经过,却无一人理睬她的香菜。好容易过来一个妇女,看到她的香菜,眼睛一亮,不无遗憾地说:“这香菜多新鲜,可是我已经买了。”老太太一听,脸色顿时阴下来,连连怪怨道:“我天天在这儿卖,你咋不过来买?”那口气,好像妇女做错了事。妇女只好允诺:“下次,下次一定买你的!”
那边两个妇女席地而坐,聊得热火朝天。看上去她们也是卖家,可是地上摆着的两三盆吊兰,花盆稀松平常也就罢了,盆里的吊兰枝株细弱,叶子泛黄。其中一个妇女用手指捏着一根吊兰,也是“面黄肌瘦”的。她心不在焉地把玩着,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与身旁女伴的聊天上。一个人走过来,见此情景,心下疑惑,不由发问:“这也卖?”妇女见问,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事做,出来玩玩!”
一对中年夫妇身着休闲衫,悠然走进市场。人近半百,已知天命,一脸安详,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又恰逢春日的早晨,光阴似箭,春意正浓,让曾经焦灼的心安静下来,迎着春阳,沐着和风,尽情享受人间烟火的温暖。可以买,可以不买,随意逛逛就好。一切随缘,一切顺其自然。事到如今才明白,人生本该这样。
香椿刚上市,好贵,六块钱一小把。说是一把,实则十来八根。虽说香椿吃得就是个鲜,可也着实贵了点。来逛早市的大多是居家过日子的,图得就是个便宜。所以那“香飘十里”的椿芽,有些寂寞。一对夫妇走过,女的拿起来闻了闻,想买,一听价格,不住咋舌,又放下了。男的却爽快地说:“想吃就买,又不是天天吃!”卖家就爱听这话,赶紧连连附和。女的见两人“一唱一和”,也就不再犹豫。于是,买卖成交。
春天的早市,就是这样风景各异,气象万千。它的繁华热闹,为的是人们在餐桌上能看到春天的影子。
花有清香
城市里生活的我们,既没有一亩三分地可耕种,也没有私家花园供打理,又想接接地气,亲近泥土,只能是舞弄花草了。
吊兰最是皮实。经过一年的生长,它们如强弩之末,实在无力继续枝繁叶茂了。事实是,一年里,叶在土上蓬勃发展的时候,土里的根也没闲着。曾经在水中生发的细小须根,已疯长成茁壮的茎根。如果不是有花盆的限制,根的发达,可能会超越叶的繁茂。如此下去,盆里的土全变成了根。失去土的滋养,不仅叶的长势会逐渐衰败,根的前景也岌岌可危。所以,春天一到,我便帮助家里的吊兰摆脱尴尬困境,让它们轻装上阵,愉快生长。先把它们连根拔起,剪掉那些多余的根,保留些许细小的须根。然后换上新土,重新栽好。再把枯枝败叶全部剪掉,给新叶子腾出生长空间。剪下的枝叶也舍不得扔掉,从中捡出一些嫩枝,插在瓶子里用水泡着。不几日,它们就会发出白色的须根,移栽到花盆里,又是一棵吊兰。花盆数量有限,我就把几株吊兰像插秧一样栽到一个长方形花盆里,嫩嫩的,绿绿的,像一畦刚出土的麦苗,好不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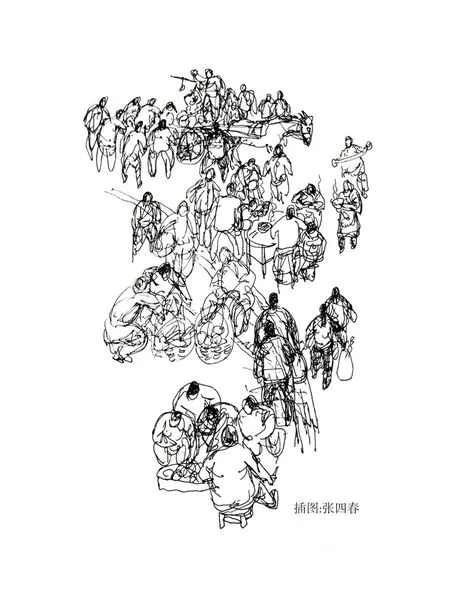
绿萝是近年来最被大众宠爱的家居植物。餐馆、酒店、商铺、茶社,只要懂一点情趣的人,都不忘在他的领地摆几盆绿萝。别说,无论哪里,只要点缀几盆绿萝,必定蓬荜生辉。家里更是少不了它。新居里,摆上几盆,能吸尘除醛;旧屋里,摆上几盆,能焕然一新;书房里,摆上几盆,更添书香;餐桌旁,摆上几盆,食欲大增。突然间,感觉到绿萝无处不在,人手一盆。它如此惹人爱,全因它的个性使然。比吊兰还易活的特性,让人人都可成为苗圃专家。泡在水里能活,插在土里能活;放在阴面能活,放在阳面能活;湿一些能活,干一些能活。如此随意洒脱,无欲无求,自然天地广阔。再说它的形态,稍一修剪,或蓬勃向上,或斜枝旁逸,或流瀑低垂。无论向哪个方向伸展,都是一道风景。虽无红花缀枝,却有绿影依依,生机盎然。
我喜爱绿萝。虽然家里的大多数盆栽均为绿箩,但每每在别处见到它,仍会眼前一亮,不由多几个回眸。春天里,我也会修剪绿萝,却舍不得动根,只把一些长势欠佳的枝叶剪去。我把那些剪下的旧枝叶泡在瓶里,一字儿排开摆到窗台上,再造一道风景。
原以为,君子兰是顶娇贵的,侍弄不好,很难存活。偶然得到一株君子兰,养了几年,觉得倒也不尽然。花是只开了一次,叶却长得肥厚,层出不穷。春来了,它旁边又长出一株小苗,长势很旺,花盆显得有些拥挤。我便连根拔起,把子株从母株上小心分离出来,趁机给母株换了新土。说是土,看上去几乎没有土的样子,全是些松软的如杂草枯枝般纠缠在一起的东西。总不放心,便搅和进去一些平常的土。其实心里是没底的,担心这么一折腾,君子兰会死。还好,纯属杞人忧天。不仅母株依旧,子株也安然无恙。只是,花终未见。据说,君子兰喜啤酒,用啤酒浇灌就会开花。若果真如此,君子兰岂不是位“饮君子”?那花该是“醉美人”了。
遇到三角梅,是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她是个十足的“文青”,喜绘画、手工、刺绣,办公室也装点得很淑女。最引人的,要数那株三角梅了。扎根于一个青花瓷样的花盆里,却长得挺拔高大,像棵树。碧绿的叶子间,缀着密匝匝的玫红色花朵。花瓣薄如蝉翼,花色艳如胭脂。偶有几朵落在光洁的地板上,朋友也不去理睬,很有几分落英缤纷的意境。每每去拜访朋友,总会想起席慕容的那首诗,总喜欢立在“花树”前认真欣赏,唯恐辜负它那“凋零的心”。朋友见我喜爱,竟然又插了一株送我。
这已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也想把自己的三角梅养成一棵花树,只是至今未如愿。它倒也实在,年年总要有一次花满枝头。花期不定,高兴了就开。有时春节前后,有时春末夏初。花色也不定,有时朱红,有时玫红。有时初绽为朱红,开着开着就成了玫红。枝株不大,花却不少,一簇一簇的,花之艳丽,惹人怜爱。那些落花,我也不忍丢弃,把她们放在鱼缸里,竟似落花流水,颇有诗意。
听人说,三角梅也需要剪枝换土。春来了,花落了,我剪去闲枝,换土施肥。之后不久,新叶争先恐后长出来,嫩绿鲜亮,如同换了件新衣。期待它的再次花俏枝头,娉婷灿烂。
花栽久了,总有一些小惊喜出来。一日,无意间发现,一个花盆里竟然长出几个花蘑菇。又一日,不经意间看到,在三角梅的主干旁开了一朵小喇叭花。一棵枯死的香雪兰,由于我的懒惰,扔到角落里不再理会。不想,春来了,它竟枯枝发新芽,而且新叶如雨后春笋般一个劲往出冒,不几日,就把个花盆挤得满满的。虽无花,那叶也足够让人欣喜的。
花花草草,不仅养眼,更养心。
踏青觅古
西林山如一道屏障,横亘于面前。
屋旁田畔,几株杏树妖娆着跃入眼帘。微风过处,一阵阵杏花雨扑簌簌落下,恰似春日飞雪。轻歌曼舞的花瓣,美丽着乡村,装点着山川,浪漫着我们的踏青之旅。
不曾想,在这美丽的序曲背后,却暗伏着令人心惊的凶险。
起初,以为领队只是出于懒惰,带我们爬上一段没有路的土坡,所以并未在意。无非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坎坷,何必上心?更何况,如果愿意,也可以绕道而行。走着走着,却发现,征服西林山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直在没有路的山石上攀援。
感谢西林山的石头们。它们巨大的身躯,以近乎七十度的角度匍匐于山体之上,拙朴,憨厚,结实,像一位山野村夫。最可爱的是它们的“皮肤”,粗糙、干涩,像有无数只小爪般紧紧抓着我们的手和脚。于是,尽管脚下是一条没有路的路,需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行,但却感觉不是十分艰难,更不必担心会滑下去。
西林山主峰只有四百余米,但它铁青着一副面孔,垂直地立在那里,让人望而生畏。除了驴友,连山脚下常年与其厮守的村民,也从不走近它。只要抬头望望,就知道它的严峻和冷酷,也领略到了它的峭拔和威武,又何苦气喘吁吁、自讨苦吃呢?而驴友,就是喜好不走寻常路。不经意间,我竟成了驴友。
我严格遵守“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的旅游规则,埋头爬山。有生以来,爬过无数次山,却从未这样爬过山。充其量,过去只是“走”山。这次,才是名符其实地“爬”。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一直全神贯注地支持着我的每一次爬行,为其提供着充足的能量。我坚信“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相信“追赶别人”的压力和困难。于是,我始终处于领先位置。
一座海拔不足五百米、方圆只有五平方公里的山上,虽然如今人迹罕至,但昔日,先人也曾不畏艰险,在此修庙筑屋,凿洞建窟,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一段石阶,虽然已经没有了下半截,但总是人类的作品。一路走来,突然眼前有段这样的“路”,倍感亲切。坐在石阶上歇息,才发现,拾级而上,就是一个山门,两边还有石头砌就的院墙。估计,这里曾是一座寺院。那院墙虽已是断壁残垣,但一块块石头紧密地依偎,依稀让人感到当年守寺人的细致与严谨。石阶旁,有一株杏树,单薄的枝干上挂着些许瘦小的花朵。在这满眼灰暗的半山腰,她孤寂、落寞,却坚持着生命的绽放,坚守着古寺的庄严。她明白,自己是寺院存在的见证。寺院的宁静,香火的缭绕,信众的虔诚,佛祖的慈悲,伴着她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而今,这一切虽已烟消云散,但只要有她,就有寺院的兴败衰荣,就有守寺人的岁月春秋。杏树,院墙,石阶,是古寺的残骸,却是浪漫而美丽的留存。
登上山巅,看到的是西林山全部的精彩。还是那些石头,伪装成一个个不同的形态,尽情炫耀着自己的本领。这是一头雄狮,仰天长啸,让人想到狮子王的威猛;那是一只玉兔,前肢直立,扭过头来,用惊恐的目光瞅着这群不速之客;那里一块飞来之峰,斜倾着身子悬在半空,随时准备一飞冲天;这里一只老龟,伸着脖子眺望着远方,誓以自己的长寿,阅尽人间的悲欢离合。人说黄山之石千奇百怪,西林山的巨石,哪里比它们逊色了?只是待字闺中无人识罢了。
原以为,到了山顶,就会是雨后彩虹,峰回路转。不曾想,更大的挑战还在脚下。向上攀爬时,眼前只有山石。只见方寸之地,自然意识不到危险。立足山巅,再往前行,两侧却是深不见底,而路仍然崎岖不平。险峻处,需要骑着石头才能翻越。又是那些可爱的石头,依旧牢牢抓住我们,让我们平安穿越山巅。
就在这巉岩耸立的西林山顶,我再一次遇到了先人的印迹。一块卵型的巨石下,凿石为洞,内塑佛像,密密麻麻,布满洞壁。是哪朝哪代,它们倍受恩宠,被隆重地凿刻于西林之巅,风叩雨拜,众人供奉?又是哪朝哪代,它们横遭浩劫,被屈辱地砸烂颜面,血雨腥风,被人唾弃?无论是顶礼膜拜,还是刀砍斧劈,它们总是默默无语。沧海桑田,柳暗花明,人间正道,否极泰来,一切都自在人心。
下山之路藏身于山石与灌木间,隐隐约约,闪闪烁烁。亏了有领队,才使我们不致迷失方向。当我们的双脚踏上既不平坦也不宽阔的乡间土路时,队友们长叹一声,“终于有路可走了!”
一路的艰辛与汗水,换来的是一树杏花的妩媚。花朵们挨挨挤挤的,笑盈盈地立在路边,用毕生的美丽抚慰着我们疲惫的身体和不安的心。见了她,好似见了整个春天,内心振奋、喜悦、安详、温暖。与杏花合个影,徒要教人比并看,奴面花面哪个好?
中山古国遗迹本是此行中我最关注的内容,却原来不过是一座新建的文物陈列馆和游客服务中心。而中山古国遗迹的全部,就是竖在入口处的一块石头上的几个字。然而,寻古探幽的心境并未因此破坏,只因那座万寿寺和其背后的塔林。它们,坐落在与西林山遥遥相对的东林山下。
寺庙也好,塔林也好,都与唐朝有关。
又是唐朝。
武媚娘的霸气令唐朝的男子们黯然失色。其四子天寿十分厌倦宫廷争斗,外出游历,路经林山,感觉此地幽静,便在此筑庙修行。于是,就有了万寿寺,就有了舍利塔。
万寿寺始建于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即将走到穷途末路,皇子天寿却不堪忍受宫廷的刀光剑影、骨肉相煎,唯有遁入佛门,方可求得心安。皇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不惑之年,才有些明白佛门清静、禅宗淡泊的个中滋味。在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世间,人性的道义良心,又该往哪里安放?于是,许多人选择了佛门。虽不能像唐皇子一样落发为僧,但以“大隐隐于市”的姿态立于天地间,也算是心有所依,念有所想吧。
这万寿寺,历朝历代毁了建,建了毁,而今,沦落得灰头土脸,一派颓废。除了那两株“阴阳柏”和那三块石碑还留有大唐的遗风外,其余,均为今人重建。然而,也已墙壁斑驳,门窗褪色,植物萧条,小径零乱,似乎很久无人光顾。不过,如果你要想进大殿,斜刺里便有位耄耋老妪横加一拦,提醒你留下香火钱。
万寿寺的神韵早已随风逝去,今人在意的,只是它的香火钱。
最耐人寻味的,就是万寿寺背后的塔林了。虽也有今人修葺的痕迹,但以我的眼光,那些塔是不折不扣的古迹。当然,我的眼光不专业,仅仅是感觉。
也见过一些塔林,但都没有眼前的这些完整、庄严、肃穆、凝重。它们的形态,一如繁盛的唐朝般高贵、气派、豪华。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打,它们依旧正气凛然,充满古老的魅力和皇家的威严。穿行期间,不由心生敬畏。皇子天寿之墓更与众不同。整个塔体宽大厚重,粗犷中透着稳健,灵秀中含着奢华,完全是匠心之作。旁边,沿石阶而下,是其地宫。当时我有些心悸,未去探访,着实遗憾。
万寿寺旁的公路边,一片杏林冰清玉洁,为破败的寺庙平添了无限生机。春日里,北方山区,最先亮相的春花可能就是杏花了。她颜色惨淡,花朵单薄,在一片灰暗的背景里,显得凄楚可怜。因此,我一向觉得惋惜,更喜桃之夭夭。可是,这次户外之行,多次与杏花邂逅,她那“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的样子,透着山野的纯朴,一次次打动着我,为西林之行增添了许多柔美和风情。
今春,突然间我就喜欢上了杏花。
清明雨上
雨,是天空对大地的思念之泪。清明,是繁花喜悦的春日里的一个悲伤日子。清明里的雨,使人因思念而生悲,又因悲伤而愈加思念。好在这一切都发生于喧闹而充满生机的四月天,阴阳中和,使人不致绝望。
最早,对清明这个节气有切身感受是在小学。那个年代,每逢清明,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而且要统一服装:白衬衣,蓝裤子,白网鞋,胸前佩戴红领巾。在那个轻薄的年龄,情感系统还十分稚嫩,又无任何阅历,自然不知什么是悲伤。虽然手里拿着小白花,组织者试图在整个活动中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可是孩子们单纯的内心实在产生不了悲痛情绪。于是,一些“调皮鬼”就会时不时说笑打闹。这情景,像在平静的湖面突然扔进几块石头,溅起几朵不和谐的浪花般,招来老师一顿呵斥。孩子们中总有胆大包天的,对老师的训斥满不在乎。老师也只能面带严厉,实则心下无奈。最让孩子们犯愁的是,每次清明扫墓回来,老师总要布置一篇作文。年年如此。我的作文成绩一向不错,都开始发怵,更何况那些组词造句不顺畅的孩子。同一个题目写五年,要有多高的水平才能次次写出新意?无怪乎我们老生常谈了。我记得,每年写的作文里,我必写的一句话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纪念碑上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
那时年少无知。现在想来,那是多么有意义的活动啊!
初中以后,这样的活动再没有了。除了学习,似乎一切都得舍弃。没了“六一”且不说,先是课外书,再是各类课外活动,进而是音乐美术体育课,到最后连自习也没了。为了隆重的高考,孩子们几乎失去了自己。可是越过高考,并不就是风轻云淡,鸟语花香。花季少年不懂人生的艰难,年过半百才知,人生就是一场探险。谁也不知,下个路口等待你的是虎穴龙潭,还是仙境桃源?
对清明节的深刻理解,是在父母去世以后。
原来,死亡是件多么无奈的事啊!好端端的一个人,那么热爱生活,开朗乐观,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却穷尽世界也找不到他的身影。于是,就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对父母的离世,我总是心有不甘,总觉得那是件可以避免的事,如果……可能父母就不会死。当情感霸道地占据内心时,理智就被挤到了角落,像一个过客般只能旁观,却无能为力。这不是对死亡的惧怕,而是对父母的思念过深。父母没了,自己就无依无靠了。周末或是节日,就没了去处。遇到曲折波澜,也只能自己扛。唯有父母才能给予的无私的爱,也随之逝去。幸福的、温暖的、安全的、真实的、单纯的我也不复存在了。我不得不孤零零面对世间的风雨雷电,崎岖坎坷;不得不把“爸爸妈妈”这个世间最亲切的称呼永远地锁在心里;不得不把住在内心的那个小女孩“束之高阁”。
父母走了,清明节来了。
此时才深深理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父母生前意愿,死后一定要葬于故乡。当年我不解其意,觉得这么做是给儿女找麻烦。今天想来,中华文化讲究叶落归根。父母虽是半字不识的文盲,却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滋养,血脉里流淌的、骨髓里镌刻的,都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父母不知道什么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却用行动诠释着它。生前,父母最忘不了的便是故乡。逢年过节,过庙赶集,婚丧嫁娶,总要回去一遭。看看故乡的山水,见见久违的亲朋,闻闻泥土的味道,尝尝熟悉的饭菜。从小生长的地方,自有一番说不出的亲切。虽已离开多年,它却令人魂牵梦绕。因此,父母每每从故乡归来,除了带回亲戚朋友送的瓜果蔬菜之外,也带回淳朴的民风,快乐的心情,和说不尽的家长里短。
父母身虽逝去,神却永存。把他们安葬于故乡,我才明白父母的神在哪里。
每年清明,必回故乡祭奠父母。虽来去匆匆,但仍然与故乡有了联系,便知道了萧河水的丰枯,猪头山的“肥瘦”,庄稼地的贫沃;便知道了邻家大婶的际遇和隔壁大爷的光景;便知道了村容村貌的改观和乡村发展的前景。不知不觉,故乡的许多细节走进了我的内心,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浸润,故乡的概念、故乡的情怀便潜滋暗长,最终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想来,这就是父母魂归故里的良苦用心。
……
我在人间彷徨
寻不到你的天堂
东瓶西镜放
恨不能遗忘
又是清明雨上
折菊寄到你身旁
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