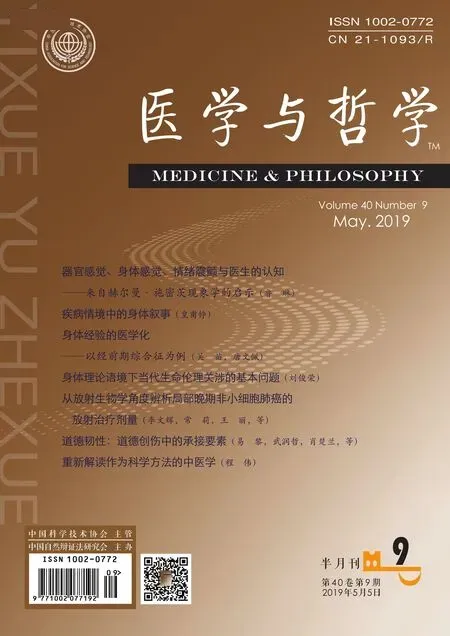从放射生物学角度辨析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放射治疗剂量*
2019-06-11李文辉
李文辉 常 莉 王 丽 侯 宇 李 岚 熊 伟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local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LA-NSCLC)放射治疗标准剂量60Gy基本共识来源于RTOG 0617临床试验,但一直存在较多争议。该试验是比较不可手术切除的LA-NSCLC放化疗同期加或不加西妥昔单抗靶向治疗、高放射剂量和标准放射剂量四个随机分组的中位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无疾病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毒副反应有无差异。试验结果研究者认为60Gy标准剂量优于74Gy高剂量,可能的原因是高剂量组食道炎、心脏损伤、肿瘤负荷太大导致严重的相关性不良事件[1-3]。其中,除放射治疗技术因素、临床实际对试验产生影响之外,放射生物学因素造成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1 放射生物学多因素决定放射治疗剂量应个体化考量
欧美许多放疗机构严格遵循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规定LA-NSCLC放化疗同期治疗标准剂量60Gy[4],理由是“RTOG 0617试验告诉了我们60Gy好于74Gy”。这是西方科学标准化、文化哲学与医保、医疗循证要求的结果。放疗医师如果不遵循这个剂量,一旦出现放疗相关性损伤或死亡,责任追究会很大。国内不少放射治疗机构和医生也严格遵循RTOG 0617试验按照60Gy标准剂量照射。符合循证医学明确要求,也是最安全、最简单的剂量给予,但更多的立场是站在“医疗安全”的角度,保护医生或医疗机构自己。如果我们真正立足于“治病救人、医者仁心”的境界,可能会更加关注RTOG 0617试验的过程、结果原因分析,追求放射治疗标准剂量60Gy基础上的个体化剂量。
1.1 放射生物学理论认为生物学效应与照射剂量呈正相关
经典的放射生物学理论,主要是涉及组织或肿瘤受照射后的“4R”效应、时间-剂量、分割方式、剂量率带来的不同生物学效应等等。“4R”效应即是受照射后的DNA损伤与修复(Repair)、组织和细胞的再增殖(Repopulation)、组织再氧合(Reoxygenation)和细胞周期再分布(Redistribution),总体结果导致肿瘤“反应性”(Responsibility)改变,即“5R”。这些结果与DNA损伤、乏氧周期阻滞、凋亡、生长比例、血供、营养、分裂机制……改变有关,还会导致分裂阻滞、免疫力变化等等。
而无论什么样的放射生物学效应,经典理论的原则是随着照射剂量增加,生物学效应提高。放射治疗就是追求最好的控制肿瘤而最小的正常组织损伤(见图1),在放疗技术精准和质量控制与保障的前提下,照射剂量越高,局部控制越好,有利于总体生存率。

图1 肿瘤与组织照射剂量升级与生物效应关系(于金明院士讲座惠供)
1.2 复杂的肿瘤学干预因素影响“标准剂量”的应用
然而,RTOG 0617试验结果是60Gy标准剂量优于74Gy高剂量(见表1),单纯以食道、心脏和放射性肺炎等放射损伤增加[1-3]难以解释。如按照经典放射生物学说,照射剂量越高,局部控制率应该越好,照射后肿瘤细胞活性下降,可事实并非如此,RTOG 0617试验结果高剂量组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比标准剂量组分别增加约10%和5%,试验设计中许多复杂的干预因素被忽略了。第一,治疗干预因素设计包含放疗、化疗、靶向药物。这种联合方式,在日常临床实践中比较少见,而更多的是放射治疗与化疗的同期或序贯联合治疗。加入西妥昔单抗靶向药物的后“三联方案”,实际效果是协同还是抑制,很难阐明;第二,放射治疗根据临床实际分为高剂量组、标准剂量组考察疗效,无法对更多的照射剂量做比较;第三,时间因素是同期进行,放化疗的相互协同作用被许多试验和理论证明,主要体现在时间协同、空间协同、“4R”协同和机制协同4个方面。其结果只能应用到对LA-NSCLC的放化同期治疗,序贯治疗时不能照搬。
表1RTOG0617试验标准剂量与高剂量组比较结果[1]

结果标准剂量(60Gy)高剂量(74Gy)中位生存期(个月)28.719.5预估18个月总生存率(%)66.953.9局部复发率(%)25.134.3远处转移率(%)42.447.8治疗相关死亡例数210
肿瘤组织放射敏感性与可治愈性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细胞本身固有的放射敏感性。不同的细胞类型,甚至相同细胞类型不同的细胞株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即同一个照射剂量引起的细胞杀灭指数不同。
目前认为固有敏感性的差异其实是因为细胞分子亚分型的不同。2011年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病学会整合多学科知识,提出“肺腺癌国际多学科分类新标准”,含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变检测、组织和细胞分子研究等新概念[5]。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突变阻滞扩增系统法(appl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ARMS)等精准医疗分子生物学技术更是发现越来越多的精准分子亚型分类。随后,外科学切除范围观念开始转变;影像融合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数字化显影更精细;肿瘤内科治疗,特别是晚期肺癌综合治疗中个体化和时空性更加突出,靶向诊治全面指导临床实践。如肺腺癌或肺鳞癌根据EGFR18、19和21外显子突变预测患者对EGFR-TKI药物的治疗反应,逐渐深入认识到下游或者融合的ALK、HER2、B-RAF、MET、ROS1、RET、K-RAS等八基因检测[4],甚至全基因检测指导靶向药物选择。RTOG 0617试验纳入标准已经远远滞后于靶向诊治、精准医疗的时代要求。
1.3 已经证明肺癌中不同的亚分型,化放疗反应不同
尽管属于内科学范畴,有必要再提IPASS等试验[6-7],因为对于放射治疗有借鉴意义。200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IDEAL(IRESSA Dose Evaluation in Advanced Lung Cancer)研究[8-9]发现吉非替尼二线或三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客观缓解率在9.0%~19.0%之间,生活质量改善,不良反应轻微等结果,快速通道批准上市,适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二线或三线治疗。可惜2004年全球28个国家210个中心比较研究吉非替尼与最佳支持治疗对复发难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二线治疗的ISEL试验[10]显示吉非替尼较最佳支持治疗无生存获益,故欧美撤销使用。2008年IPASS开放、随机、平行、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6-7](Iressa Pan-Asia Study),吉非替尼与卡铂联合紫杉醇一线治疗亚洲晚期(ⅢB或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的对比研究,发现EGFR突变患者中,吉非替尼组的PFS明显优于化疗组,而EGFR未突变患者,化疗组的PFS明显优于吉非替尼组;吉非替尼治疗组EGFR无突变者PFS远远低于EGFR突变者,分别为1.1%和71.2%。首次证明EGFR突变与否是影响吉非替尼治疗疗效的主要原因。
IPASS试验也说明肺腺癌中存在EGFR阳性和EGFR阴性等更多的亚分型,它们对吉非替尼治疗的反应性不一样, 而RTOG 0617试验亚组统计分析也证实对放射治疗有影响,放化疗同期加入西妥昔单抗靶向药物,EGFR高表达患者的PFS优于低表达者[2]。
更直接的证据是2015年Yagishita等[11]在《国际放射肿瘤学、物理学和生物学杂志》报道,根治性放化疗同期治疗Ⅲ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EGFR突变型和野生型的疗效比较。198个入组病例,17%EGFR突变率,EGFR阳性突变患者疗效好于非突变患者,中位局部复发时间(median time to local relapse,MTTLR)和中位进展后生存时间(median postprogression survival,MSPP)分别是27.8个月vs.19.4个月和18.1个月vs.13.0个月。
从IPSS试验到Yagishita等报道都提示非小细胞肺癌EGFR状态与靶向治疗和放射治疗结果有密切相关性。那么,精准医学检测使得组织学分型变成越来越细化,除了EGFR外,还有ALK、HER2、B-RAF、MET、ROS1、RET、K-RAS……基因变异[12],靶向药物层出不穷,又会不会影响到肺癌放射生物敏感性?这就是肿瘤细胞放射生物学固有敏感性问题。
1.4 不同肺癌细胞株照射剂量与杀灭效应关系存在较大差异
2010年Das等[13]报道了典型小细胞肺癌、变异小细胞肺癌、肺腺癌、鳞癌、大细胞癌、腺鳞癌等共29个不同细胞株分别照射2Gy后的放射敏感性。典型小细胞肺癌细胞株整体放射敏感性高,存活分数低,但各细胞放射敏感性均有差异。7个肺腺癌细胞株之间差异更大,2Gy后照射细胞存活分数(survival fraction,SF)相差达20%~80%。不同细胞株代表“剂量-效应关系”的2Gy、4Gy、6Gy、8Gy、10Gy剂量照射后的存活曲线也不同,最抗拒的是NCI-H661细胞,存活曲线“肩”更宽,如6Gy剂量照射时,SF较NCI-H23和NCI-H460高出10倍以上。
Das等[13]还比较了EGFR突变细胞株和非突变细胞株的放射敏感性,突变型高于野生型,但即使是9株EGFR突变型细胞或10株EGFR野生型细胞之间,照射后细胞活力也分别表现出差异。这仅仅是EGFR突变、非突变与细胞本身放射敏感性的关系,不要忘记除EGFR外,还存在ALK、HER2、B-RAF、MET、ROS1、RET、K-RAS……甚至整个基因组学固有因素与细胞放射敏感性都有关系。王承红等[14]比较宣威肺腺癌05细胞(Xianwei Lung Cancer-05, XWLC-05)、A549肺腺癌细胞株和p53突变前后,以及进一步抑制PI3K/AKT通道后的放射敏感性都存在不同。
2 微环境与代谢因素影响肿瘤的放射杀灭效应
再考察非肿瘤细胞本身的其他放射生物学因素,主要包括肿瘤细胞之外的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由肿瘤组织内血管、淋巴管和细胞外基质构成,结合被激活的纤维母细胞、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等基质细胞的参与导致了实体肿瘤异常的微环境,其结果是扭曲疏漏的微血管带来的乏氧和酸性环境。这些因素都可以促进肿瘤进展、转移、免疫抑制和诱导产生表型肿瘤干细胞,使得肿瘤对治疗产生抗拒[13,15]。
由于基质细胞、血管结构和局部细胞因子的因素,即使同一个肿瘤中的微环境都会非常复杂,不同区域之间的乏氧情况、营养、pH值和组织间渗透压等等有很大变化[16]。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余年来,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等肿瘤生物影像技术出现后,放射治疗逐渐淡化物理学剂量均匀性,反而强调“稳、准、狠”和“剂量描绘(Dose Painting)”的选择性剂量不均匀性原则[17-18]。如果一个肿瘤本身不同区域都要考虑到乏氧、代谢而雕琢出不同剂量区域,又怎么可能从RTOG 0617一个试验中得出不同患者的“标准剂量”呢?
3 放化疗反作用证明剂量不足够高可能促进复发和远处转移
一般而言,肿瘤学家最为关心的是放化疗后肿瘤负荷缩小程度和相关副反应毒性大小,要么治疗不足,要么治疗过度,而往往忽略了一个概念:“反作用”,即放疗、化疗干预后肿瘤本身的生物学行为和固有放射生物特性的改变。实际上很多文献报道过放化疗导致细胞生物学行为恶化的现象。Kaplan等[19]最早在1949年报道肿瘤照射导致肺远处转移增加,Strong等(1978年)[20]、Anderson等(1981年)[21]和Fagundes等(1992年)[22]临床试验也分别有肿瘤照射后远处转移增加的报道。
2006年Jadhav等[23]研究发现0Gy、5Gy、10Gy、20Gy照射神经母细胞瘤后,残留细胞外侵能力增强,照射剂量越高接种到动物后的残留细胞对新生血管破坏越强,残留细胞侵袭与转移相关蛋白酶金属蛋白激酶(matrix metalloprotein 2,MMP-2)和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等等表达也越丰富,说明放射后残留细胞“反作用”越明显。
Li 等[24]对裸鼠皮下肿瘤放射后残留组织接种于裸鼠肝脏,3周~4周后发现肝脏内明显播散和弥漫性病灶,而接种无放射肿瘤组织则主要在局部生长,肿瘤组织侵袭与转移相关蛋白MMP-2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蛋白明显增高,与照射剂量正相关。
Xiong等[25]发现化疗导致肿瘤细胞发生侵袭度和转移能力提升的上皮间质转化现象。更直接的化疗“反作用”实验是Yamauchi等[26]直接把荧光标记的纤维肉瘤细胞HT1080细胞注射入小鼠尾静脉,观察肠系膜微血管、微循环小血管,结果环磷酰胺“预处理”的小鼠肿瘤细胞很多溢出血管外形成转移灶,而未经过环磷酰胺“预处理”的小鼠则较少发生该现象,证明化疗有可能通过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从而促进肿瘤转移。
2017年,Karagiannis等[27]发现紫杉醇化疗可以增加肿瘤微环境转移(tumor microenvironment of metastasis,TMEM)的活性和密度,增加促进癌细胞侵袭和转移的肌动蛋白调节蛋白(mammalian actin binding protein enabled,MENA)表达,增加远处转移。Chang等[28]证明,紫杉醇直接杀灭缩小肿瘤的同时,增加了循环肿瘤细胞和TMEM丰度,改善肿瘤转移微环境。随着肿瘤细胞外泌体在肿瘤进展和转移中的关键信使作用认识越来越普遍,Keklikoglou等[29]近期发现,紫杉醇可以促进肿瘤释放外泌体,改变肺中的微环境,促进肿瘤肺转移。
以上几个试验都告诉我们放疗、化疗会增加肿瘤残留细胞的侵袭度和转移力,似乎可以解释RTOG 0617高剂量组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比标准剂量组高,并不一定是“高剂量”惹的祸,反而可能是剂量还不足够高,杀灭不彻底。
4 其他放射治疗和药物使用等干预因素对“标准剂量”的影响
RTOG 0617的作者Cox[3]提出RTOG 0617的结果可能还有更多、更透彻的原因,任何一种细致的解释都可能,60Gy照射是否一定是“标准剂量”,也还不清楚。放射损伤与修复、时辰放疗、修饰剂和放射分割模式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放射治疗对肺腺癌的局部控制率与远处转移率。所以,也可能治疗一开始而不是结束后,肿瘤就发生变化了。
4.1 放射损伤与修复、时辰放疗和修饰剂影响放射杀灭效应
Wachsberger等[30]研究报道肿瘤细胞照射后5分钟,损伤的DNA就可以大量修复,多数细胞放射后2小时内DNA双链损伤就基本修复完毕。Chang等[31]关于时辰放疗研究,不同时间点放疗肿瘤控制无差异,但比较上午照射组与夜间对时照射组,正常组织损伤情况不同,由于凋亡、周期以及时辰基因与蛋白PER1、PER2和Clock……的不同表达影响到生物学结果的改变。这些因素,在RTOG 0617试验中自然不可能匹配,“标准剂量”60Gy照射优于高剂量74Gy的结论受到影响。
真实世界的临床实践中,还要更多地考虑放疗结合多学科综合治疗因素的贡献,研究这种情况下的生物学因素:分子分型、靶向、化疗、旁效应、微循环、低剂量照射、时间节点、放射敏感性、正常组织保护性等等。如作为重要因素,放射修饰剂应用对肿瘤控制与正常组织损伤,影响到放射治疗剂量决策。14个随机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表明放射防护剂阿米福丁对头颈、胸腹盆部放射毒性有很好保护作用,黏膜炎、食管炎、口腔干燥、放射性肺炎明显下降[29]。Christofidou等[32]报道天然植物亚麻籽素有很好的放射防护作用。李文辉团队也筛选发现多个天然防辐射药物(不详述)。所以,结合临床不同的药物干预,结果也会不一样,我们不能受到“标准剂量”的羁绊。
4.2 精确放疗技术指导下的大分割模式不适用于“标准剂量”要求
精确技术指导下的放射治疗“稳、准、狠”已经成为更多的治疗和质控要求,而大分割照射模式的放射生物学机制与常规分割(2Gy/次)明显不同。经典放射生物学认为,连续的多次小剂量照射可以逐级放大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杀灭与损伤效应,有常规分割、超分割、大分割等等不同的临床尝试。但DNA损伤与修复试验则提示肿瘤细胞一旦放射干预就会变化很大、变化很快[30],应该争取一次性打击,符合精确放疗时代放射治疗界提倡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或者放射消融治疗(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之主流。
总之,通过放射生物学原理与实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放射治疗最终效应取决于很多因素,个体化、异质性、放射生物修饰、综合治疗措施……差异很大,要客观辩证分析,在尽量减少正常组织损伤和保护重要器官的基础上予以高剂量放射治疗,不应该过度拘泥于RTOG 0617结果60Gy“标准剂量”的限制。同时关注放射治疗的“反作用”,即不能彻底杀灭肿瘤时,残留细胞浸润、转移力就会增加,这样在精确放射治疗技术指导下SBRT或SABR“稳、准、狠”地杀灭肿瘤显得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