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观念·语言
2019-06-10张宪光
张宪光
哈里·列文在评论海明威及其时代时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时期里,更为广泛、更为成熟的再现往往是虚假的。”所谓“更为广泛”,或许指的是长篇小说所呈现的宏大场面和多重面向;所谓“更为成熟的再现”,无疑指的是那些小说家沉迷于自以为是的技巧。换言之,许多作家除了变换“技巧”这一花样外,已一无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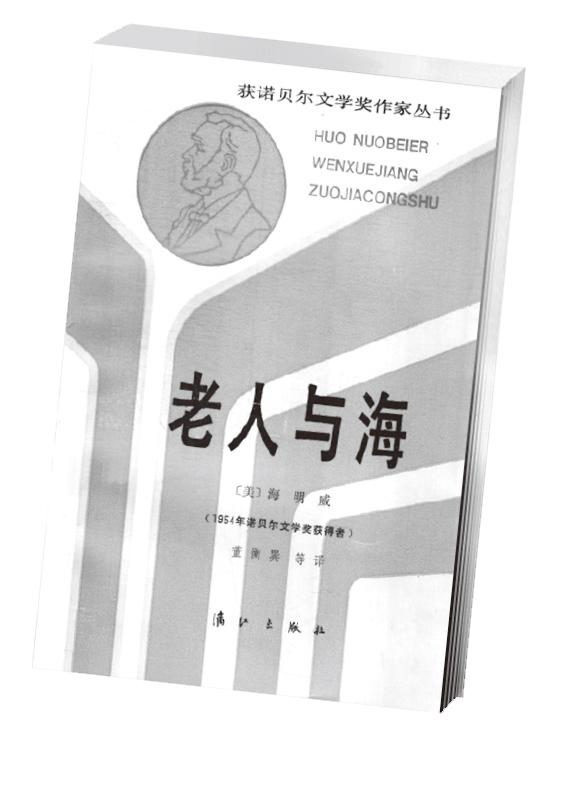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董衡巽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 年版
一个好的小说家的任务是消除先入之见,只是描述个体以及人群的存在经验,而不是政治、经济或技术的回声。卡洛斯·贝克认为要想像海明威那样捕捉自己“真实地”知道的“真正的”感觉,其根本即是:“消除自己的先入之见:这样和那样都是应该的,想当然的。” 海明威在谈到《老人与海》时说:“我尽量删去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向读者传递经验。这样,在他或她读过了以后,这就成了他们经验中的一部分,好像确实发生过一样。”我想,海明威擅长把他个人的经验变成小说人物的经验,继而变成一切人的经验。在这个方面,很多作家往往是在观念的鱼塘里撒下木偶式的鱼苗,漂浮在虚假的水面上,无法长成那头巨大的白鲸。
芥川龙之介是个道德家,只要读一读其《明日之道德》就可以见出了。海明威也是个道德家,只要读一读《太阳照常升起》就可以了。然而两个人常常被读者误解,后者尤甚,被认为是颓废生活的倡导者。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海明威 “不是一个道德家,不是一个重要的、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叙事大师”,他有的是无与伦比的伟大风格本身,一种对现实所采取的特殊的态度的隐喻。在他眼里,山林、海洋、河流、动物、战场都是隐喻的丛林,游走着现象与经验之魂。
海明威不是圣人,他的传记作者林恩也不是,可是林恩自以为自己是,可以对别人的缺点指指点点,义愤填膺。他不屑于从其他可能的角度解释海明威的一系列看似反常实则正常的举动,而将其单纯地归咎于童年阴影。在他看来,海明威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清教徒,有必要对他冷嘲热讽,使之回归正道。他太较真,没有幽默感,却试图以自己道德家的幽默感来重塑这个人。钱锺书云:“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看他为自己做的传。”此言可以拿来转赠给林恩先生。

《追风筝的人》[ 美] 卡勒德·胡赛尼著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特里林说:“人们要求海明威要热心、怜悯,有所谓的‘社会意识,要有正面的、‘建设性的、实实在在的东西。难道生活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吗?作家却不这么看。难道作家是个恶棍或反革命分子吗?”当海明威只写自己要写的那些“冷峻”“扰人”的东西时,伴随他的总是攻击和恶名;当他听从了批评界的呼声,写出《有钱人和没钱人》《第五纵队》时,伴随他的是接纳与小说的惨败。海明威后期的失败,据特里林的考察,要归咎于那个时代“沦为道德和政治说教”的文学批评,以及将海明威其人与海明威作为小说家等量齐观的阅读习俗。我想,这样的现象绝不是孤立的。
《追风筝的人》一书,以主题言之,为犯罪、赎罪、自我救赎之心路历程;以时空安排言之,喀布尔为失落的伊甸园堕落成的塔利班统治下之地狱;以宗教文化言之,则为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波斯《列王纪》叙事传统以及原型而成。虽堕入流行小说之窠臼,而绾合之妙自不可掩。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是海明威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哈里·列文说:“残暴与性爱固然是令人兴奋的题材,但麦康伯的故事其实以忧郁的方式融合了两个互不相干的主题:勇者抱得美人归和女人较之男人更凶残。”这一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了,小说题目中“短促”“幸福”的對立暗示了小说的内涵。与很多富人一样,麦康伯体面而且精通运动、打猎,但根柢里怯懦而幼稚,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吊诡的是妻子明目张胆的红杏出墙让他成为一个直面野牛的人。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勇者—在海明威的哲学里,勇者不是两手空空就是死亡,“朝闻道,夕死可也”。有些人“幸福”地活到八十岁,依然未曾被生活的雨水打湿。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收入《海明威短篇小说选》鹿 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版
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里看到的是那个庸俗猥琐的小说中的中国,而不是他们读到的诗文里的中国。张爱玲的小说书写,也是承接了通俗小说的传统,左手写虚无,右手写欢愉。那虚无是掺杂了现代性的虚无,那欢愉只是“在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使那些人的“畏缩不安的心”“得到暂时的休息”。
海明威将死亡称为他的女孩、马匹、雄鹰、猎枪、小兄弟以及敌人,但他更喜欢的是将它称为娼妓、老婊子,归根究底是雌性的。在我看来,海明威算是最好的死亡练习师之一,几乎在小说里将所有的死亡样式逐一演习了一遍。无论是栖身于墨西哥温暖湾流中的老人,还是置身乞力马扎罗雪山之下的哈里,还是在非洲大草原上狩猎野牛的麦康伯,都在为死亡样式而苦恼,可惜的是海明威在疾病的重压下将自己的死亡大戏搞砸了。
对于芥川龙之介来说,小说是其散文随笔的倒影—因为他的小说乃是观念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在散文、随笔中得到较为清晰的表达,在小说中则是隐晦曲折的。相反,对于海明威来说,其小说是经验的,观念倒是来自小说的,是经验的晶体。
内藤湖南《禹域鸿爪》之记叙焦点,不在于美人风俗,而在于考古经济,不似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之专在印象与感觉耳。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之游记,是审美的、艺术的、感性的,内藤则是理性的、考据的、历史的,故落笔便趣味有殊。谷崎、芥川之文需才高八斗,内藤之文则需胸中有数千卷书。芥川中国之行所持参考书乃池田桃川氏薄薄小册《江南名胜史迹》之类,而内藤必备的参考书则为顾炎武《昌平山水记》、马征麟《长江图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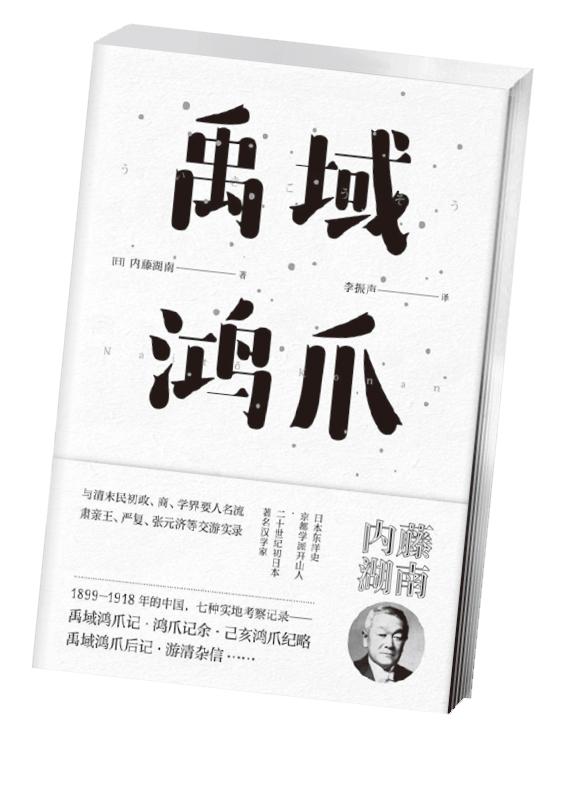
《禹域鸿爪》[ 日] 内藤湖南著李振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

《中国游记》[ 日] 芥川龙之介著陈 豪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 年版
阅读《乔伊斯书信集》,好比在阅读一部精彩的小说或者观看一出戏剧。这出戏剧以易卜生的影响开头,然后饥饿以及与诺拉的性爱构成了这部戏剧的第一个高潮—也许是唯一的高潮。至于一九二五年定居巴黎以后,那个整天哭穷的乔伊斯开始挥金如土,谈笑自如,韦弗小姐、庞德以及其他一干名流依次登场,而给斯坦尼斯劳斯和诺拉的信则一封也无。致韦弗小姐的信表明乔伊斯和评论家是怎样巧妙合作,操纵了舆论从而为自己谋利的,虽然对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来说这很必要。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出戏剧越来越乏味了,三百页以后的信函已经成了让人头痛、甚至厌恶的独角戏:胃穿孔;一个都柏林人的兴衰史;一条出水的鱼遨游名利之海;滑稽而难堪的死亡。乔伊斯再也不是那个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了。然而文学或者艺术究竟是什么东西,鬼知道呢!—然而我却依然喜欢《都柏林人》。
颁布禁酒令的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罪恶的时代,是新旧文化与道德竞技的分水岭。新技术所引导的生活方式,通过汽车的追逐在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得到了比小说更充分的渲染,而一行人抵达纽约后服务生手持冰锥的场景应和着黛西“那么我们顶好打电话要把斧头”的台词,使得镜头充满了危险的、不确定的暗示,提示了死亡之鸟扇动的双翼。与海明威刻意客观、冷静的叙事语调不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述相当主观,二者似乎各臻其妙:海明威的主人公们在失落的时候保持着优雅或者宁愿死亡也不肯摇尾乞怜,而菲茨杰拉德之所以不朽,按照爱泼斯坦的说法,在于他塑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伟大的失落主体—至少盖茨比的体验是一手的,是没有被技术与时代阉割过的,也没有成为权力的施舍。那些杀死盖茨比的人,属于精致、老派而道德堕落、总会在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类人,正如辛波斯卡诗中所言:“秃鹰从不认为自己该受到惩罚。/黑豹不会懂得良心谴责的含意。/食人鱼从不怀疑它们攻击的正当性。/响尾蛇毫无保留地认同自己。/胡狼不知自责为何物。”如果我们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首诗,黛西与汤姆正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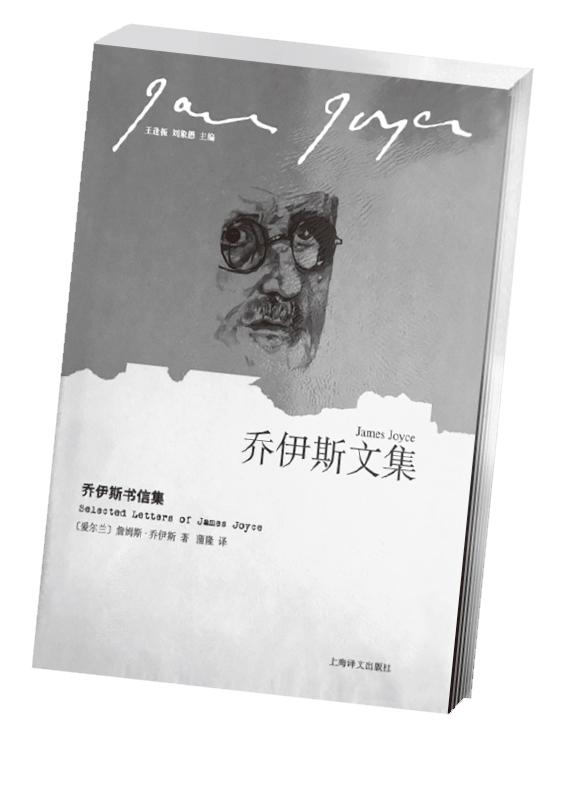
《喬伊斯书信集》蒲 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菲茨杰拉德著巫宁坤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年版
德勒兹说,思考源于一场充满偶然与几近暴力的相遇,在此,逻辑噤口,理性止步。《狂人日记》中狂人与“他们”的狭路相逢即是充满偶然性与“震惊”(“我”与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的相遇也有相似之处),并在震惊与混乱中不由自主地开始了“思”。在《狂人日记》的第一节里,蕴含着“我思”之问题,狂人的思、想、看、惧皆在建构一个非逻辑的逻辑世界。思想的起点则是与“月光”的骤然相遇,使他忽然跌出了正常的世界,于是感觉开始了延异之旅,在这一刹那间狂人意识到了此前的时间和秩序皆为虚妄,皆为“非在”。狂人突然穿越了时间的裂罅,变成了一个他者,从原有的庸人之场域出走,从而获得了域外之眼,发现了属于自己的真理。
狂人本是“域”中之人,因为疯癫而获得了“域外”之眼,于是日常世界里的月亮、狗、“他们”纷纷进入了象征域。狂人是一个域外之幽灵,从域外将利爪伸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获得了言说权并捕获了历史的真相;待他疯病结束,则重返域内,于是一切停止,归入死寂。狂人的意义,在于他可以置身场域之界,可以从容其内外:由内而外,携带着那种令人惊骇的、蛮暴的冲击波;由外而内,则震惊消失,悖谬登场。
杨凯麟在《从福柯到德勒兹》中写道:“从不存在所谓‘浪掷光阴,因为时间永远联结不可测的域外,其空洞与断裂的形式永远只能在肉身与其盲目且不自主的碰撞和缠扭后,才会浮现意义。”狂人是一个幽灵,也是一个肉身,他在时间的碎片中、话语的缝隙中思考、做梦,并开始言说、书写,他的蛮暴的声音在时间中暂时地击碎了话语的秩序,制造了真理的幻象。他好比德勒兹所描述的那个蛛网中心的蜘蛛,听到了来自时间和历史黑洞中的振动,即内心对自我吃人原罪的潜意识认知与感觉。他发现了关于吃人的真理,从而消解了历史的真理。
德勒兹说:“法律在十八世纪时的改变产生非法行为彻底的全新分配,不仅因为违法的性质有愈来愈朝财产而非人身的变化趋势,而且因为规训权力另外切割与形塑了违法,定义了一种叫作‘犯行的独创形式,使对非法行为的全新区辨与控制成为可能。”在我们的历史上,明代初期以《大诰》为标志的法律实践以及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非法行为,并借此重塑了社会、身体、思想以及灵魂,此点或为鲁迅所批驳之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成因。朱元璋是非法行为地图的重绘者,这一地图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明代的权力分配与运作。
杨凯麟在谈到用中文表达法国哲学的困境时说:“大部分的词汇,如事件、流变、系列、能量等,都将失去法文脉络中的日常性,而成为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术语,突兀地孤悬于中文字句之间。”我想,这是语言交换的常态,而且正是这种非日常性带给汉语惊异感,多多少少参与了汉语的形塑。这种孤悬,未始不是一种发明与创新。也许汉语正遭受着外来语言、网络语言、技术语言等多方面的愉悦而艰难的扰乱和重塑。我们一边哀叹古典优雅汉语的消亡,一边在繁复、矛盾、撕裂、轻佻、放肆、肮脏的语言狂欢中沉醉。权力的语法或者就在这种裂变中成为虚文,成为意义的坟墓。这股蛮暴的语言变迁,正像一场语言泥石流,造就无数的词汇死尸,制造出新的语言褶皱和叠层—而我们正置身于这一灾难现场。

《分裂分析德勒兹》杨凯麟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布尔迪厄说:“令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满足的线性生活故事是人工化的,我认识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福克纳或克洛德·西蒙所做的显然是极度形式化的研究,今天在我看来比那些我们熟悉的传统小说的线性叙述,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而且在人类学方面更为真实,更接近时间性体验的真实性。”生活以及历史绝非是线性的,正如张爱玲所指出的那样是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每个人的体验都是多元、多向的,布满了方向相反的褶皱与裂痕。美国人所写的关于海明威、乔伊斯、福柯等人的传记,在历时性叙事中夹杂着各类猛料和趣闻,以造成解构或轰动效应,即便材料十分准确,关于生平与创作关系仍是建构与逻辑的事物,而非事物的逻辑。侯旭东在谈到线性历史观时说:“线索的勾勒与深度的获得实际根植于时人所不知的历史结果—一种后见之明,根据历史的走向,立于结果,逆推其因而选择、剪接不同的史实构建出的线索,不过是‘以后推前‘以今度古思考方式的再现,即中外学者所概括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倒放电影或‘结果驱动的现象。”先入之见以及后见之明是如此之根深蒂固,是很值得学者、读者、作者所深思的。
杨凯麟《虚拟与文学》云:“如何弥合或撕裂知识与经验间的差距,已成为一个兵戎相接的肉搏战场。”在当代经验暴戾恣睢的战场里,有的人沉迷于过去经验的祖述,有的人陶醉于物质与肉欲快感的感觉品享,有的人试图描述这一战场的烽火硝烟,却因为概念的贫乏与思想的贫血沦为火线的旁观者。事件裹挟着后现代飓风与我们粗暴地相遇,新闻强光每分每秒都在喷射火焰,时间在电子搅棍的搅动中变得越来越黏稠—我们在其中,亦在其外,像太监一样面对着无数美色却无法操弄,我们置身于蛛网中央却无法感受到蛛网的震动。
如何读与写,是这个时代亟待澄清的问题。德勒兹在评论福柯的《监视与惩罚》时说:“书写的三重定义是:书写就是斗争、反抗;书写就是流变;书写就是绘制地图。”陆兴华先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读,带最大的被动性。但也出现了巴特的读:从司汤达里读出了普鲁斯特,又从新闻联播里欣赏到了童年风景。读亦可以是霸道房客租住到房东的文本中,开始自己的野蛮装修。”杨凯麟或许算是一位霸道的房客。他在《虚拟与文学》中说:“书写如果有其目的,绝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要从犁满各式意符及政权的既有语言中创造出另一种语言,且‘将自己的母语说得像外国话一样。书写是生命的一种展现,但不是透过动人的情节或华丽的辞藻来述说,而是经由对语言结构的冲撞,与对它所负载的国家、种族社会与文化意符周旋,来展现生命的强度。”他在写作中用法语文法、词汇形塑、介入母语之域,残暴地重组词与物。
语言的捆绑是我们感同身受的最紧身的捆绑,勒出思想的血痕,而我们却甘之如饴。对此,我们只能放声大笑,声振屋瓦。德勒兹说:“由防止小孩手淫的机器直到为成人设置的監狱机制,如一道锁链般展开,令人不由自主地爆出大笑,即使羞愧、折磨或死亡都无法使人闭嘴。”这令人想到鲁迅的笑:“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虽然二者的笑并不完全相同。
法国哲学家的语言—比如福柯、德勒兹、布尔迪厄等—最为诡异复杂。总是不规则地生长、拼贴、链接、组合,在逻辑中制造混乱,在混乱中指认逻辑。他们是语言的叛逆者,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思想、语言与逻辑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