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冰场,也入“笼中”法则
2019-06-10詹湛
詹湛

《熊镇》[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著郭腾坚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
有时会这么琢磨:体育运动,尤其在对抗性强的项目里,一组对手间,是否有一种无形的规则网在起作用?显然,在这个规则下允许双方频频发生某种对身体动作语言的解读,但离开了赛场该规则网可能无法继续起作用。发生在集体项目中时, 教练对场上形势局面的解读,关于对手及队友状态的判断与策略,其实都属于对这一临时规则网络的即兴解读。说得浅白一些:谁解读得更好,谁就更可能会是胜者。
有诗人曾形容,命运犹如在用一只无形的大手掐着每一个人。哲学家雅克·拉康有个著名的定义“大他者”(区别于普通“他者”),那听起来也是一种近乎浪漫的比喻,只不过分析是冷静的。简而言之,拉康认为我们身边时时穿布着复杂的规则网络,它们协调并支撑大小“共同体”的运作。对于婴孩来说,第一个占据大他者位置的人一般是母亲,继而才是饱含语言秩序与行事规则的小环境。这似乎足以解释我们自己每日的行为为何总像在某一种路向的轨道上滑行。在巴克曼的这册《熊镇》里,作者正是将拉康理论中提到的“小环境”,别出心裁地置于了一个广泛开展着冰球运动的小镇。
二○一八年年底刚拿到此书时,江浙沪难得一见地下起了大雪,笔者恰好也生平第一回观赏完一场完整的冰球比赛;朋友见我兴致盎然,又发来了长长的连载文,那是常少宏的《一位华裔妈妈与她的冰球少年成长记》。这组连载之所以关注度颇高,是因为她能以母亲的情感基底去深刻地体验这项国人所陌生的运动。文中有这么一句无奈的话:“假如哪个打冰球的孩子的爸爸妈妈说,孩子十年打冰球的历史就是充满了血和泪的历史,那我一定是相信的……”可见她对小众运动冰球的体悟已然上升到了很高的层面,比我这样的初观者,自然更有资格去评论这么一本关于冰球的书了。
还是继续《熊镇》的话题吧。令大部分国内读者最纳闷的应该是,为何会有那么多西方青少年选择将他们年轻的精力投入到这么一项运动中去呢?何况一上场就意味着面对近乎战斗的风险。书中原文是这么形容的:
打冰球可是很痛的,无论心理上或精神上,它都需要非人的牺牲。它能折断他的韧带和双腿,逼迫他在天亮以前起床。它占用了所有时间……只要保持饥渴就能够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孩子们就能轻易地爱上这个领域……(选手)每个部位都感到疼痛,每个细胞都在哀求他躺下休息……甩掉汗水,将冰球杆握得更紧,将冰球鞋踏在冰面。
那么,熊镇的本质又是什么样的呢? 按照书中背景交代,熊镇坐落于大森林中的一块相对贫穷的区域,但镇上仍住着几个富人。球会曾经濒临破产,而眼下,投资者需要的回报是:青少年代表队能杀入精英联盟。自然,某种程度上那将不只意味着熊镇未来运动行业的繁荣,也迟早将是一座小城市能够开展品牌营造的资本。书中的老教练是最好的见证人,他看着每一代球员的出生、长大,甚至还亲手训练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他都知道:球队并不只是球队,它已经成为熊镇内部的一个王国。但凡是和冰球有关的事发生了,可能就会牵扯冰球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
难怪,如果仅停留在体育层面,小说的构思自然无法巧妙到什么地步。你顶多只会承认,这一文本上上下下通晓着北方社会的种种窍门,或者会误以为,作者自己就做过冰球教练。瞧瞧作者反复描写的城市景象与北方日常服饰吧,让我不由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周遭随处可见的保龄球馆和溜冰场,以及人们出入时相当时尚的穿戴—这两者在今天的上海是不是已经不大能见到了呢?
教练之外,重要的就是明星了,明星之外还有一些帮衬的队员和初出茅庐的小球员。其实在那些正在努力阶段的小球员身上,更容易深挖出处于这一环境中的个体的内心状态,诸如:“他小时候曾听过一句话,冰球是有资历与长幼之分的。他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一旦站在冰球场上,就会知道一件事:意志力可以战胜阶层。”
在之前对所有运动项目的观看经验里,恐怕只有在橄榄球场与拳台上,才能聚集堪比冰球运动的高“密度”。我的意思是,拳手不只在用高密度的進攻来打击对手的意志,也需要用高密度的闪避来维持高站立水平,爆发方式也好,消耗时间之策略也罢,与田径等其他激烈的身体运动有着截然的不同。说实话,遵循的是一种较为“初等”的生存规则,或曰“动物化”的。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里,在别人窘迫或失误之时对其乘胜追击的做法,总会令人瞧不起。不过在拳台与对抗场上的(合理技法)规则下,被提倡的反而是:在对手失误时接着打,直至其趴下……确实是有些残忍,同时也是关于人最原始、最真实的动物性一面的展露。

冰球比赛
书里描述的冲突,终究也是在原始的人性层面发生的。那是冰球明星对其“准粉丝”的一桩意料之外的性侵事件。论时间节点的话,恰好发生在冰球少年及其粉丝即将迈入到成熟年纪的过渡阶段。然而明星毕竟是明星,被侵害者处于弱势。无论是朋友之间秘密的保守、猜疑和传话,还是民意调查与私底下计划着的昭雪和复仇,都不利于后者。当冲突迟迟得不到解决,便有警方介入,此时已经不只是同龄人的竞争和比拼,或者队内队外的斗争那么简单了。
朋友纷纷远离玛雅一家,玛雅的母亲还是律师,而父亲甚至还是冰球队的体育总监—恰恰因为对自己身份的顾忌而无法帮忙;所以最后,玛雅被迫使用了自己内心所认可的极端方式惩戒了对方。与其说受害的玛雅不被镇上的人理解,不如说这一切暗示着:即便运动本身是残酷而充满竞争的,但那与无形易变的、人际领域的“冷战”相比却已显得直白、诚实与坦率了许多。玛雅受不了的不只是身体伤害,还有周围人支持的匮乏与对私人脆弱情感的不珍惜;于是乎,直白的惩罚方式,可能倒是作者巴克曼眼中,更适合故事本身纹理的一类解决方式。
《熊镇》就是这么一本翔实交代了暴力竞技运动的正反两面的小说。熊镇里并没有熊,可是当一个环境里每个人的交谈与对未来的憧憬都围绕着一项运动运转时,其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所有人都犹如被带入无形大笼子里的熊。进一步说,没有哪個熊镇居民能够彻底抛弃“冰球”所奠定的记忆边界。宏伟的目标虽然大,也能转身成为冰冷的屏障;微弱的东西虽不起眼,却可以在关键时分维系人最珍贵的情感。
书中的人物,苏恩和戴维是青少年队的教练,侵犯玛雅的凯文就是明星,他有天赋,而班杰等人是同伴,多少需要奉承着“老大”。而另一个男孩,勤奋练习着冰球的亚马,是青少年第二梯队的成员,他的母亲是冰球场的清洁工,亚马暗恋着玛雅,但也清楚自己远不是明星。此外赞助商的位置很重要,就算是熊镇的体育总监安德森也要听赞助商的话。
这让人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冰球不只是明星运动,也是集体运动。当原本身体最弱的队员在努力成为最强时,这项运动所提倡的精神无疑是被彰显的。运动对人是极佳的塑造场(这也是笔者十分热爱观看各式运动项目的缘由),起码在赛场上,贫富之间的差距、族群性别歧视之类暂时可以靠边站。不过,唯有进一步观察集体力量是如何协作的,才能接近这项运动的真谛。在冰球比赛现场观后,笔者极大地震撼于两队之间高速的攻防切换与血性十足的冲撞。分分秒秒都可能激发出对殴来,不免令每一个未曾接触过冰球的观众觉得无比震撼。可是冰球场上,之所以向来设定着“短时间内(取掉护具与球杆)单挑”的规则,也正是为了预防两方集体不要变得过于热血,人工地创造出的一个缓冲区。
在社会学家米德眼里,“游戏”中的成员之所以能够相互配合,还在于游戏群体必须依赖明确的规则才能得以存在。在游戏尚未开始前,规则就会发生作用,任何游戏者都不能脱离游戏群体而单独行动。他以棒球比赛队员都知道怎么履行规则为例,一个球员必须考虑在自己做出动作后其余三四位队友将做出的行为反应;再如篮球,假设个体是一名大前锋的角色,他不但要抓好篮板,还要有较强的策应能力和较强的得分能力。运动“游戏”中,预判几秒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必须的素质,这是一种堪比“行为反应链”的电光火石般的神经反射过程。
这种(以体育形式)进行着的游戏看似平淡无奇,但米德说,它对于人类的发展极其重要。正是因为有了行事规则之后,“个体一旦采取了某种态度,他也就可以要求其他人采取类似的态度”。在熟习了游戏阶段的行为反应规律之后,个体就能够根据三四位以上的成员的反应作出配合,而不再像初级阶段时仅把握一个态度。唯独对于太远和太错综的“事件”,没有高素质与高训练强度是来不及考虑的。
又兜回到了文首。个体和集体之间究竟如何互动,在冰球场上与在真实的生活环境里,还真是共有的命题。雷蒙·阿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他在自己晚年的《历史讲演录》里谈及一个旁枝,虽然也涉及人的社会性究竟如何形成,角度无疑与社会学家米德不同。阿隆其实是借用哈耶克的说法来表述该理念的:“我们对于他人行为的解释都是借助自己的心灵来进行的;我们理解其他人,(像)是因为有相似的心灵。”请注意,“相似的心灵”—显然没有谁能直接地观察出他人的心灵,最多只能就他人所说和所做粗线条地辨识一下。书中更进一步提出的观点则大胆而似曾相识:某种意义上,我们之所以想要认识他人,并不是因为惯常理解中的“志同道合”,而恰恰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他们”与“我们”间存在“不同”。
在巴克曼另一册更出名,也被改编为电影的小说《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里,作家以十分调皮的方式为每一章命名,诸如: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在小区巡逻、一个叫欧维的男人拉着拖斗倒车等。回想一下,欧维先生所在的不也是小镇吗?但欧维先生的小镇与“熊镇”有着区别。人们所处的地域与阶级不论,起码欧维勤勤恳恳地付出,周遭人们大多能切实体谅他的坏脾气,因为他所抱怨的东西不是没有缘由的,虽然人们口头无法赞同他的苛刻言行,但心里都认可,欧维对世界怀着常人所不及的诚挚的眷恋与爱。在他心理落难之时,自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伸手,以不露痕迹且格外有创意的方式加以挽留。韩松落的书评说得太好了:“他总在一点点加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总在向下伸出根须”,帮人修理每一件东西,固执地维持花园的整洁,把别人的东西看得比自己的东西还重要—欧维这个角色,真的就像是一株默默生长在社区的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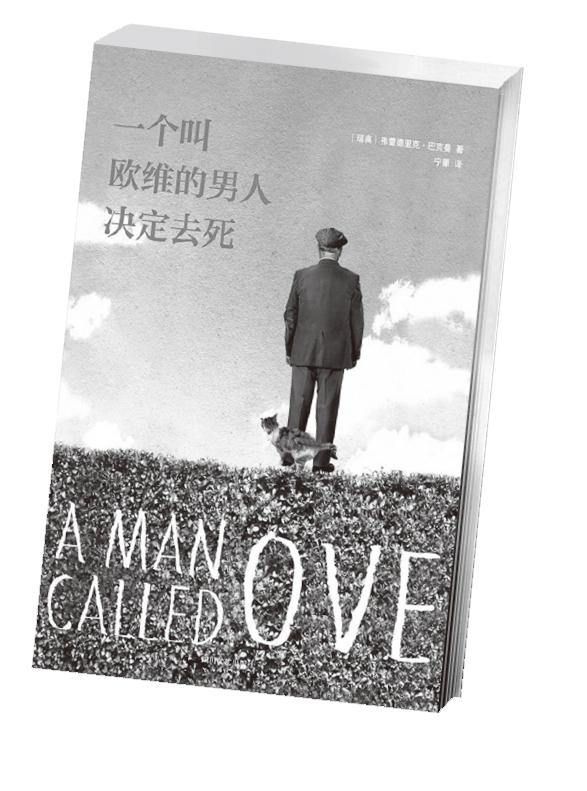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著宁 蒙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
相比熊镇(当然也是虚构的,巴克曼或许有真实的取材出处)居民,一个劲地想告别世界的欧维先生显然十分幸运,确切地说,他身边大大小小的朋友们能够知道,尽管欧维比每个人都老派、较真,但“相似心灵的不相同处”里藏着最值得珍惜的一些东西。可是熊镇里呢?那些“粉丝”,乃至被“粉”的明星男孩,都如同在迫不及待地追逐什么,而后就算追逐到了,能真正地理解与珍惜吗?
体育运动过程中,不违反体育精神的斗争一向被鼓励,在其他不少与运动无关的行业里,也多少能见到对竞争力的提倡;然而以自己或他人的受伤来换取荣耀或胜利的方法,又该何时启动,何时停止?这个设问当然极其微妙复杂。在性侵事件后,作为明星一方的凯文,唯一能想明白的是,并不是每一桩事都可以那么轻易地打赌;受伤的人遍体鳞伤地试图忘记它、回避它,然而这在短期内是做不到的。场上那样绝妙的攻防、转接、跑动,足以决定谁赢谁输,谁水平高,谁又是弱者;在场上看似无比单纯、整齐的欢呼怒号与沉寂之表面下,约定俗成的社会体系也好,被高等教育定下的理念体系也罢,确实与贫富和身份歧视一同被暂时搁置了,但当比赛一结束,不用怀疑,它们肯定又重新回来了。
毕竟,再往深处探询,人类社会关系早已进化出了犹如蚁窝组织的行为反应体系,几个球员在临场情境中所看到的与做到的固然能够赏心悦目,但那些如湖心泛起波纹般的长线事物之发酵是他们所估计不到的。冰球场之外的压力,且不说其他,伤痛和自我康复这些事情,都需要球员独自一人对全局进行思考,而借酒消愁之类的模糊处理又普遍存在。另一些复杂的问题则牵涉到立场选择,《熊镇》里受害者玛雅的父母对这一事件的事态判断,就是值得思考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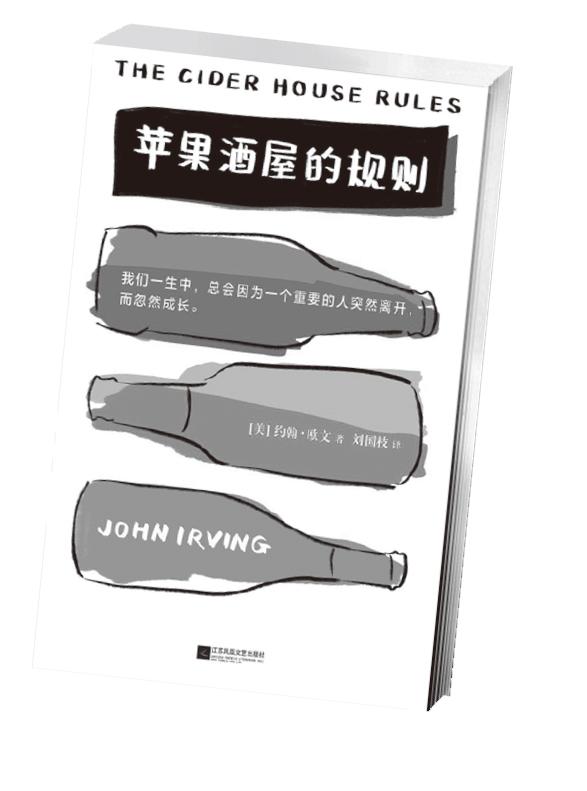
《苹果酒屋的规则》[ 美] 约翰·欧文著刘国枝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
每当博学的雷蒙·阿隆谈及近乎无解的人性问题时,总显得挺无奈,他说“我不必进入整个问题,这是极其复杂的”,起碼远比他擅长的经济和社会模型要更难捉摸。他补充道,他人的实际行为和信仰(或动机)的真假之间的关系,素来是难以透彻解释的,深究它们并无多大意义。然而,正如一向的风格, 巴克曼从不愿意以论点说教,更不会为读者假定出一些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他只是尽了作家的义务,兀自将剧情推向了复仇事件里的张力高点。你简直能透过这么一个突发事件去重新阅读这个小镇—地理位置还是没变,忽然又那么的不一样了起来,而平时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只是被晶莹的冰雪掩盖着罢了。
确实,这个任务交给文学完成会来得更妥当吧!最后想起一件事。美国大作家约翰·欧文写出过一本了不起的《苹果酒屋的规则》。主人公荷马出入于医疗行业,作者对时代的战争背景下医学条件之描绘,精确得让人咂舌,唯独无可衡量的东西是就是“苹果酒屋”的规则。最后作者采用的方法,是靠着人物间絮絮叨叨的对话去尽可能接近那一模糊的“规则”,当几个主人公已经不再年轻和单纯时,依旧在疑惑事物的准绳在哪里,能不能找到它。与约翰·欧文相比,《熊镇》的文本不算出色,有些情节交代得过于跳跃,《苹果酒屋的规则》则多一些介于严肃与娱乐间的戏谑,情节与人物对话也自有一套枝繁叶茂的魅力。如今作家欧文也已经近八十高龄了,而一九八一年出生的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还年轻得很,之前颇受好评的作品,似乎都表明着他尤为擅长为读者去“设想”一群人在褪去妆容、走下主要舞台之后的心理轨迹。欧文那样的大叙述格局,有时倒不如巴克曼只给出一些零星的“文本信号”来得更有余地。总之,巴克曼日后产出的文本,能否愈加成熟与通透,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