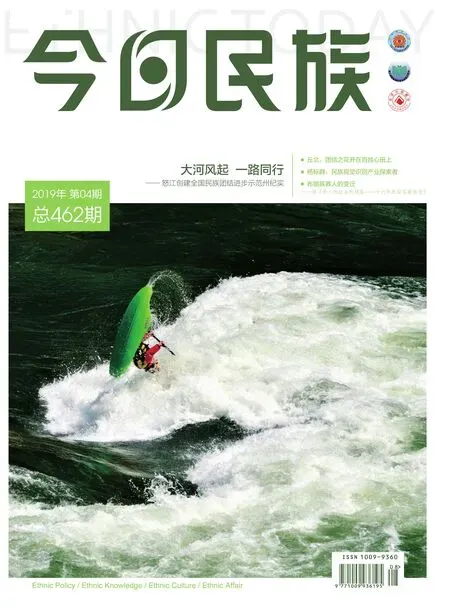布朗族莽人的变迁—读《莽人的过去和现在
——十六年跟踪实察研究》
2019-06-10龙成鹏
文 / 龙成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生活在金平县中越边境的布朗族莽人所经历的改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要了解这种改变,我们推荐《莽人的过去和现在——十六年跟踪实察研究》这本书。这本书勾勒了莽人生活的全貌,借此不仅可以了解莽人的文化,也足以管窥这70年来云南的民族团结进步历程。
不只是学者之书
我两年前去金平金水河镇龙凤村拜访省级非遗传承人陈自新。匆匆一瞥之后,对莽人的社会、文化更觉无知起来。于是,在查阅文献时,我得知了《莽人的过去和现在》(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一书。
该书作者杨六金当时在云南省社科院红河民族研究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因偶然机会接触莽人,此后16年里持续到莽人生活的地方进行田野研究,期间(1997年开始)还因为对莽人的了解,被上级借调到莽人聚居的金河镇担任副镇长,随后又被选为镇长,得以通过学者、官员等不同身份深入莽人社会。因此,书中杨六金所记录的莽人的社会、经济的变迁,其中一部分就是他参与推动的。
比如,他“亲自教他们选良种、栽菜、发豆芽、做豆腐、腌咸菜……另外,还从外地引进了25个适宜在高寒山区种植的水稻品种在当地试种,有两个试种成功,亩产达到了300多千克”。
在莽人的知识、观念、人才培养等方面,杨六金同样做了很多超出学者范围的工作。为此,他还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莽人主席”“莽人头”,并于2000年被红河州委、州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总之,彝族学者杨六金所写的这本莽人的民族志,有不同寻常的身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系列莽人社会精确的知识,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学知识的力量。
莽人的定居与安居
莽人跨境而居,除中国外,在越南、老挝都有分布。中国境内的莽人聚居地,在金平县最南部的金水河镇,共计2个村委会的3个村小组,今天的人口共计760余人。
《莽人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出版于15年前,行政规划和人口,与今天有些区别。人口有自然增长无需多言,但居住地的归并和变化,则直接反映了莽人的生活变迁。
2004年成书时,莽人生活的村子有4个,分别是南科村委会的南科新寨、坪河中寨、坪河下寨和乌丫坪村委会的雷公打牛村4个自然村(村小组),而人口则是107户,651人(根据2003年数据)。
书中还提到这4个村子的由来。1950年莽人开始定居定耕,至1958年,莽人散居在14个窝棚点。金平县政府多次动员,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以金平的拉祜族苦聪人为实例,向他们展示定居生活的好处。1958年底到1959年初,工作取得成效,莽人的14个窝棚点,合并为4个新的定居点,也就是杨六金做调查时的4个村子。
杨六金写完这本书之后的15年里,这4个村子又进一步搬迁、归并,于是就有了今天的3个自然村。这3个自然村分别是:南科村委会的龙凤村、水龙源村、乌丫坪村委会的雷公打牛村。龙凤村就是原来的南科新寨搬到新址后的名字,水龙源村则是坪河中寨、坪河下寨在新址合并而成,雷公打牛村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但也搬迁到距离原址几公里的新居。
2008年5月,政府实施莽人综合扶贫项目安居工程建设,这3个莽人聚集的村子,全都换成了带庭院的二层小楼。
迁自越南
2009年,就在金平莽人的生活环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年,莽人搁置了半个世纪的族属问题得到解决,莽人识别为布朗族,1950年代末以来,关于其族属的争议最终得到解决。
关于莽人的族属,杨六金还特别讨论了“莽人”和“芒人”的区别。莽人一度被写成“芒人”,这造成了很大误会。
越南有“芒人”,人口91.4万(1989年数据)。有人误以为中国的莽人(被误写成“芒人”),就是越南的芒人。实际上,越南有芒人和莽人两种不同族群,其中与金平莽人同族的越南“莽人”,人口只有几千。而金平则只有莽人,没有“芒人”。2001年,杨六金把关于莽人名称的研究报告递交给红河州人大、政协和金平县委、县政府,最终促成了莽人这个族称的写法。此后的民族识别,也沿用了“莽人”的表达。
莽人的族源问题,涉及历史书写,是一大难题。近期的迁徙比较明确,莽人的各大家族都来自越南。杨六金在书中,还把迁徙路线画成了直观的路线图。莽人亡灵送魂路线,也基本与家族的口传历史一致,都指向越南。
不过,杨六金结合关于“百濮”(莽人,或者布朗族,都属于云南的“百濮”系统)的民族史研究成果,认为这些莽人的祖先,可能是从云南保山一带迁到越南,而时间则可能早至明末清初。
这个基于历史文献的推测,已然超出了现代莽人的记忆范围。
原始文化的痕迹
杨六金展开田野调查时,莽人的社会组织部分已经改变,但通过长者的回忆,还能记起其中的一些环节。
比如,莽人社会内部有一种组织,叫“米”。这个组织,通常由不同姓氏(氏族)的10来个家庭组成。换句话说,“米”不是氏族组织,更像是多个氏族的联合。
“米”是莽人社会的自治组织,由氏族的长老们组成(其中一位被推举为首领),生产计划、修建房屋、婚丧喜事、逢年过节等村寨大事,都由集体讨论决定。
莽人的社会文化,就我个人的认知而言,最新奇的莫过于他们的图腾姓氏。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有以图腾为姓氏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事隔四五千年,历史文献很难确证。但据杨六金的调查,现代莽人的姓氏,就明确地反映了他们过去的图腾崇拜。
莽人有两种姓氏。一种是汉姓,这是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使用的,也是现代行政管理时的姓氏。这些姓氏,有陈、龙、盘、刀、罗等等。另一种就是图腾姓氏,这些姓氏,有水鸟氏、蛇氏、哨路鸟氏、布广树氏、斑鸠鸟氏、虎氏、熟郎鸟氏、度朱厄氏等。
这种图腾姓氏,每一种都还细分为三种颜色,即红、黑和灰。比如,水鸟氏分为:红色水鸟图腾姓氏,莽语称“度旺伦”;黑色水鸟图腾姓氏,莽语称“度旺朱”;灰色水鸟图腾姓氏,莽语称“度旺布勒厄”。
这些图腾姓氏,还有两点信息要补充。
一个是与汉姓的对应关系。比如,姓陈的是“水鸟氏”,传说,这一姓氏的先民因跟踪水鸟而寻找到水源,于是崇拜水鸟,以它为姓。其他汉姓也都对应一个图腾姓氏,且有类似的起源神话。而且,如果以某个动物或植物为图腾,这个姓氏就忌吃该动物或忌烧该植物。比如,姓陈的是水鸟图腾,忌吃水鸟。姓刀的为“布广树氏”,忌烧布广树。
另一个是图腾姓氏内部,同一颜色之间不能通婚;不同颜色,以及同一个颜色不同图腾的则可以通婚。这个知识挑战我们的原有认知。
以我们的通常经验,同一个姓之间通常不能通婚,因为同一个姓,意味着来自同一个氏族,有同一个父系祖先。实行氏族外婚制,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普遍的规律。
但是,按照莽人的图腾姓氏,一个陈姓,实际上对应的图腾姓氏可分为三种颜色,相当于进一步分为三个小的氏族,且三个氏族之间,可以通婚。
尽管氏族分化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但莽人还是提供了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方式,给这种氏族分支赋予了三种颜色。
独特的“从妻居”
莽人的社会文化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细节。
比如,被视为某种原始婚姻残余的“妻姊妹婚”,即一个男子或男子的兄弟,娶了一个女子为妻,该女子的二妹、三妹成年后也同样嫁给该男子(一夫多妻),或嫁给该男子的其他兄弟(一夫一妻)。这种婚姻方式,与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相似,恩格斯说是“一整群姐妹共夫的遗风”。杨六金调查时,姐妹共夫现象已不存在,但某哥弟分别娶某姐妹的情况则少量存在。
再比如,过去结婚时,男方请媒人,女方也要请媒人,双方都有一个主媒人和三到四个副媒人。男方去女方家提亲,要拿2串松鼠肉(一串7只,一串8只)。结婚前,男子要到妻子家住3至5年,这叫“从妻居”。期满后,女婿得到岳父岳母允许后,才能带着妻子回父母家。结束“从妻居”这天,要举行隆重的婚礼。
莽人的火塘文化也比较独特。1960年以前,莽人在一栋房子内通常设有不同性质的火塘,有四到五个。这些火塘各自有名称和功能,也是莽人文化的禁忌所在。不过,1980年以后,莽人室内的火塘已逐渐减少,到杨六金考察时,一家只有两个火塘了。
莽人的服饰比较容易区分,特别是女子,女子在头顶盘有发髻,脖子有项圈,衣领处有红绿黄等颜色的装饰线球,对襟窄袖短上衣,穿裙子,短衣和裙子之间,围一块围腰。这块围腰比较大,从腋下到大腿都能包裹。
杨六金说,这些服饰,1980年后基本改变,平时穿汉族服装,只有过节、结婚才穿传统服装。
告别刀耕火种
莽人的社会变迁,最轰轰烈烈的是生产与居住。
新中国成立以前莽人就有农业,但比较原始。种植玉米等作物,但没有固定耕地,而是选中林地,放火烧山。烧山后用木棍、木锄等工具播种(收割则用尖头木棍、竹片,或者手掐)。不懂翻土、除草、施肥。这种耕作就是通常说的“刀耕火种”,对生态要求很高。通常第一次烧山得来的地,叫处女地,种一年就抛荒。五六年后,树桩长成新的小树林,就再烧一次,这次的地叫幼林地。随后,又再度抛荒,几年后,已经烧得光秃秃的土地上树很少了,只有野草还茂密,于是再烧一回,这个地就叫草地。以上三种地,按时间肥力递减,害虫递增,再后面,这种野地就很难继续搞刀耕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莽人的生产方式变化很大。完全进入铁器工具时代,游耕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开垦固定耕地。1956年开始,有人尝试种植水稻。1958年以后,开始逐步普及。草果坪和南科的莽人,在周边瑶族、拉祜族同胞帮助下,掌握了栽培水稻的技术,当时尚未组织起来的坪河中寨和坪河小寨也在1959年播种了147斤水稻种。
书中,杨六金做了一个图表——水田的增长:1950年时是零,1960年是67亩,到2003年是350亩。
今天莽人的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变迁。龙凤村的陈小华支书说,已经不种粮食了,而是改种甘蔗。两年前,我去龙凤村,路边哈尼族的帮工正好砍甘蔗。
跟这种改变相关的是商品交易。村民回忆说,以前没有衣服、食盐,也不知道钱,不敢和其他民族交往。所以,要吃盐,就把猎获的野兽肉和编织品背到其他民族的村子边,放在路边,然后躲起来。其他民族看到物品就知道莽人来贸易了。他们就会拿食盐、铁刀、铁锅、旧衣服等物品,放在另一边,然后也躲到树丛里。“我们从隐蔽处出来拿走他们的物品之后,他们才来拿我们的物品。”于是,不见面的物物交换得以完成。
后来,交易进一步发展,公开化了,莽人与邻近的苗、瑶、哈尼、傣等民族公开交易,莽人换取的物品扩大到酒、药、火药、火枪等。再后来,货币也逐渐进入,商品贸易又进一步发展。
杨六金到这里考察时,莽人经常成群地到河谷傣族人聚集的勐拉市场赶集。往返需三四天,莽人住在傣族人家,食宿以他们带到集市卖的篾垫、凳子为酬谢。
今天的集市交易又进了一步。龙凤村的山脊下,是南科村委会驻地,这里每周会有从勐拉上来的商贩在一个建好的市场里卖衣服和各种杂货。而且,这里也有商店、餐厅和旅社。
莽人居所的巨变
在这短短的60多年里,莽人经历的人类文明史几乎长达数千年。从莽人的口传史诗看,最早的先民是住岩洞,那时候尚不知道建筑房子。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贫穷的莽人也住岩洞。杨六金采访雷公打牛村的龙大,他就回忆说,他10多岁时,就见有一家莽人住在大石洞里。“洞口用小木棍和小竹围栏围挡,洞外还种着包谷。
莽人的居所,还有一种临时性的鸟窝棚,建在树丫上,用于看守庄稼或狩猎。
单坡屋顶棚,是莽人比较古老的住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村子就见不到了,但在80年代,少数困难家庭还住这种房屋。结构简单,用田埂、岩石做山墙,把树干的一端靠在山墙上,另一端插入土中,就构成了一面斜坡,上面盖树叶、芭蕉叶、茅草,斜坡屋顶垂到地面,没有墙。
双坡屋顶棚复杂一些,有柱子,有梁,两边搭茅草,屋顶垂到地面,同样没有墙。1999年,杨六金住在坪河下寨龙三家,当时他家的房子就是这种棚屋。
比双坡更复杂的是四坡屋顶房,也就是鸡笼棚。有低矮的墙体,四面坡遮盖。
上面几种,都是一层,人睡在地上,也叫地板屋。再复杂一点的,就是干栏式楼房了。莽人的干栏式楼房,竹木结构,茅草屋顶,上下两层,用竹片和小细木做围栏。长十三四米,深十米。每栋房子有两道门,后门为背水、拿菜、生育、出殡等出入专用,文化功能异常重要。
90年代,这种建筑是莽人的主流建筑。
90年代末,莽人的房屋,开始发生巨大变化。1998年以前,莽人没有土掌房和砖房。但从这一年后,就逐步开始出现了双坡屋顶的土掌房和砖瓦房。1998年南科新寨(龙凤村)的陈士平,受易地搬迁来的苗族和彝族建盖土掌房的影响,花3000块钱,请苗族泥水匠来夯土砌墙,建盖了莽人第一栋土掌房。第二年,本村罗四华效仿,同样以3000块,建盖了一栋土掌房。随后,有另外三家建盖了石棉瓦顶的砖瓦结构房(用水泥砖砌墙)。
到写这本书时,杨六金说,莽人聚居的4个寨子,共有砖墙瓦顶房3栋,土墙瓦顶房8栋。而我们知道,2008年后,这些自发尝试的各种建筑,都被统一设计的新的庭院式楼房替代,莽人的住房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莽人的文化变迁,不只是这些宏大叙事。该书第十章还专门讨论现代文明对莽人的影响,其中提及了很多现代商品进入莽人社会的具体时间。比如,钟表是1972年2月,南科一村民用卖一头水牛所得的钱,到勐拉买回来的上海牌手表。杨六金统计,“现在四个莽人村寨有手表240只(机械表52只,电子表188只)”。其他现代科技产品,像收音机、电视机、打火机、碾米机、粉碎机等进入的时间,书中都做了交代。
杨六金完成这本书的调查、写作的时间(21世纪初),其实正是中国社会以及莽人新一轮巨变的开始,所以,在过去的15年里,莽人社会的变化,又出现了很多新情况。
两年前,我去莽人的龙凤村时,公路已经修到家门口,两轮或三轮摩托车已经很常见,手机也早已普及。但另一方面,传统的狩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丰收歌、送亡经、独特的单孔巴乌“楞弄”等文化遗产,正面临传承危机。莽人在融入现代社会时,也遇到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