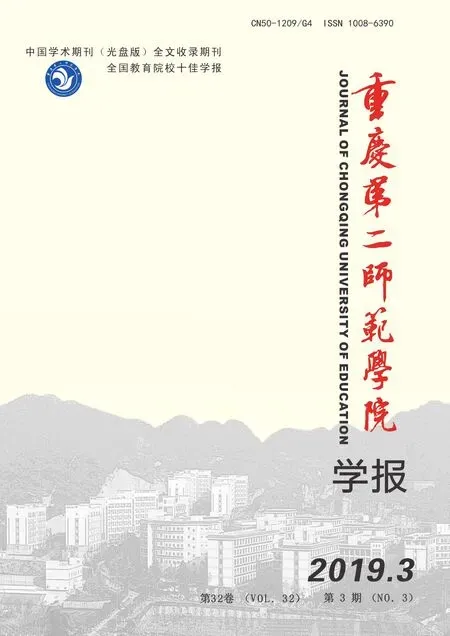沈德符《顾曲杂言》的戏曲论——以其对杂剧、北曲、南曲之“顾”为研究重点
2019-06-05王辉斌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3)
沈德符(1578—1642),字虎臣,一字景伯,又字景倩,今浙江嘉兴人。其父沈自邠,曾参与《大明会典》的修纂,未久即卒。沈德符在其父卒后,即由京师迁居故里。沈德符一生著述颇丰,有《清权堂集》《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飞凫略语》《敝帚轩剩语》(后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收录)等行世。其中,《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有22条专言“词曲”,后人将此22条“词曲”与卷二十六《嗤鄙》之“白练裙”条辑出,合编为《顾曲杂言》一卷,并为《四库全书》所收录。《万历野获编》分正编与续编,正编二十卷,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续编十二卷,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清康熙年间,钱枋得其稿本,因“苦其事多猥杂,难以查考,因割裂排缵,都为30卷,分48门”[1]7。《顾曲杂言》既然是从《万历野获编》中辑出,则其作年至迟在万历四十七年者,即可论断。四库馆臣为《顾曲杂言》所撰提要有云:“此书专论杂剧、南曲、北曲之别。……如论北曲以弦索为主,板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长短其声以就板,立说颇为精准。其推原诸剧牌名,自金代以至明代,缕晰条务,征引亦为赅洽。词曲虽技艺之流,然亦乐中之末派,故唐《乐府杂录》之类,至今尚传。存此一编,以考南北曲之崖略,未始非博物之一端也。”[2]1828既交代了《顾曲杂言》所“顾”之“曲”的具体内容,又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之肯定,如此,则《顾曲杂言》的戏曲学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而喻。
一、《顾曲杂言》的杂剧论
从戏曲发展史的角度言,杂剧的成熟与繁荣昌盛,主要是在金、元时期,且以北方为主,但随着蒙元政权的南移,杂剧亦逐渐由北而南,并最终盛行于今杭州、扬州、南京、上海、苏州等江南都市。于是,杂剧之于南方的戏剧圈,即形成了三个发展阶段①。朱明代蒙元之后,杂剧的创作与搬演在南方仍曾盛行一时,并深为时人所喜爱。对此,朱权《太和正音谱》之《群英所编杂剧·国朝三十三本》、何良俊《曲论》、王世贞《曲藻》等均有所载。而沈德符之于《万历野获编》专论 “杂剧”者,则主要是着眼于“顾”的角度而为。因此,《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之《词曲》部分,未久即成为一卷本的《顾曲杂言》。《顾曲杂言》所“杂言”之“曲”,虽“古”“今”并为,但从全书多用“今”字的实况而言,可知其侧重点乃在“国朝”杂剧。
在《顾曲杂言》中,沈德符对杂剧之所论,主要表现在“蔡中郎”“西厢”“杂剧”“杂剧院本”“戏旦”等条目中,而“杂剧院本”又为其重点之所在。杂剧与院本,借用沈德符的话来说,其在北宋徽宗时“本一种”,“至元始分为两。迨本朝,则院本不传久矣;今尚称院本,犹沿宋、金之旧也”。这是从杂剧史的角度,对杂剧的发生与嬗变所作的阐述,既简单扼要,又清楚明白。而在论及杂剧的发展概貌,以及元、明时期杂剧的现况时,沈德符则作了如下之描述:
涵虚子(朱权)所记杂剧名家凡五百馀本,通行人间者,不及百种。然更不止此。今教坊杂剧约有千本,然率多俚浅,其可阅者十之三耳。……自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以至《琵琶》遂演为四十馀折,几十倍杂剧。然《西厢》到底不过描写情感。余观北剧,尽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观,逐队吠声,咤为绝唱,真井蛙之见耳。本朝能编杂剧者不数人,自周宪王(朱有炖)以至关中康(对山)、王(九思)诸公,稍称当行。其后则山东冯(北海)、李(日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园林舞梦》《皮匠参禅》等剧,仅可供笑谑,亦教坊耍乐院本之类耳。杂剧如《王粲登楼》《韩信胯下》《关大王单刀会》《赵太祖风云会》之属,不特命词之高秀,而意象悲壮,自足宠盖一时。……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闹东京》……种种喜庆传奇,皆系供奉御前,呼嵩献寿,但宜教坊及钟鼓司肄习之,并勋戚、贵璫辈赞赏之耳。[3]215
这段文字,包含沈德符对杂剧认识的多个方面:一是指出当时教坊杂剧数量虽多,“然率多俚浅”;二是认为南戏(戏文)因杂剧之“变”而始;三是认为王实甫《西厢记》不足以为元杂剧的代表,因而那些称道《西厢记》者皆“井蛙之见耳”;四是认为本朝杂剧作家除“周宪王以至关中康、王诸公,稍称当行”外,余皆不足观;五是对元人郑光祖《王粲登楼》等杂剧大加称道;六是认为《千里送荆娘》等杂剧皆属等而下之者。此六者又可综合为两种观点:(1)因“杂剧”之“变”而产生“戏文”,这是对“南戏起源”的认识;(2)对王实甫与郑光祖的评论中,抑王而扬郑。明乎后者,则沈德符“《西厢》”一条所谓“然此类凡元人皆能之,不独《西厢》为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杂剧》”一条中,沈德符重在就“今杂剧”即明代的杂剧进行评论,认为其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是“都非当行”,如“汪太函四作”即为其例;一为“大得金、元本色”,如王辰玉《真傀儡》《没奈何》等。以“当行”“本色”论本朝杂剧,所反映的是沈德符对这两个戏曲学概念的全然接受。“当行”与“本色”,均出自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其《诗法》有云:作诗“须是本色,须是当行”。又于《诗辨》中说:“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在明代的戏曲论著中,何良俊《曲论》、吕天成《曲品》等,就都曾论及“当行”与“本色”(二人对“当行”“本色”的认识并不一致),而凌濛初《谭曲杂札》则有云:“曲始于胡元,大约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4]这是将戏曲语言纳入“当行”“本色”的范畴以论。沈德符于《顾曲杂言》中以“当行”“本色”论杂剧者,则是将明代杂剧与金、元杂剧比较后而言,即其将在艺术方面不如金、元杂剧的明杂剧,统称为“都非当行”,而视与金、元杂剧相类者为“大得金、元本色”。由是而观,可知沈德符以“当行”“本色”评论“今杂剧”者,实际上是将金、元杂剧作为其品评之标准。换言之,在金、元杂剧的文采派与本色派中,沈德符所尊崇、所钦服的是本色派,而此,即是其在《杂剧院本》中,抑王实甫(文采派)而扬郑光祖(本色派)的关键性原因。
除了以上诸方面外,沈德符之于《顾曲杂言》中所“顾”之杂剧,还曾将其对金、元杂剧的深切怀念融入其间,如“北曲传授”一条即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此条中之“北曲”,所指非散曲而为剧曲,也即杂剧之属,而“北曲传授”之所言,则是指在“吴人重南曲”之际,被视为北曲代表的杂剧已没有传人了。其意是说,杂剧在万历年间已步入了晚年的衰歇之期。所以,沈德符于“北曲传授”中,乃以擅长演唱“《北西厢》全本”的马四娘戏班为例,对马四娘卒后“诸妓星散”、无人再唱《北西厢》的这一曲坛现实作了逐一述写,并略有所评。而此所反映的,则是沈德符对于金、元杂剧的一片忆恋之情。
二、《顾曲杂言》的北曲论
《顾曲杂言》所“顾”之北曲,虽然与剧曲(杂剧)密切相关,也涉及了数量不少的散曲,也即北散套与令词。作为北散套与令词的“北曲”,和诗、词一样,虽在本质上属于文学,但却因音乐的关系而能唱,并因能唱而为乐器所伴奏,于是,也就有了“弦索入曲”之说。所谓“弦索”,在唐代本指弦类乐器,金、元人则多将用弦类乐器伴奏的戏曲也称为“弦索”,因而又使之成为北曲的一种代名词②。《顾曲杂言》有“弦索入曲”一条,其中“弦索”之所指,即为滚弦、三弦、琵琶等弦类乐器。该条之所论者,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人将弦索伴奏于南曲(词)所进行的批评,并讥讽这种现象有如金粟道人《小像诗》中的“儒衣、僧帽、道人鞋”一般,颇有点不伦不类。所以,沈德符于此条中如是写道:

据其中的“近日沈吏部(璟)所订《南九宫谱》盛行”云云,可知将弦索“入南词”者,乃始自沈璟的《南九宫谱》,以至于“今吴下皆以三弦合南曲,而又以箫、管叶之”。这种“皆以三弦合南曲”的曲坛现状,在沈德符看来是完全不符合“弦索九宫”之“定制”的,因而才几次引了著名北曲演唱家顿仁的认识,对其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今人一例通用,遂成笑海。”此则表明,在弦索是否可“入南词”的认识上,沈德符与沈璟的看法乃是完全相悖的。
沈德符虽然对“吴下皆以三弦合南曲”的曲坛实况有所不满,认为“盖南曲不仗弦索为节奏也”,但于盛行当时的一些具有俚俗特点的北曲令词,如《锁南枝》《山坡羊》《傍妆台》等,却并不排斥,而是将其以《时尚小令》为题,进行了如实之记录。如其中有云:“比年以来,又有[打枣干][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肺——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叹欤!”[3]213据《时尚小令》全文所载,[打枣干]与[挂枝儿]二曲,是与《锁南枝》《山坡羊》类似的两首俚俗之曲③,但因为“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的缘故,而使之成为一种“举世传诵”的“时尚小令”。沈德符将这种“举世传诵”的传播实况以文字进行记录,不仅成为其雅好北曲俚俗令词的最直接反映,而且也为后人研究明代的“时尚小令”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或此或彼,都是颇值称道的。
《顾曲杂言》对北曲之述论,还有“南北散套”“邱文庄填词”等条,且亦各具特点,如在“南北散套”中对元、明散套作家作品的批评,便属于此类。在这一条中,沈德符于开首即云:“元人如乔梦符、郑德辉辈,俱以四折杂剧擅名,其馀技则以工小令为多;若散套,虽诸人皆有之,唯马致远《百岁光阴》、张小山《长天落彩霞》为一时绝唱,其馀俱不及也。”这是从总体上对元人散套所做的评价。他继而则认为:“今人但知陈大声(铎)南调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与马致远《百岁光阴》,皆咏秋景,真堪伯仲;又[题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声钟》全套,亦绵丽不减元人;本朝词手,似无胜之者。”[3]202-203在沈德符看来,明人散套与元人散套基本类似,即除了马致远(元)、陈铎(明)等少数作家外,其余之作均难称“绝唱”与“高笔”,因之,无论是就其思想性抑或艺术成就而言,都是无以与这一时期的杂剧、令词媲美的。沈德符的这一认识,主要是着眼于北曲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因之,其无疑是颇符合元、明北曲发展之实况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沈德符对北曲的所“顾”之中,还表现出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即其大都是将所“顾”之北曲与南曲比较而为,如“弦索入曲”条之论弦索入南、北曲等,即属如此。在此条之中,沈德符之所以大论“弦索入曲”者,其本意旨在向世人强调弦索只能入北曲而不能用于南曲,所以,文中多次引顿仁的“不易之论”等,即都是将北曲与南曲比较所致,也即其意在通过南曲“不入弦索,不可入谱”的实况,以证实弦索是并不适用于南曲的。在“邱文庄填词”“时尚小令”等条中,沈德符之于北曲之所“顾”,亦是将其与南曲进行比较的结果,而《南北散套》则更是于条目中明白地标上了“南北”二字,以表明其所论之散套乃是南北互为的。此条所论之散套,就其次序言,乃是先元人“北调”,次为“今南曲”,再由《中原音韵》而“南词”而“吴中词人”,之后则是将元人散套与明人散套进行了比论,以针对“近代南词散套”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其“语意亦俚拙可笑,真不值一文”。比较的目的,主要在于辨明是非,判定甲乙,分出优劣,并能对其得失进行理性总结,而沈德符于此条中之所“顾”北曲者,其意亦正在于此。
三、《顾曲杂言》的南曲论
上引四库馆臣在为《顾曲杂言》所撰写的提要中,将《顾曲杂言》所“顾”之曲分为杂剧、北曲、南曲三类者,实际上是并不科学的。原因是《顾曲杂言》中的南曲,也有剧曲(传奇)与散曲(南散套)之分,前者如“拜月亭”“白练裙”“坛花记”等条目之所示,后者则多出现于“南北散套”“弦索入曲”“填词名手”“太和记”“北词传授”等条目之中。所以,准确的“南曲”之分,应是传奇(南戏)为一类,南曲(散套等)为一类。
《顾曲杂言》所“顾”之传奇,除“拜月亭”“白练裙”“坛花记”等条目外,另还有“张伯起传奇”“梁伯龙传奇”“太和记”等条目,这些条目所关涉之传奇,大都具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共同点,即其作者皆为“本”人,也即其皆为朱明时期的传奇之属。而在具体的述论中,沈德符则或着眼于“文品”的角度,指出某传奇所存在的严重缺憾,或立足于比论的角度,对同类作品进行优劣之品评等,认为其各不相同、各具特点。以前者言,“张伯起传奇”条即属于“文品论”的代表,如其有云:
(张伯起)共刻函为《阳春六集》,盛传于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亦今不行。[3]208
这是对张伯奇为李应祥作传奇“以侈其勋”的公开批评,指出其既“润笔稍溢”,又“不免过于张大”,因而认为所谓的“李应祥传奇”,实属张伯奇诸传奇中的一大败笔。后者则有“拜月亭”等条。如在“拜月亭”中,沈德符首先就何良俊与王世贞对《琵琶记》和《拜月亭》的不同认识进行了评判,认为王世贞谓《琵琶记》胜《拜月亭》者,实为“王识见未到处”。之后,则针对《琵琶记》与《拜月亭》之孰优孰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琵琶》无论袭旧太多,与《西厢》同病,且其无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则字字稳妥,与弹……胶粘,盖南词全本可上弦索者唯此耳。至于《走雨》《错认》《拜月》诸折,俱问答往来,不用宾白,固为高手;即旦儿[髻云堆]小曲,模拟闺秀娇憨情态,活脱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终不及也。[3]210
在沈德符看来,《拜月亭》远比《琵琶记》优秀,即其认为何良俊称《拜月亭》优于《琵琶记》者,乃为的评。
《顾曲杂言》所“顾”之南散套,主要见于“南北散套”“填词名手”等条。在“南北散套”一条中,沈德符除了论“北散套”之外,更多是对“本朝”作家之南散套的品评,如认为“今南曲如[四时欢][窥青眼][人别后]诸套最古”,“沈青门、陈大声辈南词宗匠,皆本朝化、治间人”,“章邱李中麓太常……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词之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侬见诮”,“吴中词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后起梁伯龙、张伯起辈,纵有才情,俱非本色矣”。所涉作家作品虽多(还有未及引录者),但据“俱非本色矣”五字可知,沈德符之于“我朝”南曲作家作品的品评,主要是着眼于“本色”而论的,这与其以“当行”“本色”评论本朝杂剧者,乃如出一辙,则其于“本色”之崇尚,仅此即可见其端倪。又,在“填词名手”一条中,沈德符认为:
我朝填词高手如陈大声(铎)、沈青门(仕)之属,俱南北散套,不作传奇。……南曲则《四节》《连环》《绣襦》之属,出于(成)化、(弘)治间,稍为时所称。……又郑山人若庸《玉玦记》,使事稳妥,用韵亦谐,内《游西湖》一套,为时所脍炙;所乏者,生动之色耳。……唯沈宁庵(璟)吏部后起,独属守词家三尺,如庚清、真文、桓欢、寒山、先天诸韵,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称度曲申、韩,然词之堪入选者殊鲜。[3]206
这段文字对“我朝填词高手”陈铎、沈仕、郑若庸、沈璟等人的南散套进行了品评,认为其虽然各有成就与特点,但从总的方面讲,却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为其评价最高的沈璟,“然词之堪入选者殊鲜”,即其散套“雅而不俗”,只能专供文人赏玩,而无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于陈铎,沈德符于《南北散套》中乃有专论,认为其散套“绵丽不减元人,本朝词手,似无胜之者”,评价甚高。
总体而言,《顾曲杂言》之论南曲,其审视的目光,虽然主要是放在“我朝”作家作品方面,但所评绝无阿谀之词,较为公允,如认为“南词宗匠”陈铎“俱南北散套,不作传奇”,被称为“独属守词家三尺”的沈璟,其南词却“堪入选者殊鲜”,如此等等,皆为明证。更有甚者,则是对一批“纵有才情”的吴中作家的散套提出批评,认为其“俱非本色”,而于“为时所脍炙”的郑若庸《游西湖》,则明确指出其“所乏者,生动之色耳”。凡此种种,均表明了沈德符对“我朝”南曲创作的关注。由是而观,则《顾曲杂言》板行之后,对于其时其后的南曲作家而言,应是不无启迪与影响的。
四、《顾曲杂言》错误举隅
《顾曲杂言》由于是辑自《万历野获编》一书,而《万历野获编》又是一部卷帙繁复、内容庞杂的野史之作,且其之所“编”,又多为沈德符“早年从祖、父听来的朝章故事,加之自己的其他见闻”[1]1,而不是取材于有关文献的记载,因之,其自然就会存在不少弊端与错误,而《顾曲杂言》亦应作如是观。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于《顾曲杂言》中的错误,《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为之所撰提要,已略有所指出:
其论元人未灭南宋以前,以杂剧试士,核以《元史·选举志》,绝无影响,乃委巷之鄙谈。其论《辽史·乐志》有大食调,曲谱讹作大石,因有小石调配之,其意以大食为国名,如龟兹之类,不知自宋已有此名,故王珪诗号“至宝丹”,秦观诗号“小石调”,不由曲谱之论。其论五六工尺上四合凡二,为出于宋乐书,亦未免附会。考南曲无凡二,上字有高下之分,宋时乐歌未必分南北曲也。如此之类,虽间有小疵。[2]1828
所言甚是。只是以“间有小疵”言之,则不的,盖因在《顾曲杂言》所收录之22条 “词曲”中,类似之“小疵”几近半数,且有的还较为严重。为便于对《顾曲杂言》错误之认识,兹举数例,以窥其一斑:
例子之一为“张伯起传奇”条。此条有云:“同时沈宁庵璟吏部,自号‘词隐生’,亦酷爱填词,至作30余种,其盛行者,唯《义侠》《桃符》《红蕖》之属。沈工韵谱,每制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诸书,欲与金、元名家争长。”按,沈璟为明代中期吴江派的一位领袖人物,以精通南曲之音韵与声律而闻名当时,并曾撰《南词全谱》《南词韵选》等专书以规范南词,对此,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吕天成《曲品》卷上等,均有记载。因之,沈璟“每制曲”者,是绝不可能“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诸书”而为的,原因是此二书皆为北曲、北韵之作。所以,《顾曲杂言》之此载,显然为沈德符所误记。
例子之二是“舞名”条。此条有云:“至若舞用妇人,实胜男子,彼刘、项何等帝王,尚恋戚、虞之舞。唐人谓‘教坊雷大使舞,极尽工巧,终非本色。盖本色者,妇人态也’。”按,此段文字为陈师道对苏轼豪放词之批评,语出《后山诗话》,所以,“唐人谓”应为“宋人谓”之误。而且“雷大使”即舞者雷大庆,也为宋人(具体参见《铁围山丛话》卷六),则唐人绝不可能“谓”宋人“雷大使”,如此,则知此载乃必误无疑。又,陈师道《后山诗话》的原文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能迨也”[5]。两相比较,可知沈德符之所引,并非《后山诗话》的原文,而是撮其大意而为。
例子之三是“俗乐有所本”条。此条有云:“又吴下向来有妇人打三棒鼓乞钱者,余幼时尚见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万不失一。”按,此处所言之“王文通”,当为王文举之误。据现存资料可知,最早记载“三杖鼓”者,为宋人陈晹《乐书》所载“唐咸通中,有王文举好弄三杖” ,明言为王文举。其后,明、清著述多转载之,如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十九即云:“今吴越妇女用三棒上下击鼓,谓之三棒鼓。……咸通中,王文举好弄三杖鼓打撩,万不失一是也。”[6]可见,应以王文举为是。
仅就所举三例而言,可知《顾曲杂言》在引书方面,乃是有欠严谨的。《顾曲杂言》既从《万历野获编》中辑出,则《万历野获编》之引书亦当作如是观。而此,即成为引录《顾曲杂言》者所应注意的。在《顾曲杂言》中,还存在另外一类错误,也是应引起读者注意的,即沈德符所作之结论,往往因前后矛盾而自说难圆。如在“弦索入曲”一条中,沈德符所反复论证的,是弦索只能入北曲而“不入南词”,但其于《拜月亭》中却又如是写道:“《拜月》则字字稳妥……盖南词全本可上弦索者唯此耳。”作为“南词全本”的《拜月亭》,既然“可上弦索”,则其于“弦索入曲”中认为“ 而弦索不入南词”的认识,也就与之互为抵牾而显得毫无意义了。这种错误的存在,其实是沈德符因顾此失彼而导致的。
注释:
①杂剧之于南方戏剧圈所形成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至大德(1279—1307)、元武宗至大(1308—1311)到元文宗至顺(1331—1332)、元顺帝朝(1331—1368)到明初。具体参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24-325页。
②关于弦索在唐、明之际的演变情况,具体参见拙作《究心与录载北曲的佳构——论李开先<词谑>的戏曲学价值》,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4期。
③关于[锁南枝]等为俚俗之曲者,可具体参见李开先《词谑·词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