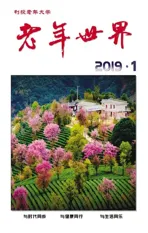回望乡村年味浓
2019-06-03孙虎原
孙虎原

腊月二十八,家族一行回乡。
眼前的故乡,已无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但我每年要回去。一来跪拜一下父母高卧的坟头,二来看看度过我快乐童年的这个村子以及所发生的变化。此乃多数国人回乡过年或祭祖的共同心情吧。
我们在老屋前下了车,提着供品和纸钱,徒步直奔家坟。望着熟悉而又陌生的蓝天白云山壑草木,忽然想起朋友描述他自己的一句诗来:
两鬓飞霜浑不见,一梦还是少年人。
如今,我已“两鬓飞霜”,且久居城市,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少年人”的记忆犹在,特别是那乡村的年味,酽得像牧民沏的砖茶,经口难忘——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热气腾腾,忙着自制过年的食品:做豆腐、压粉条、蒸馍馍、炸麻叶……我一边搭手搭脚地参与其中:团豆腐渣、端笼屉、取柴火、拉风箱;一边“近水楼台先得月”:豆腐出筐、粉条出锅后,母亲见我强咽口水,就切上半碗,捏撮咸盐滴点儿胡油让我拌着吃。
那时村上的人全住窑洞,黄泥皮又不瓷实,时间一长难免出现一些裂裂缝缝坑坑洞洞,我家也毫不例外。父亲从远处掏回一箩筐胶泥,再去饲养场铲一泡现牛粪。母亲挽起袖子用手将胶泥与牛粪拌匀,再倒上温水和成泥团,继而细心地涂抹到要修补的地方。屋墙上立马出现了大大小小不规则的“补丁”。待“补丁”干透,父亲拿出秋天就已扎好的草刷子蘸满白泥浆,先把“补丁”刷若干遍,再通体把墙皮刷两遍。待扫去犄角旮旯里的垃圾灰尘,把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擦抹干净,贴几张年画后,不但屋子的容颜变了,而且闻起来特别清新。
过年的前一天换窗纸,基本是固定日子。窗户是木头窗棂上粘一层麻纸,个别人家装两小块玻璃,能窗里窗外地看,很是新潮。糊窗纸这活儿,一般由女主人及姑娘媳妇们完成。先撕去又黑又脏又破的旧窗纸,再用白面煮成的糨糊把新麻纸粘上去,还要根据窗格的图案,衬映一些花花绿绿的剪纸或是从集市上买回来的窗花。窗户纸一换,屋子更加亮堂了。
贴对联不是站在窗台上就是站在凳子上,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多数由家中的成年男子来做,并且清除头一年的老对联,很费工夫。除了居室的门楣和窗框上要贴对联外,库房柴草棚牛羊圈猪狗窝都要贴,以图驱鬼避邪喜庆纳福。还有的人家在箱柜上贴个斗方,用上下连体的形式书写“黄金萬两”。就是“黄”的“八”字底做了“金”的“人字头”,“金”下面的“两点一横”又做了“萬”的“草字头”……这样的斗方,对于多数不识字的老乡来说,好像那是祈福的密码。
除夕,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清早,我把头天睡觉前放在枕边的新衣裳换上。所谓的新衣裳有时是把哥哥姐姐穿过的裁小,有时是新面旧里子。即使是旧料,经过母亲的浆洗,我就视其为新了。吃过早饭,我从炕席底取出鞭炮,小心地拆开线绳,把比筷子还细的红色或绿色鞭炮分解下来,放在空火柴盒装进衣兜,约上要好的同伴“跑大年”。村子比较大,常常是上午跑左半个村,下午跑右半个村,边看谁家的窗花鲜艳院子干净,边说笑嬉闹放鞭炮。最初我把鞭炮插在麻秆的空心口,在香火上点燃后斜举一侧,然后赶紧把头歪向另一侧闭上眼睛等待爆炸,心跳得快从嗓子眼窜出来。等响过多次后便消除了这种恐惧,敢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着炮屁股响了。也有用线吊起来、放在石头上、栽在雪地里,点燃后迅速抛出去多种响法。但很少有点一串连续响的,觉得那样太“浪费”。偶尔有“瞎捻炮”,总要猫着腰找回来,用缝衣针从炮肚上锥个孔,再穿上火药捻子响。还玩过“老婆打汉子”的游戏:把没捻子的鞭炮折成两段,截口与截口隔两指的距离对放,用香火头引燃其中一断,“哧哧哧”的火焰便把另一段引燃,膨胀气体迅疾喷出的反冲力,把鞭炮管反推得不知去向——老婆把汉子打跑了。
天终于黑下来,家家户户院子里挂起了或纸糊或玻璃罩着的煤油灯笼。孩子们藏头缩脑指指点点,因为乡村农家的院落一年四季黑灯瞎火的。只有大年夜,黄兮兮的灯笼照耀着黄兮兮的窑面子和黄兮兮的地皮,映着红彤彤的对联,伴着有近有远有大有小的爆竹声……说不清是神秘是浪漫还是圣洁。
过年是中华民族最盛大最传统的团圆节日,家人中如有在外做官经商耍手艺或其他事由的,总要尽力赶回来——仿佛是一种朝拜。年夜饭的餐桌上除了自产自制的,似乎不能少了鸡和鱼,图的是“吉庆”“有余”。鱼盘上桌时鱼头要朝向“一家之主”,并由其“剪彩”后别人才好动筷子。其实有威望的“一家之主”也并不先吃,往往是先挑一只鱼眼睛放到儿子或孙子媳妇碗里,表示“高看一眼”;再夹一片鱼鳍放在上班或上学的儿女碗里,表示“展翅高飞”;也有给年龄较大或较小的碗里送肥厚的鱼背肉,表示“备受关怀”……
吃过年夜饭,就进入难忘的除夕守岁。往日灶膛烧的是柴草,今天换成木头劈柴,也有的人家烧大炭。不管烧什么,灶台里的火不能灭。香炉里燃着的黄香青烟袅绕,缕缕如丝;主屋内红蜡烛的火苗子上下跳动,格外明亮——一派温煦祥瑞之气。妇女们开始包饺子,姐姐擀饺皮特别手快,能供得上两三个人包馅。只见她的上身一前一后,烛光投在白泥墙上的影子高低左右晃动。木擀杖与木案板轻碰发出木质的声响,很是动听。其余的大人们高高兴兴地唠嗑、听收音机、品酒、嗑瓜子、喝茶。我们左邻右舍的小孩凑到一起玩一些打扑克、抓石子、猜谜语、比糖纸之类的游戏。往往是这家玩一会儿再挪到那家玩,不管去到谁的家,大人一点都不嫌弃,还热情有加,让着吃这吃那,并腾出我们所要的活动领地。
凌晨三四点钟点旺火,俗称“接神”。因为在腊月二十三已将旧神送上天界,在新一年即将开始之时,要将新神接到家。农村不少院落在建造时,就在窑面子的中央垒砌了一个一尺见方的神龛,老乡叫“天帝窑”。这个空间或供奉某个神的牌位或贴一张全神像。接神时男主人要跪着敬黄表,嘴里念念有词。我家的旺火柴是父亲从野外砍回来的柠条,捆成比人还高的圆柱形,点起来火势强盛,照如白昼。这时全家人围在旺火周边响炮、取暖、说笑。大年夜,讲究的是灯明火旺、热热乐乐,寄托着人丁兴旺、家事顺达。
等旺火熄灭了,母亲已把“分年饺子”煮好。所谓“分年”即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嫩白嫩白的饺子挤在笨瓷盘里,圆滑得像一个个元宝。大家蘸着蒜泥米醋,就着豆芽和冷肉吃。饺子里包有镚子,有“谁吃出来谁好运”的说法。我怎么也吃不出来,哥哥姐姐们趁机取笑,母亲见我沮丧,就偷偷塞一个镚子到饺子里,假意到锅汤中捞一下直接倒进我碗里。我吃到镚子后洋洋得意,全家人笑声不断——后来我才懂得,这是一件“众人皆知唯我独愚”的事情。
从大年初一开始,大人们领着小孩走亲访友,互相拜年吃请。这期间一般只吃现成的年食品,忌讳生米生面下锅。总之是尽情地吃喝、尽情地玩乐——女人们不能裁剪缝补,男人们不能推碾拉磨……连院子里烧下的旺火灰堆,也就那样摊着,任人践踏,一派逍遥自在、什么都不管不顾的景象。
直到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才将屋里屋外清除一遍,把所有垃圾收撮到箩筐里,倾倒在村边路角,照样少不了敬表上香放炮,叫“送穷”。至此,过年的高潮告一段落,多项禁忌随之解除。
……
过年,起源于农耕先民,发展传承于广阔的农村以及宽敞的农家大院,主体是勤劳而且相对自在的农民。而如今,商品化、产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已与传统“农耕”相距甚远。当大家叹惜春节缺少年味时,先理智地透析各自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农耕”“农村”“农民”这些基本元素?不过,回想曾经的“年味”是值得的,那就从回想前辈们为了今天而含辛茹苦的历史吧——如此才会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