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看守人
2019-05-28亨利克·显克微支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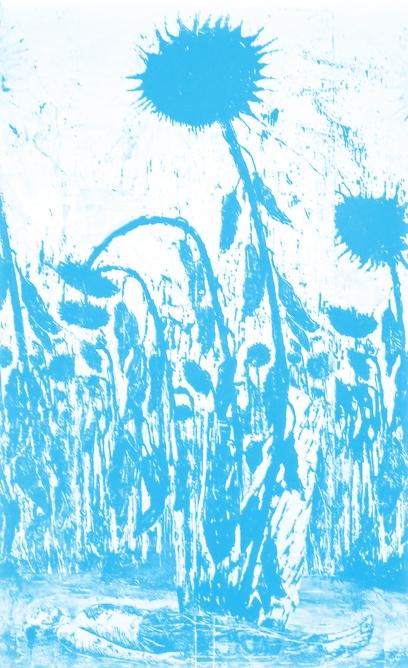
一
有一次,离巴拿马不远的阿斯宾华尔岛外的灯塔看守人忽然失踪了。因为他是在暴风雨发作的时候失踪的,所以大家疑心这不幸的人是行走在灯塔所在的那个石骨嶙峋的小岛边上,被一个浪头卷去了。到了第二天,一向系在山凹里的他的小船都找不到了,于是这种猜测似乎就格外近情。燈塔看守人的职位空了出来,这是必需赶紧补派的,因为这个灯塔,对于本地的交通,以及从纽约到巴拿马来的船舶,都极为重要。蚊子湾里又多沙碛和礁石。在这些碛石中间,白天行船已经很不容易;到了夜间,尤其是因为在这热闹的烈日所灼热的海面上常常升起浓雾,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时候,给许多船舶作唯一的向导的,便是这座灯塔。找一个新的灯塔看守人,这是驻巴拿马的美国领事的任务,而且这任务竟也不小:第一,因为绝对必须在十二小时之内物色到这样一个人;第二,这个人必须是非常忠诚小心的——因此当然就决不能把第一个来应征的人便贸然录用;而最后一个理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应征候补。灯塔上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它对于那些喜欢过懒散自由的放浪生活的南方人,可以说是毫无吸引力。这个灯塔看守人差不多就等于一个囚犯。除了星期日以外,他不能离开他这全是石头的小岛。每天有一条小船从阿斯宾尔岛上给他送粮食和淡水来,可是马上就开了回去。在这个面积不过一亩的孤岛上,再没有别的居民了。灯塔看守人就住在灯塔里;按照规律管理它。在白天,他悬挂各种颜色的旗帜来报道气象,在晚上,他就点亮了灯。他必需爬上四百多级高又高又陡的石级,才能到达塔顶上的灯边;有时在一日中还得上下好几回,要不是这样,这也就算不得艰苦的工作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僧人的生活,实际上还不止此,——这简直是一个隐居苦修者的生活。因此,无怪乎那领事艾沙克·法尔冈孛列琪先生非常着急,不知道打哪儿去找这么一个有耐性的继任人;而就在这一天,竟意想不到的有一个人来自荐继任此职,法尔冈孛列琪先生的快乐如何,也就很容易了解了。来者是一个老人,约有七十来岁了,但精神矍铄,腰背挺直,举止风度,都宛然是一个军人。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脸色黑得像一个克里奥尔人,但是看他那双蓝眼睛,可知他决不是一个南美洲人。他的脸色有些阴沉和悲哀,但却显得很正派。法尔冈孛列琪先生一眼就中意了他。只要盘问他一遍就成了。因此就有了底下这一番对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波兰人。”
“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做事?”
“做过好些事,没有一定。”
“可是一个灯塔看守人是要肯长住在一个地方的。”
“我正是需要休息啊。”
“你办过公事没有?有没有公职人员的证明文件?”
这老人就从怀里掏出一块褪色的绸包解开来,说道:
“这些就是证件。这个十字勋章是在一八三0年得到的。这第三个是法国勋章,我从卡罗斯党战争里得到的;这是第三个法国勋章;第四个是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此后我又在美国跟南方打仗;可是这一次他们没给勋章。”
于是法尔冈孛列琪先生拿起那张文件来看。
“哦,史卡汶思基?这是你的名字吗?哦!在短兵相接的时候获得两面旗。你真是个勇敢的士兵了。”
“我也能做一个忠诚小心的灯塔看守人。”
“做这件事要每天好几回爬上塔楼去的。你的腿够不够劲?”
“我就是靠两条腿穿过大平原走来的。”
“你懂不懂海事?”
“我在一条捕鲸船上做过三年事。”
“你倒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做过了。”
“我没有懂得的就只有一个‘安静了。”
“为什么?”
老人耸耸肩膀道:“这就是我的命啊。”
“不过我总觉得你去看守灯塔,似乎太老了。”
“大人,”这个应征者忽然神情激昂地说,“我已经流浪得很疲倦了。你知道,我做过的事情也不少了。这是我心里热烈想望着的一个位置。我现在老了,我要的是休息。我得对自己说,‘你得在这里待下去,这是你的港口了。啊,大人,这件事情全得仰仗你。倘到将来,恐怕不容易碰上这么个位置。现在我恰巧在巴拿马,这是多么运气!我求求你,看上帝的面上,我好比一只漂泊的孤舟,万一错过了港口,它就会沉没了。如果你愿意使一个老人得到幸福——我可以对你发誓,我是忠实的,但是,我已经厌倦这样的流浪了啊。”
老人的蔚蓝的眼睛里显示出一种真挚的祈恳的神色,使这位心地淳善的法尔冈孛列琪先生感动了。
“好吧,”他说,“我就录用你。你去做灯塔看守人吧。”
老人的脸上透出莫可明状的喜悦。
“谢谢你。”
“你今天就可以到灯塔上去吗?”
“可以。”
“那么,再会吧。还有一句话,万一有什么失职的情形,你就得革职的啊。”
“知道。”
当晚,当太阳在地峡彼端沉下,一个阳光辉耀的白天已经消逝,马上就接上了一个没有黄昏的夜晚,那新任的灯塔看守人显然已经就职了,因为灯塔已照常把明亮的光映射在海面上。夜色时分平静,是真正的热带景色,空中弥漫着澄澈的雾,在月亮的四周形成了一大圈柔和而完整的彩晕;大海只因潮水升涨而微有动荡。史卡汶思基立在露台上,从下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小黑点。他努力想收束他的种种思想,以接受他的新职位;但是他的心绪紧张得竟不能有秩序的思索。他此时的感觉,有些像一头被追赶的野兽,终于在人际所不能到的山崖或洞窟里,获得了藏身之处。他终于获得了一个安静的时期,安全之感使他满溢着说不出的幸福。现在,在这个小岛上,回想起从前种种漂泊,不幸和失败,简直可以付之一笑。他实在像一只船,帆樯绳索都被风暴所摧折,从云端里被抛入海底了——一只被风暴打满了风暴和水花的船,但它还是曲折前进,到达了港口。当他把这种风暴的情景,和如今正在开始的安静的未来生活相比较的时候,这种惊涛骇浪便在他心头迅速地一一映现。一部十分惊险的生活,他曾对法尔冈孛列琪说过了;但是此外还有无数的没有提起。原来他命运很坏,每当支起蓬帐,安好炉灶,正想做久居之计,便总有大风吹来,摧倒他的木桩,熄灭他的炉火,逼得他归于毁灭。现在从灯塔的露台上看着闪烁的海波,他想起了平生所经历的种种旧事。他曾经转战四方,而在流浪之中,又差不多什么事情都做过。由于热爱劳动和正直无私,他曾不止一次地积蓄过一些钱,但是尽管他能未雨绸缪,尽管他怎样小心谨慎,他的积蓄还总是分文不剩。他曾在澳洲做过金矿工,在非洲掘过钻石,又曾在东印度做过公家的雇佣兵。他又曾在加利福尼亚经营过一个牧场,——旱灾来破坏了他;他又在巴西内地与土人贸易,可他的木筏在亚马逊河上撞碎了;他孑然一身,手无寸铁,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在森林里流浪了好几个星期,采食野果为生,随时都可能葬送在猛兽的嘴里。后来他又在阿尔干萨斯州的海仑那城中开设一家铸铁厂,不幸碰上全城大火,他的厂也付之一炬。此后他还在落矶山里给印第安人捉去,幸而遇到加拿大猎户,仿佛是个神迹似的,把他搭救出险。再后,他在一只往来于巴希亚及波尔多之间的船上做水手,又到一艘捕鲸船上充当渔师,这两条船都是出事沉没的。他在哈瓦那开过一个雪茄厂,当他生黄热病的时候,被他的合伙者卷逃一空。最后他才来到阿斯宾华尔,或许这是他失败的终点了——因为这个石骨嶙峋的荒岛上,还有什么能来打扰他呢?水,火或人,全都扰他不到。但是从人这方面,史卡汶思基一生并没有受到过很多迫害;因为他所遇到的毕竟还是善人多于恶人。
但是在他看来,宇宙间地,水,火,风四种原行却仿佛都在迫害他。凡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的命蹇,于是解释他的种种遭遇,都以此为根据。到后来,连他自己也有些变成偏执狂了。他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而仇怨的手,在一切的陆地上或水面上到处跟着他。然而,他并不高兴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只有当人家问到他,这只手可能是谁的,他才神秘地指着北极星说道:“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的确,像他这样接二连三地失败,真是古怪得很容易逼死人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饱受过这些失败的人。但是史卡汶思基有的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坚忍,还有一种从心地正直里来的极大的镇静的抵抗力。从前他在匈牙利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因为不肯向人讨饶,不愿抓住人家意在搭救他非凡给他的鞍蹬,因而身上受了许多剑刺。他的不肯向忧患低头,也正是如此。他正如爬上一座高山,勤奋得像蚂蚁一样。虽然跌落了一百次,他还是安静地开始第一百零一次的攀爬。他真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人。这个老兵,不知经过了几次烈火中的锻炼,苦难中的磨砺,但是却还有着天真的童心。当古巴大疫的时候,他之所以害上黄热病,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许多奎宁丸完全施舍给病人,而自己不留一颗的缘故。
他还有这样一种卓越的品质——在许多失意之事之后,他还是满有信心,毫不失望,以为将来一切自会好转。在冬天里,他反而精神抖擞,还预言着未来的大事,整个夏季就在这些大事中过完了。但是冬季一个个的消逝,而史卡汶思基还是一无所遇,惟有头发却雪白了。终于他老了,渐渐地失去了他的精力;他的坚忍逐渐地憔悴下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在支配着他——那就是希望休息。这念头完全支配了老人,把他所有别的希冀和欲望全都吞没了。这个仆仆风尘的流浪人,除了想得到一角平安的地方,以静待天年之外,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宝贵,更值得希冀的事情了。或者,尤其是因为他被命运所驱策,流徙于天涯海角,使他忙碌得不遑喘息,于是以为人间最大的幸福,便只是不再流浪而已。这种菲薄的幸福,实在是他应该可以享受到的;但是因为他失意惯了,所以他的想望休息,正和一般人之想望一件绝不容易办到的事一样,因此他简直就不敢有此希望。如今在十二小时之内,他竟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好象有人替他从世间百业中挑选出来的职位。所以我们就无怪乎他在晚间点亮了灯之后,就好象目眩神迷,——心中自问着这究竟是不是真的,而竟不敢回说是真的了。但同时,当老人在露台上一点钟一点钟立下去,现实却给了他显著的证明。他呆看着,于是自己也相信其为真事了。他好象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大海。灯上的凸透镜在乌黑的海面上投射了一道巨大的三角形光亮,在这以外,老人的眼光所及,完全是远远的一片神秘而可怖的黑暗。但这遥远的黑暗好象在身着光亮奔来。长列岛腳下,于是喷溅着泡沫的浪脊,在灯光中闪耀着红光,也看得清了。潮水愈涨愈高,淹没了沙礁。大洋的神秘语声,清晰的传来,愈加响朗,有时像大炮轰发,有时像森林呼啸,有时又像远处人声嘈杂。有时又完全寂静;既而老人的耳朵里,听到了长叹的声音,或者也像一种呜咽,再后来又是一阵猛厉的大声,惊心动魄。终于海风大起,吹散了浓雾,但却带来了许多破碎的黑云,把月亮都遮没。西风越吹越紧,海涛怒立,冲激着灯塔下的石矶,水花直舐着基墙。这是有一场风暴在远处开始发作了。昏黑而纷乱的海面上,有几点绿色的灯光正在船桅上闪烁。这些绿点儿正在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飘摇不定。史卡汶思基走下塔顶,回到自己的卧室里。风暴开始咆哮了。在塔外,船里的人正在与夜,黑暗及浪涛相斗争;而塔内却是安逸与平静。便是风暴的吼声也不能侵入这坚厚的墙壁,只有单调划一的时钟滴答声,在诱使这个疲倦的老人颓然入梦。
二
一个小时又一小时,一日又一日,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航海者都说,当海上风暴大作的时候,常常听到黑夜中有呼唤他们名字的声音。如果这大海的幽冥能够这样呼唤,那么当一个人老起来的时候,或许在另外一个更黑暗更神秘的幽冥中,也会有呼声来召唤吧;一个人愈厌倦于生活,便愈觉得这些呼声的亲热。但是如果要听到这些呼声,就需要安静。况且,老年人大概都喜欢离群独处,好象先已有了入墓之感。对于史卡汶思基,这座灯塔也就一半等于坟墓。没有比灯塔上的生活更单调的了。倘使有年轻肯来担任这个职务,他们一定会随即就跑掉的。所以看灯塔的大都不是年轻人,而且还是些忧郁好静,不涉世务的人。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偶尔离开灯塔,身入人丛,他总是踽踽独行,好象一个酣睡初醒的人。在普通的人生中,有种种细密的观感会指示人们去适应一切世事,但灯塔上并不具有这种观感。一个灯塔看守人所能接触的,惟有一片苍茫高远的海天,漫无圭角。上面是浑然的天,下面是浩然的水;而这个人的心灵便孤独地处于这二大之间。在这种生活中,所谓思想,简直就只是不断地默想。而且也没有一件事情能把这灯塔看守人从默想中警醒过来,即使他的工作也没有这能力。今天与明天完全一样,正如串索上的两颗念珠,只有天气的变换,总算形成了惟一的不同。但是史卡汶思基却觉得这是生平最幸福的生活了。
他黎明即起,早餐后,揩抹好灯上的凸透镜,于是坐在露台上,远望海景;他的眼睛永不厌倦当前的景色。在这浩大的蓝宝石似的洋面上,总看得见有好几群饱满的风帆,在阳光中闪耀,明亮得使人目眩。有时,还有许多船只,趁着所谓贸易风,排着长长的队伍,鱼贯而来,好像一串海鸥或信天翁。红色的浮筒在微波上徐徐漂荡。每天午后,总有好多浅灰色的像鸟羽似的烟,一阵一阵地从帆篷中间升起。这便是从纽约载了客人和货物到阿斯宾华尔来的轮船,航程所过,船后的浪花,曳成一条泡沫的路。在露台的那一边,史卡汶思基可以看见阿斯宾华尔全市及其忙忙碌碌的港口,港中帆樯林立,舢舻相接;再远些,便可见城中白色的屋宇及高耸的塔楼,都了如指掌。从他的灯塔顶上看来,那些小屋子就宛如海鸥的巢,船舶都如甲虫,而人在白石的大街上行走,却像点点的黑子。清晨,和缓的东风吹来了一阵喧哗的市声,其中以轮船的汽笛声最为响亮。到午后六时,港中一切动作渐次停息下来,海鸥都躲进岩穴里去;波浪渐渐衰弱,好像有些懒倦了;于是在陆地上,在海上,以及在这灯塔上,一时都归于寂静,不受任何喧扰。波浪退落之后,黄沙滩闪着光,在这汪洋大水上,宛如一个个金色的斑点;塔身在蔚蓝的天宇中,显得轮廓分明。一道道的夕阳从天空中照射在水上、沙滩上和崖壁上。这时候,便有一种十分甜蜜的疲倦侵袭了这老人。他觉得现在所享受的休息真是最美妙的;当他一想到这种美妙的休息可以尽他继续享受下去,便觉得心满意足,毫无缺憾。
史卡汶思基给他自己的幸福陶醉了;而且,因为一个人对于改善了的境况很容易满足,所以他渐渐地有了信仰与希望;他心想世上既有人为残废人造屋,那么上帝为什么不终于也收容了他这个残废人呢?一天天的过去,他对于这种思想愈加坚信了。这老人对于他的灯塔、灯、岩石、沙滩和孤独的生活,都已渐渐熟悉。而且他对于那些巢居于岩穴中的,每到薄暮时便飞集到塔顶上来的海鸥也熟悉了。史卡汶思基常常将残余的食物丢给它们,不久它们都驯服了,此后每当他给它们喂食的时候,便有一大阵白翅在他周围飞扑,于是老人在这些海鸟中间走来走去,正如牧人在羊群中间一样。退潮的时候,他便走到沙滩低处,拾取潮汐所遗留下来的美味的玉黍螺和绮丽的鹦鹉螺。月明之夜,他便到塔下去捕捉那些常常成千累万地游到岩曲里来的鱼。后来,他竟深爱着这些石矶和这个小岛了。这小岛上并无树木,只是到处生着许多分泌出粘脂来的丛莽,但是远景甚美,尽足以给他弥补缺憾。下午,如果空气非常清朗,他可以看见那林木茂翳的整个地峡的全景。在这种时候,史卡汶思基就好比看到了一个大花园,一丛丛的椰树、巨大的芭蕉,夹杂着像一个个华丽的花束,纷纷披于阿斯宾华尔万家屋宇之后。再远一些,在阿斯宾华尔及巴拿马之间,还有一个大森林,每天清晨及薄暮,都有蒸气升腾在这上面,凝结成一重红雾。这个森林脚下积着死水,上面缠绕着古藤老蔓,无数巨大的兰草、棕桐、乳汁树、铁树、胶树充斥其间,发出一片林海的声音;这是一个真正的热带森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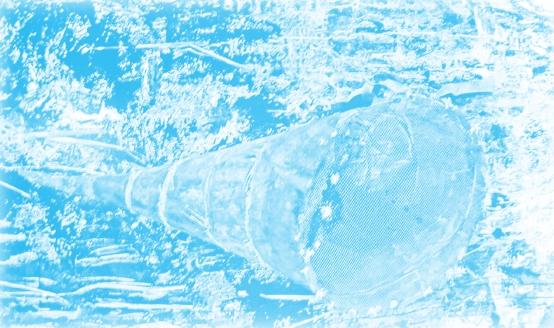
從望远镜中,老人非但能看见这些树木和阔大的香蕉树叶,他甚至还能看见成群的猿猴和巨大的鹳鹤,还有鹦鹉,不时成群地飞起,竟像一曲彩虹围绕在这茂林之上。史卡汶思基对于这种树木很为熟悉,因为他在亚马逊河上碎舟之后,曾在类似的林莽流浪过好几个星期。在这种外表奇丽可亲的树林中,他看见有不知多少危险和死亡隐伏着。在夜间,他曾听到过附近有猿猴哀号,猛虎怒吼,又曾看见过蟒蛇像藤蔓一般缠绕在树身上;他还知道在这种沉寂的森林中的沼泽里,充满了电鱼与鳄鱼;他又知道在这种未开垦的荒野里,人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在这地方,就是一片树叶,也比人大上十倍——总之,这是个充满了吸血的蚊虫、水姪和巨大的毒蜘蛛的荒野。他因为对这种树林生活有过经验。亲眼看见过,亲身遭遇过;现在他能够从高处远眺这些荒野,欣赏它们的美丽,而自身不会受到它们的危害,因此就使他觉得格外快乐了。他的灯塔给他以万全的保护。只有在星期日,他才离开它几小时。那时他穿上了银钮扣的蓝色制服,胸前挂上了他那些勋章。当他走进教堂门的时侯,他听见那些克里奥耳人都在窃窃私语道:“我们有了一位可敬的灯塔看守人了,他虽则是个洋鬼,却不是个异端”。老人听了这话,昂起了他的乳白色的头,不免有些傲色。做完弥撒,他立刻就回到他的小岛上去,而且心中非常愉快,因为他对大陆还不很放心。在星期日,他还在城里买了西班牙报纸来看,或者向领事法尔冈孛列琪先生那里借看《纽约先驱报》;在这些报纸上,他急切地寻找着欧洲的新闻。所以这可怜的老人的心,虽然在灯塔上,却一直在怀念他那在另一半球上的故乡。有时,当供给他每天粮食饮水的小船来时,他也下塔去和港警约翰生闲谈。但后来他好像有些害羞了。他不再进城去看报,也不再下塔来跟约翰生谈政治了。这样地过了好几个星期,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他也不见一个人。放在岸上的食物,过一天就不见了;灯光也仍旧每晚都照耀着,正如旭日每晨从这一片海面上开起来一样地准时不爽;只有这两件事情,表示老人还住在这个塔上。显然这老人已对于人世很淡漠了。但这也不是因为怀乡之故,而是由于,他连怀乡之心都已经渐渐消失了。对于史卡汶思基,这小岛就是他整个的世界了。久而久之,他就惯常地这样想,他将一辈子都不离开这个灯塔了,因为他简直已经记不起,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些什么。甚至,他竟变成一个神秘的人,他那双温和的蓝眼睛开始像小孩的眼睛一般呆望着,好像看定了远处的一个东西似的。当着四周这些异常单纯而伟大的景色,这老人已消失了他的一己的感觉;他的存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逐渐与周围的云天沧海溶为一体了。如果间他的周围之外还有些什么,他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只是无意识地有些感觉而已。最后,他就仿佛这些天、水、岩石、塔、黄金色的沙滩、饱满的风帆。海鸥、潮汐的升降——全都化合做浑然一体,成力一个巨大的神秘的灵魂;而他仿佛就沉役在这个神秘中,感受着这个自动自息的灵魂。他沉没在这中间,任其摇荡,恬然自忘其身;于是在他的逼仄的生命中,在这半醒半睡的状态中,他发现了一种伟大得几乎像半死的休息。
三
但是惊醒的时候来了。
某一天,小船送来了淡水和食物,一小时后,史卡汶思基从塔上下来,看见平时照例的那些东西之外,还多了一个粗布包裹。包上贴着美国邮票,写着“史卡汶思基大人收。”
老人满心奇怪地解开包裹,见是几本书;他拣起了一本,看了一看,随即放下;于是他的手大大地颤动起来。他遮掩着眼睛,好像不信似的,仿佛在做梦一般。原来这本书是波兰文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又是谁寄来的?起初,他分明已经忘记了当他初来做灯塔看守人的时候,他曾从领事那里借看《纽约先驱报》,看见报上载着纽约成立了一个波兰侨民协会,于是他立刻捐助了半个月薪俸,因为他在塔上没有什么用度。那协会里就寄赠他这几本书,以表示答谢。这些书来得并不奇突,但是老人起先却没有想到。在阿斯宾华尔,又是在他这个灯塔上,在他孤寂的时候,却来了波兰文的书籍,——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一种非常的事情,一种从古昔发出来的声息,一种神迹。现在,正如那些水手在夜里一样,他好像听见有人用很亲爱的,可是几乎已经忘却了的声音叫唤着他的名字。他闭目静坐了一会儿,几乎要以为如果把眼睛一睁开,这梦境就会立刻消逝了。
包裹摊开在他面前,被午后的阳光照得清清楚楚,这上面的一本已经翻开了。当老人伸出手去想再把它拿起来的时候,他在寂静之中听见了自己心房的跳跃。他一看,这是一本诗集。封面上用大字印着书名,底下印着作者的名字。这个名字对于史卡汶思基并不陌生;他知道是一个大诗人的名字,他曾经在一八三O年在巴黎读过他的著作。后来,从军于阿尔及利亚及西班牙的时候,他曾经从自己本国人那里听到过这位大诗人的正在日益高扬的名字;但那时他却忙于打枪,身边简直不带一本书。一八四九年,他来到美洲,在流离颠沛的生活中,很难遇到一个波兰人,至于波兰文的书,更是一本也没有看到过。因此,他以更大的热枕,心房也跳得更活泼,翻开了第一页。这时他好像在这孤岛上,将要举行什么庄严的典礼了。实则,此刻正是很静穆的时候。阿斯宾华尔的大钟,正在鸣报下午五时。无宇清朗,净无云翳,只有几只海鸥在空中盘旋。大海好像在摇摇欲睡。岸边的波浪,都在唱唱低语,轻轻地漫上沙滩。远处阿斯宾华尔的白色房屋及离奇古怪的棕榈树丛,都好像在微笑。的确,这时候那小岛上真有一股神圣、肃穆、庄严的气氛。忽然,在这大自然的肃穆中,可以听到那老人的颤抖的声音,他正在高声吟诵,好像这样才能对他自己有更好的了解——
你正如健康一样,我的故乡立陶宛!
只有失掉你的人才知道他应该
怎样看重你,今天,我看见而且描写
你的极其辉煌的美丽,因为我正在渴望你。
到这里,他读不出声了。文字好像都在他眼前跳跃起来,仿佛心坎里有什么东西在爆裂,像波浪似的从他心头渐渐地汹涌上来,塞住了他的喉咙,窒息了他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勉强镇定下来,再读下去:
圣母啊,你守护着光明的琛思妥诃华,
你照临在奥斯脱罗孛拉摩,又保佑着
諾武格罗代克城及其忠诚的人民,
正如我在孩提的时候,我垂泪的母亲
把我交托给你,你曾使我恢复了健康,
当时我抬起了奄无生气的眼睛
一直走到你的圣坛,
谢天主予我以重生——
现在又何不显神迹使我们回到家乡。
读到这里,心如潮涌,不能自制。老人便哽咽起来,颓然仆地;银白色的头发拌和在海砂里。他离开祖国,已经四十年了;不听见祖国的语言,也已经不知多久,而现在这语言却自己来找上他——泛越重洋而到另一半球上访他于孑然独处之中,——这是多么可爱可亲,而又多么美丽啊!使这位老人站在那里哽咽不止的,并不是什么苦痛,——而只是一种油然而起的博大的爱心,在这种爱心之前,别的一切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他只以这一场伟大的哭泣来祈求热爱的祖国给他以饶恕,他的确已经把祖国丢在一边,因为他已经这样的老,而且又住惯了这个孤寂的荒岛,所以把祖国忘记得连怀念之心都在开始消失了。但是现在,仿佛由于一个神迹似的,它竟回到他身边来,于是他的心就跳跃起来。
过了好久,老人还躺在那里。海鸥在灯塔上空飞翔呼叫,好像在惊醒它们的老友,该当是把残食喂伺它们的时间了;所以,有些海鸥便从灯塔顶上飞下来,渐渐地愈来愈多,开始在地上啄着寻食,或是在老人头上拍着翅膀。这些翅膀的声音惊醒了他。他已经哭了个痛快,这时才得宁静与和霁;但他的眼睛却反而神采奕奕。他不知不觉地把所有的食物都丢给这些海鸟,海鸟便呼噪着冲上前来争食,他自己却又取起那本书来。夕阳已经沉到巴拿马园林背后,正在徐徐地向地峡外降到一个大洋上去;但是大西洋上还很光亮;室外尚能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便读下去:
现在请把我渴望的心灵带到那些
山林中,带到那些绿野上去罢。
终于,短如一瞬的暮色沉下来,遮隐了白纸上的文字。老人便枕首于石上,闭着眼睛。于是那“守护着光明的琛思妥诃华的圣母”便把他的灵魂送回到那一片“被各种作物染成彩色斑斓的田野”上。天上还闪耀着一长条一长条金色和红色的晚霞,他的灵魂便乘此彩云,回到挚爱的祖国,耳朵边听到了祖国的松林在呼啸,溪流也在淙淙私语。他看一切风物,都宛然如昔;一切都在问他:“你还记得吗?”他当然记得的!他看见了广大的田野,在这些田野之间,便是森林和村庄。这时无已入夜。平时在这时候,他的灯总已照耀在黑暗的海面上了;但是此刻他却正在祖国的村庄里。他的衰老的头俯在胸前,他正在做梦。种种景色,稍微有些纷乱地,都在他眼前很快地闪过。他没有看见他所诞生的屋子,因为已经给战争毁了;他也没有看见他的父母,因为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侯,他们已经死了;但是村子里的景色,还依然如旧,好像他还是昨天才离开的,——整整齐齐的一排茅屋,窗子里都透着灯光、土阜、磨房、相对的两个小池塘,通夜暄闹着蛙鸣。有一回,他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担任全夜守卫;现在,当时那些景象,又立刻历历呈现在眼前。一会儿他又是一个枪骑兵了,他正在那里站岗;远处便是一家小酒店,他不时向那里溜一眼。在夜的寂静中,可以听到喧哗、歌唱和叫喊的声音,还有呜呀呜呀的小提琴和低音四弦琴的声音。后来那些枪骑兵都上马疾驰而去,马蹄在石上踢出火星来,而他却骑马独自立在那儿,疲倦得很。时间慢慢地过去,终于人家的灯火都熄灭了;现在,眼光所看得到的她方,尽是一片迷蒙;已而浓雾升起,显然是先从田野里开始,如一片白云包裹了大地。你可以说,这简直是一片海洋。但这实在是田野;不久你就会得在黑暗中听到秧鸡啼声,而芦苇丛中的白鹭也会叫起来了。夜色很平静,很冷——一个真正的波兰之夜!在远处,松林正在无风而自响,宛如海上的涛声。东方快发白了。真的,鸡已在篱落间啼起来,一家家的互相应和着;天上已经有鹳鸟在飞鸣而过。这枪骑兵觉得精神很爽快。有人曾经讲起过明天的战争。嗨!这将是像别的一切战争一样,挥着枪旗,呐喊着,厮杀上去的呀。青年人的血,尽管为夜寒所冻,却还如号角一般地在响着。但天已渐明,夜色逐渐衰淡下去;林树、丛莽、村庄、磨坊以及白杨,都已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井上的辘轳正在像塔楼上的金属旗那样吱吱地响。在鲜红的晨曦中,这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的国土呀!啊,这至爱的国土,这唯—的国土!
别做声!这守望着的哨兵听见有脚步声在走近来。一定是有人来换班了。
忽然,有人在史卡汶思基头上喊道:
“喂,老头儿!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睁开眼来,吃惊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人。残余的梦景在他头脑里和现实斗争着,终于是这些梦景由模糊而至于消失。在他面前,站着的是港警约翰生。
“怎么啦?”约翰生问,“你病了吗?”
“没有。”
“可是你没有点灯。你得免职了。一条从圣吉洛谟来的船在海滩上出了事,亏得没有淹死人,要不你还得吃官司呢。跟我一道上船走吧,其余的话,你会得在领事馆里听到的。”
老人脸色惨白;当夜他的确没有点灯。
几天之后,有人看见史卡汶思基在一条从阿斯宾华尔开到纽约去的轮船上了。这可怜的老人己经失业。新的流浪的旅途又已展开在他面前;风又把这片叶子吹落,让它飘零在无涯海角,簸弄着它,直到快意而后止。这几天来,老人大大地衰颓了,腰背伛曲了下来,惟有目光还是很亮。在他新的生命之路上,他怀中带着一本书,不时他用手去抚摸它,好像惟恐连这一点点东西也会离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