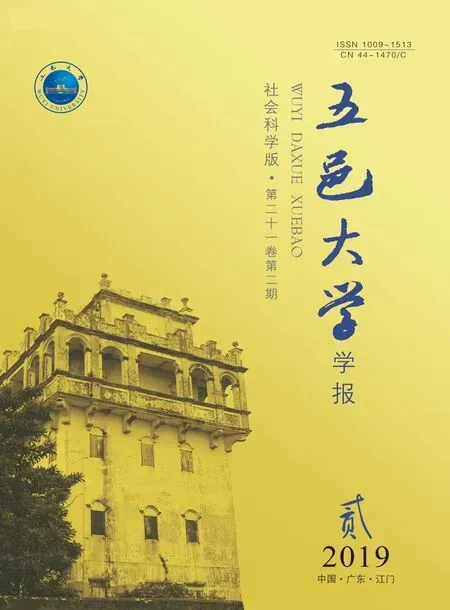半为怀人半自怜
——从《仲氏闺秀集》看明清扬泰地区女性文学创作的情感特质
2019-05-17贺闱
贺 闱
(泰州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半为怀人半自怜”之句出自广陵女史赵笺霞的《寄两妹》一诗,其《辟尘轩诗钞》亦收录于仲振奎所编《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五 附二种》①(下文简称为《仲氏闺秀集》)。这一感喟不仅是女诗人对于自身文学创作情境和人生经历的剖白,也明显体现出《仲氏闺秀集》中女性文学创作在题材内容和情感内涵等方面的特征。《仲氏闺秀集》是一部家族性的女性诗歌合集②,其中所收录的作品在创作方式和内容表现等方面均具有较为集中的家族内向型发展特征,女诗人们在诗歌中描写出对家人、亲友的思恋和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刻画了对自身生活情状和生存处境的真切感受。本文试以“怀人”和“自怜”两个层面为《仲氏闺秀集》诗作研究的路径,通过文本解读和作品分析,讨论仲氏闺秀文学创作情况及其艺术风貌,进而呈现明清时期扬泰地区女性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与特征,力图实现对明清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的深入考察。
一、“怀人”念远——《仲氏闺秀集》的主要描写内容
仲氏家族的女性诗歌创作,主要是指以清代乾嘉时期泰州仲鹤庆为家族中心者的女性文学创作情况,主要包括其妹仲莲庆、其女仲振宜和仲振宣、其子妇赵笺霞与洪湘兰以及其孙辈仲贻銮、张贻鷮等七位女诗人③,仲鹤庆之子仲振奎将她们的作品结为《仲氏闺秀集》。仲氏闺秀的诗作,主要表达对家人、亲友的思念之情和对故乡、团聚的期盼。女诗人通过描绘与父母、手足、夫妻以及子女之间的深挚亲情和浓郁天伦,体现出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女性的生存境地和情感空间。她们多是从日常生活的某一场景或情境入手,围绕家庭生活、家族成员进行具有感情寄寓的描述与刻画,展示出传统女性的生活日常和情感世界,也表现出闺秀笔下较之于男性文人更为细致生动的体会和情绪,透露出知识女性温和善良、敦厚通达的气质特点。
《仲氏闺秀集》中直接以“怀”为题来表达对亲人思念的诗歌,就有仲振宜《月下怀兄弟姐妹》《怀父》《怀母》《怀云磵大兄》《怀书云姊》《怀芝云三妹》《怀云江六弟》《怀云浦七弟》、仲振宣《怀芗云二姊》《再怀二姊》、赵书云《怀绮泉二妹》《再怀绮泉》《怀锡之二弟》等多篇作品。仲氏闺秀还常以“书”“思”“寄”等语词来传递对于亲友、家人的牵挂与思念,尤其是在遥和、寄赠一类的诗作中,此种情怀的表达更为明显,如仲莲庆作有《寄二弟蜀中》《寄怀二弟时闻罢官消息》,仲振宜写有《寄呈姑母》《将归外家呈两大人》《寄怀云磵大兄》《月下思家》《盼云磵大兄不至有作》《寄怀云江六弟》《寄怀云浦七弟》《寄芝云》,赵书云创作了《寄两妹》《寄绮泉二妹》《寄外》等诗作,都传递出真挚动人的思念情怀。以笺霞《寄外》诗为例:
百里未云别,高怀且自由。诗书能快意,风雨漫牵愁。
夜读休伤酒,春寒莫典裘。萧条家室虑,瓶绠自能筹。
诗中并没有直接描绘别离之时伤心摧肝的场景,而是以“未云别”的轻淡笔触起篇,写出了在“外子”(仲振奎)读书仕宦生涯中别离的寻常与普遍,将女性深幽的情思隐藏在了对分别的轻描淡写之中。作为知识女性来说,“诗书”固然能够提供人生的快乐与慰藉,但风雨之夕,思及分离的愁苦及自身的孤独情形,怎能不令女诗人内心感慨、引动愁绪。这首诗歌尤为难能可贵之处,是出于女性的笔端但不见哀婉之态、不闻怨苦之辞。在淡淡点染别离后忧愁、孤寂的情绪之外,赵书云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传统女性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诗的后半段,转而宽慰远人要善自珍重,“夜读休伤酒,春寒莫典裘”两句可以说是糅进了女诗人的百转愁肠、万般情思,想到丈夫因为夜读书而忽视了对身体的保重,想到丈夫可能因爱书嗜酒、典当衣物市之,从而难以抵御料峭的春寒,笺霞(赵书云字笺霞)如何不对“外子”远行离家的异乡生活充满忧虑与牵挂?末句以家中生计虽已“萧条”、但尚能“自筹”为安慰,请丈夫不必为“家室虑”,则体现出传统文化之下女性美好的品质与美德。总体而言,这首诗歌以“寄外”写思夫怀远,而笔调细致、淡远,情真意切,深挚动人,体现出传统文化浸润之下知识女性善良敦厚的美好品德和情深意笃的文学特质。
在仲氏闺秀的诗歌创作中,“怀人”主题的呈现是多样化的。她们不仅有如上述诗作的直接抒写,也常通过节日场景来具体构建对家人、故乡以及安宁平和生活的向往。如仲振宜的《元夜思乡》一诗:
辗转愁怀滞海滨,雨中佳节病中身。虚房睡起添离感,故国灯围忆老亲。
梦里关河虽有路,春来鱼雁总无因。不知此夕团圞酒,几度停杯念远人。
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远,诗中开头以“愁怀”和“佳节”构成了强烈的比照,通过对自身漂泊情状的简笔勾勒,即凸显出女诗人多愁多病的状况与风雨萧瑟“海滨”的滞留处境。病中睡起,在一盏孤灯之下回忆起当年与家人的融融天伦之乐,徒有一室冷清的“虚房”,怎不令人更为感慨此时的离索与孤寂。前两联中情景相生、虚实结合,诗人对于家乡、亲人的思念得到了较为深入、生动的描绘,然而囿于现实境遇,虽思乡而不得归、虽怀亲而不得近,个中沉郁情思被鲜明地展现了出来。第三联中的“关河”“鱼雁”是女诗人情感的外化与寄托,却仍然化为“无因”的虚妄期盼,最后只能将内心郁结的情思托付给想象:是不是家中的亲人在今夜齐庆团圆、举杯共饮之时,也会牵挂远在他乡、孤单飘零的自己呢?结尾一句“几度停杯念远人”,看似疏慰了前文无奈与悲苦之音,但这只是出于作者的想象罢了,虚妄与现实的明显对比更加显现出怀人、思乡之情的不可消解,反而将深沉的感情又翻上一层、深入一层。仲振宜另有《将归虎阜志别》《冬夜月下思家》《春夜作》《春日自遣》《海上午日》等诗作,亦是通过此类手法来表现“怀人”的主题,尤以《和芝云三妹韵》一篇为集中和沉恸。在这首写给胞妹仲振宣的作品中,女诗人以对“团圞”之乐的期待来抵消心中“百事苦无成”的伤感之情,用一家团聚的“至乐”场景来宽慰内心“万种离怀”的沧桑感喟。除绮泉女史(仲振宜号绮泉)外,仲莲庆的《旧日有感》一诗、赵笺霞所作的《除夕》《清明雨》《立春》诸篇以及洪湘兰《上元对月偶成寄外》、仲贻銮《邗上中秋和家严韵》、张贻鷮《立春前二日雪》等诗作皆是以对亲人、家园、故乡的思恋来表达出“怀人”的情感和思绪。正如仲振宣《怀芗云二姊》诗中所言“情多令节增长恨,诗到分题几怆神”,节令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和空间场景更能触动女诗人或远离亲故、飘零自叹的心绪,抑或是因亲友远行而引发望人盼归的情思,仲氏家族的女性诗人将自身真切的感受和深挚的情感融合于节日等独特的场域之中,愈加突出了“怀人”念远内容主题的真挚、动人。
二、“自怜”“薄命”——《仲氏闺秀集》的主体情感构成
仲氏闺秀的诗歌创作,在内容方面具有“既定的社会角色和局限的生活空间致使女性很少关注国家社会的历史变故,也很少有男性文人那样远大的政治抱负,写作一般不拈大题目,多写家庭伦理与日常生活场景,字句里流露着浓浓的亲情”[1]的主要特点,她们所描写的感情意蕴涵盖了父(母)子、夫妇、手足、师友等各个层面,尤其以“怀人”念远、希冀团圆安定的层面最为突出。同时,在《仲氏闺秀集》中,女性在描绘自身生活境况与情感诉求时,则相对地具有“私人写作”和自我化的特征,这种情感特质最突出也最为鲜明,展示了仲氏女性诗歌中自叹“薄命”的主体情感。
学者方雪梅在论及江苏女性诗歌写作的总体特征时指出,江苏女性的诗歌写作中“满蓄着薄命意识”[2],并从婚姻不幸、寡居情状及生活贫困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通过对《仲氏闺秀集》中有关“薄命”抒写作品的总览即可发现,仲氏女作家在上述的共同面貌之外,展示出了因自身病苦、生计劳顿和飘离难归等更为具体而深重的内涵。在仲氏闺秀的诗作中,“薄命”的自我定位和情感述写表现在诸多篇什中,诗歌中直接以“薄命”“命薄”来表述怨艾、哀婉之情,就有近20首(见表1):

表1 《仲氏闺秀集》中的“薄命”之语
仲氏闺秀在诗歌中所述写的“自怜”“薄命”,涵容了传统社会环境之下女性自我身份与社会生活所面临的诸多层面,又在此基础之上融入了才女的细致情思和深沉心绪。《仲氏闺秀集》中,女诗人也常常通过如“愁”“怜”“病”“苦”等语词来进行此种情绪的表述,仅以表2简单列举:

表2 《仲氏闺秀集》中“薄命”类情绪的表述
在这些诗歌作品中,仲氏闺秀对“自怜”“薄命”的身份定位和情感特质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对于传统文化之下女性的生活情状、生存状态予以了深入、细致的表现。需说明的是,《仲氏闺秀集》中涉及因别离而产生“薄命”感慨的作品,如仲振宜《寄芝云三妹》《早春自感》《怀云磵大兄》《海上午日》《梦中诗》、仲振宣《怀芗云二姊》及赵笺霞《寄绮泉二妹》)等诗,因前述“怀人”内容时已有所涉及,故此处将主要从仲氏闺秀诗作中因自身境况、家庭生活而生发“薄命”“自怜”感喟的两个层面进行简要讨论。
首先,“薄命”之感体现在女诗人对于自身“一身多病百愁牵”(赵书云《怀锡之二弟》)的感慨中,如仲莲庆《自叹》《九日有感》《雪》《病中作》等诗、仲振宜所作《寄书云大嫂》《元夜思乡》《述怀》《春日自遣》《寄怀》《怀芝云三妹》《怀云浦七弟》等,还有仲振宣的《上元》《再怀二姊》《长歌行》以及赵笺霞的《秋思》《寄瑶泉三妹》《春归自遣》《怀锡之二弟》等诗作都是此种情绪的述写。其中描写最为直接、现实性强烈的当属仲振宣的《长歌行》,诗作以“幼长名家”“一门风雅”起笔,写出早年较为优游、娴雅的书香生活;然而随着出嫁张祥风,“家业既尽,逋欠大哗,弃产卖屋不足以偿”的贫窘困苦逐渐侵袭向瑶泉女史(仲振宣号瑶泉女史),女诗人本自多病:“昔予抱病心怦怦,时作时止如悬旌。沉疴日痼不可药,四肢皴裂肤如黔。手爪拳曲鬓发秃,衣不能整带难束。攀树空餐范女花,此身虽存如朽木”,加之“去年颓废卧空床,三月不起神羸尪”,她愈加哀叹病体难支、甚而表现出“生死茫茫且听天,知在何时抛世事”的悲观消极心理,将病痛折磨之下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感受刻画得真实、深刻,“薄命”而“自怜”自叹的悲吟由衷而发。
其次,“薄命”之感体现在仲氏家族女作家对于婚姻、家庭生活“可堪天意不怜人”(仲振宣《秋怀》)等落寞之辞的哀叹中。《仲氏闺秀集》中所收录七位女诗人的具体生平、经历虽已难以确纪,但从其诗作文本及序跋等文字中,亦可找到对她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进行讨论的依据。仲振奎为姑母仲莲庆《碧香女史遗稿》所作序言中说“姑母素工声律……不数年,姑母诗裒然成集矣”,而出嫁之后的情形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既出阁,适洪氏。洪世业医,无解声律者……中年以后,家事日零,八口嗸嗸,惟仰姑母十指以给。于是积劳成疾,而凄风苦雨之声,时亦见诸诗歌”,家庭的负担、生活的困苦使得仲莲庆诗歌中有着“积渐年衰积渐贫”(《自叹》)的悲凉与感伤。赵书云在为仲振宜姐妹所作《留云阁合稿序》中,先忆及早年与二姝“读曲歌诗,更倡迭和,既相爱又相敬也”,但两姐妹“出阁”后,“以旷代之淑质名姝,不逢赏音之士,日在愁城泪海中,伤已!而又殀其年,无后,天之阨之何其甚也”;笺霞甚至悲愤发出了“两妹何辜于天,而俾其支离憔悴若此,其诸命为之乎”的向天呼告。正像赵书云在这篇序言末尾所言“予痛两妹之肮脏以终,而又自伤命之蹇也”,她的生命中也是苦难相随、多艰多悲的。在《避尘轩诗抄》的序中,赵书云被称为“远迩悉称之贤”的广陵女史形象,却因其夫(即仲振奎)“才拙运蹇,淹滞场屋,书云属望过痴,常是戚戚”,“无子”的女诗人幸有女儿仲贻銮能承欢膝下,然而赘婿宫淮浦(桐山)[3]与女儿先后过世,赵书云抚养他们的儿子(即杏春)“瘁尽心力,精气遂大耗矣。丙春一病,及秋而逝”,这样的一生怎能不令人感慨唏嘘。女诗人自己也在诗歌中也不禁发出了“潦倒襟怀聊寄傲,伶仃病骨哪禁球”(《秋思》)、“莫苦咨嗟伤薄命,秋风容易到芭蕉”(《寄绮泉二妹》)的多方感慨。《仲氏闺秀集》所收录的仲氏家族第三代女诗人中,除仲贻銮年仅27岁早逝,仲振宣的女儿张贻鷮在母亲去世后由仲振猷嗣为女、未嫁,20岁就去世了,“薄命”的生命状态和“自怜”的心理动向在其诗作文本中也有着充分的表现。
仲振宜《自叹》一诗中有“贫极不知人世乐,愁来惟觉地天孤”的哀叹之辞,与“薄命”一类低沉、萧瑟“自怜”之音互为映衬的,是在仲氏闺秀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象幽微狭仄的特点。传统社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女性生活境遇及生存空间相对狭窄,导致她们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着对于外部景物描写的固定范畴化、抒写个人情感的固式化等现象和特点,闺阁、院落、窗庑及簾栊等具有幽闭空间特质的意象在女性作家诗词创作中频繁出现。仲氏闺秀的诗歌创作中亦具有此种情形,在《仲氏闺秀集》中较常出现的意象如表3所示:

表3 《仲氏闺秀集》中的常见意象举隅
女诗人或是悲叹“垂老何堪愁又病,暮云西望几怀人”(仲莲庆《自叹》)的愁苦心绪,或是描绘“灯残孤馆簾垂后,叶碎闺人枕上心”(仲振宜《蟋蟀》)的孤寂情形,抑或是于“寂寥东阁未回春”中感慨“底事生来同薄命,可堪天意不怜人”(仲振宣《怀芗云二姊》),也在“挑尽银灯未成眠”的景况下因念远怀人而生“隔断烟云百馀里,教人心水易生波”(赵笺霞《寄两妹》)的哀鸣,这些诗作,通过自然景色、外部物象与“薄命”之感的融合,呈现出情景交融、含蓄深蕴的抒情格调。例如赵笺霞的《寄绮泉二妹》诗中写:
海天云树影萧萧,雁字分开最寂寥。绣阁伴愁均有妹,吟笺写恨我无聊。
一庭凉月残灯暗,百里羁魂晓梦遥。莫苦咨嗟伤薄命,秋风容易到芭蕉。
据诗作中“海天”等文字来看,书云其时可能随其夫仲振奎求幕在外,与仲振宜、仲振宣姐妹分离已久,所以在夜晚中兴发了深远的思念情绪,“雁字”“吟笺”二语是对当年闺阁联吟的回忆,“无聊”即百无聊赖之意,显现出如今所感受到离情别绪的难以排解。怀念之深,自然引出“梦”中之情景,虽有梦而受到外在条件“百里”和生存境遇“薄命”的重重羁绊,女诗人做出了“莫苦咨嗟”自我宽慰之辞,然而抬头所见“一庭凉月”、一盏“残灯”,诗作的情绪最终只能归于凄凉、黯淡,末句以“秋风”中备显萧瑟的“芭蕉”作比,将女性因别离怀远、“命薄”自伤等情态之下的复杂感受描绘得相当细致。
仲氏家族的女性作家,除上述七位女诗人外,另有仲振履之女仲贻簪、仲贻笄和仲孺人三姊妹的诗作[4]113-114得以保存、流传。虽然由于存诗数量很少——共计6首,仲贻簪和仲贻笄仅见同题悼亡诗《挽弟蓉宾》各1首,仲孺人则写有《偶成》《昌口道中》《月下口占》《行舟》等4首体制短小、风格清丽的五七言绝句,恐未能呈现三姝文学创作的全貌,但就所能看到的诗作来说,作品基本呈现出与《仲氏闺秀集》中相近的内容取材、情感构成和艺术特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仲氏闺秀“一门联吟”的文学创作生态和“怀人”念远的主体抒写、“自怜”“薄命”的情感构成在明清时期扬泰地区的女性诗词中并非鲜见,甚至可以说是呼应之声众多,如《扬州历代妇女诗词》中所录张氏《方顺桥店中泪笔》、阮芷孚《题旅壁并序》中同有“薄命红颜千载恨”的怨苦之句,汪氏《和张氏泪笔序》发出了“深叹予同此薄命,因和之”[4]11的感喟,黄景仁之女黄仲仙(嫁兴化顾氏)《秋夜》诗中“米盐价贵悲来日”“几回幽怨不成眼”等文字;以季娴、宫婉兰、唐庆云(及阮氏众妇)等为代表的明清扬泰地区女性文学创作“蕴藉含蓄、摇曳多姿,却晕染着刻骨的寂寞与哀伤”[5],与仲氏闺秀诗歌写作的题材表现、情感内涵有着较为明显的相类(近)态势。
注释:
①本文所讨论的作品文本主要依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五 附二种》(嘉庆十二年刻本)的影印本。
②《仲氏闺秀集》的版本、家族性创作特点及其文学创作生态,笔者另撰有《乾嘉时期泰州仲氏闺秀诗歌创作的文学生态论》(见《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6卷第5期,104—107页)。
③学者戴健在其《清初至中叶扬州娱乐文化与文学》一书中论及了仲振履妻女的诗歌创作情况,并指出她们擅诗才,均有作品传世,但因其诗作未入《仲氏闺秀集》,故本文对此不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