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军、海盗与跨境贸易:17世纪初期的中朝海域交涉研究*
2019-05-05刘晶
刘 晶

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北黄海区域
万历壬辰御倭战争期间,明朝为协助朝鲜抵御日本进攻,跨越鸭绿江大量运送军需、官兵与商人至朝鲜,并定期开放边境贸易,极大地加强了两国间物资和人员的流动。为了节省时间与运输成本,天津、山东、辽东与朝鲜之间的海路运输亦被开通,在天津、山东等地筹集到的粮饷得以通过渤海西海岸、渤海海峡和辽东沿海地带到达朝鲜西海岸。在壬辰战争后期,海路运输已成为中朝间粮饷调配的重要方式,为朝鲜战场提供了大量补给。[注]壬辰战争的第二阶段,根据朝鲜史料的记载,从中国通过海运到达朝鲜平安道弥串堡交卸的粮饷应至四十余万石,朝鲜西北海岸亦开通大规模海运,完成了对中国粮饷的转运,极大地减轻了朝鲜境内陆运的负担。崔岦:《简易集》卷1《弥串海运碑》:“……造船百四十余艘,募沿海人行使,运时则得功食于公,休时则复得自同渔商,而船则固在我之具也。用是运到米豆之收在弥串者四十二万五千八百余石,义州陆运之余者十五万石。由其船制得宜,海路益熟,帆风一踔数百里,向之所患毕除,而天兵之饷不匮矣。”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9辑,首尔,1988年,第214b-215a页。随着海路运输的开通,中朝沿海居民大量参与到粮饷的运输之中。为济战争物资之需,壬辰战争之前实施的海禁政策亦被废弛,民间海上贸易得到发展。[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75,《辽东海防》:“万历十九年,倭奴从据朝鲜……然而更驰海禁,使商民给引抚道,听海防同知盘验出海贸易,是亦济辽急务也。”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1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与此同时,渤海、北黄海区域的冲要地位亦得到明朝当事者的重视。朝鲜与中国一海之隔,若朝鲜沦陷,日本则可直接渡海侵犯辽东、山东、天津等地,因此从战争之初,中国北方海防的强化即被提上日程。经略备倭军务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尤其强调辽东、山东沿海地带与近海岛屿在防倭上的门户作用,认为“惟是辽左自鸭绿江以至山海关,其海口延长更纡迴于二镇(笔者按:指蓟州镇、保定府),东逼朝鲜,北临虏穴,其兵力防范又牵制于一时;在山东沿海以及天津,在在皆称险要,而登莱各海岛处处皆宜设防,其增将添兵更不宜缓于蓟保二镇也”[注]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2,《议设蓟辽保定山东等镇兵将防守险要疏》,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133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荒废已久的山东、辽东海防藉壬辰战争得到加强,新的变化应运而生。例如沿海枢纽山东登州、辽东旅顺等成为海防重地;海防官大量设置;善于水战的官兵从江南调至北方沿海地区,成为当地重要的军事力量;北方沿海地带出现常备水军等。[注]有关壬辰战争期间中国对北部海防的经营,见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2-471页;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0-359页;赵红:《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第69-88页。
壬辰战争时期,北黄海区域的战略地位得到提高,沿海各地的互动也大大增加,为17世纪初中朝之间频繁的海上交流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之前政府用海禁等政策定义为“非法”的活动和人群,由于战争中对人力物资的需求,大量从事到官方许可的军事、运输和贸易活动中。比较显著的例子如朝鲜西海岸和辽东金州沿岸的私人船只被政府征用进行粮饷运输;在胶辽间诸岛(主要指今庙岛列岛)居住的岛民被纳入海防体系,转变为军事武装化力量等。[注]例如战争后期朝鲜政府对平安道、黄海道民船编号分组,将其用于粮饷运输,见李好闵:《五峰集》卷14《御史前呈文》,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9辑,第539a-540a页。宋应昌对如何征用金州沿海居民船只和庙岛群岛岛民亦有系统讨论,例如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3,《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第207-209页;《移辽东抚院咨》,第258-259页。战时对“非法”海洋活动的宽容和利用极大地刺激了17世纪初私人海洋经济的发展。而模糊化了的“官方”和“非法”界限亦催生了另一令人瞩目的现象,即战后北黄海沿海地带的明朝官军不仅没有成为海防海禁的主力军,反而加入甚至促进了官方禁止的海洋活动。例如万历三十年(1602),辽东巡抚赵楫报告称,“金州地方广阔,愚民山野十勾九抗,奸商违禁私自下海,贩卖私货,夹带逃军,而武官不遵明禁,贪肆无怠,莫敢谁何”。因此他建议“宜如山东闽浙事例,于金州添设海防同知一员,于凡海防哨探、战守机宜同游击并金复将官商确计而行,兼理军民一切事务,稽查往来奸商船只,并覆仓库各项钱粮。悍野官民赖以弹压,水兵海禁俱有责成矣”[注]《明神宗实录》卷399,万历三十年(1602)十二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7134页。。为了防止沿海商民水军违反禁令,下海走私,将官稽查不严的情况,赵楫提议加强金州海防,设置海防同知。这一情况正说明了17世纪初北黄海沿岸海防军势力与海上私人活动紧密交织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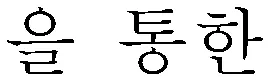
以中江开市为载体的走私贸易在这一时期甚至联络了整个朝鲜西海岸。如前段所举朝鲜京外商人至中江贸买火药即为一例。更有甚者,中江走私者满载货物,到达朝鲜南部沿海,“尽卖于东莱”(今韩国釜山市东莱区)。而东莱倭馆的日本商人见利益丰厚,“问其所从来,至欲借路,自取于辽东开市之处”[注]《朝鲜光海君日记》(鼎足山本)卷53,光海四年(1612)五月辛酉条,第32册,第65页。。由此可见,中江开市与东莱倭馆贸易已经被朝鲜沿海走私者连接起来。而从我们要探讨的吴宗道和吴有孚的案例中可知道,中江贸易亦与辽东、山东沿海地区存在紧密联系。尽管中央政府严令禁止,17世纪初中朝间的北黄海海域已通过走私网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而其中沿海、边境官兵的参与尤为频繁和重要。以此为基础的海洋贸易在东江镇兴起后得到进一步发展:1621年后金占领辽沈,明朝与朝鲜间陆路隔绝,次年毛文龙以朝鲜皮岛为据点设立东江镇,形成了一个包罗明朝各地和朝鲜商人,乃至延伸至后金、日本、东南亚的“由军人主导的海上贸易网络”[注]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88页。。
与活跃的越境走私相对应的是中央政府对边境控制的减弱。以中国而言,引发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1590年代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壬辰援朝之役和播州之役)对国力的大量消耗。明朝在边镇的经费支出本就庞大,经历“三大征”后,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这一危机加剧了自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边防储备日渐空虚的情形,进一步削弱了战后辽东的国防力量。[注]关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边防经费不足、边储空虚的研究,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太监高淮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三十六年(1608)在辽东以征收矿税为名敛财上供皇帝,尤其激化了与地方社会的矛盾,以至其“所过城堡,马骡猪羊,鸡犬鹅鸭,荡然一空。而军民老幼妇女亡魂丧胆,奔山窜岭者,不可胜数也”[注]何而健:《按辽御珰疏稿》,《横剥愈甚疏》,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95页。。边防松弛、秩序紊乱、军民困苦,是此时频繁越境活动的社会背景。
若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17世纪初期以北黄海海域战略地位提高、沿海区域间人员资源流动加强为契机发展起来的中朝海洋走私贸易,正是16世纪至17世纪前半叶全球性商品经济勃兴的一个环节。明代中后期白银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涌入中国,以此为支点的商业活动迅速发展。受到高额利益的驱使,北黄海沿岸的明朝军人群体亦不顾禁令加入到国际贸易的潮流中。岸本美绪以“边境”势力的兴起和扩张来解释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北方和东部、东南部地区出现的军阀团体,包括辽东边境的李成梁、毛文龙和努尔哈赤等,并借鉴John E. Wills Jr.的观点,认为其共同特征是集“商人、军事领导者、(与官僚或外国势力间的)中介者这三种身分于一身”[注][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85页。。从我们接下来对吴宗道和吴有孚案例的分析来看,尽管其规模和结局称不上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军阀,但身份却同样具有集商人、军人与中介者为一身的多元化特征,反映出17世纪初期中国与朝鲜间海洋军事势力开始崭露头角的趋势。
二、北黄海区域的水军贸易:以吴宗道、吴有孚案为中心
上述提到的吴宗道与吴有孚,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被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之时,其职位分别是镇江游击和山东防海副总兵。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熊廷弼对二人罪责的概括是:“防海副总兵吴有孚、镇江游击吴宗道役纵水兵兴贩海上,每装载货物撒放中江,勒商民取直。甚至改换丽服,潜入属国压取貂参,其资本出有孚,而宗道为之窝顿地主。”[注]《明神宗实录》卷455,万历三十七年二月癸丑条,第8579页。根据明廷讨论后,三月间对二人作出“革辽东副总兵吴有孚任,行巡按御史提问镇江游击吴宗道革任听勘”的处罚。这一案件直接引发明廷对沿海官兵私自出海现象的严禁和重惩,其结果是“以后沿海将官再有违禁纵放军兵越境生事的,都参来从重拟罪”[注]《明神宗实录》卷456,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乙巳条,第8607页。。
熊廷弼在《重海防疏》中对二吴罪状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万历三十六年(1608)冬天,熊廷弼在镇江公署停留之时,曾有中江商民“百数十人”与朝鲜义州府尹前来控诉。根据中江商民的说法:“两年以来,外洋海船,装载货物,络绎不绝。漏报皇税,逼勒各行,强栽货物,不一应承,辄以兵器。”而义州府尹亦称:“有等棍徒,潜应丽人,付货要参,侵虐万端,或勒卖房屋,或杀散人居。搪突衙门,詈骂备至。甚至易换丽服,混入迤东,及被获解,还则又掜赖抢夺,蒙诉勒追,必至荡产后已。”[注]熊廷弼:《按辽疏稿》卷1,《重海防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91册,第437页。于是,熊廷弼迅速委派辽东都司严一魁督同镇江游击吴宗道进行调查,结果是:
果获登莱虎船三只,水兵捕盗魏忠等三十三人,货物约银千余两,发行者十八,寄顿吴宗道衙内者十二,令票三张,皆总镇印号硃票标“九月十四日”,皆小汛将毕时事。问何籍贯,则皆以浙江人充登莱副总兵标下水兵,为吴有孚所差。问谁押货,则伊亲马英,为吴有孚表弟、吴宗道外孙。后从宗道衙内拿出。问船几何,则两年陆续到镇江、旅顺、金、复及海外各岛者,约三四十只不等,俱有孚家人梁贵、郑三等,捕盗卢中信、熊德等往来兴贩。问何发卖,则明以其半撒放中江及朝鲜商人取值,而暗以其半同吴宗道所收丽人为家丁者,变丽服、乘辽船,潜往铁山、别东、大张各岛,换买貂参等物。问谁资本,则出自吴有孚,而吴宗道则其窝顿地主也。[注]虎船即唬船,因船行疾快,常被用于做军事哨探船。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438页。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可以概括出此案的几个特点:首先,吴有孚、吴宗道利用职权便利,为吴有孚下属水军的走私买卖保驾护航,而二吴及其亲族为其出资、包庇、押货、销货。这些行为背后都需具有极强的官方力量作为支撑。其次,其走私活动具有一定规模,连接了北黄海沿岸及中朝边境地带,先至辽东镇江、旅顺、金州、复州及海外各岛获取货物,然后一半运送至中江贸易取值、一半走私到朝鲜沿岸换取貂皮人参等物。再者,这一案件中,水军、走私者、暴力团体、鲜人、明人等身份之间边界含混,在不同境况之下可以转换自如。

杨文已详细分析过吴宗道的生平,尤其是其在壬辰战争之中的重要作用。吴宗道为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壬辰战争期间以各武职散官身份承担朝鲜事务、对日和谈中消息传递、刺探军情等任务。作为在明朝与朝鲜之间协调中介的重要角色,吴宗道保持和朝鲜君臣的紧密联系,不仅在政治上为其出谋划策,于私人关系上亦交情匪浅。战争结束后,他曾以征倭钦依守备的身份管理两浙水师,并率领三千水军,参与朝鲜的防汛工作,还有在江华岛驻守的经历。明军撤退后他留任辽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升任镇江城守游击。[注]杨海英:《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第160-165页。
吴宗道对朝鲜大小事宜相当熟悉,在与朝鲜商议战后明军撤留时,曾对朝鲜官员李德馨说过:“俺自癸巳年(1593)在贵国,贵国诸官多相识者。俺则与朝鲜官一般,凡干事体,何所不知”[注]李德馨:《汉阴文稿》卷9,《与吴宗道问答留兵事宜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5辑,第426页。。这一特长在其担任镇江游击后得以继续发挥。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九连城)位于鸭绿江沿岸,与朝鲜义州隔岸相对,是壬辰战争时明朝为加强辽东南部防御新筑之城。[注]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424页。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镇江游击直接参与和朝鲜相关的文书传递、事务交涉、边防安全、情报搜集等工作。吴宗道得以成为镇江游击,或许正是由于他具有和朝鲜君臣相处的经验。镇江游击在中江开市问题上亦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例如1610年朝鲜请求罢市时,曾论及明朝方面对此事的意见,认为“礼部、辽广抚按、以至镇江游击府,皆不关于此市,而必是革罢之愿者也”[注]《朝鲜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光海二年(1610)二月庚申条,第26册,第533页。,说明镇江游击是商议处理中江罢市问题中的一环。吴宗道在壬辰战争中形成的朝鲜社交网络,对朝鲜社会环境的熟悉和领导水军的能力,都为日后其建立海上贸易网络奠定了基础。而他担任镇江游击后,又可直接接触中江事务并施加私人影响力,利用职权之便为海上走私货物找到消化途径。
吴有孚是吴宗道族侄,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担任山东防海副总兵,驻守登州。[注]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35,《武秩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杨文据《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言吴有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任山东副总兵(第167页),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则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未知孰是,兹暂从府志之说。这一职位和镇江游击一样,是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为加强山东沿海与辽南地区军事防御力量而设立的。[注]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424页、第426页。尽管吴有孚本人和朝鲜没有直接关联,但他掌控山东沿海地带,支持手下同为浙江籍的水兵进行跨海走私,是中朝海上贸易的出资人和具体执行者。由此可见,吴宗道、吴有孚二人利用政治资源、境外经历、家族关系、地域联系、军事才能等种种条件将官方身份变为海上走私、中江销货的有利掩护。
最后,我们应注意吴案中“官方”与“非法”界限不明确的现象在水军活动中具有的普遍性。陈波在研究倭寇、飘风人、被掳人与卫所军人的关联性时曾指出,明初沿海卫所旗军很多从元季“诸岛强豪”继承而来,随着明中期纲纪的废弛,制度的束缚性减弱,这些旗军从事非法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注]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页。这一情形在壬辰战争之后变得更为瞩目。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过,此时明朝大量利用北部沿岸、近海的民间劳动力运输粮饷、增强海防,将原先被视为社会边缘甚至非法的靠海而生的人群纳入国家规范之内。战争结束后,面临财政危机、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等矛盾的加剧,中央政府控制力随之减弱,这些人群即得以通过操纵和利用官方资源谋取私利。这一情况为熊廷弼所注意到,在《重海防疏》的开头他就写道:
今西北防虏,东南防倭。边防海防,两者并重。顾边防之难难在虏,而海防之难难在中国。往时中国之难,难在海上之亡命,而近日之难,难在防海之官军。自国家惩倭之诈,缘海备御,在在置戍,所招蜑户、岛人、渔丁、贾竖、以至无赖恶少之辈,皆得衣食于县官。而此辈惯走海上如平地,既习知远夷财宝之饶,又有器械以藉之,糇粮以赢之,战舰以资之,而又有主将之资本以为营运,出入之印票以为符验,关津不敢阻,有司不敢诘。经年镇月,出没于海岛之间。[注]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页。
不仅如此,条件激化以后,这些人群还极易由官兵转变为不受制约的非法暴力团体。例如南京官员顾起元就写道,壬乱时期为备倭而驻扎在南京龙江关的有数千名浙江义乌兵,而这些人在战争之后却成为地方社会治安的一大难题。由于“其人多趫悍,间有事故死亡,若归故土者,雇请本地恶少年冒充之,而享其糈”,因此政府商议裁撤。然而“才议撤,已飞语鼓噪不可听闻矣”。他们还为祸一方,“群聚剽市人之物,或公然为劫盗,奸乱无所不至。有被其害鸣于官,官畏众嚣不敢问,甚且反笞被害者。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妇,嬲而淫之,同人道于牛马。”[注](明)顾起元著,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客座赘语》卷1,《浙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页。同因裁撤问题,在登州和旅顺戍守的浙兵还分别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和万历三十五年(1607)发生哗变。[注]光绪《续修登州府志》卷13,《兵事》,第138页。大抵正是由于战后水军秩序的极不稳定,才导致熊廷弼到镇江一开始听到海兵生事时,因“固习闻此弊,不以为意”[注]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页。。
这些在海防力量与非法暴力之间游走的中国水军,是如何和17世纪初朝鲜西北海岸猖獗的海盗行为相纠缠的呢?而朝鲜政府又怎样认知这一情况?其与中国官员关于越海案件的交涉又是如何反应微妙的边境关系呢?以下部分即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三、水军、海盗与中朝交涉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17世纪初的朝鲜。随着壬乱时期中朝两国海禁的解除和海上交通的无阻,“水贼”对朝鲜平安道、黄海道沿海的侵袭开始变得频繁。例如1596年朝鲜政府讨论从山东海运粮饷的种种困难时,曾提到“欲运山东之粟,则船只不敷,水贼亦多,又难输来”的情况。[注]《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九年(1596)五月丁亥条,第22册,第711页。猖獗一时的“水贼”活动在17世纪20年代之前达到巅峰,成为朝鲜海上安全的重大威胁。在分析这一时期朝鲜政府对“水贼”的认知之前,我们应首先了解“水贼”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内涵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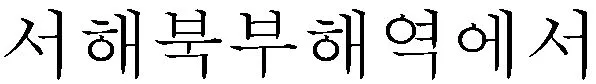
然而17世纪初“水贼”的活动性质却发生改变。与16世纪朝鲜方面零散的记录相比,17世纪初的“水贼”对朝鲜平安道、黄海道的侵扰明显更为集中和暴力,是公然以抢劫为生的海盗团体。饱受侵扰之苦的朝鲜政府为了解“水贼”的真相,进行种种调查,并以“海浪岛水贼”或“海浪贼”这一专有名称来指代这些海盗。这一称呼有其依据,从回到朝鲜的“海浪岛被掳人”的证词来看,“(海浪岛)其地之长广,视京畿德物岛差大,而全无兵器,只持石块白挺(梃),载船出行”。至1603年时,“海浪贼”对朝鲜的威胁已相当之大,正如朝鲜备边司所言:“海浪岛水贼,自弥串运来粮船潜抢之后,甘于得利,恣意出没于两西(笔者按:指平安、黄海两道)沿海地方,近益尤甚”。[注]《朝鲜宣祖实录》卷164,宣祖三十六年(1603)七月乙卯条,第24册,第499页。不仅如此,此等人“窃发于海西(笔者按:指黄海道),或得正西风,向南而下,转入忠清、全罗等道”,对整个朝鲜西海岸都产生不小的影响。[注]李恒福:《白沙先生别集》卷2,《白翎设镇事宜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2辑,第370a页。对于“海浪贼”的组成人员,朝鲜政府也进行了一定讨论。1607年初,备边司首先指出“以其巾服观之,似是唐人所为”的推测。但因其成分或许比较复杂,朝鲜人和其他海上诸岛的逃民也有可能加入,因此备边司提议继续加以调查。[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09,宣祖四十年(1607)三月丁丑条,第25册,第314页。之后,通过询问熟知海浪岛水路之人并对比相关地图,备边司得出“今此作孽之辈,必是海洋、石城(笔者按:今辽宁省海洋岛、石城岛)之人,相聚出没,攘夺我国人衣粮也”[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11,宣祖四十年(1607)五月甲子条,第25册,第331页。的结论。以上种种讨论,大抵可以看出朝鲜政府对17世纪初“海浪贼”的认知是辽东海洋岛、石城岛居人,他们频繁出没于平安道、黄海道进行抢劫,但也会顺风而下达到朝鲜半岛南部海岸。其武器威力并不大,只持石块、木棍等物。
实际情况却比朝鲜政府的归纳要复杂许多。从以下两则案例中可以看出,不仅军人和海盗身份之间具有很强的弹性,在朝鲜政府和辽东官员以及明廷的交涉沟通中,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也会有意识地调整对越海人员身份的解读。第一个案例发生在1606年末,当时朝鲜国王接到黄海道监司柳梦寅的上报,在海州捕到胡惟忠等19人。根据其所持文书判断,“则似是天朝旅顺口地方将官之标下,漂流到此”。这个案例在朝鲜后期李肯翊编纂的史书《燃藜室记述》中也有简略提及,点出了胡惟忠等人的籍贯为浙江,“(宣祖)丁未, 浙江人胡惟忠等十九名,漂到海州。千秋使李庆涵,押赴奏闻”[注]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17,《荒唐船》,《古典国译丛书》11,首尔,1982年,第745页。。然而备边司在调查胡惟忠等人时,却发现其供言“或有疑端”,而船上所载之物中,有水磨石及朝鲜木碇等物,亦非同寻常。[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05,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一月己卯条,第25册,第285页。尤其是,此人等以追赶朝鲜盐船而来,其情状和海盗相似。[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丁巳条条,第25册,第329页。此人等还十分顽悍,为讨要上岸时在和朝鲜边将冲突中损失的财物,不仅“击钟诉冤”,还欲直入朝鲜宫城,“号哭隳突,无所不至”,以致朝鲜官兵“不得已掩门拦阻”,引发了一场骚乱。[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辛丑条,四月壬寅条,第25册,第323页。胡惟忠等人所持文书和实际行为之间所显示的差异使朝鲜官员对其身份产生了不小的疑惑。备边司在接到黄海道监司的上报后,虽然对其身份有所怀疑,仍然做出“此人等不是海贼,而系是天朝军兵”[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05,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一月己卯条,第25册,第285页。的初步判断。礼曹大臣则等以为,“此人等虽似漂流之人,而真的情状,有难知之”[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06,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二月甲寅条,第25册,第296页。。
然而,当他们即将被遣返北京时,备边司和朝鲜宣祖之间却就是否应据实记载其可疑之处并奏报明朝引发了一场讨论。宣祖认为,在将此案正式录入咨文时,应该删去查报镇江时记载的“追赶本国盐船,情迹亦难所知”一语,以免胡惟忠等人回国之后遭到责罚。而备边司则认为,以其无赖行迹来看,此辈“与向来漂海唐人不同”,怕其回国之后反构陷朝鲜政府,因此提议将其“充突追逐事状及船中什物我国之物居多”的情况略为提及,以备后患。宣祖的答复则是:
惟忠等倘是海贼,则船上岂有文书与礼单等物乎?予意,断然以为漂流者而非海贼明矣。其曰追赶盐船,此边将要功之说,盖将拟以为直捕海浪之贼者然。万一由我数字之非其真情,使数千(笔者按:应为“十”)人命,因此获罪,或不免于死,此非仁人之所忍为也。宁人负我,我不可负于人。不惟此也。凡咨文,上奏之书也,万一失实,是藩臣而欺罔朝廷,罪孰大于此?予为是惧,报镇江咨草一勾(笔者按:应为“句”)付标删去矣。近观此辈所为,颇为不雅,恐有赴京之后构捏之患,予亦为虑,然不过无知所为。然群意必有深见,参酌亦可矣。[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丁巳条,第25册,第329页。
这说明宣祖最终以胡惟忠所持官方文件为准,认定其不是海贼,而是明朝军人,并将其追逐朝鲜船只的行为解释为朝鲜边将为了邀功捕捉“海浪贼”的借口。这一判断是否基于宣祖的坚定想法呢?之后他的解释告诉我们,宣祖并非对他们的身份没有怀疑,但是一则害怕其因朝鲜之言获罪,二则没有确定证据,不敢妄言欺瞒明廷。尽管我们无从得知朝鲜咨文的细节,但从《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朝鲜确实称其漂海旅顺官兵。朝鲜对明朝就此事的嘉奖进行谢恩时写就的《胡惟忠等发解降敕谢恩表》中,也只是描述称“流播之官兵,适然漂到于弊邑”[注]《槐院誊录》卷2,《胡惟忠等发解降敕谢恩表》,第54a页,韩国藏书阁所藏写本。,并不提其他。反而是明廷下令山东“查验收伍操练,如系私贩下海,别有情弊,究处以闻”,表现出对胡惟忠等人行迹的怀疑。[注]《明神宗实录》卷437,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乙酉条,第8280页。可以看到,朝鲜选择向明廷隐瞒胡惟忠案的疑点,实际是出于谨慎事大的考量。我们知道,朝鲜将此案查报镇江时,其实是记载了其可疑之处的,但是在正式咨文中却又将其删去,这其中未必没有避免交恶于辽东的想法。
如果说胡惟忠案的细节反映了中国防海官军和海盗之间似有若无的联系,以及朝鲜最终有选择性地记录此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案例则侧重展现了辽东官员在交涉越海人员身份时的微妙态度。1607年闰六月,朝鲜平安道铁山郡守柳旻和弥串佥使康孝业与“水贼”之间爆发了一场小型战事,斩杀“水贼”十三人,而朝鲜军人亦有十人被杀,柳、康二人皆负伤。[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1607)闰六月庚辰条,第25册,第349页。这次冲突使朝鲜国王意识到处理海盗问题的紧迫性:“海浪岛水贼近年出没海上作贼之事,具录事状,移文辽东,请为禁断。预为张本,则虽有今日转战厮杀之变,事势不至于难便,而惜乎其不早处也。”[注]《朝鲜宣祖实录》卷214,宣祖四十年(1607)七月辛卯条,第25册,第351页。《事大文轨》中的相关咨奏文书包含了这一事件的细节经过和交涉过程。当年七月,朝鲜国王给明朝礼部的奏文和辽东都司的咨文中详细记录了近年来朝鲜遭遇的多起海盗事件。[注]由于篇幅所限,这些事件的内容不再列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拥有火器等武装力量,主动向朝鲜海岸公私船只开炮投石、抢劫财物。见《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63b-68a页。尽管朝鲜政府称犯案者为“海浪贼”,但这些人和上述朝鲜政府总结的只持石块、木棍的流民相比,显然有所不同。根据朝鲜政府的调查,柳、康所遭遇的海盗“所骑船只系是我国所造,而该载物件则天朝人衣服文书,及我国人衣服相杂载置”,并且由于贼船上还留有去年朝鲜官兵所射之箭,因此朝鲜认定“本贼等自前出没抢劫之状,明白无疑”。在这份文书的最后,朝鲜还为杀害了疑似中国人的海盗做出解释,说明其“猝然遇变,黑夜之中,苍黄应敌,各自救死,互相杀害”的不得已,并“将本贼文书所录姓名具咨辽东都司”,希望其“以凭查明虚实,以防贼患”。[注]《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65a,68a页。
然而有趣的是,辽东官员回复朝鲜时,却避免承认柳、康二人所遭遇的是海盗,并由镇江游击吴宗道参与此案的继续调查,“严查朝鲜捕获船几只,要见系某衙门差人若干驾往某处公干,彼风漂流,朝鲜官军何不认实,擅自射死。是否遗有公文、衣服各若干,见在何处。或系贼船假诈,务要根查明白”。尽管朝鲜在之前的咨文中已经说明了柳、康事件中由于海盗主动攻击因而迎战伤亡的情况,辽东却倾向于用“公干”“漂流”“擅自射死”等词来形容这场冲突,而对事件为海贼的可能性,仅一笔带过。之后,根据吴宗道的调查,辽东官员称“查得漂流海船人役数多,尽行杀死,又无称出何处人氏,亦无下落,干系众多,人命有碍”,并再次要求详细查明情况。这一次的说法不仅重复了第一次的叙述,还责问对这些“因风漂流”的衙门公差,朝鲜政府“为何不行羁留”,而且“擅自射死一十九名,止报十名,因何容隐,岂有情弊”。对于朝鲜政府称其为贼船,辽东则继续追问“有何凭据,是否真正”[注]《事大文轨》卷48,《辽东镇江等处地方游击将军指挥吴(宗道)咨朝鲜国王(镇江捕获贼船咨)》,第85b-87a页。,面对辽东的反复责问调查,朝鲜政府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此事曲折,既经具奏,又为查报各衙门,非不详尽,而今又再问。原行奏咨之外,岂有一毫他端?近来西海一带,水贼窃发,节次抢掠,另行各处沿海官司严加隄备间,彼乃骑坐我国船只,各持刀枪,乘夜先犯,则认为贼船,岂无所凭?彼既以贼而来,自不能致疑于天朝某衙门差人。而黑夜之中,苍黄相战,救死不及,何暇活拿羁留乎?十九名内只报十名者,船上存留文书中拈出该写十名开报而已。初非谓此十名的系杀死人姓名,若欲容隐,岂于原数内直称一十九名而不没其九名乎?[注]《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咨游击将军吴(宗道)(回咨)》,第92页。
以上辽东和朝鲜争论的焦点正是如何定义明朝越境人员的身份,而这一关键问题直接影响到该事件的性质。一方面当然再次说明海盗和官军之间的模糊界限,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实际交涉过程中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的解读差异:究竟是衙门公差漂海后被朝鲜边将擅自射杀,还是中国海盗侵扰朝鲜而产生的军事冲突?如果是后者,辽东政府当然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辽东倾向于将该事件理解为公干漂海,反复要求朝鲜拿出其为海盗的真实依据,并尽可能地将杀害中国人的责任推到朝鲜身上。而朝鲜是否对这些人可能具有的官方身份毫无所察呢?从其耐人寻味的回复“彼既以贼而来,自不能致疑于天朝某衙门差人”来看,或许朝鲜也意识到了明朝官方人员与犯越海盗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却不能直接点明,只能将其简单认定为海盗,避免得罪辽东地方政府。
巧合的是,《重海防疏》中也叙述了同一案件,并记载了辽东当事者的应对方式。熊廷弼称其于镇江公署中见到朝鲜节制使柳旻的状文,其中写道“是月(1607年闰六月)初八日,又有异样大船三只,自外洋直向戎岛,夜袭丽船,为朝鲜官兵所击,杀死贼十九名,余船脱走,而柳旻、韩(康)效业两节制使亦皆被伤,及查衣服文书,则系中国人物”。接着他又记载了同月朝鲜发生的另一起事件:“朝鲜国王咨称异样大船一只自外洋来,扬旗鸣金,追赶丽船,不意落浅,为丽兵所获者十九人,问之,皆原籍浙江军兵人数,及查船所装载,则皆铳炮、刀筅、鸟枪、火药诸器,与青蓝布匹、杂色货物。”熊廷弼提到,对于这些案件,“当事者秦越人视之,或以隔省事体置不问,如所称前件者,大都苟且完事,而不以法一究之”。从我们所分析的相关咨文中辽东官员对待柳、康案的态度来看,熊廷弼的指责确实不无道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镇江游击吴宗道在这些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熊廷弼在弹劾其罪状时,直接将这两起事件和吴有孚手下水军魏忠等的走私案联系起来,认为涉事人“皆向者捕盗魏忠等之类也。在境内则为商贾,犹以买卖为名,在境外则为贼盗,专以虏掠为事,逢船则抢,遇人则杀,剽劫岛屿,莫敢谁何。一月之间,连犯数次,盖朝鲜受水兵之害亦极矣”[注]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9页。。这些案件的参与者中都少不了吴宗道的身影。在柳、康案中,吴宗道是两国文书的传递人和案件的报告者、调查人。发生胡惟忠案时,朝鲜政府向镇江查报,而吴宗道其时正担任镇江游击一职。熊廷弼所举的第二例尽管和胡惟忠案时间不同,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例如涉事者皆为浙江籍军人,都是在追赶朝鲜船只时被捕等等。朝鲜政府在正式咨文中删除了胡惟忠案的疑点,是否和吴宗道与朝鲜过从甚密的私人关系有关?而吴宗道处理柳、康案时在调查中无所作为,是否正因为其和涉事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事情的真相,却能从这些案件中管窥辽东与朝鲜之间的微妙关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明廷在处理柳、康案时的态度。由于这一案件的影响重大,1607年七月,朝鲜政府与辽东交涉的同时,就已咨会明廷。[注]《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咨礼部(捕获犯境海贼船只闻奏)》,第68b页。和辽东政府的指责推脱不同,明廷的处理可以说是完全站在朝鲜一方了。兵部官员在叙述此案时不仅接受了朝鲜的说法,用“盗舰”称呼涉事者,并且还支持朝鲜对近海海盗进行捕杀,不论其是否为中国人民:
臣愚因为,该国当此旧疆新复之后,又值倭奴饰好之时,其武备时宜加饬,而防守时宜加严。于凡视风之时遇有船舰,若系漂流商民不操器械,不与相敌者,悉行送还中国。如系劫贼,不论是否中国人民,概行剿截,如船在外洋,则不得使之直趋,船在近地,则不得使之登岸。两阵交击格杀自宜相当。如有就执者,审系中国人民,即当生致阙下,置之典刑。务使贼民晓然,知该国之不可易与,而该国又晓然,知天朝之不纵奸,则字小之恩正所以成其事大之顺。[注]《事大文轨》卷48,《兵部咨朝鲜国王(兵部捕获贼船咨)》,第94页。《明神宗实录》中也记录了这一段内容,除有所删略外,大意相同。《明神宗实录》卷440,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一月己酉条,第8348页。
这一处理方式一方面正如明朝兵部官员所述,是为了维持和彰显明朝、朝鲜之间“事大字小”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应了明廷对这一时期中朝海域混乱、海贼频发的认知。其在处理海疆安全问题上也一向以控制和打击私人海上活动为主。这一态度不管是从前文提到过的设立金州海防同知,革除吴宗道、吴有孚职位,还是从彻查胡惟忠案、支持朝鲜政府击杀中国海盗中都能够体现。明廷对海疆安全的处置不仅和17世纪初中国地方海上军事势力在北黄海区域的发展形成对比,也和辽东政府在处理越海事件中推卸消极的态度有所差异。
四、结 语
上文分析了17世纪初北黄海区域变迁与中朝跨境经济交流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吴宗道、吴有孚案为中心分析了在这种作用的影响下,中国边境与沿海官军如何紧密地与非法海上活动交织在一起,并极大地模糊了水军、走私者与海盗之间的界限。陈波在分析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几则中朝间漂海人送还案例时(其中包括1602年旅顺海防军徐上龙的漂海),认为明朝卫所军人有日本学者村井章介所提出的“境界人”的特征,是“活跃于海陆交接的地理边缘,游走于国家体制内外,也是东亚社会文化心理认知中的边缘群体”[注]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第60页。。本文所举的吴宗道、吴有孚案也是这样一例,显示了17世纪初中朝海域间超越国家界限、制度束缚的频繁交流。而吴宗道、吴有孚在中朝社会转型之际,利用多样化资源,建立起连接北黄海海域与中朝边境贸易的走私网,亦是岸本美绪所提出的明末“边境”势力兴起趋势的一个反映。
本文还从17世纪初朝鲜西北海岸频发的海盗问题入手,从中朝边境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两个与吴宗道、吴有孚案相关联的跨海案件。胡惟忠案强调的是朝鲜政府在面临区分海盗与水军的困难时,如何确定涉事人员身份和有选择性地上报案情,体现了其在外交层面的复杂考量。而柳、康案则侧重于辽东政府在与朝鲜的交涉中,如何利用官方与非官方身份的模糊性来处理案件,以使情势有利于己方。明廷与辽东政府处理方式的不同,则进一步展现了中央与地方在海疆安全问题上所具有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