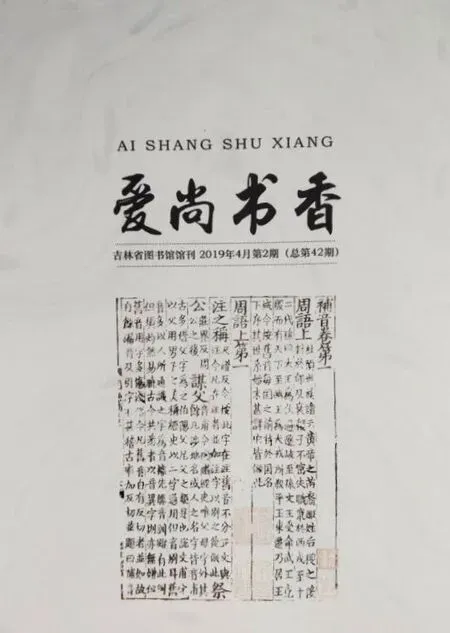东北风情的灵性表达
——序卢海娟女士《东北的土灶》
2019-04-22刘诚龙
刘诚龙
一个人,只有修炼成一颗舍利,才能沉到水里,沉到土里,沉到万物的深处,沉到我们动荡飘摇的内心。
因此,真正的写作就是一场修行。修得慈悲心肠,笔端就有众生,就有爱、有情;修得人生智慧,文字就成了度牒,成了地狱与天堂的苦海慈航。
不嗔、不怨、不惊、不怒——在遥远的长白山南麓,在那个被冰雪覆盖几乎达半年之久的北国,有一位徜徉而沉醉于文字的灵性女子,像虔诚的修行者,她专注、执着,倾情散文写作,一只妙笔尽写东北风情。
她的文章,一花一叶皆有诉不尽的衷情,一雪泥、一鸿爪全是说不完的妙趣。女子散文,笔底自可以婉约,自可以清丽,自可以性情,自可以带上晦暗和小感伤……她却把这般小女子的姿态弃之不顾。相对于凡俗的生活,她独立于莽莽苍苍长白山下,瞭望云色,俯瞰原野,有风翻起她心中的经卷,但见憨态可掬、妙趣横生的文字便会叮咚叮咚,大珠小珠落玉盘。
卢海娟,这是个知鱼懂果、惜物识人的女子,她生就一颗兰心,长就一双慧眼,你的眼光所忽略的事物,恰被她灵敏的心灵捕捉,经她轻拢慢捻抹复挑,常态下的人与事,便鲜活起来,激情重现。读她的文章,是从《渍在酸菜里的冬天》开始的,精彩的生活细节让人忍不住要大声喝彩——原来东北人的日子过得这样冰爽、有趣,等到读到文章结尾,“一棵大白菜走过属于它的时光之旅,慢慢地、慢慢地演绎、变化,最终发酵成味美可口、醇香绵长的酸菜,就像窖藏在记忆深处的,从容安逸的老东北的慢生活。”这样的生活太让人羡慕啊,在城里头生活得狼奔豕突,见到了这样家常慢生活,不知不觉中,已泪泫于睫。
我最喜欢的,是海娟女士东北风情系列,那里有迥异于西北,迥异于江南的独特风情,湖南杀年猪,吃不完,将其腌制,将其腊制,东北呢?将猪肉埋在雪地里,开春了,一镐子挖下去,便是一块新鲜猪肉冒出来,想想那情景也是醉了(《雪里挖年货》),如《俺们东北不饮茶》,《东北人:你可真有意思》,这一系列文章所呈现出来的异样景致,不让人饶有兴趣吗?难怪《工人日报》《甘肃日报》《内蒙古日报》《大众日报》……全国各地报纸杂志那么喜爱,纷纷登载这些文章,惹得万千读者兴致勃勃,愿意透过她的文字来看东北。如果说,从迟子建的小说中认识的是有些沉重的东北,那么,从卢海娟的散文中,我们又会看到东北的另一个层面:平淡中的真味,简易里的精致,清素下的高贵。
写民俗散文,很容易流于粗糙,流于低俗,流于浅薄。她却把民俗写得诗意盎然,饱蘸生命的清芬。“如今冬天又来了,我仍然会去肉案那里逡巡,默默地缅怀那些不断把美味从雪里挖出来的日子,真希望能把温馨宁静的北方生活从雪里挖出来。”就是这样,大面积诙谐幽默的叙述,生动有趣的解说,刚刚还是忍俊不禁,笔锋一转,只一句话,读者却忍不住要泪崩——诗意的语言,魅力大概就在于此。
最重要的还在于她的选材。在东北,孩子出生时要睡米枕,满月后要上摇车,母亲的后背就是孩子的幼儿园;在东北,有温暖的火炕,身份暧昧的驴厩,杖子上的陈年往事;在东北,有粘火烧,苏叶饽饽,除夕饺子还有种种彩头……东北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新鲜事,东北生活,有太多太多的小精彩。
我最欣赏海娟女士写东北风情,并不只是猎奇心理,我感觉这里,有作家的责任,有作家的担当,高速时代,浮躁时代,一万年形成的风俗习惯,就在朝夕之间消亡了,我们如何寻觅过去?海娟女士笔下那个东北,也是渐行渐远了,也是快与世界同质化了,当地球果真成为一个村,所有景致都一样,你不觉得乏味死了?海娟女士文章深刻在于,这些文字也是一种拯救,一种挽留,给我们提供一种对地域独特文化的遥遥记忆。也许她瘦弱的肩膀掮不起太多的沉重,但她坚守着,承担着,拾掇往事的碎片,祈望以此连缀成一个完整的东北。就让我们透过她打开的这一扇窗,透过长白山南麓的皑皑冰雪,向东北引颈翘望吧。
我与海娟女士结识多年,多是远隔万里烟云,以文字相对望,常常为其轻灵、清秀而细语娟娟的文字,而拊掌,而点赞,而歌哭笑乐,而忍不住QQ上给她留言。也曾兀自慨叹,何日彩云会?没承想,人生何处不相逢,有缘万里可相会,2014年8月份吧,感谢河北《思维与智慧》杂志,邀我参加大连笔会,太有缘啊,我与海娟女士相逢大海。见了文字,再见真人,其欣喜为何如?海娟女士话不多,沉静,一如其文字所展现出来的灵性面貌。
相聚日短,情谊绵长。在大连听海娟女士说,她那里五味子可泡茶,味道酸酸甜甜。是吗?真想去一趟,切身感受东北风物,再向海娟女士讨一杯五味子茶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