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岁月以痛加冕
2019-04-18小龙
小龙
1
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我和刘先生之间的关系。每当有人提起他时,我的心底都会升起一片失落的茫然。
在长久的疏离中,时间早已将他氤氲成一个模糊不清的背影。也只有那些潜藏于灵魂深处的疤痕。才会在午夜梦回时,提醒我曾经有这样一位父亲。
年幼的时候,我的作文里经常出现刘先生的身影。当初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他精通无线电,会做美味的糖醋鱼,还在地方小报上发表过一些零零碎碎的短文。
每当小伙伴们向我炫耀自己的零花钱,我一句话便能轻易镇住全场。
“你们知道吗?我的零花钱可是我老爸的稿费!”
“稿费?”一时间,小伙伴们全都瞪大了眼睛,他们惊讶地问,“你爸爸是记者吗?”
“不对。那应该叫作家吧!”我夸张地摇头晃脑,就像一只骄傲的小孔雀,享受着被众人羡慕的殊荣。
青春期的我有着强烈的虚荣心,毫不掩饰地去争强好胜。进入初中以后,我更是如此。然而初二那年,我却遇见了一个讨厌的男生。
“爸,今天我们班转来了一个讨厌的家伙,他叫黄毛。”
“爸。那个男孩儿居然还喜欢搞小团体。”
“爸,今天黄毛故意撕碎了我同桌的作业太……”

那时候,我每天回家都会跟刘先生分享班里的新闻。而那个黄毛,也一度成为我的话题中心。
好动的天性和无法无天的做派,让黄毛成了年级的小首领。他喜欢恶意地去开毫无底线的“玩笑”,通过揭开他人的伤疤来哗众取宠。
还记得。当时刘先生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有没有欺负过你?不要怕,告诉我实情,我会去处理!”
我当时摇了摇头,然而第二天,我就带着一身墨水渍哭着狼狈地回到了家。
刘先生言出必行,当即气势汹汹地杀到学校。1.68米的他居然将年轻气盛、身高1.75米的黄毛,吓得屁滚尿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的另一面。他目光犀利,紧握的拳头上青筋凸起,仅仅是一声大喝,就令黄毛落荒而逃。
也正是那时我才发现,原来人真的可以如川剧变脸般,拥有很多面。就像刘先生,他可以是慈父,可以是文人。也可以是施暴者……
只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料到,这样多面的他有朝一日也同样会伤害到我。

2
直到長大后我才明白,生活的剧本中,从来都没有永远光辉的圣人,也没有毫无瑕疵的伟人。很多人,只有当命运的风暴来临,才会显露出内心的底色。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几乎每周都会发生一次争吵。母亲总是无缘无故地突然发火,她一反过去贤惠温柔的模样,拿着东西摔摔打打,说话更是咄咄逼人。
而刘先生也从最初的沉默不语,发展到后来的反唇相讥:“你就是没事找事,实在不行咱们就分开过吧!”
“你总算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找好了下家?”母亲瞪着眼睛,如同暴怒的狮子。
而刘先生的脸色变得阴冷吓人。
母亲还在不依不饶:“你怎么不说话了?这就是你们刘家的家教吗?你……”
不等母亲说完,屋里便响起了一声吼。
家里的板凳被摔得四分五裂,叫骂声、哭喊声,歇斯底里,客厅中一片狼藉。
当时我并不清楚,刘先生究竟做了什么。那天晚上,他居然特意带我去吃了一顿肯德基。一路上,我非常忐忑,脑海里反复出现美术课上的一幅名画——《最后的晚餐》。
我望着脸色阴晴不定的他,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小声地说:“爸,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和妈吵架?”
刘先生有些不耐烦,他敷衍地挥挥大手:“大人的事情,你小孩子不要管。谁家能从来不吵架?牙和舌头在一起还有摩擦,更何况是两个大人呢!”
“哦。”我默默地低下了头。
过一会儿仍不死心,我又小心翼翼地追问“那……那你们会分开吗?”
不等他开口。我就紧张地抢先说:“当然不会,你们肯定不会的,对吗?”
我不安地留意着他的表情,然而,他却匆匆转身。把我的问题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我去再给你买一个汉堡吧。”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并不认识刘先生。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
曾经,他看见我学习到深夜,会细心地给我装热水袋,温牛奶;三伏天,他仍旧会跑半个城去给我买玩具熊;我们一起过马路时,他总是自然而然地站在我的左侧,理所应当地替我挡车……这样的他,当然应该算一位好父亲。
可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好父亲,又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美满的家?为什么他从未想过那些谩骂会让眼睁睁看着一双至亲互相推搡的我难过?
他确实对我很好,这种好却只限于我们的单向联系,并不包括整个家庭。
从小到大,我们一家三口甚至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

3
生活之所以被称为生活,就是因为它充满了出其不意的转折。
在去民政局的最后一刻,母亲竟突然反悔了。纷纷扬扬的纸屑被她抛向空中,那份协议书和他们的过往一样。四分五裂。
他们一起回到了家,依旧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然而两个人却形同陌路。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只是从那天开始,他们生活在了两个泾渭分明的空间里。
家里,北面的房间是刘先生的,南面的房间是母亲的。每天我都能看见各自紧闭的两扇房门。即使同一顿饭,我也常常要吃两次。跟母亲一起吃一次。再跟刘先生一起吃一次。因为他们不会坐在同一张餐桌前。
有时候。母亲还会凶巴巴地质问我:“你没吃饱吗?怎么又去他那儿喝酸奶?你知不知道你的牙就是这么坏掉的?!说过你多少次了,你们姓刘的怎么一个个都故意跟我作对?我欠你们的吗?!”
母亲咬牙切齿的声音不像是在骂我,倒更像是在刻意地表演给谁看。
北屋里依旧一片死寂,但在这死寂背后,我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
不知从何时起,刘先生把他的钱物全都收了起来。以前他的钱包会随意放在抽屉里,后来再也没有了。
一次,我无意中推开他的房门。当时他正在整理东西,看到人影闪过,他居然想也不想就把两张卡下意识地藏到了枕头下。那防贼似的动作。让我觉得这并不是他的家,而是一间人多眼杂、需要随时保持警惕的旅社。
每逢月底,这个冷清的家里就会变得沸反盈天。因为每个月的28日,是他们结账的日子。
他们针锋相对的声音,充斥着所有房间。
“你天天用电脑,凭什么不多掏电费?我为什么要跟你平分?”
“家里的醋和酱油都是我买的,上一次我忘了写在记账本上,今天要补上!”
“一共是八百八十块三毛,那三毛你记得下个月补齐给我!”
他们手中有本油腻的记账本,那上面每一个字都在刻薄地计算着物价,也在残忍地算计着人情。
然而,就是这样锱铢必较的两个人,在外人面前却格外大方。他们常常在饭局上抢着买单,热情地请朋友吃饭。在我眼中,那样的场景真像是黑色喜剧。而他们就是最优秀的演员。
我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们。但我很想让他们知道,从那些计较与争执中,小小的我已然窥见了成人最狰狞的恶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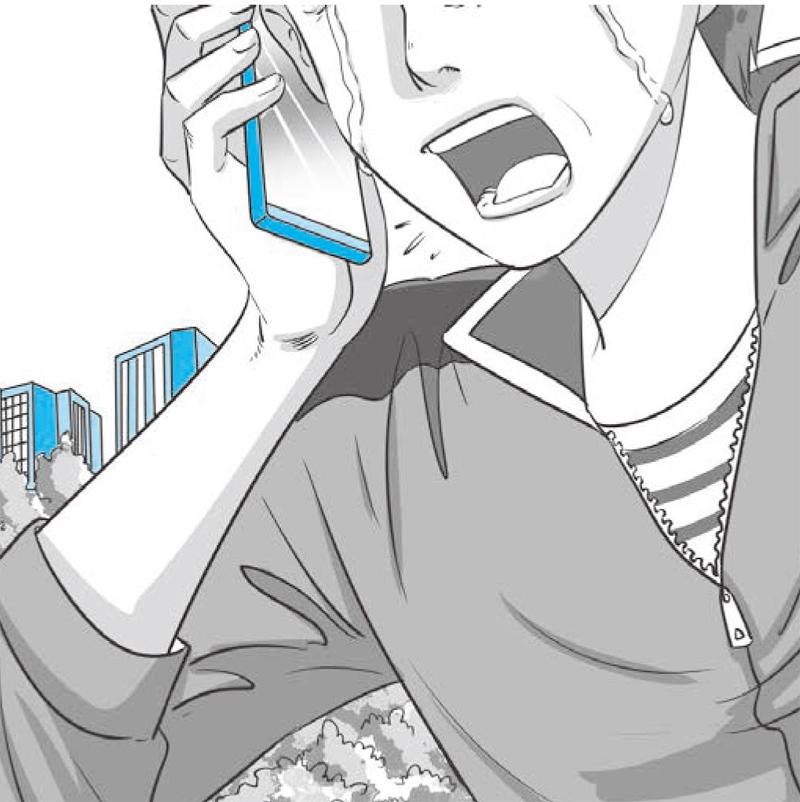
4
高考前的一個月,我做了平生最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我拿起电话。对刘先生破口大骂。
“你究竟是不是个东西?现在同学、邻居都在传你的丑事,你还知道丢人两个字怎么写吗?你就是个败类!”
我气急败坏,几乎把知道的所有脏话,全都不留余地地骂了出去。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能变成利刃,狠狠地剜进他的心房。
因为,我终于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也犯了那个“男人都容易犯的错”。唯一不同的是,这件事被揭露的时间点。恰恰是在我高考之前。
大杂院里。好事的邻居们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看见我和母亲总是故作同情地说:“唉,你们家的事情也真是……算啦,不说了。你一个女人也不容易……”
可我们刚走,她们就开始窃窃私语:“这夫妻之间的事情真的不好判断,说不定孩子他妈也……不好说,不好说啊。”
即使到了今天,我仍就记得当时母亲听见这些话时的表情。她苍白的脸上黯淡无光。那是一种刻意伪装成漠然的愤怒和解脱。
这个一直粉饰太平的家,终于大白于天下。而她也总算可以狠下决心,痛快地结束这段苟延残喘的关系。
那天,我最后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地告诉刘先生:“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爸爸!”
刘先生怒不可遏,他的声音一直颤抖“你……你再给我说一遍。”
“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爸爸。”
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我竟突然想起了黄毛。没错,就是那个初中时欺负过我的黄毛。我蓦然发现,原来旁人最多也只能伤我一分,只有家人才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人诛心。
5
进入大学以后,我经常陷入失眠。午夜里,所有的伤痛都蹿进黑暗,在波涛汹涌的情绪里四处流离。
我躺在床上,望着异乡冰冷的月亮,发现原来归属感才是我生命中最奢侈的东西。
我很少跟同学们提起我的家乡,更不愿同他们聊起父母。
记得父亲节那天,班长曾提议大家给自己的父亲打一通电话。当时所有人都拿起手机向父亲嘘寒问暖,只有我一个人愣愣地握着电话,一脸木然。
同学晃了晃我的胳膊:“我打算给我爸买一双凉鞋。你打算送给你爸爸什么?”
听完这句话,我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猛地站起身,直接冲出了教室。
教室外,艳阳高照,我却通体冰寒,仿佛每个毛孔都在不停向外释放着寒气。
我知道,自己可以轻易将刘先生从我的手机里删除,却终其一生都无法将他从我心底拉黑。
我听说,离婚后他和那个女人迅速重组了家庭,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恨他吗?不!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对他的感情早已超越了恨,这太过复杂,根本就无法用文字去归纳。
我只是嫉妒,疯狂地嫉妒。尤其是当听见身旁有同学抱怨她爸爸要求太严格的时候。当得知辅导员冒着大雨,去给他女儿买爱吃的蛋挞的时候,当看到公园里虎背熊腰的壮汉,提着小熊挎包,慈爱地跟在孩子身后的时候……
我真的好嫉妒。
我也曾安慰自己。人各有天命。谁又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呢?比起那些孤儿,比起那些残疾人,我所拥有的已经太多太多。
可是,每次当我路过街角的肯德基,看见别人一家三口温馨用餐的画面,曾经的自欺欺人都会不攻而破。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小,理应过了追责的矫情年纪,也明白我必须成为一个不动声色、坚强勇敢的大人,但即使再多理智,也無法抵挡别人父子或父女之间一个充满关爱的眼神。
过去,恐怕永远也无法过去。
6
在这如流云的世上,大概没有什么是恒久的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命运漂来什么,我便捡起什么。
曾经,我会因为旁人一句“你真坑爹”的抱怨,就当场翻脸。
如今想来,其实都怪我太过偏激。
我如同一只没有归属感的寄居蟹,偶尔才敢钻出硬壳,谨小慎微地跑上一圈,然后又飞奔回壳里,用一双小眼睛,默默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直到去年8月,我才渐渐有所改变。那时候,刘先生因为脑瘤突然住院。我得知消息,连夜搭飞机赶了回去。
请假,乘机,探病,所有动作一气呵成。连我都很诧异,自己做这些事的时候,居然没有丝毫犹豫,一切都如同本能。
似乎,他病床前的那个位置,理所应当就是我的。
我出现在医院那天,刘先生非常惊讶。长久的疏远,让我们同时都有些手足无措,彼此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四目相对,只是一秒,我便率先错开了目光。
手术前,刘先生的脸色格外苍白。他的嘴巴张张合合,仿佛执意要对我说些什么。
我凑过去,认真听了两遍,才听清他说的是一串密码。在他以为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向我托付了全部身家。
一瞬间,我泪流满面。
虽然,他不再被我叫作父亲,但他依旧是唯一能让我愿意用命去保护的男人。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那场风险极大的手术,最终尘埃落定,刘先生顽强地挺了过去。当他度过危险期后。我把那张银行卡,又悄悄地塞回了他的皮夹。
“我走了,刘先生。”
发完这短短六个字,我再次登上了归程的飞机。我没有跟他当面告别,不是不愿意,而是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后来我曾多次接到过刘先生的电话,但只是跟他寒喧几句就会匆匆挂断。
我觉得,有些人,还是永远留在岁月里吧。
往昔,我曾一直认为自己是这苍茫众生中,上苍最无暇顾及的那一个。如今,我却发现其实上苍待我还算不错。起码,它满足了我希望刘先生平安的心愿。
既然如此。我又何必不放过别人同时也放过自己呢?
世事哪有完美?我只愿,错轻微。
那些年少时不懂的事。我长大后终于懂得……
编辑/梁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