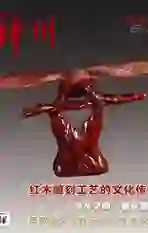严歌苓文学作品中的作者现象
2019-04-15王迩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严歌苓”作品被改编,搬上大屏幕,从《金陵十三钗》、《归来》到《芳华》,这位华裔女作家也被大众所熟知,而我也想在此分析下:
在传统意义上,她就是一个极出色、极具天才的女作家了,无论说是对戏剧性的把握、细节的选取,还是台词运用上。
首先,在情节的设置上,情节即所谓“故事”,故事讲得好,是一个编剧最基本的素养,严歌苓的素养极具张力,引人入胜,会让人有种想一口气把它读完的冲动,而且处处体现着她天才的构思能力。
比如,在《小姨多鹤》中,二孩妻子小许是因为日本人而流产不育,可最终却要妥协二孩和日本女人“传宗接代”。人物在这一因一果之中被命运拉扯,既展现出在抗战结束后的那样一个特殊时代下小人物的无力和深深的宿命感,又在这一来一回中体现戏剧张力,成为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
再如她的短篇小说《天浴》,下乡的城里少女文秀,因为爱干净而总要求要洗澡,但却因想要回家而出卖自己身体这种“肮脏”的手段,在这一黑一白,纯净与肮脏之间的转化中,小说主题也就被揭示出来了。
其次,是严歌苓在细节选取上的慧眼独具。冯小刚导演曾直言,他是看到严歌苓在《你触摸了我》中这样一段细节,就决定把其拍成电影了。“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冯导说,后来,这也成了《芳华》的电影海报。
是的,其实书中抓人的细节还远不至于此,或是《陆犯焉识》中描写的监狱生活,或是《天浴》中描写的老金的金牙,都曾让我不止一次的怀疑她是否真的在那里生活过。让我想到《陆犯焉识》中最打动我的一段:冯学锋后来是从陆焉识的回忆录中得知了老伉俪最后的情话——妻子悄悄问:“他回来了吗?”丈夫于是明白了,她打听的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虽然她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叫陆焉识。“回来了。”丈夫悄悄地回答她。“还来得及吗?”妻子又问。“来得及的。他已经在路上了。”“哦。路很远的。”婉瑜最后这句话是袒护她的焉识:就是焉识来不及赶到也不是他的错,是路太远。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极致的生活观察者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呢?在那个扭曲的时代,她把被压抑的人性写得淋漓尽致。不像有的伤痕文学的一味卖惨,也没有站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这近半个世纪的民族災难,而是以一种感同身受的而又不拘于其中的姿态去书写这个时代一切本善本美之物。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总是有着足以照亮黑暗的闪光之处,而他们身上的这些惊人之处又往往象征着那个时代,如《小姨多鹤》中小环与多鹤这两个女人,一个总说“活下去便是好的”,而另一个却总是希冀以自杀的方式来解脱,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性就在这一故事里被探讨,但是没有指责、没有批判,有的只有互相拯救、互相温暖。再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葡,她坚毅、果敢,单纯而又善良,凭一已之力将“父亲”寄养在窑洞之中,直至其终老。
而与这些单纯、善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相比,严歌苓的小说中也总有这么群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品行优良,而且总能“大义灰亲”,在最关键的时刻,出卖自己的“必坏分子”亲人。或是善良,医者仁心的孙少勇,或是伶俐可爱的冯月钰,都似乎逃不开这个魔咒。而正是在这一对比中,时代对人的摧残,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无奈,便显现出来了。
严歌苓她总是有这超乎常人的巧思,她的小说更显光彩。在《白蛇》中,她以三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一事物,而这三个视角的书写方式又不相同:小说通告与那个时代特有的审训体,这三种方式相辉映,不仅完美了这个故事,也使得读者更能深入时代本质去探求。这是在叙事结构上,而在事件的写作上,我印象最深的便是《第九个寡妇》中“灯火大殡葬”那一段。
她以“灯”这个物件来指代去为亲人收尸的人,这削减了事件中的残酷意味,而多了几分凄美的无耐。
以上三个方面,便是我归纳出的“严现象”的原因。
作者简介:王迩静(2001.5.22)女,籍贯:湖南省湘乡市,学校: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