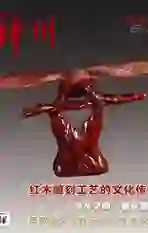《峡谷的夜》:女性的癫狂与复仇
2019-04-15蔡潇璇
摘要:日本小说《峡谷的夜》通過阿仙这一女性的癫狂与复仇,表达了作家对于日本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阿仙的癫狂根源于传统家制度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身份认同的丧失,而其以孩子作为武器的复仇方式,则是对既定传统秩序的嘲讽和对于希望的绝望。该小说是对文学史上“狂人谱系”内涵的深化与延展,也是现代思潮中一种独特的启蒙言说。
关键词:女狂人;癫狂;复仇
江口涣的《峡谷的夜》是由开创中国“狂人谱系”的鲁迅译介到国内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女性的癫狂与复仇:农村妇女阿仙,因遭丈夫背叛和失去儿子导致精神失常,向“我”掷去尸孩施以复仇。“阿仙”与《祝福》中的“祥林嫂”可谓属于同一“女狂人”系列,作家通过女性悲剧命运和癫狂状态的书写,表达了对封建传统秩序的控诉和反抗。
一、癫狂:现代性话语
“癫狂”是作家在作品中戏剧安排的形式,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神秘性、非理性的怪异图像,实质上承载着一种反叛性的真理,它凝聚了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审美观照和理性思索,具有悖论式的美学特质。癫狂者因在生理或精神遭受某种程度的迫害而呈现出极端状态,但正因如此,个体才能无视任何权威和社会道德规范,显示出文明在他身上的溃败,从而引起人们对既定文明和秩序的疑惑和焦虑。明治35年《文艺俱乐部》杂志刊登的《狂人日记》社会问题小说,标志着“狂人”在明治文学中的正式登场,并逐渐发展起了自身的现代性话语系列。
二、“想做奴隶而不得”:身份认同的丧失
疯狂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1]71阿仙的疯癫是其悲剧的最终呈现形式。日本的家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丈夫掌握了权力,而妇女被贬于家庭和社会的最底层,成了家族继承人的生育工具。中国传统儒家的女性观也给日本带来影响,本土与外来封建文化的双重夹击使得女性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早在律令时代,儒家的“三从四德”等礼教思想就已传到日本,并逐渐成为日本妇女的生活准则。日本还模仿中国的女训出版了《女大学》《女诫》等规诫女性的书籍,其奴役和歧视女性的立场甚至更为偏激极端。此外,本是宣扬母亲在家庭中的教育作用、体现西方现代性别分工思想的“良妻贤母”的观念,传入日本后也为本土思想所浸染,而发展成了为封建传统服务的儒家女性观。明治32年政府颁布《高等女学校令》,标志着培养儒教型良妻贤母已上升为国家规定的女子教育理念。可见在这强大的性别政治与伦理制度之下,女性背负着重重封建枷锁。
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2]225在这强大的性别政治与伦理制度之下,女性被禁锢在传统的铁屋子里,她们比男性背负了更多的历史、道德、文化、伦理和社会的重负。女性甘愿沦为服从的奴隶,自觉遵循男权秩序以求稳定生存状态。阿仙承受着父权制度下“包办婚姻”的悲剧——丈夫的不守规矩、懒散,生计的艰难和家长的刁难。在强调女性依附性的封建传统中,婚姻是女性得以证明自身存在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她们通过夫和子获得自身的身份认同。阿仙恪守着作为妻子的本分,以“良妻贤母”的儒家女性观规训自身,以求讨好丈夫和封建家长,却仍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丈夫的背叛。她作为一个外村人,无法从丈夫身上获得身份认同,在家中毫无立足之地,这是引发其走向疯癫的第一层文化要素。
对于做惯了奴隶而言的传统女性,她们自有一套适应男权规则的生存之道。阿仙并未放弃挣扎,“倘若生了孩子,这便引转男人,静了心,同时和姑的关系,也就会变好罢”[3]515她将希望寄托于腹中胎儿,专为孩子活着。在封建伦理文化中,妻子没有独立人格,只有成为了母亲,才能确立和巩固家庭地位。阿仙试图通过繁育后代将自身与丈夫的家族建立起血脉的联系,从而获得丈夫家族和社会的认同,以求“暂时坐稳了奴隶”。然而江口涣将阿仙推向绝境——孩子夭折了。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封建文化语境中,阿仙被动地丧失了妻子身份和母亲身份,从而丧失了作为女性存在于社会上的价值,沦为一个“女狂人”大概是她进行抗争和复仇的唯一出路。
三、复仇:对希望的绝望
在文学之中,“狂”提供了一个呐喊的空间,标志着个人对一脉相承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规则的反叛。尤其是在向来恪守温顺贤良的女训的女性身上赋予其癫狂的状态,更能以一种反传统、反逻辑的边缘者身份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冲击,也更能传达作家的启蒙话语。
江口涣极力渲染峡谷中阴森恐怖的氛围以衬托“女狂人”的疯癫可怖,显现出其复仇的决绝性。阿仙的复仇也呈现出柔弱——刚强的鲜明对比,凸显出悖论式的艺术张力。她的形体是单薄无力的:“缠着白衣的裸体上,衣服上几乎没有附体”[4]506。但她的复仇是刚强有力的:“迸涌出来似的惊骇与忿怒和憎恶的呻唤,用了吐血一样的猛烈”[5]509然而她越是拼命的挣扎与反抗,便越突显出女性的悲哀与无助。阿仙用孩子尸体作为复仇的武器,向扼杀女性话语权的男权世界施以复仇,这具有黑色幽默的反讽意味。此前阿仙试图通过孩子来获得身份认同,证明自身生存的正当性与价值,孩子是她婚姻生活中的精神支撑,同时孩子也象征着新生的希望和力量。如今阿仙将孩子作为唯一武器投向世人,意味着她对这希望的绝望,也表达了对这既定的生存规则的嘲讽。
江口涣塑造了在日本封建家制度文化下“想做奴隶而不得”,而最终走向癫狂和复仇的女性形象,试图通过“狂人”这一非理性的意象来反思传统和进行现代性的启蒙。“狂人”是过去传统的反叛者,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而孩子应当代表着希望和光明,而不应负担着历史的罪恶与鬼气。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05.
[2]鲁迅.鲁迅全集 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2.
[3][4][5]鲁迅.鲁迅全集 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2.
作者简介:蔡潇璇(1997-),女,汉族,广东揭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