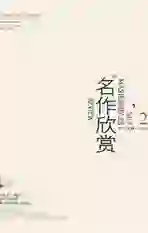论“隔”与“不隔”对赋比兴价值认定的偏颇之处
2019-04-15赵晓莹
赵晓莹
摘要:《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重要的词学批评著作。在该书中,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包含“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隔与不隔”“写境与造境”等。其中,“隔与不隔”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该命题是受西方“直观说”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古诗词进行解读和阐释。王国维先生认为“不隔”属于价值肯定的审美范畴;“隔”属于价值否定的审美范畴。但是,本文认为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论述“隔与不隔”时,对于中国传统诗学文论中赋比兴的价值认定却有失偏颇。
关键词:隔与不隔 赋比兴 王国维 直观说
一、“隔”与“不隔”的论述与分析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中“隔与不隔”是“境界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在《人间词话》的第三六则、三九则、四十则、四一都曾明确提到了“隔”与“不隔”。
在王国维先生的文艺理论批评中,“隔与不隔”是一个重要的词学批评概念:“隔”者,诗词写情、写景之病,表价值否定;“不隔”者,即诗词“妙处”所在,表价值肯定。但是何为“隔”与“不隔”?王国维书中只是举例说明,在理论上并无明确界定。近现代以来,诸多文艺批评家对于“隔”与“不隔”,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上面见出。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模糊零乱或空洞,情趣浅薄或粗疏,不能在读者心中现出明了深刻的境界,便是隔。”朱光潜先生认为情趣和意象是诗歌的两个重要因素,“隔”与“不隔”是在阐述二者关系的状态。叶嘉莹先生的观点则立足于作者的角度,认为“不隔”是作者的真实感受能够被真切地表达出来,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者的情愫感同身受;作者有真切之感受,且能做真切之表达,使读者亦可获同样真切之感受;相反,如果作者没有真实感受,或者真实感受难以被真切地表达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之为“隔”。叶嘉莹先生在这里把“隔”与“不隔”这对命题理解为创作过程中作者是否投入了自己的真切感受,是否做出了真切表达。
二、“隔”与“不隔”对比兴的疏远
以上各文艺理论家对于“隔”与“不隔”都做出了自己的界定与分析。然而王國维先生在论述“隔”时,所举例子:“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等,细细思量,可发现都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运用了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比兴手法。在比较美成与白石咏荷之作时写道:“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盖因美成两首词有“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之句,以“舞衣”“红衣”来比喻荷花,运用了拟人手法,不如周美成白描手法直抒物理。王国维先生在论述“不隔”时,认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夜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在所举“不隔”的诗词例句中,也可看出有一共同点,即主要是运用了赋体白描的艺术手法。唐圭璋先生称此为“专赏赋体”。由此可见,关于“隔”与“不隔”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与“语语都在目前”的区别。要语语都在目前,避免隔,就是要用通俗的白描艺术手法。王国维以“隔”与“不隔”来定词的优劣,讥讽白石词有“隔雾看花”之恨。但是白石的《暗香》《疏影》两首词健笔写柔情,在“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等一些运用拟人、比喻、用典的艺术手法背后,寄托着作者的家国之悲和身世之叹。唐圭璋先生称赞“出语峭拔俊逸,格既高,情亦深,其胜处在神不在貌,最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刘永济认为正是因为白石作词运用比兴手法,将身世之感贯穿于咏梅之中,才深得范成大的赏识。词意幽微婉转,比赋体白描下的直露无余要好。且若是艺术才能不够,白描作品往往最容易流于浅俗鄙陋。从吴文英到周密、王沂孙多是托物言志。藏情于诗词内,欲露不露,是反复缠绵,深加锻炼的结果。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有“隐”“显”之论:“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以此论词,词之妙处在于意内而言外,以隐胜,不以显胜。托物言志,寓情于景。此乃词在比兴手法下表现出的隐秀之妙处,王国维反以“隔”病之,难以认同。
“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还可看出“隔”与“不隔”也是对词史的价值判断。王国维认为唐五代、北宋词为“不隔”,南宋以后词则多“隔”。唐末诗衰词兴,词之初起,词人作词未曾过分修饰雕琢,词风真切自然,保留着相当浓厚的生活气息。杨海明先生《唐宋词史》中说:“王国维论词,曾提出过‘隔与‘不隔的论题。借用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说,民间词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之间,是关系密切而‘不隔的。举凡时政大事,生民疾苦,战争动乱……它都有所描绘有所反映。”受此风格影响,北宋词大多相当率直地表达情感,时有真趣。及至周邦彦,词法遂立,南宋诸家作词更是精雕细琢,律精语密,使得词体发展受到限制;且姜吴典雅派词人作词多用典故代字,王国维病之为有隔而境界不高,词道逐渐凋敝。
王国维先生在论述“隔”与“不隔”时,“不隔”为价值肯定的范畴;“隔”为价值否定的范畴。在其书中所举“隔”的例子多是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不隔”的例子多是用赋体白描。我们或许可以由此看出,王国维先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比兴手法存在某种价值认定上的偏颇。赋体白描固然重要,“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感慨人心深处的悲凉、无奈,是至真至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艺术境界浑然天成,动人心弦,给人以或幽美或壮美之感受。然而在历来诗歌创作中比兴手法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唐圭璋先生在《评(人间词话)》中说:“赋体白描,固是一法;然不能谓除此一法外,即无他法也。比兴亦是一法,用来言近旨远,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慨遥深,固不能斥为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