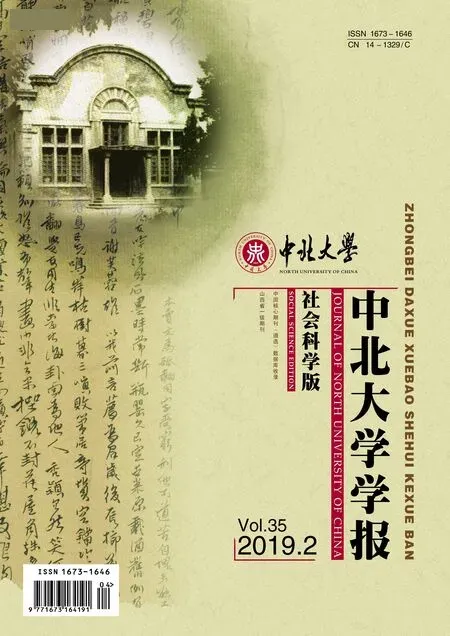李有《古杭杂记》成书背景探赜
2019-04-08石勖言
石勖言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1 《古杭杂记》的版本与体例
《古杭杂记》是元人李有编撰的以南宋史事为题材的作品, 现流传有两个版本。 其一源自百卷本《说郛》卷四(以下简称《说郛》本), 题署为“《古杭杂记》四卷, 元李有, 字听贤, 庐陵人”, 共19条, 各条无标题。 关于作者李有, 除此一行题署外, 别无文献可征。 此本在明清两代被广泛传刻、 传抄, 先后收入《古今说海》《历代小史》《雪窗谈异》《八公游戏丛谈》《重编说郛》《绣谷杂钞》《说林》《学海类编》《逊敏堂丛书》《小渌天丛钞》等多种丛书。 其二为《新刊古杭杂记诗集》四卷(以下简称《诗集》本), 不题撰人, 共49条, 每条有标题。 修《四库全书》时由浙江汪启淑家征得一部抄本, 列为存目, 该本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 八行二十字, 有翰林院官印。 台北故宫又有蓝格旧抄本一部, 为原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 传自晚清翰林夏孙桐藏书, 十行二十字。 光绪年间, 丁丙另得到汲古阁抄本一部, 将之与《说郛》本一并收入《武林掌故丛编》[注]丁丙所得汲古阁本卷端题“新刻古杭杂记诗集”。[1]418, 乃成今日通行之本。
从《说郛》本题记可知, 陶宗仪所见的《古杭杂记》原书与今存《诗集》本卷数相同, 皆为四卷, 而检按内容可见, 两本互相重合的条目只有三则, 即《说郛》本开篇的前三则《一担担》 《天目山崩》 《函首乞和》[注]《说郛》本各条无标题, 此据《诗集》本标目。, 它们分别位于《诗集》本的卷一与卷四, 格式互有差异(详下)。 虽然重合度不高, 但《诗集》本的目录中有两段识语, 足以说明两个版本间存在同源关系。 这两段识语乃自元刊本迻录而来, 其一云:“一依庐陵正本”; 其二云:“以上系宋朝遗事, 一新绣梓, 求到续集, 陆续出售, 与好事君子共之。”[2]93首先, 如前所示, 李有正是庐陵人氏。 其次, 在识语中书坊表示今存《诗集》乃是一系列关于“宋朝遗事”的出版物的第一帙, 此后更有续编。 而三则重合的条目集中于《说郛》本卷首, 便可说明, 陶宗仪很可能是在进行抄撮之时, 先从《古杭杂记》的初编中选录了此三则, 之后的16则, 当即摘自今已不存的《古杭杂记》后续部分。 四库馆臣便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案陶宗仪《说郛》内亦载有是书, 题作元李东有撰, 然与此本参较, 仅首二条相同, 余皆互异, 未喻其故。 观书首标题, 殆《古杭杂记》为总名, 而诗集为子目, 乃其全书之一集, 非完帙也。[注]“李东有”之“东”字盖为衍文。[3]1234
四卷本《新刊古杭杂记诗集》之所以以“诗集”为题, 是因为此书体例乃“杂录南宋逸诗及歌谣等作, 各记实事于题下”[4]73, 很像诗词本事类的著作, 四库馆臣即认为其形式摹仿《本事诗》。[3]1234书中每条大抵举一首或两三首诗词(卷四若干条目只有一联诗或一些对句, 末条《射潮箭》则是一段碑铭), 侑以一段或几段叙述诗歌本事的文字, 叙述文字低一格排, 眉目颇清晰。 而《说郛》本的编撰形式则与之不同, 诗句不是单独列出而是夹插于正文中, 与一般的诗话著作类似。 且以全书第一则为例:

表 1 《古杭杂记》首则两版本对比
从表 1 可以看出, 这两种版本之间明显存在着改编与被改编的关系。 从《诗集》本书名中的“新刊”以及“一依庐陵正本” “求到续集”的刊语来看, 在其之前已经有“庐陵”本行世, 而这个“庐陵”本的写作格式应当更接近于《说郛》本。 理由如下: 在《诗集》本的各则内, 诗句与叙述文字虽然分开, 文气却都一脉贯注。 同时, 诗句与叙述语的相对位置并不固定, 叙述语或在诗前, 或在诗后, 有的条目记载了不止一首诗, 叙述语则与诗句交互错出。 偶尔, 叙述语中还用“云云”代替诗句。[2]103这些迹象似乎指向一种可能性, 即《诗集》的编者乃为了醒目的考虑, 才将每则中的诗句抽取出来, 提行刊刻, 相应地也对正文进行了少许改编, 随之在书名中增加了“诗集”二字以表示与原编的差异, 并在改编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刊落了原撰者李有的姓名、 字里。 元末陶宗仪得到的全本《古杭杂记》, 大约则是庐陵一系的原本。 这一假说也可以解释为何陶宗仪所见的包含了续集的全本共计四卷, 而今存仅含原书初集的《诗集》本亦为四卷的问题, 盖《诗集》本在进行改编时, 顺便重新分割了原书的卷帙。
陶宗仪所见的《古杭杂记》, 从书名上看更像一部野史笔记。 《说郛》本所抄录之19条目可分为两部分, 前12条皆与诗词有关, 与《诗集》本内容相似; 后七条则不再包含诗词, 仅记载南宋史事。 这或许意味着, 续出的《古杭杂记》在编刊到某一阶段后转变了体裁, 起初仍是诗话, 后来则变为史料笔记。 实际上, 虽然《古杭杂记》最初的部分是以诗话的面貌出现的, 但是从一开始, 编者的兴趣便更侧重于历史而非诗歌。 四库馆臣将此书著录于小说家类, 而非诗文评类, 也许便是读出了书中对于历史故事的特别关切。 书中多数条目记载的并非是诗歌背后的个人琐事, 相反, 大都与朝廷政治关连, 如御制诗、 政治美刺诗, 许多诗歌直接反映了理度两朝的政治历史事件。 对读者而言, 可借由阅读诗词而阅读南宋的史事、 掌故。 尤其可注意的是, 编者亦常在叙述语中发表褒贬的意见, 这些议论皆非率尔操觚的闲言, 往往既有鲜明的观点, 又饶有意味, 例如:
姚勉为状元, 常作是词, 用六更事。 昔宋太祖以庚申即位, 后有五庚之说。 五庚渐周, 禁中忌打五更鼓, 遂作六更。 前辈歌诗闲有言六更者。 理宗宝佑癸丑临轩勉作, 大魁赋此, 然则五更既可加为六更, 六更之尽不可复加欤?[2]95
(卷一《六更鼓》)
西湖苏堤上有三贤堂, 杭人奉祠白香山、 林和靖、 苏东坡之所。 稼轩辛幼安帅越时, 刘改之寓西湖上, 稼轩送以酒物, 就招其过越, 值雨, 改之不果去, 答以《沁园春》。 后人谓改之此词与一大鬼说话, 谓三贤皆诗仙, 改之心慕乎三贤, 是亦精神之感召, 故心声不觉如是之发尔。 不然, 孔子梦周公亦可谓之与鬼说话乎?[2]95
(卷一《与鬼说话》)
孔门弟子具称夫子以字。 自唐以来, 诗人多立号, 后人尊之而称其号。 二三十年来, 虽贫儒下士以一斋一轩自名者, 人辄以为道号而称之, 况一命以上者乎?有题于旅壁者, 乃草茅之言, 似亦当理云。[2]101
(卷三《道号》)
此类论说皆可谓得风人之旨, 文笔也非常老练, 绝非一般书坊作品雇佣下层写手随意敷衍者可比。 《诗集》本之外续出的部分, 对政治的关切仍然一以贯之。 《说郛》本的前12条中, 讽刺了袁樵卖酒、 贾似道推排田亩等事件; 后七条脱离了诗话体裁的笔记, 也无涉委巷丛谈, 而俱为朝政、 礼法、 风俗之事, 持论颇为严正, 既批判社会道德, 又指斥史弥远、 贾似道等权相。 可见无论体例如何, 《古杭杂记》的编者李有都是本着著史的态度精心结撰此书, 而最能体现此书史的性质的莫过于《诗集》本卷三《上马裙 泪妆》一条:
理宗朝宫中系前后掩裙, 名曰上马裙, 又故以粉点于眼角, 名曰泪妆, 四方效颦, 其亦过北之谶乎?古云:
宫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 宫中好广眉, 四方且半额。[2]103
此处叙述理宗朝故事, 诗歌却用汉代《城中谣》, 显然, 本则的主旨并不在于诗, 作者意在评论历史, 而诗话之形式完全成了一个幌子。[注]此种编撰形式, 在宋末元初并非独一无二的特例。 蒋正子的《山房随笔》便与此类同。 其书为史料笔记, 多记宋末元初时事, 但亦采取了诗话的形态(仅有一条例外), 借诗讲史, 与《古杭杂记》盖为同一书籍文化之产物。
2 《古杭杂记》与太学生
《古杭杂记》亦有一些条目记士林和民间的故事, 如卷三《西湖柳》, 记女子为士人殉情事, 近似传奇小说。 此外一个重要主题则是关于太学生的种种逸事。 《诗集》本关于太学的条目有《太学前廊别厨》 《归美》 《养鸽》 《李瓘挂冠》 《无故犯罚》 《朱圈题名》 《函首乞和》 《善对》 《代言之失》共九则, 占全书将近五分之一。 《说郛》本有三则也与太学生有关。 四库馆臣评论此书“多理宗、 度宗时嘲笑之词”[3]1234, 所谓“嘲笑”盖有两重含义, 一则指对于朝政、 奸臣的讽刺诗, 例如书中数条讥嘲贾似道的故事; 一则指带有谐谑性质的条目, 关于太学生的若干逸事便是如此。 例如《太学前廊别厨》一条:
太学旧例, 职事颇侵诸斋食。 盖由厨子辈观望, 欲以献勤, 是致诸斋食味不丰, 有士人作俚语以戏前廊云:
尀耐前廊烝拯正职, 减我外厨乘脤盛食, 教人没个轻顷磬吃, 愿得天雷俜品并霹。[2]95
又如《无故犯罚》一条:
率履斋生一夕集饮, 一人歌唱声喧, 直宿李官闻知, 令甲头取问。 直日供以读书声高, 非唱歌也。 又令供读书声高人姓名, 时同集者俱有校定, 偶一同舍在富阳县就馆, 未有校定, 遂以其姓名供上, 后果遭罚。 同舍戏作诗曰:
书读富阳县, 声喧率履斋。 闭门屋里坐, 祸从天上来。[2]101
这些有趣的逸闻说明编者接触到不少关于太学生的一手资料。 此外若“郑文妻词”一则云:“此词为同舍见者传播, 酒楼妓馆皆歌之, 以为欧阳永叔词, 非也。”[5]84也可以看出编者对于太学生群体有相当亲切的了解。
戴表元《送曹士弘序》记载了庐陵人与南宋杭州太学、 京学的密切关系:
岁壬戌, 余初游武林, 识庐陵欧阳公权先生于秘书之署。 其人清纯简重, 虽居蓬莱道山间, 而布袍蔬食之气, 郁郁然见于眉睫。 余时年少自衒饰, 每从其所归, 未尝不发惭面汗也。 以杭学博士弟子, 识拜刘先生会孟。 会孟亦居庐陵, 其人英爽峭迈, 下笔造次数千言不休, 而蹑之无复近世轨迹。 至于清谈滑稽, 四面锋接, 一时听之, 略与李谪仙人何远。 然举足不忘欧阳先生, 十有八九语称吾师。 当是时, 欧阳先生以迂废, 高卧里巷不出。 余受刘公之爱, 于文字间特厚。 未几刘公亦归。 而余年长, 四方之游从日以泛滥, 其士大夫自庐陵来而喜与余交者, 则以二先生之故焉。 最后入太学。 太学之徒庐陵为多, 余一皆识之。 大抵其人之恢中强项、 敦志业而好洁修者, 欧阳公之教也; 其人之英资高裁、 多风声而精体要者, 刘公之法也。[6]185
戴表元初为京学即临安府学生员, 而刘辰翁于咸淳元年(1265年)为京学教授, 故二人为师生关系。 南宋京学吸纳外地游士, “凡着籍其间, 得以类申补太学诸生, 人以比古之外靡”[7]309。 戴表元大约也借由此途于咸淳五年(1269年)升入太学, 于是又发现太学中麇集着众多庐陵士子。 欧阳守道、 刘辰翁等庐陵名公在杭州成为侨寓乡党领袖, 庐陵人也通过太学与京学在杭州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到元初, 太学虽然已为陈迹, 但师生之间的联系仍然得以延续。 汪元量行脚至庐陵, 便特意拜会了太学旧友。 他与赵文曾为同舍生, 寄诗云:“六馆风流不可寻, 形骸土木泪痕深。 有时咄咄空书字, 俗子宁知我辈心。”[8]127-128刘辰翁之子刘将孙为汪元量赋《西湖棹歌》十首, 其中也写到太学今昔景象:“春燕弟子头船棝, 三学诸斋日日争。 宝佑坊街无角伎, 西湖书院有书生。”[9]72而在杭州, 故宋太学、 京学生群体更加活跃。 南宋投降时, 元军主帅伯颜命令“学中要拣秀才人”[8]15, 将100名左右的三学生员掳到北方, 道途亡死者众, 至京仅46人, 两年后得官南还的只剩18人, 都回到了江浙境内, 有人还被授予了杭州教职。[10]173-174,[11]182多数三学生员则躲过一劫, 学废士散, 有的人就此归乡, 但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了杭州。 据郑元祐记载, 内附之初, 游显为江浙行省平章来杭, “时三学诸生困甚, 公出, 必拥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注]原文作“尤公”, 盖为“游公”之误, 但据姚燧《荣禄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 游显乃于至元十四年以浙西道宣慰使来杭, 至元十九年方升任江淮行省平章, 次年即薨。 任平章时, 行省治所在扬州。 与郑元祐所记颇为不合, 暂存疑。[12]364可见逗留者为数不少。 在元初杭城的文人群体内, 许多名士拥有故宋学校背景, 如诗坛名家浦城人杨载、 衢州人吾衍, 都出自于定居临安的太学或京学生家族。 在月泉吟社中拔得头筹的福建人连文凤, 也是由京学入太学的生员, 他在元初的杭州度过余生, 与同学刘汝钧、 丁强父等人保持着往来。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 连文凤、 刘汝钧等太学舍友还发起了祭奠徐应镳的活动:
丙子二月二十八日, 迫太学生上道北行有日。 经德斋徐君应镳字巨翁, 三衢人, 为文祭告土神, 携三子登楼纵火自焚, 不克, 乃自沈公厨之井。 长男琦, 二十一; 次男崧, 十一; 女元娘, 九岁; 同溺死。 后十年丙戌, 三山刘汝钧君鼎、 连文凤伯正率同舍举四丧, 焚而葬于南山栖云兰若之原, 私谥曰正节先生。[13]365
这是方回对此次事件的记录, 方回在咸淳年间曾任太学博士, 故以教师身份受邀参与此事。 同祭者还有林景熙、 何梦桂等太学同舍生, 各有诗文纪念此事。[14]72, [15]67, 153这次义举是一场太学师生的集体行动, 显示了亡国后的十年间, 学校这一关系网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不少故宋太学生对学校怀有深厚感情, 例如福建人叶福孙, 入元后便孤身寓杭, 终老于太学故址之侧。[13]682有许多人乐于谈论太学故事, 乃至整理太学文献。 戴表元记述故太学生杨鹏举云:“余为咸淳诸生时, 杨鹏举去太学久矣。 然以乡里前后辈, 见余辄说太学不休口。 此其天资笃厚, 绸缪旧故, 岂如他人朝游暮忘、 若逆旅相逢之为哉?去仕各二十年, 始以所编《太学登科题名》示余。”[6]262林景熙为周元龟作墓志铭, 嫌行状所载有阙, 于是奋笔补充了两件史事, 一件为太学六士, 一件为推排公田, 正是对于宋末太学生群体而言感触最深的政治事件。[14]439-441可见留杭的太学、 京学生们积极地讲述与传播着自己的历史记忆, 因此, 《古杭杂记》的庐陵编者不难从他们的社交场中得到这些原始材料, 这样的推测虽然尚无绝对严密的论据, 但应当不失为合乎情理的解释。
3 《古杭杂记》与庐陵采诗之风
除了关于太学的佚闻以外, 《古杭杂记》的主体内容仍然还是有关杭州的“宋朝遗事”, 庐陵书坊究竟是如何得到这些史料的呢?显然, 庐陵与杭州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交流的渠道,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元代庐陵地区的另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即“采诗”之风。
所谓“采诗”, 就是收集各地诗人的诗作, 将其编定成书的行为。 这一行为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采诗官与《诗经》, 但是元代的采诗活动性质已然大为不同, 纯粹是一种民间活动, 并主要兴盛于江西地区, 江西内部又以吉安路即庐陵为尤盛。 元初的庐陵人赵文便说:“今采诗者遍天下。”[16]14刘将孙也说:“近年不独诗盛, 采诗者亦项背相望。”[9]89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许多学者关注, 杜春雷[17]、 杨匡和[18]、 黄二宁[19]、 史洪权[20]等各有论文, 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 元人采诗的方法, 主要是走访各地大小诗家, 向他们索要作品。 如安成(即吉安路安福州)彭丙翁、 胡复初二人出门采诗, 首先便来到吉安府城拜访当地诗坛领袖刘辰翁, 刘辰翁“一见, 喜其质可深造, 繇是倾囷倒廪以付之”[9]99。 另一种方法是从诗集中选录作品, 如傅若金《邓林樵唱序》写道:“庐陵邓彧之, 尝采诗至岳阳, 得临湘邓舜裳所著集曰《邓林樵唱》者, 来长沙以示余。”[21]321可见采诗人不仅征求零散诗作, 还会以整部诗集为单位进行采访。 第三种方法是从各种文献载体上搜辑逸佚, 例如抄录题壁作品。 刘将孙便曾向一位采诗人提出如下建议:“往先君子尝见教云: ‘少时京华道中, 爱观壁间留题, 亦有佳处。 玉山旅邸有题一词者, 中两语云:‘如许凉宵无可恨, 恨只恨故人头白。’ 洎再过, 则失其壁矣。’……念哉, 学中, 虽壁间者, 且不可失也。”[9]90总之, 江西采诗人力图通过种种手段, 几欲将天下诗歌网罗无遗。 风气流行之下, 采访的对象进而越出诗的范畴, 也有人开始采词。 刘将孙便曾为萧学中、 饶克明两位采词人作序, 其中写道“年来采诗多, 未有及词者”[9]90, 可见采诗之文体扩展的次序。 萧、 饶两人所采的词集今虽不存, 但现存《精选名儒草堂诗余》一书, 即为“庐陵凤林书院”所辑, 有大德刻本存世, 值得参考。 此外又出现了采文者, 如刘孟怀便曾周游四方访求诗文, 编为《崇雅》一集, 其采访重点是宋代讲学家一派的文章。[22]179-180《崇雅》集虽然也已亡佚, 但今存安福人周南瑞的《天下同文集》, 也可视为同类的标本。
为什么江西地区会形成采诗(词、 文)的风气?上引四家文章都尝试给出了一些解释。 杜春雷、 杨匡和、 黄二宁三位学者的思路比较接近, 概括言之, 从背景上说, 是因为江西地区文化自古发达, 诗坛创作繁荣, 士人有较强的文化担当意识, 并且崇尚游历, 士人领袖也鼓励采诗活动, 等等; 从目的上说, 采诗一是为了保存文献, 二是为了相互交流增进诗艺。 这些说法确有一定道理, 但仍存在许多疑问。 江西诚然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 但何以文化的兴盛会表现为采诗的活跃?其次, 保存文献与交流诗艺的确可以成为采诗的动机, 但仅凭这些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采诗活动独盛于江西的事实。 江南其他地域的士人也不乏文化担当、 文学交流意识, 但采诗者的数量却远不及江西。[注]据黄二宁文所统计的元代25名采诗者中, 江西人21名, 浙江人二名, 福建人一名, 剩余一名籍贯不详。因此, 上述理由尚欠缺充分的说服力。 除了以上解释外, 黄文还提及“元代还存在采诗功利化的现象, 将采诗作为求仕干谒、 售诗谋利的手段”[19], 但只是附带论及。 而史洪权则在此思路上有所推进, 他将采诗者分为“江湖采诗邀利者”“有意千载之事者”两类, 其依据是揭傒斯《与太虚书》, 揭傒斯在此书中向友人介绍来自江西进贤的采诗人杨显民:
进贤杨显民, 其兄弟叔侄皆爱吟, 且愿得当世作者之诗, 刻而传之。 而先生之作, 企慕已久, 望尽取得意而可传者, 并录而归, 幸勿以江湖采诗邀利者视之。 此公实有意千载之事者, 非其人者, 决不与兹列者也。[23]501
史文据此并举出若干例证认为, 元代有一种“出于职业的需要”的采诗者, 旨在邀名求利, 借采诗结交达官权贵与文坛豪隽; 同时有另一种采诗者, 其动机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 旨在以诗存人、 互通诗艺, 抑或借采诗替本地诗学张目。[20]
史先生的这一区分无疑是有益的, 而立论则较为谨慎。 实际上, 揭傒斯的言论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实, 即认真严肃的采诗者实属凤毛麟角。 尽管文坛名公们赠予采诗者的诗文多将他们比作先秦采诗官, 似乎其目的主要是观风俗、 察民情, 但这只能是一种修饰的话语, 因为这在元代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如果采诗的主导目的是纯文学的, 恐怕也很难形成一种社会现象。 所以, 江西采诗之风的社会根源, 总体而言应该归因于利益驱动。 所有采诗活动的最后一步都是刊刻。 如吴澄《诗珠照乘序》云:“庐陵郭友仁, 穷闾之士也, 以采诗自名而行四方。 诗有可取, 必采以去, 锓之木而传之人, 俾作诗者之姓名炳炳辉辉, 耀于一时。”[24]371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叙述葛生:“遂溯三峡, 至于蜀都而止焉。 求名卿大夫、 文雅之士, 居数年, 得诗六百余篇。 归庐陵, 将刻而传之。”[25]498以诗存史、 以诗存人的作用, 最终都需通过出版得以实现, 采诗者在外漂泊可以长达数年, 但最终都要回到家乡, 将作品锓枣刊行。 因此, 采诗行为必然要依托于江西特别是庐陵发达的刻书业。 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一文虽然与采诗无涉, 但很好地反映了庐陵文化事业之影响力:
丙子春, 江南方被兵, 而云南独于此时落成新宫, 始行释奠礼, 此岂非天哉。 于是五十年, 然礼器周陶, 岁岁春秋取具有司。 廉访副使安公固始议范金, 而难其费, 始刻《孝经》以摹本市民间, 积钞万一千缗。 会廉访使汪公寿昌至, 是其议, 以江西治铸良合古制, 白之平章囊嘉岱。 合中庆路儒学正孙彬、 学录杜余庆, 驰驿江西, 檄行中书省、 廉访司。 江西以吉安为尤良, 以总管杜公元忠历任宪使, 檄公董其事。 公被檄, 以国家崇明祀怀远人为重, 申饬惟谨。 而达噜噶齐托果齐, 尝宣慰云南, 尤喜赞成之。 选良工, 考古制, 为簠、 簋、 登、 铏、 爵、 玷、 尊、 勺, 凡五佰六十有八, 用铜十六石三钧有奇, 缗五千六百七十缗有奇。 既成, 仿古而尤工, 以其余财购经史子集以归。 公喜形于色, 曰:“此庐陵工师之良, 典籍之富也。 今四方名能文辞可传远者, 亦莫如庐陵。”求记以昭示无穷, 则相与属笔于刘岳申。 既辞弗获, 则谂于使者曰: 自古圣人皆修文德以来远人, 而后世壹之以威武, 至有求书籍于中国而不与者。 元德如天, 远人既来, 而省宪大臣知求学校礼器于钱谷甲兵之外, 使者知求书籍于礼器之外, 吾庐陵太守于簿书期会之间, 又知承流宣化于封疆之外, 将天地之气藏蓄而不泄, 以待今日耶?[22]246-247
云南使者不远万里专程来到庐陵铸造礼器及购买书籍, 可见庐陵的对外文化交流颇为兴盛, 文化产品行销各地, 而书籍正是其中重要品类。 庐陵作为江西的出版业中心, 经营经史子集各类图书, 书籍市场对于诗文选集理应存在一定需求, 采诗者们收获的作品也可在此得到便捷的刊刻。
采诗之风的另一个重要成因, 诚如黄二宁先生所指出的, 是江西人的远游风气。 此风之显著, 本地与外地士人都有亲历体验, 袁桷曾云:“今游之最夥者, 莫如江西。”[26]1187庐陵当地人也认为:“日吾党士之东下者舟相望, 所可知者已百许人, 何如其多也!”[9]109虽然间有批评的声音, 但即使是地方士人领袖, 也坚定地支持士人游历, 如刘将孙在《送倪天全序》中大篇幅地回忆了宋末游士拜谒贵邸的盛况, 而后评说道:
浮游湖海, 行不赍粮, 曳裾趿履, 有余以及妻子。 江山名胜, 无不可乐。 犹有立谈白璧一双之叹, 犹有堂下一言不知子之恨。 摩劘搪激, 张为虚声, 落落气出公卿大夫上。 劫而下之, 且有所不满。 嗟乎!此道废又二十年矣。 后生裹足不敢出丘里, 先辈车轮草莽生四角。 兴言昔者何可得也。 每寤寐嘅叹, 何地复歌骊驹, 别南浦, 送人四方, 作游客乎?……当今王公大人, 皆魁磊杰特, 如黄河泰山, 高大深厚。 吾闻古称四公子, 其宾客立拔卿相, 金千镒, 车千乘, 客之客且结驷轻肥倾邑都, 固有朝窭人 夕封君者。 行矣, 大梁之墟, 有如夷门生之遁迹焉; 冀之北上, 有望诸君之墓焉。 君振臂而风云合, 举袂而名声流。 安知史所称游士之遇者, 不于君乎见之也?[9]115
其《送戴石玉序》亦云:
自孔孟来, 士未有不游。 或以师友游, 或以宾客游, 或以学问游, 或以才艺游, 或以辞华游。 二千年才贤特达, 未有非以游而合也。[9]116
刘将孙所描述的游士, 完全是干谒权门之流, 在一般社会观念中, 这类人是受到轻视的。 然而庐陵地方领袖却极力赞成这样的行为, 则可见其地士风、 民风如何了。
发达的刻书业与游历风气相结合, 于是形成了采诗之风。 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云:
吾闻庐陵之文溪, 生息繁夥, 其俗好远游, 不间于稚壮强艾也, 特其志尚之不齐, 则执业有悬絶者矣。 葛生存吾独曰: 今天下车书之同, 往昔莫及, 吾将历观都邑山川之胜, 人物文章之美, 使东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见焉。 且夫风物之得以宣通, 咏歌之易以传习, 则莫盛于诗。 缘古者采诗之说而索求焉。[25]498
可见, 行走江湖的庐陵游士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 采诗不过是其中一种。 前文提及的采诗人杨显民也是一位游士, 曾计划“游秦淮, 历齐鲁之墟, 过泰山, 拜孔林, 而迤北至于京师”[27]717。 他后来归乡隐居, 在乡里口碑颇佳, 被称为“终不肯一出以干时取誉” “江南之士渐其泽”[28]卷四。 大约他相对于一般采诗人来说, 是比较纯粹的文学人, 确以保存文献为职志, 功利意图没有那么浓厚, 所以才受到了揭傒斯的另眼相看。
有时, 采集诗文的形式不止是访求, 还可以征集, 后一种形式的商业特性尤为明显。 《山房随笔》记载了一则趣闻:
吉州罗西林集近诗刊, 一士囊诗及门, 一童横卧枨闑间。 良久, 唤童起, 曰:“将见汝主人, 求刊诗。”童曰:“请先与我一观, 我以为可, 则为公达。”客怪之曰:“汝欲观吾诗, 汝必能吟, 请赋一诗, 当示汝。”童请题, 客曰:“但以汝适来睡起搔首意为之。”童即吟曰:“梦跨青鸾上碧虚, 不知身世是华胥。 起来搔首浑无事, 啼鸟一声春雨余。”客骇伏。 同入见西林, 款之数日, 取其菊诗云:“不逐春风桃李妍, 秋风收拾短篱边。 如何枝上金无数, 不与渊明当酒钱。”童子, 罗之子也。[29]
罗氏足不出户, 外地诗人主动地上门投诗, 可见庐陵人几乎将编选诗集做成了一门产业。 在今存若干元代庐陵人编选的总集中, 能看到不少这样的痕迹。 例如周南瑞所编《天下同文集》, 目录后有“随有所传录, 陆续刊行”的九字刊记, 四库馆臣评论道:“其体例与今时庸陋坊本无异。”[3]1708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目录页后也有刊记一则, 曰:“本堂今求名公诗篇, 随得即刊, 难以人品齿爵为序, 四方吟坛士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 倘有佳章, 毋惜附示, 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 李氏建安书堂谨咨。”[30]目录这则广告性质的刊记与《古杭杂记》目录后的识语如出一辙, 可知两部书籍的编撰方式大致相近, 都是成系列地编刊。 而孙存吾《皇元风雅前集》有虞集序, 其中提到:“清江傅说卿行四方, 得时贤诗甚多, 卷帙繁浩。 庐陵孙存吾略为诠次, 凡数百篇。”[31]卷首卷端则署:“旴江梅谷傅习说卿采集, 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编类。”[31]卷一《皇元风雅》的两位编者傅习与孙存吾存在着有趣的分工, 傅习负责出外访诗, 孙存吾则坐镇庐陵负责编定。 孙存吾家有“益友书堂”, 为范梈、 虞集刊刻过诗集, 是出版业中老手。
如此源源不断的采诗、 集诗、 编诗活动, 无疑是以逐利为目的。 元末杨维桢在为上海人释安所编《蕉囱律选》时写道:“是集行, 则《皇朝风雅》之选于赇者, 君子有所不遗。”[32]251《皇朝风雅》概即《皇元风雅》, 元代以此为名的诗集今存两种, 其一即上述傅习、 孙存吾所编者, 其二乃建阳人蒋易所编。 而蒋易所收集的诗作有一大部分来源于其师杜本的积累。 杜本是江西清江人, 除《皇元风雅》外自己还采编了《谷音》诗集。 此外, 采诗人中的傅习、 熊思齐等人也都来自清江[33]452, 足征清江乃庐陵之外另一处采诗者渊薮。 总之, 两种《皇元风雅》都是江西采诗的产物, 无论杨维桢在这里指斥的是哪一种, 都说明江西采诗业存在“选于赇”的情况。 采诗者不仅通过销售诗集获取利润, 选诗也可带来直接的收益。 采诗活动“以诗存人”的宗旨, 并不单纯是历史责任感的体现, 看来也是深刻地抓住了中下层文人企图留名的普遍心理。
以上论述已经说明, 《古杭杂记》是庐陵采诗之风的产品, 而庐陵人李有之所以要编写一部以杭州为题材的作品,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杭州作为南宋的象征, 为读史者所热切关注, 另一方面, 杭州作为江南第一都会, 人物荟萃, 号为“东南诗国”[6]114, 因而, 也是采诗者的重要目的地。 彭丙翁、 胡复初出乡采诗时, 有人赠诗送行道:
君行为我观海潮, 浙江亭下风萧萧。 君行为我泛湖月, 苏公堤上杨花雪。 只今何处不闻诗, 南音寥寥君得知。 海风吹寒翡翠尾, 秋露滴老珊瑚枝。 山川光怪岂敢閟, 采之采之尽君意。 愿君勿学梁昭明, 是非未定轻闲情。 愿君但似吴季子, 四海之风定谁美。 马蹄跌宕舆地开, 幽燕浩浩风云来。 丈夫西游今可矣, 前日江南数千里。[34]319
显然采诗者的下一站便是杭州。 刘将孙《送临川二艾采诗序》也写道:“自此而杭, 而金陵, 予之欣然跃然为何如哉。”[9]89杭州文人也常遇到来自江西的采诗者, 如张雨赠庐陵人陈仲诗云:“载酒人稀徒好事, 采诗官废失编年。”[35]277陈仲不知是不是采诗者, 但张雨提及采诗, 至少是有意地将庐陵人与采诗联系到了一起。 郑元祐居苏州时, 与江西采诗人杨季民有往来, 记述道:“季民沿江入浙, 而遂留于吴者几一年, 见人所赋诗一篇一什, 辄皆采而录之。”[12]194可见, 杨氏之前也曾在杭州居留过一段时间, 以采诗为业。
元代庐陵地区生产的以杭州为题的书籍, 除《古杭杂记》外, 还有杂史作品《钱塘遗事》。 其作者刘一清, 在《说郛》中题为“武陵人”, 但《钱塘遗事》与《古杭杂记》两书有若干条目互相重合, 王瑞来先生即以此作为证据之一, 论证刘一清的真实籍贯亦为庐陵。 其结论可信与否尚值得进一步讨论, 但两书文本的亲缘关系是确凿无疑的。 如前文所述, 采诗者的采访对象包含了诗、 词、 文各体作品, 如果再扩大范围, 将掌故逸闻涵盖在内, 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甚而言之, 即使并非专门的采诗者, 每一位在杭游历的江西人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参与此地的言论世界, 在元初的故都杭州, 关于南宋的口头与书面文本正大量流传, 士人非常易于接触到各类记忆、 言论与史料。 因此, 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 杭州活跃着一批江西籍游士, 他们采集诗文, 同时也采集关于南宋的史料、 故事, 他们将这些资料带回江西, 庐陵书坊于是出版了各地文人的诗词文章, 也出版了各种史料笔记, 而两者混合的形式, 便是《古杭杂记》。
4 结 论
李有作为庐陵人, 得以撰写一部以杭州为题材的书, 背后反映了庐陵与杭州两地密切的文化交流。 两地各为江西与浙江两省的文化中心, 大量的流动士人成为它们之间的联络者。 从《古杭杂记》这部著作中, 我们便可以发现两条重要的联系纽带, 即太学生与采诗人。 南宋太学吸纳了大量庐陵士人, 而元初杭州的太学生群体保存着他们的文化记忆, 为著述者提供着采撷的资源。 庐陵的商业出版与游历之风相结合, 形成了采诗风气, 庐陵人主动地访问江南各地, 搜集文献, 编刊作品。 这些人际关系网使得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在地域之间传播, 于是, 关于杭州的种种记忆在1 700里以外的江西庐陵得以结集。 《古杭杂记》不仅是一个书籍史的微观案例, 也使我们看到元代江南的各个地域是如何组成了活跃的文化共同体, 如何在文化格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