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铸盾
2019-03-22马京生
马京生
2018年11月21日,身盖鲜红党旗的程开甲静卧在鲜花丛中,社会各界人士满怀悲痛,前来送别这位曾经为共和国隐姓埋名、干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百岁老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是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中的最年长者。2014年1月10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当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程开甲颁发奖励证书,这年他96岁高龄。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开创者之一。程开甲的名字与中国核试验基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爆响了震撼世界的惊雷。
尚未出生,“开甲”寄托全家厚望,可他小学竟然连续两年留级。“开窍”后初露天才,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乘方表和立方表脱口而出。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于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商人家庭。祖父程敬斋精明能干,练得一手经商的绝活儿——左手拨算盘,右手写字,一心二用,既准又快。他发家致富后娶了两位太太,却只有一个男孩。程敬斋一心想光宗耀祖,让儿子科举取士。无奈儿子程侍彤连个秀才也没考取,程敬斋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给未来的长孙取了一个“开甲”的名字,意思是名列榜首。
让程老爷子大为失望的是,他让儿子娶了洪举人家的姑娘为妻,却一连生下六个孙女,无一人可领“开甲”之名。于是,他又让儿子娶了一个潦倒书生的女儿董云峰。家境贫寒的董云峰进程家不久就怀孕了。巧的是,在祖父程敬斋病故的第二天,程开甲呱呱问世了。
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程开甲6岁时,父亲病故,生母董云峰在程家成了多余的人,受尽了白眼和屈辱。有一天,她给儿子小开甲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和鞋袜,还塞给他20个铜板,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儿子的身上,说了一句:“儿子你要为妈争口气呀!”说完转身踏上了小船,从此再也没有回程家。
母亲走后,小顽童程开甲既没人疼爱,也没人管教,他无依无靠,像匹小野馬独来独往,有时孤僻不愿见人,有时顽皮胆大包天。开始,家里将他送到私立小学,课上课下他都玩得不亦乐乎,不好好读书,连读三个二年级。直到有一天,他小小年纪独自一个人从吴江跑到上海,全家人急得到处找他。他到上海三姐家找饭吃,才被家里人接回了吴江老家。
家里将他转学到盛泽观音弄小学读书。程开甲的五姐程钟伟调到观音弄小学教书后,当老师的她对顽皮的小弟弟很有耐心,让程开甲每天背着小书包跟着她去上学。在五姐的指导下,他对数学和音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成绩逐渐好转,从四年级直接跳到六年级。
1931年,程开甲考入离家2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和陈省身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程开甲在这里读了整整六年的初中和高中。读初一的时候,程开甲还是成绩平平。读到初二,程开甲从图书馆里借来许多科学家的传记,他着迷地读着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居里夫人、巴斯德、詹天佑等科学家的传记。这些书开启了他心中的一道智慧之门,使他对科学家的人生充满了兴趣。那些重大的科学发明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使他渐渐萌发出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理想。
这时候,程开甲有幸碰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数学老师姚广钧。姚老师十分重视对学生数学技能的记忆训练。在姚老师的指导和训练下,程开甲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数;乘方表和立方表脱口而出;他牢记学过的每一个数学公式。这对他在日后科研中推导和演算数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嗜书如命,与同学打赌得了个洋绰号“程BOOK”。26岁的小助教证明了世界物理大师的推论,因为听信学术权威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37年,程开甲同时接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所是上海交通大学,一所是浙江大学。最终他选择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因为录取通知书上清楚地标明了他属于极其优秀的考生,进而成为公费生,可以享受每学期100元资助。当时,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程开甲所读的物理系是浙江大学的一支“王牌军”,在这里他幸运地遇上了对他影响很大的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为他日后留学和科研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一道考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跑?”大多数同学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的考题。只有两位同学得了满分,其中一个就是程开甲,他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束星北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认准了他这个学生日后定有作为。
程开甲读书十分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位同学跟他打赌:如果他整夜读书不睡觉,就给他出灯油钱。程开甲毫不含糊地读了三天三夜书,于是同学们都戏称他为“程BOOK”。
大学二年级时,程开甲开始听王淦昌主持的物理讨论。此时年仅27岁的王淦昌已经在德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同学们称为“娃娃教授”。程开甲从“娃娃教授”那里学到了科学家的科研作风:一是紧跟前沿;二是抓住问题,扭住不放。
1944年,程开甲在浙江大学任助教,他完成了一篇有意义的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王淦昌后来将该论文推荐给来浙江大学考察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李约瑟看到论文亲自进行修改润色,并将论文带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但狄拉克亲笔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结果论文未能发表。
之前,狄拉克曾亲自将程开甲《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的论文推荐给剑桥大学的《剑桥哲学杂志》,论文对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给予了证明,而狄拉克本人并未证明过此方程。程开甲考虑到狄拉克是物理学界的权威人物,既然狄拉克亲自回信,程开甲也就没有怀疑权威,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然而,程开甲放弃的“发现”,30多年后被一个重要实验所证实,而且,实验所测得的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这项成果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奖,让程开甲颇为遗憾。在科学的道路上程开甲虽然紧跟了前沿,但抓住问题没有扭住不放,没有坚持到底,这成为他终生遗憾的一件事,也成为他在日后的科研中引以为戒的事。

程开甲有关“新粒子”的论文虽然没有发表,但李约瑟记住了他,在李约瑟的积极推荐下,1946年8月,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的程开甲远渡重洋,来到英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爱丁堡大学M.BORN(玻恩)教授的研究生,并于两年后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玻恩十分欣赏他的才能,希望他能留在这里,把夫人孩子都接来,专心做学问。
1949年10月,程开甲获知新中国成立了,下定了决心,回祖国去!他婉拒了玻恩教授的好意。
程开甲考虑建设新中国需要工业,他开始学习金属物理,收集购买了有关资料书籍,于是“程BOOK”带回祖国的大箱小箱都是书。
1950年8月,程开甲回国后,在母校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52年,程开甲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教材《固体物理学》。1956年程开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一年,程开甲找到了分别30年的亲生母亲。
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在物理方面有许多研究成果的程开甲,突然从大学校园、大家的视野里消失了,甚至没有跟他的物理同行们打声招呼。
走进戈壁滩铸造中国核盾牌。钟情于在小黑板上演算惊天动地的大方案。罗布泊上爆响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0年3月,由钱三强“点将”,经邓小平批准,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副所长。已经先期到达的另外两位技术副所长是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和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朱光亚是技术总负责,郭永怀和程开甲各自领导一方面开展科研工作。1961年4月,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和彭桓武来了,也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科学家们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历程。1962年,原子弹的关键问题有了突破。为了两年后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经钱三强拍板,让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开始做准备。
当时,场区初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大家喝苦水,战寒风,靠打野兔会顿餐。不仅粮食吃不饱,戈壁滩上水也珍贵,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澄清了洗衣服。有时水紧张几天不洗脸。
程开甲是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测得爆炸时的各项参数和试验产生的效应数据,工作起来经常废寝忘食。
有一次,程开甲一门心思研究光辐射和力学冲击波的能量问题,当走出办公室,看到别人在休息,他生气地问:“你们为什么上班睡觉?”大家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告诉他现在是午休时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午饭还没吃呢。
工作在戈壁滩,他家里有一块小黑板,办公室里放着一块大黑板。他边思考边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个又一个技术方案和公式,计算出那些复杂的参数,解出一道又一道难题。由此,程开甲养成一个独特的习惯: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
程开甲常说:“科学实验就得讲严谨,没有严谨就没有成功。”只要见过程开甲的人,都知道他的认真是出了名的。第一次核试验前从原子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程开甲提出要在电缆沟里垫细沙,以保证电缆本身和测试的安全。但在一次检查中,他发现没有按要求去垫细沙,他立即要求施工人员返工。这时工程队的人不干了,因为已经铺了不少,光返工就得重拉几百车沙子铺上。但程开甲坚持说:“不这样就是不行!”问题很快反映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果断拍板:“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何种方式爆炸?程开甲以渊博的学识和研究结果,大胆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原计划,提出用铁塔来实施,以后再采用空爆的方式。
1964年9月,在茫茫戈壁滩深处的罗布泊上竖起了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原子弹就安装在铁塔的顶部。程开甲信心十足地对张蕴钰司令员说:“我们没有理由会失败,一定爆响,一定成功!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原子弹一定能响,不能不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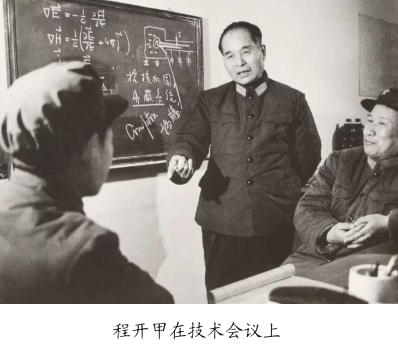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百米高塔上腾起蘑菇云。当时,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激动地拿起电话报告说:“总理,我们成功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周恩来也很激動,但他用平静的语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大家的目光转向技术专家程开甲。他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出核爆炸的巨大当量,肯定地说:“是核爆炸,没错!”
为了测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炸的性质、当量等参数,当时布放了1700台测量仪器。在原子弹的起爆瞬间,自动控制系统分秒不差地启动了全部测量仪器进行全程测试,记录数据准确、完整。正如程开甲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首战告捷。
据世界上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资料记载,法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也仅拿到了一部分数据。
完成了周总理交给的科研任务,就是没有完成学说普通话的任务。地下核试验后,他不顾核辐射,勇敢地进入地下爆心测试室
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程开甲马上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思考氢弹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上。氢弹试验的三个突出特点是:当量大,爆点低,沾染重。首当其冲,就是安全问题。
程开甲昼思夜想,在小黑板上一遍遍地计算、思考难点,组织科技人员研讨,拿出了具体方案,并在氢弹原理试验前,组织人员进行了一次常规炸药的化爆模拟试验。他心里有了底。
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在罗布泊获得成功。大家举杯欢庆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已获得解决,程开甲任务完成也心情放松。他太累了,眼皮一下粘到了一起,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还没睡醒,一项新的试验任务——全当量空投氢弹到来了。为了准确地算出氢弹爆炸高度,程开甲开始计算爆高。在空爆试验中,他亲自抓安全和取样定当量,提出了两个首创性意见:一是火箭取样的新方法;二是改变投弹飞机飞行方向。
程开甲为安全把关赢得大家的信任,也得到了周总理的信任。
有一次,周总理听取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总理问:“飞机的安全是否有把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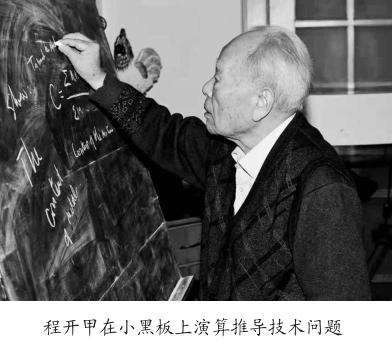
在场的一位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这些数据是他计算的,他知道。”
周总理用询问的目光转向程开甲。
“安全绝对没问题。”程开甲回答得很干脆。周总理很仔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他一一对答如流,但就是方言太重。
程开甲话音一落,总理突然又问一句:“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啦?”
程开甲一愣,一时竟然没有答出来。
周总理笑笑把话岔开说:“程开甲同志,你要学说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
百岁老人程开甲,说话还带有浓浓的江苏吴江口音。说起这些来,他遗憾道:“周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就是没学好普通话。”
程开甲早在1964年准备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就前瞻性地开展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并坚持推动了向地下核试验方式的转变。之后,我国地下平洞方式的核试验和地下竖井方式的核试验接连获得圆满成功。
爆心,是生命的禁区。
在地下深层岩石中发生的核爆炸,核能的释放产生了瞬间的光、热、声和冲击波,巨大的能量被封闭在地层深处。那里埋藏着看不见的核爆现象,也埋藏着看不见的核污染的恐怖。由于地下核爆方式的特殊性,对核爆炸试验的现象和填塞的安全性都无法有感性的认识。为了能对地下核爆炸做到心中有数,程开甲决定要解剖“这只麻雀”,他提出爆后开挖。开挖后,他曾多次进入坑道、测试间和爆心,获取第一手资料。
在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后,经过开挖,程开甲和朱光亚决定进入地下核爆后的测试间去实地考察。这两位科学家明知核爆后现场辐射剂量很大,是有危险的,但程开甲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无惧危险,穿上防护衣、戴上手套和安全帽进入坑道,钻进刚刚开挖的直径只有80厘米的管洞,匍匐着爬行10多米来到了测试间,见到这里四周布满了黑色玻璃体,就像一座怪异的水晶宫。他们继续在一个个异常闷热的孔洞中匍匐向前爬行,最终爬行到坑道末端的产品房——爆心,仔细观察四周奇妙的爆炸效应,完成了洞内探察。程开甲和同事们终于取得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与应用开拓出成功之路。
对于这些永载中国史册的光辉业绩,程开甲认为,这是许多科技人员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隐姓埋名20多年,用青春和智慧在大漠戈壁的核试验场铸造了共和国的核盾牌。有人问他:“你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他感慨道:“如果当初我不回国,没有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可能个人会有更大的科学成就,但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与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耄耋之年,腰杆挺直,生前仍在进行着独具创建的研究。榮誉满身却淡泊名利,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
1984年,程开甲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加固的研究。
他的大女儿程漱玉子承父业在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工作,后来父女天各一方开始了科研合作。1991年程开甲出版了专著,向现有的超导理论提出挑战。接着程漱玉又为程开甲整理出版了17万多字的《超导机理》。由于父女在学术上配合默契,后来组织上干脆把程漱玉调来给程开甲当了技术助手。他对女儿这个助手要求极严,交办的工作绝不能出一点差错。
他生前一直保持着许多过去的习惯。在他的居所里又装上一块更大的黑板,他仍旧喜欢在上面写写画画,推导公式。同时他还能操作计算机,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着独具创建的研究。
这位世纪老人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程开甲说:“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创新背后是非常艰苦的奋斗。是多种意义上的无私奉献和拼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活到老奋斗到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