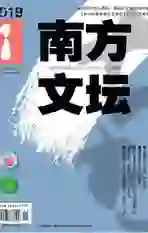林莽论
2019-03-21张立群
张立群
由于本文最终的目的是将林莽的诗歌创作置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并试图与当代诗歌批评完成某种对话,所以,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就诗论诗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无论是阅读林莽诗集的“作者简介”还是关于他的评论文章,“‘白洋淀诗歌群落代表诗人之一”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定位”;而在另一方面,林莽的诗创作早已跨越了20世纪,不断在拓展和变化中实现自身的历史化。上述隐含在命名与创作之间的“时间差”或日“现实的错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诗歌批评及其认知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缺乏有效的“生长性”机制,常常拘囿于概念化、无法与创作进行及时、有效的对话,而诗歌创作与批评之间由此呈现出某种“分离的状态”。
一
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林莽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白洋淀诗歌群落当然包括马佳等同一倾向但不同地域的人。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结构,它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个诗歌组织。这群人里除了诗人,还有搞哲学、经济学和绘画的。”白洋淀由于距离北京近的地域优势和相对自由的环境而汇聚了一大批知青。他们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诗歌群体,即为后来为学界所熟知的“白洋淀诗群”。当时,“白洋淀诗群”的主要成员包括岳重(根子)、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孙康(方含)、张建中(林莽)、宋海泉等,他们在当时主要通过阅读、创作朗诵诗歌、交换诗歌的方式进行活动。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国外诗歌资源的影响,而其中很多作品已具有现代主义倾向。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真正产生影响应当在1972~1973年间,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加入北京文艺沙龙后获得诗名,还体现在一批未到此插队但常赴白洋淀以诗会友的文学知青的到来。这些人包括甘铁生、北岛、江河、彭刚、史保嘉、郑义、陈凯歌等。其中,北岛与芒克的结识促成了日后《今天》的创刊,而作为一种群体的划分,他们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被视为广义的“白洋淀诗群”成员或应该被纳入“白洋淀诗群”之中。当然,作为一种事后清理和历史追溯,“白洋淀诗群”或日“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命名要晚于其创作史以及原本在其之后的“朦胧诗现象”。1994年5月,《诗探索》编辑部组织了“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的系列活动:“曾经与白洋淀诗歌有关的原来的知青,集体‘寻访故地,举办讨论会,撰文讲述当年的情景,披露‘有研究价值的原始资料……这一工程的主要成果是,为这一诗歌事实做出许多人认可的‘诗群的定位,巩固了它在当代新诗史上的具有开创性的地位。”“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称谓和诗艺特征也由此得到落实和进一步的确证。
林莽于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同年11月写出《深秋》一诗,这是林莽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首诗。翻阅《林莽诗画:1969—1975白洋淀时期作品集》,可知林莽在1969至1975年白洋淀时期共存有诗十六首、画三十一幅。林莽于1975年写出《悼一九七四年》一诗后回到北京,这一时间跨度与“白洋淀诗歌群落”发生与主要活动时间为1969至1976年基本一致。是以,林莽是“白洋淀诗歌群落”代表诗人之一本身是理所当然的、恰如其分的。
考虑到“白洋淀诗歌群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掀开历史的面纱,我们有必要将这一命名的现实影响力适当向后延伸,进而扩展至世纪初几部有代表性的当代新诗史如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2003);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2005)等出现的年份。但从林莽诗集《记忆:一九八四——二〇一四诗选》的收录情况来看,林莽从未停歇其在诗歌道路上探索的脚步。因此,“白洋淀诗歌群落”代表诗人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概括林莽的创作,但却无法涵盖林莽诗歌创作的全部。为此,我们在面向林莽诗歌创作的同时,至少要做到两方面考察:其一,是将“白洋淀诗歌群落”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并关注它留给林莽这一代诗人的精神财产和经验之源。其二,是明确林莽诗歌创作的阶段性、变化性进而发现新的言说角度。限于篇幅,本节只围绕第一方面展开。
在孤独、寂寞甚至带有绝望的日子里,林莽于插队的白洋淀找到了诗“这种与心灵默默对话的方式”。正如在其存留的第一首诗《深秋》的结尾,诗人写下:“深秋的湖水,/已深沉得碧澄。/深秋里的人啊,/何时穿透这冥思的梦境。”插队期间,诗是林莽“生命最隐秘的书写,记述自己的心灵之声”,也是其缓释内心焦虑的重要方式。尽管,这些诗要到很多年后才和读者见面,可作为“地下写作”,但从其文本表达来看,通过写作寻找自己,在与心灵进行对话的同时倾诉最真实的灵魂世界,是这些作品突出的特征之一。至1974年,通过有限阅读获得现代经验的林莽开始进人了现代主义的诗歌领域。由二十六首系列短诗组成的长诗《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年岁》,使林莽找到了更为深邃、内敛的表达方式,而稍后完成的《悼一九七四年》中的——
时辰到了,炉火还没有止熄
让雪花飘落在你的荆冠上
收住凄艳的歌声
走了,没有马车,也没有仆从
翻过三百六十五页数字
只有这最后的时刻,你庄严而肃穆
既可视为即将回京的林莽向过去告别,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诗人正步入一条新的诗歌道路的开始。
毫无疑问,白洋淀插队经历几乎填满了林莽全部的青春记忆。他在这一阶段不仅阅读了常常为之感动的普希金、雪莱、拜伦、莱蒙托夫、洛尔迦、泰戈尔等的诗,而且也发现了存在主义、印象派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以及以波德莱尔、聂鲁达、艾吕雅等为代表现代派诗歌创作。白洋淀时代是林莽诗歌的起点,留存着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为其日后创作积累了简单而又丰厚的精神资源。
如果说白洋淀时代的起笔奠定了林莽诗歌创作的基础,潜藏着林莽诗歌写作技艺的密码,那么,就具体写作来说,我们可从“秋天”意象谈起。在白洋淀时代留下的十六首诗中,有一半以上提到了秋天,而像《深秋》《暮秋时节》《秋天的韵律》《第五个金秋》更是直接以“秋”为题。即使不必过多援引主题学、原型批评的理论,“秋天”意象也足以告訴人们诗人“此刻”的心境:这是一种真正可以和诗人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的生命体验,它苍茫、宁静、寂寞、萧瑟,融合着诗人对于生命、自然、时间的共同体验和综合处理,它在林莽之后相当长的诗歌创作中反复出现,成为解读林莽诗歌的重要意象,可作为白洋淀时代凝结而成的“诗歌母题”。
二
林莽曾自言1984年是其诗歌写作自我调整后的新起点。为了能够全面评述这种有意的调整,我们有必要注意林莽作为诗歌理论家的身份。1984年1月,林莽在《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谈诗及审美意识的转化》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当代诗歌艺术探索的看法。“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那些年写了许多激情洋溢之作,写了许多凄凉沉郁之作(这不光指情感,更多的是指政治情绪),它们在回顾与指责中站住了历史的位置,那已经是一个阶段。它们不再使我感动。”联系当时的诗歌主潮及其表现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林莽的言论既指向了当代先锋诗歌过分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缺少对诗艺本质探寻的倾向,同时也对“伪现代派”只注重形式、忽视内容、玩弄语言词汇的行为给予中肯的批评。“是应该走向平静,走向艺术的时候了。”以一个当代新诗潮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对短短数年、诗坛便经历几个阶段进行反思,这种自省意识当然与林莽诗人兼理论家的身份密不可分。但更为可贵的是,林莽同样也对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思考。“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经历了几年的对诗歌本体的思考,开始努力摆脱以往以社会生活为主体的那种韵味,更多地贴近心灵,更多地贴近生命的感知与领悟,寻找语言艺术的真谛,让诗歌作品更具现代艺术之美。”而这,正可以作为他适度改变白洋淀时代诗歌写作方式的一个注脚。
自我调整之后林莽的诗相较以往透明、从容了许多,同时也融入更多理性的思考,《杜鹃声声,沿乡路走入寂静的山谷》《在一本书与另一本书之间》《是春天,也不是春天》等都可以作为个案加以举证。但就主题内容而言,最吸引我的是“记忆”和“故乡”:它们在《故乡、菜花地、树丛和我想说的第一句话》《灰蜻蜓》《一封远方的来信到底要说些什么》《故乡的风》《车过故乡》和组诗《记忆》中时隐时现,也可以是《黄昏,在异乡的寂寞中》《风中的芦草》等诗作中的“另一种表达”,但最能说明其意义的或许是两者的“相遇”和“叠加”——
黃昏,在一片紫色中多么宁静
一丝幽鸣在水面上缓缓地展开
把寂静凝结在旷野里
如果这时,突然间升一串布谷鸟的叫声
村镇小学的晨钟湿润地振荡
那么,故乡,在你和我记忆的深处
那些无声的对应,悬挂着,沉默着
在泊着许多条船只的村口
一年又一年地吹着黄昏里的风
当守候的钟声骤然间敲响
我知道,故乡
你用以往的眼睛认出了我
——《湖边晚归》
故乡是记忆之源,记忆中故乡似乎很难回到最初的状态、旧日重现。如果由此联想“返乡”与“回归”、“漂泊”与“远离”是诗人偏爱的诗歌情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那些无声的对应,悬挂着,沉默着”是两者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它们是真切的、可感知的,但又是触不可及的。在持续“返乡”和终生“远离”中,诗人实现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书写转换。
但林莽的思考显然并未就到此结束,他在“故乡”与“记忆”之间体验到了时间的意义——
那时间到底有多久了
他年的激情
已混同于以往的风雨
隐约的云层
遮住了远在异乡的人
——《故乡的风》
和年迈的母亲谈起久别的故乡
时间让往事沉寂
他年的河水
今年已遥远得听不到喧响
——《风中的芦草》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让一切成为历史。对于个体而言,时间唯一馈赠的礼物就是记忆,让人将过去珍藏。但记忆是选择性的,只有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才会成为记忆的组成部分,并在适当的时候浮现在眼前和叙述之中。诗人将自己的记忆写进诗中,显然是因为这份记忆可以在“深刻的重复”中再现自己的诗意想象。在岁月的延展中,诗人体味到了时间的无情和时间的秘密,因而,他在向后漫溯时选择了故乡——与故乡相比,另一个可以唤起永恒记忆的极有可能是爱情,但爱情却无法像故乡那样生动、深远。故乡不仅可以嵌入诗人的真实体验,还可以丈量出迄今为止“记忆的距离”。伴随着多少经历同时也是多少往事的烟消云散,“故乡”“记忆”成为刻绘“时间”的主题。不像当年“秋天”那样诉说心境或呈现眼前之景,林莽将生命的体验融人诗中,“阳光震颤/扩散于枝头和草的茎秆上/悬垂初秋的果子/静默/听雨水/淡淡地润化/润化绵延的时光”(《感知成熟》),迥别于当代新诗潮的种种写作取向,他在古典和现代中游弋出自己的诗歌世界。
但无论怎样,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喧嚣热闹的诗坛,林莽还是过于沉稳、低调了,这也正是评论家叶橹认为其“不合群”、“有意无意地成为诗坛的独行者”的原因。当然,对于没有在当时成为诸如“朦胧诗”式的先锋诗潮的一员,林莽自有自己的观点:“回顾四十多年来的写作,除了极少数因工作之需的写作,所有的作品都是诚心以求的。它们都是源于我的情感体验和对生命的领悟,都是忠实于我的诗歌理念的。在将它们呈现给读者之际,我的内心是平静而坦然的,因为它们没有阿谀奉承之作,没有跟风随潮之作,没有追名逐利之作,有的只是一颗虔诚的心,这些诗首先是写给自己的,它们与我内心所发出的旋律是一致的,它们与我的生命同步。”忠实于内心的律令、忠实于自己的诗歌理想,不因他人的变化影响自己的节奏,是林莽诗歌难以归类,一度成为诗坛孤独行者的重要原因。林莽的诗歌随着生命阅历的加深当然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加深和逐渐稳定、成熟,需要反复阅读他的诗才会有所发现。
三
林莽很长时间内的绝大部分诗都可以作为抒情诗,如果借用别林斯基的话概括,那么,“在这里,诗歌始终是一种内在的因素,一种能感觉、能思维的沉思”;“在这里,诗人的个性占着首要地位,我们只能通过诗人的个性来接受一切,理解一切。”“能感觉”“沉思”是林莽诗歌的特点,同时也是理解林莽诗歌的有效方式。当然,“能感觉”“沉思”也是一种难度,如果林莽是那种外放式的浪漫抒情诗,那么辨认其诗质自然会容易很多;但林莽沉稳、内敛、追求内在质地的策略却让人们觉察到其“个性”的同时,常常陷入“得意忘言”的状态。但就语词和意象选择、组合的情况来看,林莽从不复杂,他只是在坚守自己诗歌理念的过程中营造出属于自己的诗歌美学,它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理想——
如果在最后的日子里
我能心安理得地
奉献出我的九十九页诗选
灵魂的歌声萦绕着那些美好的瞬间
我渴望在人们心中抛下一片火焰
——《九十九页诗选、污水河和金黄色
的月光》
并在面向读者的过程中成为“明净沉着的体验型”而非讲究技术和语言组合的“认知型”。
“体验型”的写作绝非仅意味着量的增长,其更重要的还包括质的拓展以及诗歌信念的坚持。在写于1990年7月的《寻求》一诗中,林莽写道——
寻求美好的事物
注视一只陶罐的宁静
浑圆的曲线
出自终生沾满泥浆的手
落日般的饱满
墨色浸润
多年的寻求
让花朵开放得富丽而灿烂
迈过不惑的门槛
才知道有些字不能轻易地吐出
短暂的光辉
把背景的黑暗沉入了无底的岁月
我寻求
我痛苦
我将一件件往事酿成浓酒
不惑的年龄让诗人感慨良多,因为他深知感受和体验有时比言说更为重要。他在寻求中将“一件件往事酿成浓酒”,正如他写下的一首首诗一样。一切都将沉人无底的岁月,一切都将随着岁月流逝并改变,但理想主义的光辉在林莽的心中和诗中从未逝去。为此,他应当还有许多渴望表达;为此,我们有必要注意林莽笔下这样一些诗行——
我们都是在寻找语言的归属
我们在各自的空间里神秘地飞行
但我们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完成
——《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完成》
而许多事情潜在的意蕴
经年累月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味道
——《一切都可能改变》
尽管凭借几行诗就断言林莽诗歌发生的年份会是一种言说上的冒险,但诗歌心愿未了和心态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到写作的变化。从《夏末十四行》(十六首)、组诗《记忆》及其对历史题材的关注中,我们可以读出某种关于主题和形式的嬗变。
只要对比“白洋淀时期”和组诗《记忆》中关于“秋天”的书写,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场景的置换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昔日的眼前之景和心中的抑郁,虽常常会在一个偶然的瞬间重回视野,但毕竟已成抽象的记忆、物是人非,因而,“秋天”已不是心境的缩影,而更多是现实的记录表,书写着岁月流逝过程中沉积于心头的体验。“秋天飘落了它最后的叶子/光秃秃的枝干指向湛蓝的天空/短暂的激情骤然冷却/草丛小径上留下零乱的身影”;“岁月是一条滔滔汩汩的河/它把记忆的触角磨圆/把一颗颗心化作沉甸甸的石头”(《记忆(第一部分)·三》)。同样地,在《记忆(第二部分)》中,叙事的形式和成分也远远超过了往日抒情诗歌的凝练、精悍,以至于让人联想到此刻诗人想将更多的体验融人诗行之中并与90年代诗歌主潮整体发展趋向相呼应。而在《记忆(第三部分)》中,林莽依旧书写着他终生难忘的白洋淀,但就文本来看,白洋淀已开始在其笔下追本溯源,通过历史人物与故事的导引,白洋淀在更为久远、广阔的“历史的屏幕”上“无声的穿行”、展开其“巨大无比的底片”。“一切都已过去令我们寻找/切都已消失让我们思索/切都不再回来只给我们留下记忆,它们将永驻于心灵与历史的契合点上”,而白洋淀的故事就这样从往日的“青春曲”转为此刻的“回忆录”与“自叙传”,成为刻在纪念碑上栩栩如生、难以忘怀的历史浮雕。
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诗歌批评正步入尴尬的境地:诗人不再相信批评,读者看不懂批评,早已作为一个流行的话题、成为诗坛“共识”。如果上述关于批评本身的危机状态,更多情况下是由于创作与批评的分离、诗坛权利分配客观存在的问题以及批评的覆盖度不够进而引发所谓的意气之争等,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诗歌批评有效性、准确度的匮乏恐怕也是其声誉欠佳的重要原因。尽管,按照研究界“通例”,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会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但既然进行批评,批評的发现性、新意以及对未来文学史写作提供研究的基础就应当成为批评本身承载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对于批评和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韦勒克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一书中早有论述——
主张文学史家不必懂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不是始终借助于批评原理,便不可能分析文学作品,探索作品的特色和品评作品。“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
反过来说,文学史对于文学批评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文学批评必须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的判断。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会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是师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
既然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文学批评就应当在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尽量与创作保持互动,从而在持续保持“生长”态势的前提下,为以后文学史的写作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而文学批评的及时性、准确性,在时间上往往优于文学史写作的特点也由此得以凸显。
由上述引证对照林莽的诗歌创作: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内在演变来看,“白洋淀诗歌群落”代表诗人之一虽可以概括其特定的同时也是最具历史影响力阶段的创作,但却无法涵盖其全部创作。这种存在于林莽诗歌批评中的画地为牢的现象,反映了当代诗歌批评对于晚近时期诗歌创作一直存有约定俗成、简单命名的倾向。其就认知逻辑及限度而言虽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就发展的眼光来看,却可以作为当代诗歌批评缺乏活力和发现能力的表象之一。林莽是“白洋淀诗歌群落”代表诗人之一,“白洋淀诗歌群落”由于获得历史较为稳定的评价和人们的“共识”而很容易成为一种写作和命名意义上的有效“归属”方式。但在另一方面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着眼,“白洋淀诗歌”只是林莽诗歌的一部分、一个重要阶段,是我们考察林莽全部诗歌创作时必须要明确的认知前提,这一点对于林莽这样创作时间长、跨度大,持续处于变动状态的重要诗人来说尤为重要。自然,它也提醒我们要同样以动态的眼光去评判林莽的诗歌创作本身。
事实上,关于林莽诗歌创作的变化很早就有人从文学史的角度予以指出:“林莽风格较为鲜明的作品,产生于80年代中期以后,如《雪一直没有飘下来》,如《滴漏的水声》等。它们与‘地下诗歌,与‘朦胧诗运动已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关注人的心灵的隐秘情感波纹。”出自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这段话,与前文所引的林莽“自我调整”的话不谋而合。在林莽同代诗人如北岛、杨炼、多多等90年代以后海外诗歌创作不断引起研究者关注、可作为独立的对象或阶段加以研讨的前提下,林莽的诗歌虽由于自身的特质、受众度等原因未能及时拓展出新的生长点,但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我们对其整体创作关注得不够或者说还未找到有效的、合理的命名与角度——只要我们面向林莽的诗歌,上述问题就会出现,而当代诗歌批评的“生长性”问题也由此产生。
诗歌批评的“生长性”提醒我们要以一种历史化、整体化的眼光去看待当代诗人的创作:当代诗人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往往使批评对其晚近时期的创作很难做出准确、明晰的判断,但当代诗歌批评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将当代诗歌批评理解为一柄双刃剑,那么它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当然,就“生长性”而言,或许并不存在所谓的过多的“历险”,强调诗歌批评的“生长性”并不是要颠覆已有的结论,它只是期待在秉持发展和实践态度的过程中对已获某种稳定评价但目前仍在创作的诗人进行更为全面、合理和及时的评价,进而丰富、扩大同时也极有可能是夯实文学史写作的文献基础。
关注诗歌批评的“生长性”有助于我们从持续认知一个诗人的过程中认识当代诗歌的历史,而作品的价值、阐释的必要性和批评者自身的当代关怀、才学识力又是其实践的先决条件。“生长性”既强调批评的长度,也强调批评的宽度与厚度,就批评本身而言,它其实是对批评的主体维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以自我发现的方式完成了批评本身的自我完善,从而增强并深化当代诗歌批评体系本身的实践性与能动性。总之,当代诗歌批评的“生长性”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结论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它在追踪当代诗人创作的同时期待批评者灵魂与诗人杰作之间的“奇遇”。它之于林莽诗歌的意义或日与林莽的诗歌关系也完全可以借用诗人写于不同时期的诗行来加以证明——
一切都发源于此
一切都归还于此
——《寄自高原》(1985年一1986年秋)
语言的匕首心中磨砺多年的银色之刃
把人类的苦难削得透明
它將制成一只震撼人心的大鼓
让苍凉的记忆擂响每一个遗忘的年头
——《记忆(第一部分)-四》(1996年
夏一1998年秋)
而它的合理性不仅取决于批评者的发现和诗人的创作等因素,还取决于批评本身如何有效地完成,并在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