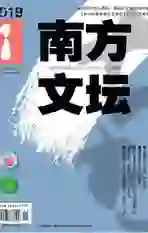李敬泽的批评伦理
2019-03-21张光芒
张光芒
一
李敬泽最近几年接连出版了《会饮记》《会议室与山丘》《青鸟故事集》等引起读者热议的书,这些书里的篇章,文体杂糅,内容多样,在各种叙述形态、审美意象或者语言形式间自由穿梭。对于这些颇具挑战力的文本,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其作为“中国之文”的散文美学、自由精神等方面的特色。在我的阅读感受中,它们依然是智性和审美并重的批评文本,在这些难以归类的文本背后始终站立着一个李敬泽,始终灌注着一种带有李敬泽特色的思维规律和伦理逻辑。如果说大家印象中那些更为典型的文学批评是作为批评家的李敬泽的创作,那么这些新的篇什也可以视为作为作家的李敬泽的批评文字。
实际上,李敬泽本来也不能用学院派批评家的范畴可框定,那么从文体形式上说,李敬泽那些关于文学经典或者中外作家的读书随笔,那些针对当下写作的对话体文章,那些给评论家写的序文或者书评,等等,都完全可以视为是各种变体形式的文学批评。如果从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这一对相对应的概念来说,李敬泽这些作品在美学上无论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文章”,还是被视为带有文体革命色彩的“散文”,无疑都属于文化批评的范畴。李敬泽早就深刻地意识到,“实际上,文学的问题只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问题,或者说,很多问题,就文学谈文学是谈不清楚的,我们要跳出去看看,除了会议室,还要有山丘”。显见,李敬泽的散文、随笔、读书笔记类文本其实正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有机性扩展和有效补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的文学批评还需要从他的另类文本中寻找从“小问题”中“跳出来”的路径。所以,以李敬泽的最新文本形式为切入口,谈论他的批评伦理,感受其思想言说与审美话语打开的新空间,触摸它们与此前文本或互文或跃升的轨迹,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也许只有透过这些文本,并联系李敬泽众多更加典型的评论文章,我们才有可能更完整更清晰地看到他文学批评的内在逻辑。
当我们强调李敬泽是一个“中国”式的批评家,或者将他许多散文化的批评文本视为“中国之文”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他整体性的批评话语与近代以来的批评话语传统之间所形成的独特关系。20世纪初,有两篇评论文章作为重要的标志,典型地预演了一百多年以来的两种文学批评范式。一篇是周作人1922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沉沦》一文,该文以美国阿尔伯特·莫台耳的理论著作《文学上的色情》为直接依据,以其对于“不道德的文学”的系统分析为批评标准,同时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理论方法,得出结论说《沉沦》“虽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一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就预演了现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即以西方理论为标准和依据,对中国文学文本进行审美阐释和价值评判。
另一篇文章是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此文也包含着同样的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两个东西,即以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为核心的悲剧理论和《红楼梦》。但与周作人完全不同的是,王国维关于《红楼梦》乃“悲剧中的悲剧”的结论并非完全是根据叔本华的理论推导出的,他对于《红楼梦》之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分析也不完全以叔本华的理论为批评标准。钱钟书等学者也早已注意到其中的矛盾。这里无意展开分析,只是想强调王国维此文与周作人本质上的不同。在王国维这里,叔本华与《红楼梦》都是研究对象,都是言说话题,所以他不仅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阐释《红楼梦》,同时也以《红楼梦》的表象世界来言说或者重新阐释叔本华。
这就意味着,中国文本在这里也具备了部分的美学理论价值,而西方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可以被进行个体化阐释的另一种形式的文本。也就是说,在周作人那里,西方理论是批评的尺子,中国文本是被衡量的对象;而在王国维这里,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则是互为标准,互为对象。学者李庆本将王国维注重“中西方平等双向的互文性关系”的研究模式称为“跨文化阐释”,以与“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笼统说法相区别,就十分富有启发性。当然,这两篇文章的内在区别与二位大师的言说动机,即其批评的问题之所在是直接相关的。周作人不仅要为郁达夫的《沉沦》“辩诬”和正名,更是为了新文化运动之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价值宗旨保驾护航;而王国维批评的动因更多地则来自对于文化现实的思考,也包括对于人生痛苦体验的困惑。
20世纪初以来,周作人的批评范式占据绝对的主流。以至于到现在,似乎一篇评论文章如果没有引用几个西方的理论方法,就显得缺乏学术深度。而王国维所开创的批评方法则日渐式微,较少有批评家能够自觉地对于中国文本与西方理论同时进行反思,也少有批评家以传统美学或者古代经典的审美意象、审美资源来阐释当代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李敬泽的批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王国维的文学批评范式,它代表了一种几近消失的批评话语的复兴,并由此激活一种新的批评伦理。
二
如果只是习惯于孤立地看待一位作家或者批评家的某些观点,很难以抵达其话语背后的深层问题域和思想的真实面目,这在浅阅读盛行的今天尤其需要警惕。我想我们可以从批评问题、批评资源、批评方法和批评价值四个层面,特别是从这四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去理解李敬泽的批评伦理及其突出特色。
从李敬泽批评切入问题的角度和提问问题的方式来看,他的批评文本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其一是从具体的文学本文或现象本身出发提出问题,拒绝使用先在的视角和外在的概念;其二是从当下的生活出发;其三是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他尤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向着新鲜活跃的人类经验开放的能力”,他把那种“抓住一点死理,就以为拿到了万事万物的尺子,一路比量过去,轻易而坚决地下判断”的批评家称为“浅薄固执的陋儒”,“这个物种我们自古不缺,于今也不缺”。正是基于此,李敬泽再三强调:“我想做的,是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这个时代的纷繁的感受和想法赋形,使它获得某种问题意识,呈现出某种形式。”
批评家的问题意识直接决定了他要调动怎样的批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理论上、思想上、审美上乃至来自社会和生活的赐予与启悟等。而一个批评家的批评资源的矿藏也必然会进一步影响着对于问题的分析途径和方法。我注意到李敬泽早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一两年间,也就是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因为母亲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接触到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里面选的都是夏濟安、夏志清、余光中、叶维廉、杨牧、刘绍铭等,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大陆以外华语批评界的重要人物的批评文章。80年代以后,在现代文学批评领域,西方理论和批评话语很快成为主流,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而恰恰是置身西方的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批评方法等有深入的体会和娴熟的运用。尽管李敬泽后来在80年代也读了很多西方理论,但这一本书却使李敬泽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有一种特别的认同。“像叶维廉和杨牧诸位都受过新批评的影响,他们把中国传统批评对‘审美机枢的直觉敏感与精巧的、细致的文本分析熔于一炉,如庖丁解牛,应手而自由。”应该说,这也就是人们都注意到的,李敬泽是一个“中国”式的批评家的重要原因。
李敬泽常常自谓读书颇“杂”,学问极“杂”。谈到自己的批评观念的建立时,他有一个突出的感受,那就是“那些隐秘地指引着我们的阅读和批评的很可能并非我们抽象出来的条款或理论,而是一种类似于童年经验一样的事物”。他慨叹,以后不管读多少书,“只有这本借而不还的书,是真的留下来了,它在生长”。读过李敬泽的文章和著作的人惊异于作者读书之广与深,熟悉李敬泽的人也常常慨叹其眼界之高远和目光之敏锐,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其源源不断、立体化的和活的批评资源。
不过,人们尽管可以羡慕李敬泽的勤奋善思,也可以羡慕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条件,但是任何丰厚的资源都不能替代个性化和创新性的批评方法对于资源的使用和调动。在李敬泽看来,天下最应该怀疑的可能就是“那堆材料”,“资料下面,是复杂含混的人心,不能或不愿形诸文字,若对人心无感觉,所能摸到的大抵只是皮毛”。比如,李敬泽曾谈到自己最早读过的一本外国文学,是《吹牛大王历险记》。这本小说对于作为读者的他来说,“那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虚构精神,是大胆地用语言创造现实,是一种神奇的魔力”。显然,这种“神奇的魔力”发生在一本书与一颗心之间,发力于一对一的隐秘通道。他越来越认为这才是“小说的神髓所在”,才是“小说的秘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他的批评方法的演绎之下,文学是创造思想的,而不是传达思想的。进一步说,文学创造的思想不是以一个固定的面目来面对全体读者的,它有时候也许只是面对一个特殊的读者。这是一种敞开的思想,一种不能被事先歸类的思想。
基于这诸多的自觉意识,李敬泽的批评方法就显得极其深微细腻而力量丛生,圆融无痕却敏锐逼人,且能够根据对象范畴的不同而辗转于不同的方法之间。王国维那种学无中西、法无新旧之理念在李敬泽这里得到了自觉的实践。一方面,李敬泽的文学批评特别体现出中西对话、古今交融、理论与文本互释的突出特点;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从来不拘囿于知识的框架之中,而孜孜追求着历史与审美的互证互补,锐意追踪着社会生活与文学叙事的互文和罅隙,潜心探讨着文学形象与人性人心之间的矛盾和悖谬。他的批评文本内在地要求“对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有一种直觉的和经验的把握”。因为对文学批评来说,“不知世道、不贴人心,无论如何都是致命的问题”。他深知作家们都在慨叹着“生活大于想象”,但他不认为这是生活的问题,而是文学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作家的问题。“我坚信,网上、微博上那些把我们的作家忽悠得六神无主的信息绝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依然有很多很多东西留在沉默的区域,等待着作家去写它。我甚至认为,那些让我们如此惊慌惶恐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幻觉,它本身就应该是审视和观照的对象。”可以说,他对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这种极为独到的理解和判断力,在今天尤其富有启发意义。
三
下面进一步谈的是第四个层面,即李敬泽批评伦理的价值指向问题。这也是最为复杂和最有潜在意义的一个问题。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到章学诚的《知难篇》,李敬泽从中深深地感悟到:“知言难,知心更难,知言知心而又知人与人世者,又比更难还难。”凡是有着价值创造和整体性旨归的野心的批评家,有这种难乎其难的感喟实在是出乎必然。批评家要直面的主体不止一个,他要面对作家主体,同时要面对文本形象主体,还要面对读者的接受主体。其中读者的接受主体不包括两种,一是文学文本的接受主体,另一个是批评文本的接受主体,二者之间也大不相同。批评家无论是对于作家主体内在精神及其复杂性的梳理和把握,还是对于人物形象主体性的阐释和透视,最根本上还是面对着读者的言说,最终还是要归结于给读者及其背后的这个世界以新的价值启示。
我注意到,李敬泽念念不忘他十岁左右时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感觉。这个小说本来是要告诉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他当时却“只盯着一个冬尼娅”,最喜欢的人也是冬尼娅,是她的美,是“她穿着类似海魂衫的上衣,短裙飘动,灵巧地奔跑,闪闪发光的笑声在林间回荡”。我想,这对于多年以后李敬泽面对各种潜在的读者阐释文学作品时是有极大的启示性的。假如他评论的对象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他必定会拒绝直接地去教育读者,因为这样就会“陋于知人心”;他也不会仅仅告诉读者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因为这样会切割了人世的整体性和主体的丰富性;他会用更多的笔墨去告诉读者,冬尼娅为什么会在一个中国男孩那里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正是因为参透了批评之难,李敬泽的批评文本不拒一切资源和合理的方法论,同时也不认同任何带有偏见或者片面性的流行范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敬泽特别重视作为批评家主体的“自我”的在场,“这样一个‘我,对批评家至关重要。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对作品,批评家的‘我摆进去,就不仅仅是资料和学理,资料和学理是他的力量而不是规训他的力量,这个‘我有可能把他引向难以测度、难以被定见所囿的人类经验的复杂之域”。显见,李敬泽充分意识到了批评家所面对的多元主体及主体问性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潜在悖谬,唯有极力扩张批评家主体,才不至于陷入批评对象的纠缠,才有望克服阐释的命定的困难,从而抵达价值启示的彼岸。
李敬泽的文学批评所呈现的有“我”之境,既进一步表现为锐意解构人们往往习以为常的宏大伦理,又表现出对于个体哲学与个体性伦理价值的追求。创作文本常常会存在着宏大叙事的阴影,批评文本则常常充斥着宏大批评伦理的遮蔽。在李敬泽的批评视野中,这种宏大伦理有两个主语值得重新认识。这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一是历史,一是人民。他从布罗代尔那里获取了对于客观“历史”的解构启示,而同时又互文性地从萨拉玛戈那里获得了对于“人民”重新加以理解的启发。他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历史在“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那些“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在解读《修道院纪事》的时候,他则敏锐地指出,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隐于人群,隐于时代,他们是无法被历史叙事识别出来的“人民”的成员,“但他们的梦想和痛苦,他们从人群中采集起来的意志却消解了君王、教会的神圣权力”。
李敬泽特别强调,即使是史学家布罗代尔“也不能让那些伟大的无名者发出声音”,“这只有小说能做到”。所以,他的批评文字志在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的踪迹,倾听他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这里不妨以一个例子来看李敬泽是如何“倾听”声音和如何“辨认”踪迹的,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他批评的问题、资源、方法和价值等层面之间互动的运演机制。
比如,在解读盛可以《道德颂》这部意蕴复杂的长篇小说时,李敬泽就很认同尼采所说的:“没有道德现象这个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在他看来,道德并非一个自然事实,它不能自我呈现,它有赖于人的体验和论证,也只能依赖人的“解释”,而拒绝解释的“道德”是僭妄和悖谬的。李敬泽进入《道德颂》时就是由此文本本身所聚焦的道德现象而提出问题的。他发现,一方面主人公旨邑的全部斗争就是要从“天经地义”之处取回可以被重新进行解释的道德;但另一方面,小说叙述彻底的独一视角却在逻辑上让她追求的道德流露出“自我封闭”的危险倾向。因为在道德问题上,个人的生命体验必应敞开,“我”要走向他人,我的境遇要与他人的境遇交换。李敬泽发现《道德颂》就表露出这样的道德敏感:盛可以没有回避旨邑的矛盾性,道德上的“我”与“我们”之间的斗争不时会在叙述中跳将出来。可以说,这里既发现了作家主体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微妙悖论,也与李敬泽自身的道德困惑相碰撞。实际上,李敬泽对于道德问题的时代性和个体性有着长期的观察、思考与体悟,比如在《那些做不到的事》一文中,他就独到地质疑了“道德底线”的现实逻辑及其危害。人們常常把“道德底线”视为做人的“最低纲领”,殊不知,事实恰恰相反,“道德底线与其说是我们最易达到的,不如说是我们最易逾越的”。令人惊讶的结论中充满着促人猛醒的启示性。当李敬泽指出《道德颂》中那个微弱的“我们”,“它应该在,但它破碎、微弱、难以确认”时,的确是抓住了“这个时代精神之病的真正要害”。
李敬泽的批评伦理所向直指人的救赎,但他不认为有一种共同的道路可供借鉴,或者有几种既定的方向可供选择。他精辟地指出,中国的作家们和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有一个共同的写作倾向,那就是“都喜欢哼哼唧唧地歌颂他们的童年”,结合对孟子的解读,李敬泽发现歌颂童年实际上就是歌颂他们的本性是善的。令人敬重的先贤孟子一不小心就这样“为后来的无数赖汉提供了耍赖的口实”。可见,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样的本质性命题或者宏大叙事,在批评伦理的建构中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唯有聚焦于人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幽暗地带,方有希望抵达那难以测度的“复杂之域”。